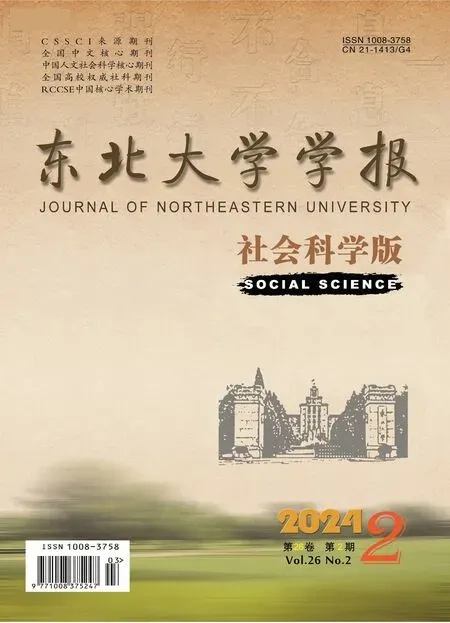現象學還原作為認識還原對審美還原的僭越
——羅曼·英加登《論文學作品》對審美時間性的耽擱
劉 彥 順
(江蘇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現象學還原為何不適用于美學?為何要從審美時間性來研究藝術理論?審美時間性對于文藝美學的重要性何在?且現象學還原為何耽擱了審美時間性?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由美學研究對象自身特性所決定的,而現象學還原與此相悖。審美生活作為感官愉悅感是美學唯一且最高的研究對象,其根本特性有四——所需、所能、所顯、所構,即意義、能力、狀態、構成。第一,就其意義而言,感官愉悅感要適時宜而起,適時宜而止,其間流暢無礙,充滿持續欲,且人們執著于享受其綿延時段或審美過程,此即審美時宜。第二,就其能力及實際顯現而言,感官愉悅感只能經由感官直接感受可感之審美對象,只具有記憶能力,不可能具備回憶、反思能力,只能是一次性、原發性的,這是審美生活的絕對時機化或審美時機化。第三,就其狀態而言,首先,審美生活只能是正在進行時的,這是其時態,也可稱為審美時態;其次,審美生活所顯現時間意識在持續狀態上,只能是流暢的,即由審美滯留—審美原印象—審美前攝這三個審美時位構成了流暢時程,毫無遲滯、壅塞與卡頓,這是其時體,也可稱為審美時體。第四,審美生活的構成方式只能是主—客或主—主之間須臾不可分離的,這是絕對意向性,也可以稱為絕對同時性。審美生活意義上的審美時宜、能力上的絕對時機化、狀態上的正在進行時之審美時態與流暢之審美時體、構成方式的絕對同時性,就是審美生活的五大時間性,即五大審美時間性。不落實這五大審美時間性,就無法把握審美生活的意義、能力、狀態、構成的具體內涵。可見,審美時間性對于美學是至關重要的。
英加登《論文學作品》(1931)共分三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第二章所占篇幅雖短,但為本書提供了思想奠基,是該著作的機杼、核心,第二、第三部分是基于此機杼、核心的具體演繹與展開。英加登忠實執行了胡塞爾現象學還原思想與策略,以知識還原或認識還原僭越了審美還原,也就是把知識或認識可以在回憶與反思中保持不變視為審美生活的特性,但回憶之中的審美生活已經不是原發的審美生活,而是審美生活標本。把審美生活標本視為審美生活原本,這就在根本上耽擱了對審美生活在所需、所能、所顯、所構這四大根本特性的把握,也就自然耽擱了對審美時間性的把握。待下文詳述。
一、現象學還原僭越審美時宜
時間性問題是現象學哲學一以貫之的核心,且現象學使時間哲學成為真正的哲學事業。如果把現象學時間哲學分為以時間意識域的時位構成分析為志向的胡塞爾路線與以存在—時間為旨趣的海德格爾路線,把現象學審美時間哲學分為側重審美時位構成分析的胡塞爾路線與著重把握藝術作品內容的正在進行時審美時態的海德格爾路線,大體上是符合實情的。胡塞爾路線的意識現象學基本上是一種認識論哲學或科學哲學。胡塞爾所專注的領域雖然是號稱大一統的所有直觀行為現象,其實只不過是認識行為、知識行為而已。現象學還原的核心就是還原意向活動之中的意識在事后的一般性剩余,而這個一般性剩余只適用于科學知識,因為科學生活的意義在于獲得知識,由此獲得的知識本身就只能是一般性的。簡而言之,只有科學知識才可以在回憶—反思中進行無損運用,因為它不會發生任何改動與變動——這正是科學知識的無時間性。知識不僅在一個正在進行的科學生活中可以保持其絕對客觀—剩余之身,而且這種剩余可以在回憶里完滿呈現,并在反思活動中持續地保持自身的無時間性。“1+1=2”會在每一次計算活動中被回憶從意識—記憶里提取,并在每一次計算活動結束之后保存于意識—記憶之中,且可以絕對保全自身。知識在意識中的保全是絕對剩余。胡塞爾在《小觀念》中所說的一句話堪稱現象學還原的精髓,“如果我們在這里探討的僅僅是認識的現象學,那么,我們所涉及的便是通過直接直觀可指明的認識本質,即:一種直觀的、在現象學還原的和現象學自身被給予性的范圍內進行的指明,以及對‘認識’這個廣義的名稱所包含的雜多性質的現象作分析的區別”(1)埃德蒙德·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倪梁康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6頁。。可見,“認識的現象學”以及其所追求的“通過直接直觀可指明的認識本質”就是現象學還原的核心。一切所謂加括號、懸置、終止判斷,都是這一思想內涵的具體策略與操作手段。
一個巨大的美學風險便潛隱于此,尤其是把現象學還原中的“認識還原”視為一切理性活動的根本。科學生活的意義在于尋求無時間性的知識,知識在科學生活的事前、事中、事后,都是以無時間性的狀態存在著的,即不變化。知識本身無時態、無時體、無時機。審美生活的意義則在于尋求感官愉悅感,僅享用其愉悅時程的事中狀態,它是一次性的、時機化的,而且在時體上還只能是流暢的。可見,科學生活與審美生活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是根本的。以科學生活為對象的科學哲學與以審美生活為對象的美學,卻都是理性的認識活動,也都必須利用回憶—反思才能達成。因此,認識還原中的美學與科學哲學作為“認識科學”上的一致性,恰恰抹去了兩者在研究對象或內容上的根本區別。這實在是一個邏輯上的嚴重錯誤,錯就錯在沒有看到科學生活與審美生活作為人生意義的根本區別,更沒有看到處于還原階段的知識—意識是“原本”,而處于還原階段的感官愉悅感—意識是“標本”。就“知識—意識”作為“原本”來說,知識在回憶、反思里都可以保持不變,因為其特性是絕對客觀的、一般性的、絕對普遍有效的、無時間性的。就“感官愉悅感—意識”作為“標本”來說,處于回憶、反思里的審美生活雖然帶有原發的審美生活的本質或基因特性,卻已經徹底喪失了生動性、原發性,因為回憶—反思沒有舌尖、眼睛、耳朵、肌膚等感官。因此,一個審美生活結束之后,就不存在絕對剩余,而只存在相對剩余。美學作為認識科學恰恰要通過回憶—反思之中的審美生活標本,在理性上還原一個原發性的、一次性的、絕對時機化的審美生活所具有的時宜、時態、時體、構成上的絕對同時性。因此,審美還原是一種理性還原,而不是徹底、完全意義上的絕對還原。在審美還原上,如果把審美生活標本視為審美生活原本,那就會把審美生活的意向對象視為絕對客觀之物,就會認定審美生活完全由審美對象所決定,也就會只研究審美對象在質料上的客觀屬性,且以此質料的客觀屬性充當審美生活的一致性。這種思想與操作,不就是認識還原嗎?
如果把審美還原置換為認識還原,并把這種思想與策略運用到藝術理論上,就會把作為欣賞對象的藝術作品視為絕對客觀之物或唯一根本之物,且會在回憶—反思中把藝術作品視為純意識或絕對意識,其機制與角色就像在回憶—反思之中的知識,毫無二致。胡塞爾對旋律感所顯現審美時間意識域的審美時位構成分析在美學史上前無古人,尤其是他所提出的“一時三相”——審美滯留—審美原印象—審美前攝的涌流模式更是具有劃時代的卓著貢獻,但是他的基本用意卻在于通過旋律感的時位構成分析來獲得“聲音”流逝現象的一般性規律。他說:“我們可以在想象中將一段曾為我們在特定的音調中、根據完全特定的音類而聽到過的旋律轉用到其他的狀況上。”(2)埃德蒙德·胡塞爾:《內時間意識現象學》,倪梁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44頁。這就是現象學還原的典型操作,其中所言“想象”即回憶—反思,“旋律轉用”即旋律感作為感官愉悅感這一本質的消失與被排除,“其他的狀況”即“聲音”所顯現時間意識的一般性剩余。
文學理論當然要研究文學作品,但文學作品只能作為感官愉悅感的對象來存在,且與讀者斯須不可離,也就是說,讀者與文學作品之間的構成方式是絕對同時性的。英加登在《論文學作品·導言》里的第一句話便是“我要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文學作品”(3)羅曼·英加登:《論文學作品》,張振輝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3頁。,而且他明白無誤地把文學作品視為胡塞爾所說的純意識之中的純意向性客體,把“文學作品的本質”視為文學理論的最高且唯一的對象。雖然他與胡塞爾在實體與觀念的思想上有所不同,但其現象學還原的基本立場與胡塞爾毫無二致。如果在思想上不把審美生活作為唯一且最高的對象,也就等于在陳述中不把審美生活作為唯一且最高的主語。在使用“文學作品”,尤其是把某一個語言組織稱為“文學作品”的時候,必定有一個以此為對象的審美生活在此前已經發生。但是,在英加登的思想與陳述中,他把隸屬于審美生活的“文學作品”作為最高的主語與對象,這意味著“文學作品”不是作為絕對同時性的意向對象而存在的,也就不再是審美生活之中的構成因子,而是絕對自立或自足之物。
下面這段話集中體現了英加登把審美還原當成認識還原的錯失:“我認為,一部‘現成的’文學作品必須是其中所有的語句和每一個語詞的發音、意義和它們相互之間的設定都是很明確的。對于它的‘現成性’來說,主要不是它事實上已經謄寫出來了,或者只是在口頭上表現出來了,而是它——經過也可能是多次的朗讀之后,沒有本質上的改變。這樣我們就把文學作品產生的階段和一切關于藝術創作的問題,都放在我們研究的范圍之外了。”(4)羅曼·英加登:《論文學作品》,第42頁。其間的問題鏈是:第一,一個“現成的文學作品”是什么呢?顯然它不是純然的一摞紙,在紙上有黑色的印刷痕跡,而是在“多次的朗讀”之后,才被稱為“文學作品”的。第二,多次的朗讀是什么又意味著什么呢?而且英加登為什么不對朗讀行為進行深究,并把它作為唯一且最高的對象呢?為什么不把文學作品視為朗讀行為的意向對象呢?為什么不把對文學作品的朗讀行為視為斯須不能分離的、絕對同時性的意向行為呢?第三,“朗讀”是審美生活的一種形態,其對象是文學作品,其時宜是感官—愉悅感的欲求,其時機是一次性的,且其狀態一定是正在進行時的,其時體一定是前牽后掛的、流暢的。第四,僅就流暢時體與文學作品諸要素的空間構成關系而言,處在這個正在興發著的、流暢的審美時間意識域之中的文學作品,也就是作為被流暢地朗讀著的對象的文學作品,才能被冠以“整體”或“不可改變”之名。這里所說的“沒有本質上的改變”顯然不是指朗讀絕對不能改變文學作品的構成,或者說朗讀不可能從事消耗性的行為,而應該是指這個作品朗讀起來是美的、流暢的,所以才是一個既不多余什么,又不缺少什么的整體。但英加登顯然把“沒有本質上的改變”視為每一次朗讀行為結束之后剩余下來的共同之物,這就是他要尋找的文學作品的“本質”,而且顯然是在回憶—反思中作為純意識出現的本質。通過以上四個問題鏈可見,這段話就是現象學還原中的典型的認識還原操作,也是以認識還原僭越審美還原的典型操作,其中被排除的便是閱讀—審美生活的意義或審美時宜。
借排除作者心理主義之便,把所謂的讀者心理主義一并摒除,把審美時宜的沖動、欲望、需要全都排除在外,這是英加登現象學還原、認識還原的核心機杼。作者與讀者的心理本來含義就不同,更不是一個層面上的問題。英加登本來應該通過對作者—心理主義的批評,顯露出文學作品作為意向性客體的意義,也就是文學作品作為審美生活對象的意義,但他還是以文學作品作為最高與唯一的對象。在批評讀者的心理主義時,他也沒有注意到——對文學作品的錯誤感受與正確感受之間的根本區別,還把所有意向行為之中的感官愉悅感給清除掉了,最后只剩下了文學作品或文學作品本質。英加登本人也是讀者之一,而且是專業讀者,怎么能把自己也排除掉了呢?看來,如果要這樣做,而且能成功的話,那就只有一種可能性——把文學作品作為“知識”“認識”來看待。但是,英加登又堅決否認文學作品就是知識,而且他始終都堅持在文學作品之前冠以“審美”作為定性。他說:“如果我們一定要對一部作品有所理解,特別是對文學作品作為審美客體的那個方面一定要有所認知,那么我們就要通過一個主體的認定,使這類客體能夠直接呈現在我們面前了。”(5)羅曼·英加登:《論文學作品》,第42頁。在這里所使用的“審美客體”就著實讓人費解,既要排除掉審美主體的感官愉悅感,又要談論、研究作為感官愉悅感的意向對象。
英加登孤立地探究文學作品本質的思想及其操作,就是要在所有文學閱讀活動里找到一個無可置疑的、自明性的共同之處。這個共同之處便是可以從意向活動中無礙地脫落下來的意識,在這個意識里完全保存了該意向行為的基因特征。但是,只有科學生活、宗教生活中的意識,才可以無礙地脫落下來,且在回憶里被忠實地還原,絲毫沒有什么損耗,這就是科學生活中關于知識的意識與宗教生活中關于神祇的意識,以及受知識與神祇支配與決定的思考過程與信仰過程。不過,這個世界需要的是多種意義——科學、宗教、審美、道德,同時也需要區分意義領域、分道而行的哲學。胡塞爾的現象學其實是以科學認識論為核心的,他尤其擅長描述與分析的現象大多是中性的,比如聲音、顏色等等。即便他所操作的是旋律感這樣的審美現象案例,也是把它作為通達一切時間意識現象的一般性本質的一個通道,因此也就忽視了像旋律感這樣的審美現象自身的意義、能力、構成與狀態。同時,不可忽視的是,胡塞爾在學術生涯中時常調整、改變自己的思路,突出現象學還原中審美還原的特殊性,“一首旋律也不是一個個直觀的總和,因為屬于同一首旋律的音型(Tongestalt)序列(或者說音型的逐次展開)行進在同一個(時間上延續的)行為之中”(6)埃德蒙德·胡塞爾:《文章與書評(1890—1910)》,高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311頁。。這里所強調的旋律感的整體性,其實就是音樂—審美生活作為感官愉悅感的意義。
現象學的意識還原、時間意識還原其實只是認識還原,它必須被意義還原所替代,在美學上必須被審美還原所取代,否則就會出現意義僭越。所謂意義還原,就是把審美生活、科學生活、道德生活、宗教生活的意義做根本區分,根據特定的意義領域來自然而然地解決各自的問題。如果能做到意義區分,那就一定會產生意義區分的思想。如果把這些已經完滿地區分了意義的思想付諸語言陳述,那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涇渭分明的意義語言與意義語法。所謂審美還原,就是美學要把最高且唯一的對象設定為審美生活,即時機化的、興發著的、流暢的且主客之間斯須不可分離的、感官直接所感的愉悅感。但是英加登延續了胡塞爾意識現象學這一不區分意義的缺陷,主張不管審美價值或審美意義的事,只要關切所有審美現象或所有文學作品都有的一般性“結構”就可以了。他說:
我們深信這樣一個真理:在一個文學的藝術作品中,既有肯定的價值,也有缺點和錯誤。它們會給文學的藝術作品的主要整體共建一個特殊性質的價值。關于這類價值的本質的問題,也暫時不是我們研究的對象。要回答這個問題,一方面,應首先解決什么是一般價值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要懂得文學作品的結構。而后者正是我們要研究的對象。因此,我在研究文學作品時,并不考慮它是不是有肯定的價值,還是根本沒有價值。(7)羅曼·英加登:《論文學作品》,第43頁。
雖然英加登對審美價值持較合理的寬容態度,因為人們的審美能力、愛好確實各有所好,但是最要緊的審美價值或意義問題,他卻沒有把握住。審美生活的意義或審美時宜不可能是抽象的,而是具體而細微的,且是一個正在興發著的、流暢的審美生活,即感官愉悅感。審美生活之外,沒有什么審美的意義或價值;也可以說,審美生活的意義或審美時宜必定顯現為審美時機、審美時態、審美時體與審美絕對同時性的構成關系。英加登常常在著述中列舉自己所欣賞的文學作品,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欣賞、喜好這些意義或價值也給回避、排除,最后只剩下“文學作品的結構”了呢?而且經過認識還原之后作為剩余物存在的“文學作品的結構”,正是英加登《論文學作品》在第二部分、第三部分進行文學作品多層次構成分析的對象。審美生活的意義或審美時宜的被輕視、被忽視,必然導致其他審美時間性被耽擱。
二、拆解審美生活絕對同時性與審美時間性消失
認識還原只能在表面上把握審美生活構成方式的意向性,卻會耽擱其在構成方式上真正的絕對意向性或絕對同時性。在此,最迫切的便是區分人生意義以及認識各種意義活動在意向性構成方式上的根本差異,科學生活與審美生活的比較就成為真正的問題。一旦審美主體的感官不再直接感受審美對象,兩者之間一旦脫離接觸,審美生活便告結束。人的感官感覺本身并不具備回憶與反思能力,且對曾經發生的審美生活的回憶與反思只能是第二度的。但科學生活之中的知識,卻是絕對客觀的、一般性的,在科學生活結束之后仍然存在,且可以在回憶與反思中確保自己的完整性。因此,科學生活的構成方式是相對意向性或相對同時性,審美生活的構成方式是絕對意向性或絕對同時性。1+1=2并不絕對依存于某一個計算活動,但是閱讀《紅樓夢》、聆聽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樂》卻是一次性的。當且僅當我們正在閱讀《紅樓夢》、正在聆聽《第五交響樂》之時,獨一無二的審美生活或感官愉悅感才如其所是地存在著。
以自足的文學作品、自足的文學作品本質之名,英加登把與此無干的東西清除出去,既清除掉了應該清除的,又清除了不應該清除的。
第一,對于應該加以清除的,那就是作者心理主義。英加登說:“作品的總的構建和它的各種屬性的形成也可能有賴于它的作者的心理屬性和才能,決定于他的思想的類型和智慧。在這種情況下,作品也可能或者明顯或者不明顯地帶有作者個性的痕跡。照這個意思,它就‘表現了’作者的個性。但這并不能改變原先那個我們經常是已經了解得很清楚了的事實,即作品和它的作者創造了兩種不同類型的客體。”(8)羅曼·英加登:《論文學作品》,第43—44頁。
英加登把文學作品中作家的風格——其實就是作家所創造的作品的風格,與文學創作過程中的作家具體感受、體驗進行嚴格的區分,這的確是富有創見的。在這里,他當然也沒有忘記強調文學作品不是一個絕對獨立的客體,但是經過現象學還原之后的文學作品卻成了一個獨立的客體。更為重要的是,文學作品的風格或個性又顯現在哪里呢?難道不是只能在一個正在進行著的審美生活之中被給出的嗎?其實,幾乎所有的文學研究者都會認為,在“事后”談論、品評文學作品是天經地義的,而且一旦談論、品評文學作品成為一種職業,這種天經地義就更會作為一種回憶—反思制度橫行天下,卻遺忘了回憶—反思作為美學知識生產的機制是絕對還原還是相對還原,是認識還原還是審美還原。因此,必須對英加登這種天經地義一般的行為進行徹底質疑,而且依據只有一個,那就是一個正在興發的、流暢的、時機化的、事中的審美生活。
第二,對于不應該清除的,那就是讀者的體驗屬性與心理狀態。英加登說:“讀者的體驗屬性和心理狀態也不屬于文學作品的構建。這個觀點好像很平庸,但實證主義的心理主義暗示在文學研究家、藝術理論家和藝術史家中卻一直在起作用。在你手頭不管是一本什么樣的文學研究領域的書中,都可見到許多關于‘再現’、‘印象’和‘感情’等論題的觀點。在談到藝術作品特別是文學作品時,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種把文學作品看成是某種心理的東西的傾向是多么強烈。這種很明顯是平庸的傾向已經不具文學研究的性質,一定要明確地指出其中一些這樣的論斷的實質。尤其是在談到美或者——一般的——談到作品的藝術價值的時候,這種心理學的傾向表現得特別強烈。”(9)羅曼·英加登:《論文學作品》,第44—45頁。這不是“平庸”,而是審美生活的常態、自明態、自然態。如果把審美生活中審美主體的感受給清除掉的話,那才是非常態的、變態的、遮蔽態的。美學或文學理論如果做不到對審美生活的意義還原,繼而如果做不到對審美生活絕對同時性構成方式的還原,又何談對審美生活整體的保全呢?又怎能去談論一個處在審美生活之外的、脫離了審美主體絕對同時性施與的審美對象呢?如果被談論的還被稱為審美對象或審美客體,那的確看不出“愉悅”“美妙”的感受在哪里。
英加登對海德格爾的觀感一向不怎么好。他認為海德格爾的藝術理論也是持這種讀者心理主義態度的。他說:
這種把一切價值都看成是一種“主觀的”東西的總的傾向,由于我們在閱讀一部文學作品時所采取的一種特殊的態度,也會得到加強。此外如果作品的價值對意識的主體來說——這里用了海德格爾的表述——只是為了把它“揭示出來”,而不是把它作為客體來掌握的話,那么因為主體必須具備的條件,這種主觀的傾向也會得到加強。(10)羅曼·英加登:《論文學作品》,第45頁。
這里所說的“揭示出來”指的是海德格爾關于藝術作品中真理或藝術作品內容存在狀態的思想。海德格爾對胡塞爾現象學之精髓可謂了如指掌,他一方面對胡塞爾現象學中的意向性、范疇直觀、先天的原初含義之思大加贊賞,給胡塞爾應有的極崇高的哲學史地位;另一方面也對胡塞爾現象學中的意識現象學向度大為不滿,認為胡塞爾現象學總是在純粹意識里打轉轉,從而耽擱了對意義(存在)的原初把握。海德格爾曾說:
意識是一個這樣的領域:第一,它是內在的存在。第二,這一內在的存在是絕對既與的存在。……第三,這一在絕對的被給予性(absouluten Gegebenheit)意義上的存在在下面這個意義上也同時是絕對的:這個存在nulla re indiget ad exstendum(無需存在者也可達到存在)[這里接受了古老的實體定義(Substanzdefinition)],為了達致存在(um zu sein)并不需要任何res(存在者)。在這里,res(存在者)是在狹隘的實在性、超越的存在之意義上的被理解的,它就是所有非意識的存在者。第四,這兩種意義上的絕對存在——絕對的被給予性和無需一種實在性——是作為屬于體驗的本質存在(Wesenssein)、屬于體驗的觀念式(ideal)存在的絕對存在。(11)馬丁·海德格爾:《時間概念史導論》,歐東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137—138頁。
這些話可謂招招見血。一句話,胡塞爾的意識現象學及其現象學還原不僅缺少“意義”(存在),而且同樣缺少由意義實現所顯現的“時間”——簡言之,只有一個人喜歡做一件事情,他才會持續地做下去,而且在做這件事的過程中,意義與能力還會提高,之后更會繼續做下去。因此,海德格爾才會開創自己的存在—意義—時間現象學。海德格爾所說意識現象學之中“意識”的這四個特性,當然也是四個缺點,同時也適用于英加登對讀者的排除,其中就包括對審美生活絕對同時性構成方式的排除。如果把海德格爾的言論套用于英加登,就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文學作品是一個內在的存在;第二,文學作品是現成的、既成的;第三,讀者的審美生活被懸置起來了;第四,文學作品本質是一個離開了所寓居整體,即審美生活的絕對之物。只不過,海德格爾也沒有明確地指出各種意義活動在構成方式上的根本區別,尤其是審美生活在構成方式上的絕對同時性。
英加登虔信胡塞爾的現象學還原,因此才指責海德格爾對待藝術作品過于主觀化。他認為,不僅可以把文學作品作為意識進行還原,而且可以把文學作品本質作為時間意識還原出來。但是這個“意識”正像海德格爾所說的,是一個無意義的、無沖動的、無時間性的絕對之物,因此才能從審美生活或閱讀生活之中脫落下來卻毫發無損,就像一個在審美生活這棵大樹上所結的果實。如果沒有審美生活這棵大樹,文學作品就只是一些紙張與鉛字而已;有了這棵大樹,文學作品就成了意向之物,就成了審美對象;這個果實一旦成熟,就自然會從審美生活這棵樹上脫落下來,就成為完全自主的獨立之物了。但是,事實上,文學作品與文學—審美生活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絕對意向性、絕對同時性的關系。文學作品不是樹上的果實,而是這棵樹本身。雖然它還不是這棵樹的全部,它也不可能從中脫離、脫落,成為自主、自足之物。
問題的癥結在于——這既是胡塞爾、英加登與海德格爾之間的根本性歧異,又是美學、藝術理論作為一種理論在性質、形態上的巨大矛盾與困難,那就是——如何理解并維護一個正在流暢地興發著的審美生活,以及有沒有可能做到。英加登說得非常干脆,當一個人正陶醉、沉浸于審美生活之時,不可能進行回憶與反思行為。這的確說出了美學、藝術理論最難的一個問題:美學與藝術理論是理性的,而所思的對象則是感官愉悅感,感官愉悅感只能是自發的,而不能是強迫的;從原發的顯現狀態來說,其審美時態只能是正在進行時,其審美時體只能是流暢的。因此,當審美生活正在興發之時,一旦有理性活動——比如最為常見的便是回憶與反思參與其中,審美生活要么會立刻中止,要么會變得磕磕絆絆、踉踉蹌蹌,流暢時體變成卡頓時體,感覺苦逼。
英加登說:
讀者往往不是在精神上和藝術作品(特別是文學的藝術作品)積極地打交道中和它發生直接的關系,不是直接地對它進行觀察(不能把這和對客體的理論上的認識等同起來),不是在藝術作品中享受到一種愉悅,在愉悅中不用對價值客觀化的處理就對作品進行評價,而常常把藝術作品當成是一種外部的刺激,在他的心中引起某種感情和形成其他一些他所重視的心理狀態。(12)羅曼·英加登:《論文學作品》,第45頁。
這段話傳達了現象學還原的精髓,但這種還原對審美生活是無效的。英加登所說的在“精神上”與藝術作品打交道就是在審美生活之事結束之后,在事后對藝術作品進行回憶與反思。這一思想的問題是,即便是在事后進行的回憶與反思活動,其對象也是曾經的審美生活,而不只是藝術作品;如果是藝術作品的話,那也是處在曾經正在進行著的審美生活之中,且絕對不可能從中脫離、脫落出來的絕對意向之物。藝術作品只能作為審美生活絕對同時性的意向之物被回憶與反思。英加登還認為,讀者——其實就是不專業的一般讀者,在藝術—審美生活之中的感受或這個藝術—審美生活本身妨礙了他的思考,而且他只能沉浸于他自己的、完全個人化的審美生活之中。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在一個審美生活正在興發之時,確實無法做到冷靜的回憶與反思,而且在根本上也是違反人性的。一個人一旦快樂起來,總是希望能流暢地持續下去,并自然而然地結束。但是,英加登對此的描述卻不是為了還原審美生活的原發狀態,而是為了否定這一原發狀態,其手段就是拆解審美生活的絕對同時性構成關系。其實,這正是一個審美生活所顯現審美時間意識正在興發的過程。文學作品正是在這個流暢時程之內,作為絕對同時性的意向對象存在著的。
英加登卻要把人們對藝術作品的感受、感覺清除出去,這既取消了審美生活的意義或審美時宜,也拆散了審美生活在構成方式上的絕對同時性。連感官愉悅感都沒有了,那藝術作品于我們又有什么意義呢?而且當我們不去欣賞并貫注于藝術作品的時候,審美生活就停下來了。在這個時候的“藝術作品”又恢復到它孤零零地擺放在書架、博物館、墻上的純然之物的狀態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一個人的審美生活越是強烈、綿長、流暢,就會給審美生活之后的回憶與反思提供越多的動力與可能性。人們總是樂于回憶讓他幸福、快樂的時光,并對此進行反思與籌劃。回憶要保持審美生活的完整性,反思要在忠實回憶的基礎上進行更高理性的工作。但是,回憶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還原審美生活的原發狀態,反思作為高階的理性心智也不比作為感官愉悅感的審美生活更高。這里所說的高階的理性心智,只是相對于回憶而言的,并不是在感官愉悅感與理性之間進行對比,更不是說感官愉悅感沒有獨立存在的意義,只能充當理性心智的質料,并由理性進行所謂的高級、高階的文化操持與學術處置。更根本之處在于美學的回憶與反思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為了保全、交流審美生活,并提高審美生活。但是英加登在審美生活結束之后所進行的回憶與反思,卻要徹底改變審美生活,改變其意義、能力、構成、狀態。這就在根本上扭曲了審美生活,把一個絕對意向性或絕對同時性整體大卸八塊。
三、感官愉悅感與回憶—反思能作為時間意識并存嗎?
實際上,英加登混淆了感官愉悅感中的意識與理性中的意識,這是意義混淆或生活意義的混淆,也是現象學還原運用于美學的必然結果。他說:“事實上他對作品進行評價并不是由于它的價值,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它的價值根本就沒有顯現,而被他的感情完全遮蔽了。他認為它很‘珍貴’是因為它是一種工具,能夠引起他的美好的體驗,而不是因為他對它作了審美價值質的某種選擇。”(13)羅曼·英加登:《論文學作品》,第45—46頁。這里的“感情”是感覺或感覺的形態之一,也就是審美生活本身。那么,審美生活本身不是審美價值或意義的具體顯現嗎?難道審美價值或意義是抽象的存在嗎?如果是這樣,審美價值就是絕對客觀的,也就只能是無時間性的了。當藝術作品內容正在我們心中興發之時,也正是審美生活興發之時,且這一感官愉悅感是絕對同時性地黏著在藝術作品內容之上的,這一切都來自審美主體對藝術作品形式——構成藝術作品所有質料或物因素之間固定空間位置關系的貫注。感官愉悅感怎么可能與藝術作品及其中的內容、形式分離開呢?其實,英加登要進行分離的、析出的,便是在這個感官愉悅感之中的“意識”。由此產生的問題便是,要從感官愉悅感之中分離、析出意識,就必須使用回憶、反思。那么,感官愉悅感作為注意力是始終流暢地向前運動的,回憶與反思能與之并存、并置嗎?能夠在一個審美生活中前后相續且流暢無礙嗎?或者說,它們能否造就一個流暢時體?
因此,必須深究感官愉悅感與回憶—反思作為注意力在意義、能力、狀態與構成上的根本區別。第一,就感官愉悅感而言,由審美滯留—審美原印象—審美前攝這三個審美時位所構成的感官愉悅感只能向前奔流。一方面,審美時宜作為感官沖動而顯現的審美前攝被充實之后,形成最切近且最清晰的審美原印象;另一方面,由審美原印象累積而成的審美滯留非但不向后流逝,而是作為愈來愈飽滿、愈來愈清晰的審美記憶或感官記憶向前接納著審美原印象而行,而且人們自知或意識到審美滯留本身尚不完滿,這種欠缺感會源源不斷地滋生出審美前攝,直至人們意識到審美滯留已經徹底完滿,也就不再滋生審美前攝。審美前攝并不是未來,而是基于審美滯留尚有缺欠的期待;尚未實現的審美欲望只是準審美前攝,還不能被稱為審美時位。審美滯留并不是過去,更不是對過去的回憶,而是在感官記憶中的持存。這就是一個前牽后掛的審美流暢時程的產生。第二,就回憶—反思而言,則必須先向后回顧,從記憶里提取所貯存的內容,再進行種種反思。回憶是人類理性心智的最低階能力,而反思則屬于理性心智的高階能力。回憶為反思提供對象,反思對回憶提供的材料進行高級加工。欣賞音樂的感覺意識與計算一道數學題的理性意識,在意義與價值上是完全不一樣的。只是在某些情境中,我們才能承認與陳述這兩種意識之間的共同性,比如與其他動物相比較。從兩者的對比可以看出,對于審美生活及其流暢時體來說,它們根本不可能作為兩個時間意識并行、同在。
英加登要做的,則是試圖通過否定與清除審美生活之中的主體感覺,來尋求一種普遍性的、一般性的、絕對穩定與一致的對文學作品的“認識”,而不是感官的“感覺”。他說:
這種對于作品的態度的確是很經常出現的,特別是對某些音樂作品,是經常出現的,從中得出對于審美價值表面上看是有根據的主觀主義的看法。這種看法之所以真的有道理,是因為對于這一類的讀者來說,那種有價值的東西的確存在于一些特殊質和由詩歌喚起的充分的感情中,但是藝術作品本身的價值在讀者藝術感知的那些客體中根本就沒有顯現。但事實上,這只是說明要改變讀者在接觸作品時所表現的這種態度,因為它使得作品在他面前出現的時候完全變了樣,同時這也說明了主觀主義的價值理論是錯誤的。(14)羅曼·英加登:《論文學作品》,第46頁。
可見,英加登對審美生活的豐富性感到恐懼,至少是讓他惶惶不安。美妙感覺的變化被稱為“主觀主義”,其實這只是一個自明且日常的審美現象而已,而且在這個現象里,人們的感官感覺所尋求的意義——陶醉的、全神貫注的、沉浸的且流暢無礙的審美生活,已經完滿地實現了。但在英加登眼里,這種感官愉悅感有什么意思呢,這根本不在他的法眼之內。他絲毫都不在乎審美生活的意義或審美時宜,卻極其在意文學作品本質的一致性或同一性。他說:“應當指出的是,促使這種理論的形成的還有一種因素,它的事實上的存在和某種被普遍接受的至少是值得懷疑的認識論的信念有關,并要求我們承認對價值的主觀主義的看法。”(15)羅曼·英加登:《論文學作品》,第46頁。在這里,英加登終于交了底,美學只不過是知識—認識論的一種,而且美學所處置的也是認識材料。為什么感覺在英加登那里不受待見?為什么感官愉悅感在英加登那里不受待見?就是因為英加登對文學作品本質或文學作品作為現象學還原剩余物的一致性、同一性的執著。為了獲得無時間性的、超穩定性的、不變化的本質與一般性的“認識”,就要拋棄與“認識”完全沒有任何關系的感覺或感官愉悅感。其實,一同被拋棄的,還有英加登心心念念的文學作品內容的原發顯現狀態,因為文學作品內容唯一的顯現方式就是正在進行著的內容感。如此,為了還原文學作品本質,就必須突出在回憶—反思之中作為純意識存在的文學作品的多層次構成,那就把流暢的審美時體給忽略或者給排除了。
既然審美生活所顯現的流暢時體與回憶—反思不能共存與并置,英加登就必須給回憶—反思提供從審美生活原發狀態而來的純粹意識,否則,所回憶的對象就不堪其用,更無法給反思提供高質量的對象了。由此出發,英加登設想了一種讓愉悅感與超然的旁觀感并存、并置的觀念。其實,尊重并保持原發的審美生活的完整性,并不是要在一種絕對相同的意義上,對曾經發生的審美生活進行徹底而完全的還原,而是為了在事后的回憶與反思中,對其進行理性的審美還原。因此,審美還原就是相對還原。雖然審美生活已經過去,但我們仍然可以清晰地記得它的各種特性,諸如本文開頭所言審美生活的意義、能力、構成、狀態以及與此相應的審美時宜、審美時機、審美時態、審美時體、審美同時性,并付諸語言表達。
但英加登沒走這條正道,《論文學作品》中的錯誤是路線性錯誤。要把對感官愉悅感的意識從感覺之中脫離、剝落出來,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它只能是原發的、一次性的且正在進行著的、流暢的。一旦有理性心智的介入,比如回憶與反思,審美生活便告結束,或者卡頓難耐。英加登想出來的辦法,就是一種超然的、旁觀式的所謂審美態度,以此為回憶—反思或現象學還原提供最好的材料,在原發的審美生活與被還原的文學作品本質之間搭建一個過渡的橋梁。他說:
不管是美學價值還是其他的價值,只有在意識主體對價值客體采取了一種相應的態度,在我們這個情況下采取了審美的態度時,才會對我們顯現出來。這種態度和一個文化不高的讀者的強烈的激動相反,它表現為一種旁觀者的內在的冷靜,沉浸于作品的本身,這種狀態是不會有我們自己的體驗的。但是這種旁觀者的冷靜卻可以和最大的欣喜并存,它不同于一個人的那種冷淡的或者——說得更好一點——完全中立的,在對研究的客體作純理論的和理性的分析時所采取的一種純研究性的、一點也不激動的態度。在這種純理性的研究中,構成價值質的藝術作品的因素不會實在地顯現出來。(16)羅曼·英加登:《論文學作品》,第46頁。
這種超然的審美態度是“旁觀者的內在的冷靜”,因為“沉浸于作品本身”,就不會有“自己的體驗”了。既然不會有自己的體驗了,那怎么言說文學作品呢?原來,英加登是讓自己不動聲色地、毫無快感地,但也沒有什么痛感地閱讀一部文學作品或欣賞藝術作品。難道英加登是復制《紅樓夢》與《浮士德》的掃描儀與照相機嗎?英加登的這一設想實在讓人匪夷所思。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英加登認為,這種冷靜的旁觀者情緒與最大的欣喜情緒是并存的。那么,這種并存是把兩種情緒雜糅為一種情感嗎?既有最大的欣喜,又是旁觀者,這是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的,因為這并不是所謂的愛恨交加。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行為,怎么可能被融合為一個同一性的行為呢?而且更根本的否定性依據就是審美時間意識域所呈現的流暢時體。當最大的欣喜作為一個流暢的時間意識正在興發之時,就不可能同時存在一個冷靜的旁觀者的情感所顯現的時間意識也在并行、平行地綿延。
從注意力這一心理現象來看,人們都有不可能突破的心理能量瓶頸,心理能量是有限的。因此,人們必須明智地使用有限的心理資源,去高效地處置對于他們自身來說最有意義的心理操作,全神貫注、聚精會神便由此而生。當然,注意力也存在分配使用的實際情況,即人們可以同時關注多個對象。比如我們正在讀書的時候,往往可以同時聽音樂,或者把音樂作為背景音樂來對待,這就是注意作為時間意識的多行道。但是這種注意力的分配并不是針對同一個對象,而是針對不同的對象,而且更為重要的一個事實是——能夠并行處理的多個心理行為都是較為熟練的自動加工,一旦多個被并行處理的多個心理行為中的一個需要更多的,甚至全部的注意力之時,其他并行的心理操作都必須停止。比如一個人正在開車的時候,可以同時聽音樂,并跟同行的人交談,但是一旦遇到緊急狀況,那就無法同時并行處置了。這其實就意味著其中注意力的自動加工轉變成了控制加工。自動加工所花費的心理能量較少,難度較低,而且多個操作往往可以被壓縮為一個步驟里完成;而控制加工所需的心理能量較多,難度較大,而且只能按部就班地按照一個接一個的步驟來進行,這是注意作為時間意識的單行道。
反觀英加登所說的“最大的欣喜”與“旁觀者的冷靜”,它們與注意力的分配使用根本不是一回事,因為這兩種情緒或情感指向的是同一個對象,而不是一個人的注意力指向不同的對象。比如“最大的欣喜”所指的是A,而“旁觀者的冷靜”則指的是B,這兩個對象的性質根本不一樣,而且都是具體的事物,而不是兩個抽象的屬性。英加登的這一說法無法讓人信服,這要么是他的托詞,要么就是他很狡黠的一種策略——也就是說,他既要堅持審美生活不同于純反思性的、一點也不激動的態度,又要保持冷靜與中立。或許他自己知道這是無法做到的,所以只好如此含糊其詞且充滿矛盾地進行陳述。
英加登把與這種超然的審美態度相對立的態度稱為“文化不高的讀者”,這是一種歧視,而且這種歧視也只是一種職業優越感的幻覺而已。這種超然的審美態度,英加登本人做不到,而且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人都做不到,就是因為這種愉悅感與旁觀感在時間意識的存在方式上存在根本錯誤,而不是因為境界太高、太難。他說:
實際上——根據對構建在審美價值基礎上的價值的客觀體現的理解——它乃這些價值唯一的體現。在這種情況下,剛才提到的那種認識論的偏見對思考的過程是有影響的。這種偏見說的是:只有那種永遠從屬于每個認識主體的客體的屬性的東西才是客觀的,它不管在什么主體和客體的條件下,都完全是處于被動的狀態。這種偏見還認為,純理論和理性的認識至少在原則上能夠創造這種條件。(17)羅曼·英加登:《論文學作品》,第46頁。
從這里可以看出,英加登在語言陳述上有很多困窘。審美價值如果不是在審美生活之中呈現出來的,那就只能是一種事后對歷史的追認了,或者是事前對未來的期許,而不可能是在“事中”——一個正在流暢進行著的審美生活之中顯現出來的。因此,英加登在此既要與“文化不高的讀者”的主觀主義劃清界限,又要與純粹認識論之中的絕對客觀劃清界限。其實,他所說的“主觀主義”就是正常的、常態的審美生活的絕對同時性構成方式。看來,英加登通過現象學還原要尋求的文學作品本質只能是一個既不是絕對客觀,也不是主客之間不可分離的絕對主觀之物了。只不過,這個絕對主觀之物被英加登冠之以審美價值的客觀性而已。
綜上,英加登《論文學作品》在整體上采取了現象學還原的思想與操作,從而耽擱了對審美時間性的把握。需要補充的是,他對審美現象的具體描述則在多個局部突破了這一理論窠臼,做到了審美意義還原、審美還原。這就形成了他文藝理論著述中極突出的“現象高出思想”“描述高出概括”現象。尤其是到了《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識》中,他還自覺運用胡塞爾內時間意識現象學的思想與概念,對審美時間意識域之中的時間透視、滯留與前攝、流暢時體、時—空語法、積極記憶、時流視域內的文學作品多層次構成等有諸多創見,留待他文另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