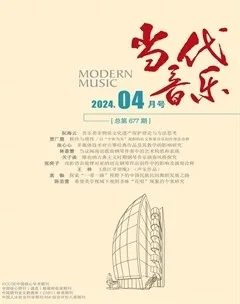秩序與理性


[摘要]在斯特拉文斯基的音樂美學觀念中,“秩序”是他音樂創作中最重要的理念,通過對秩序的整體建構達到對音樂情感的“理性”化表達,進而形成對“和諧”美的追求成為斯特拉文斯基音樂理念的主要特征。通過對藝術作品的客觀性建構,注重本體的審美價值,從而形成主、客觀的辯證和諧統一,達到“無過無不及”的思想理念,符合中國傳統美學主張的主客觀辯證統一的理想審美境界。基于此理念,斯特拉文斯基的音樂作品中充分顯現了中國傳統思想的“中和”的美學思想。本文將以“中和”為視角管窺斯特拉文斯基音樂美學思想來源,探尋其秩序與理性的深層次內涵,進而發現在其音樂作品中的價值呈現。
[關鍵詞]中和為美;斯特拉文斯基;秩序;理性
[中圖分類號]J6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2233(2024)04-0029-03
[收稿日期]2023-00-00
[作者簡介](賈廣晨(2000—),男,山東師范大學音樂學院碩士研究生。(濟南 250000)
《樂記·樂論》中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意思是說,音樂表現的是天地間的和諧,禮所表現的是天地間的秩序。因為和諧,萬物才不斷生長;因為秩序,萬物才顯現出差別。伊戈爾·菲德洛維奇·斯特拉文斯基(Igor Fuodorovich Stravinsky)對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在他的音樂作品中也體現了“和”的音樂思想。對于斯特拉文斯基來說,音樂從本質上來講,就是在大腦經過理性思考后的秩序化重建,是理性思維的產物而并非感性,音樂的表達不能超過“禮”的規范,也就是“秩序”。他反對像阿諾爾德·勛伯格(Arnold Schoenberg)那樣的無調性音樂和過度極端的情感宣泄,因為那樣的音樂超過了“禮”的規范,不是正確的審美情感。相反,他強調的是通過音樂秩序化的客觀性建構達到音樂的“中和”,也就是理性化的情感表達。“和”的音樂美學觀念經常在他的《音樂詩學六講》中被提及,他認為音樂本身就是和諧的整體,因此才能引發聽眾在思想感情和審美價值上的共鳴進而呈現出其美學內涵。音樂的“和”主要體現于思想意識層面,通過對藝術要素的結合從而實現其新的發展。而這種思想意識就是強調旋律和節奏及調性等音樂要素在作品中的有機整合。本文就以斯特拉文斯基的音樂思想淵源、秩序和理性的深層次內涵、“中和”的音樂思想在斯特拉文斯基音樂作品中的價值顯現三個方面把斯特拉文斯基的音樂創作理念放置于中國傳統美學觀念“中和”的語境中進行考察。
一、斯特拉文斯基音樂美學思想溯源
(一)俄國形式主義文論的影響
斯特拉文斯基早期音樂作品注重對主觀情感表達的追求,這種情感表達的追求集中體現在他這一時期所創作的最后的作品《春之祭》中。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Niesengrund Adorno)認為,《春之祭》中殘酷、狂暴、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結構背后,隱藏著一種對集體、種族的“反人性的獻身”的思想感情。《春之祭》中那種令人發狂、興奮、神智昏迷的音樂表現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中所謂“潛意識壓抑力”的理論也不是毫無關系。但是,在創作完成《春之祭》后,他的音樂風格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進入“新古典主義”時期,音樂創作思想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他摒棄了對感情的過度表現,轉而追求感情的節制。就音樂的本質而言,他認為音樂并不能表現任何東西,無論是情感還是精神狀態,表現從來都不是音樂的本性。這種看法顯然同漢斯立克的形式-自律論的觀點相一致。這種音樂哲學觀念的轉變,顯然和20世紀初興起的俄國形式主義文論以及20世紀40年代興起的美國“新批評派”相聯系。
20世紀的俄國形式主義文論主要以文學批評家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為代表,他們的基本理論觀點是“文學性”。所謂“文學性”是指把文學作品本身作為研究批評的對象,也就是語言邏輯和結構等形式,而不是通過心理因素、作者的生活經歷以及社會學等角度進行考察和研究。斯特拉文斯基接受了俄國形式主義的觀點,并從形式方法論的維度來整合音樂作品內在的形式要素,通過對形式、結構的高度理性化的平衡和謹慎的構思,斯特拉文斯基在音樂創作上表現出了自我節制并竭力控制情感的流露的特點,同時也顯現出了他的音樂哲學觀念。這在1915年之后創作的《詩篇交響曲》《普爾西奈拉》等作品中也得到了較為明顯的體現。
(二)美國“新批評派”
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興起了“新批評派”,而“新批評”一詞源于美國文藝批評家、詩人約翰·克羅·蘭色姆(John Crowe Ransom)的著作《新批評》一書中,其流派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艾略特和瑞恰茲。新批評派的代表人物蘭色姆提出了著名的“結構肌質”二元論,把詩歌分為“結構”和“肌質”兩部分。所謂“結構”就是作品的意義得以連貫的邏輯線索,是可以用散文加以轉述的東西,是它給予了感性資料以方向和秩序。而“肌質”則是非邏輯性的部分,也就是作品中深刻的精神內涵。蘭色姆認為,結構和肌質無關,也就表明了形式與內容無關,內容比起形式來說,其重要性較低。因此,藝術批評家要忘掉那些所謂哲學、道德、倫理等思想情感意識形態,專心去洞察詩的形式。可以說,斯特拉文斯基音樂中對“結構”“秩序”“形式”的追求和美國“新批評派”的理論主旨相符。斯特拉文斯基作為新古典主義者,他音樂作品中所體現的形式嚴謹簡練、情感含蓄理性、結構風格清新典雅,同“新批評派”蘭色姆等人所主張的固守格律、凝練清晰的結構、避免感情外露的詩風極為相似,這并不是偶然的。因此,美國“新批評派”的詩風又被稱為新古典主義文風。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音樂還受到象征主義理念以及未來派美學思想的影響。前者使得他在1925年至1950年在其藝術創作領域探求音樂形式的象征意義,后者對俄國形式主義產生了較大影響的同時,強調形式的創新,這也成了斯特拉文斯基在繼承俄羅斯音樂傳統的同時,如何創作出新穎的并符合其時代特征的音樂所要思考的問題。
二、以“中和為美”觀其秩序與理性
“中和為美”強調一種適中的情感表達,與中國儒家學派的思想相一致。孔子主張音樂的審美必須用辯證統一的哲學思想才能真正把握音樂的真諦,正確的審美應當是把握事物的形式美,進而把握事物的本體與生命的存在,而這種審美情感應當是有限度的、節制的,符合“禮”的規范,也就是斯特拉文斯基所認為的“秩序”。孔子的美學強調“和”的重要性,如果超出“禮”所規范的情感,那么這種審美感情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只有做到“以中為立”才能達到對立統一,進而做到情理的統一,“美善”相合。在斯特拉文斯基看來,音樂應該是理性的,這與孔子的觀點相符,同時,他也認為音樂是“智力”和“思考”的產物,音樂就是人的“思考現象”。在音樂創作中,是人有意識的創造性活動賦予了聲音與時間以形式。問題是怎樣賦予聲音和時間以形式?斯特拉文斯基認為,要通過“組織”和“秩序”,要將時間和聲音的特定組織形式納入特定的音樂秩序中去。音樂創作的過程是作曲家對材料進行選擇和控制的過程,結果往往是能夠建立打動觀眾并且能夠說服觀眾的結構形式,所以音樂并不在于過度的感情訴說,而是在于音樂高度組織化、形式秩序化的結構。這種秩序是理性的,能夠進入音樂“中和”的審美范疇。相反,如果作曲家摒棄這種秩序,進行無限自由的情感表達的話,這樣的音樂便會失去聲音和時間的有組織化的建構,進而失去平衡,導致音樂形式扭曲畸形發展,從而喪失了其審美價值。斯特拉文斯基以此觀念對瓦格納的樂劇中“無窮的旋律”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認為這種“無窮的旋律”使得音樂不斷生成,既沒有理由結束,也沒有了理由開始,形成一種“無序性”,從而給旋律結構造成嚴重的破壞,失去了旋律本有的藝術魅力。同時,斯特拉文斯基對瓦格納的批判還在于其“主導動機”的使用,他認為瓦格納把音樂所不能承擔的責任強加于音樂本身,因為在他的音樂思想中音樂并不能代表一個人的心理情緒,音樂的本身在于其形式,而不在于其模仿人的心理特征。斯特拉文斯基對于以瓦格納為首的浪漫主義極端個人化的自欺欺人的理想進行了無情的批判,著重體現了20世紀知識分子在面對異化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空前繁榮所體現的對客觀和理性的回歸,也體現了他對于理性的認識與表達,通過統一秩序與理性,進而達到他所認為的“中和”的理想境界。
總的來說,斯特拉文斯基對于秩序和理性的認識集中表現在其著述的《音樂詩學六講》中,這是他研究美學的重要載體。在其書中,斯特拉文斯基不斷從形式的方面來探討音樂的本質,他從形式出發,不斷對形式進行創新,在創新的背后給予形式以內涵和規律,在混亂的音樂材料中建立秩序,以“禮”為規范,進而表達其理性的感受,也就是“中和”的理想。
三、以“中和為美”觀《彼得魯什卡》中的價值呈現
《彼得魯什卡》是斯特拉文斯基早期的代表作品,雖不屬于新古典主義時期,但舞劇《彼得魯什卡》的音樂具有鮮明的理性色彩、凝練的旋律、豐富的管樂音色,并預示著某些音樂形式的創新,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筆者以《彼得魯什卡》為例,來探尋“中和”理念在這部作品中的價值顯現。
(一)節奏節拍方面
《彼得魯什卡》打破了傳統節奏原有的律動性。這體現了斯特拉文斯基作為音樂形式論的探索者在節奏形式方面的創新,他通過利用不規則的重音以及頻繁變換的節拍來塑造新的音樂效果,并以這樣鮮明的節奏形式來說服觀眾,從而給予觀眾以新鮮感。比如不斷重復其節奏型、不規則的重音和每小節就換一次節拍等,發展了節拍在創作中的運用。如譜例1所示。
斯特拉文斯基利用節拍自由不斷的變化對節奏進行自由的組合,以這種新穎的創新方式達到了他所要表達的藝術效果。斯特拉文斯基通過對節奏的建構,達到了其“秩序”化的追求,而節拍的自由運用也體現了他對“創新”的探索。由于顛覆了節奏節拍強弱順序從而給觀眾造成了刺激的心理效果,給人以興奮的心理感受,因此這部舞劇有了獨特的藝術魅力。斯特拉文斯基認為正是在這種客觀理性的秩序的構建下,才激發了觀眾的感官,因此音樂作品的價值不在于情感的表達,而在于秩序的建構以達到“理性”也就是“中和”的境界。
(二)旋律與和聲方面
《彼得魯什卡》的和聲突破了傳統和聲體系限制,形成了獨特的音響效果。在作品中使用各種不協和和弦,但不是無節制的。同時,還使用了很多的三度疊置結構,但不是無調性的。有時調性比較模糊,由于使用了復和弦,形成了多調性。如譜例2所示。
在《彼得魯什卡》的音樂進行中,不管斯特拉文斯基使用的和聲多么復雜,和聲功能多么難以判斷,其和聲的進行往往是在其主和弦上終止的,看似和聲調性復雜,實則調性明確有度。這樣的音樂特點區別于瓦格納所使用的“調性游移”,在斯特拉文斯基看來,這種音樂與理性背道而馳,是過度感性的表現,這種表現超過了“禮”的規范,不具有審美價值。在旋律方面,斯特拉文斯基好像并不擅長于創作旋律,他的旋律是服務于和聲功能的。斯特拉文斯基認為過度追求旋律的優美和華麗往往會陷入情感的陶醉而喪失理性,所以,在他的思想中,旋律的重要性是要低于節奏的重要性的。在《彼得魯什卡》這部作品中,音樂的旋律要從屬于和聲和節奏,有時旋律的進行給人以平和、平穩的感覺。在他的許多作品中,旋律會重復好幾個樂段,并給人以平和的感覺,從而形成了一種“靜止性旋律”。因此,他的旋律也是靜止性的、片段性的、枯燥單調的。這種鮮明的音樂特征表明斯特拉文斯基在構思音樂時所采取的謹慎簡潔的態度,通過對結構的客觀化建構,達到其“無過無不及”的“中和”理想。
(三)題材的選擇方面
斯特拉文斯基打破了以往選用神話故事作為音樂創作題材的原則。在以往,選用神話題材來表現浪漫的愛情故事是舞劇以及歌劇的傳統,舞臺的光鮮亮麗,舞蹈的優雅曼妙,以及音樂的抒情動聽等,在《彼得魯什卡》中都未得到體現。瓦格納的歌劇經常使用童話傳說以及神話作為其歌劇創作的題材,比如《羅恩格林》《唐豪瑟》等。但斯特拉文斯基認為選用神話并不具有社會現實性,那是理想化的狀態,是感情的過度宣泄。所以,斯特拉文斯基改變了過去采用以歌頌美好愛情故事為主的神話題材,轉而以表現更多的諷刺和悲劇為主要主題,題材的選擇往往以社會底層平民的悲慘遭遇為主。這部舞劇的主角是一個追求愛情而又遭遇“毀滅”的小丑彼得魯什卡,他在追求自己心愛的情人面前無能為力,暗含了理想中的愛情在現實中的脆弱。斯特拉文斯基并沒有像朱塞佩·威爾第(Giuseppe Verdi)那樣在塑造瑪格麗特死亡時所使用悲傷的旋律來渲染悲劇的氛圍,也沒有像賈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那樣在刻畫蝴蝶夫人巧巧桑時的那種戲劇性矛盾,而是較為平靜理性地刻畫了彼得魯什卡的形象與命運,似乎全劇從一開始就預示著彼得魯什卡必定走向死亡的命運。或許正是這種理性的刻畫,才使得觀眾對彼得魯什卡的遭遇產生巨大共鳴。
結語
通過以“中和為美”的維度看斯特拉文斯基的音樂理念的闡述,能夠更好地理解他所強調的“理性”觀念,通過對其“秩序”和“理性”的深層次解析,能夠看到斯特拉文斯基音樂美學思想與中國傳統的音樂美學思想有很多相似之處。斯特拉文斯基對秩序和理性的闡述與儒家美學思想所主張的審美辯證的統一,以及情理的統一,并以此來達到“中和”的審美標準相符。因此,從“中和”的審美觀來看斯特拉文斯基音樂作品的清新典雅、理性含蓄的情感表達也就有了中國語境的視角。
參考文獻:
[1]斯特拉文斯基.音樂詩學六講(修訂版)[M.姜蕾,譯.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4.
[2]于潤洋.現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2.
[3]張楠.從《彼得魯什卡》看斯特拉文斯基的創作及美學思想[J].音樂創作,2014(12):170-172.
[4]張洪模.現代西方藝術美學文選——音樂美學卷[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1.
[5]高佳欣.斯特拉文斯基舞劇《春之祭》的音樂特征分析[J].大眾文藝,2021(7):118-119.)
(責任編輯:馮津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