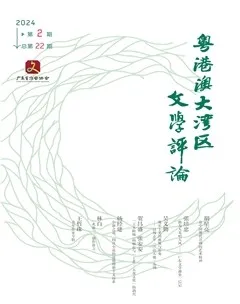事件敘述中的時間與空間
白溢陽 孫基林
摘要:事件是世界的基本要素,是具體的、流動的實在。于堅是“第三代詩歌”的代表人物,“事件”在其詩學思想中占據重要地位。于堅以事件作為詩歌構成的基本元素,力求在詩中展示時間和空間的綿延,并以事件的發展歷程探尋某些存在。本文以“事件”的視角切入,試圖通過解讀詩歌文本中時間的流動與空間的轉換,探討于堅詩歌所反映出的現在性和過程哲思。
關鍵詞:于堅;事件;敘述;時間;空間;意味
于堅是第三代詩歌的代表人物,他自覺以日常生活為題材進行口語化的寫作,并不斷進行詩歌本質的探索。八十年代之后,于堅“更加重視語言,更重視語言本身的還原,使一個詞能在它本來的意義上使用”,并提出了“拒絕隱喻”的詩學觀念,有意識地在詩中引入敘事性元素。其后,于堅有意識地“對日常生活經驗進行深入的描述”1,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事件”系列詩歌。“事件”在于堅的詩中承擔著重要功能,于堅有一部分詩歌是直接以“事件”命名的,如《事件:裝修》《事件:挖掘》《事件:鋪路》等;除了這些直接命名為“事件”的詩歌,還有許多詩歌在題目上直接描述了事件的內容,如《那時我正騎車回家》《有一回、我漫步林中》等,都能看出是對日常生活中事件的記敘。動態化的事件描述成為了于堅書寫日常生活經驗的表達方式。“事件”是于堅詩歌在內容層面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詩歌結構上也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單元。如巴迪歐所說,“事件乃是變動本身”,于堅的詩歌呈現出一種動態的事件流變。在描述事件時,于堅善于捕捉事件發生的瞬間和細微的發展變化,運用大量的動詞敘述事件內部事物的行動狀態,注重時空的同時移動,造成強烈的動態感。
關于“事件”與“事件詩學”,中國古代文論中有很多與此相關的描述,比如“緣事而發”“理、事、情”“歌詩合為事而作”等,“事”都在指涉客觀發生的事。由此可見,事件在中國古代詩歌傳統里承擔著重要的功能,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中國總體上有一個遮蔽和輕忽敘述維度的詩學傳統,自古以來便以抒情詩作為文學的正宗相標榜”,2詩的抒情性成為本質,抒情也更引人關注,而事件的敘述性則相對被輕忽。于堅曾在采訪中提到,中國傳統文化對他是“一種民間的、地下的影響”;而西方對他更多的是“方法上的影響,提供一種理性的思維,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形式”1。因此,西方具體而又具系統性的“事件”理論則對他的詩歌創作實踐產生了更為顯著的影響。
西方的“事件”理論從哲學領域轉化而來,在不斷地闡釋和解構中進入了文學的視域,進而又發展到敘述學這個特定的學科范疇中,成為研究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切入點。懷特海在著作《自然的概念》中對事件視角下的時間和空間進行了比較系統地闡述。“事件的流變和事件的相互擴延,在我看來是性質:時間和空間作為抽象的東西就是從其中產生的。”2懷特海認為,事件是具體的、唯一的,它是自然中實際發生的東西,是一個時空連續體。宇宙中最主要的單位是事件,這是一個在時空中發生的事實,事件帶來的是流動的綿延,即使進行無限的劃分,最小的本質也仍然是事件,最小的時空也仍然是綿延,因此事件具有時間上的綿延性和空間上的擴展性。懷特海堅持時間和空間并非獨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的,他把時間、空間都看作是一種擴延,從而把事件轉化成一個活動的過程。
過程是一個變化,一個發展,從而事件必須以時間序列或時間先后順序為其先決條件。事件本身在一定的時間內,以一定的秩序出現。3而當事件進入到文學的領域,敘述時間和敘述空間便出現了“故事時間”與“話語時間”“故事空間”與“話語空間”的區別。詩人為了敘述事件、建構情節,常常在話語層次上“任意”撥動、調整時間和空間,時間和空間的綿延和變化使事件的發生立足于詩人此時此地的生命體驗之中。以于堅為代表的第三代詩人及其之后的詩歌寫作,便大都進行一種“事件化”的敘述抒寫,在把握事件的動態和過程的綿延中深入日常行為和體驗,從而呈現和表達詩人對外部世界的感受與內在世界的認識。由此亦可見出,事件往往是“從某一狀態向另一狀態的轉化”,它強調的一種動態性和過程性,作為第三代詩人的于堅,看重這種事態的轉化和過程的綿延,與傳統意象詩學觀念不同,他無意在詩中進行意象化描寫,反而對其進行消解,在對隱喻的拒絕中使得這種事件化的敘述成為他詩歌中占主要地位的表達形態和方式。
一、敘述時間的流動
在敘述類詩歌中,事件的存在是由無數瞬間流動綿延而形成的一個過程。正如同懷特海的觀點,即使是最小的時間單位也是一段的,是綿延的而不是瞬間。《現在的哲學》中提到,“綿延是一個現在持續不斷地過渡到另一個現在的過程。”4于堅將這種理念融入了他的“事件化”寫作中,他在事件敘述的時間處理上隨機而變,對詩歌的時序和時距靈活處理,將日常生活詩化的同時,展現出一個在時間上具有強大容量的詩歌世界。于堅以事件作為基點,試圖用潛在的時間來詮釋自己的過程意識,并借由事件的發展過程來證明某種存在。
1.敘述時間的時序倒錯
詩歌是高度強調藝術處理和形式加工的文類,因而建構了更為復雜的時間環境。于堅的詩歌往往出現故事時間和話語時間的不對等現象,事件發生實際上所需要的故事時間往往很長,而于堅敘述事件的話語時間卻很簡短。話語時間遠遠短于故事時間,必然會產生時間壓縮和時間倒錯的現象。于堅的視覺捕捉能力極強,他善于將綿延流動的時間投射到靜態的參照物上,從而展現出獨特的審美性。《一只充滿傷心之液的水果》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展現出時間的流動:
一只充滿傷心之液的水果 擱置在清晨的桌面上
塞尚的白桌布 野獸們夢想中的鉆石
陽光旋轉 搬動著影子 讓它青色的一面向著光源
紅色的一面在黑暗深處 綠色的一面在鏡子中1
時間的變化轉化為影子的變化,隨著影子的移動,時間一點點地流逝變得可見可感。詩人呈現給讀者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個微小片段,通常情況下,陽光的位置發生很明顯的轉動,才會發現被“搬動”的影子,于堅把半天甚至一天的變化壓縮到短短一句話中,詩歌的話語時間與故事時間出現較大的裂隙,由此產生張力,帶動詩歌向前發展。這種敘述方式也體現在詩歌《一枚穿過天空的釘子》中:
一直為帽子所遮蔽 直到有一天
帽子腐爛 落下 它才從墻壁上突出
那個多年以前 把它敲進墻壁的動作
似乎剛剛停止 微小而靜止的金屬
露在墻壁上的禿頂正穿過陽光
進入它從未具備的鋒利
在那里 它不止穿過陽光
也穿過房間和它的天空2
詩人在前兩句描寫的是帽子掉落的當下,從第三句開始,時間回溯,詩人描寫這顆釘子在“多年以前”被“敲進墻壁”的動作,卻“似乎剛剛停止”,詩人用倒敘的表現手法,省略了釘子“為帽子遮蔽”的這些年,把“多年以前”視為“剛剛”,造成一種時空上交錯擴容的藝術效果。這顆釘子是靜止在墻上的,但是詩人卻關注它“正穿過陽光”的瞬間,同樣也是將動態流動的時間投射到靜止的釘子上,使詩歌文本的現場感和現在性得以強化。由時間的具化引發瞬間的存在與被感知,當下的意義和價值得以體現。同時,時間量度本身具有不確定性,于堅有意對時間進行模糊處理從而使詩歌超越了時間限制而獲得了縱深感。
2.敘述時間的時距效應
陳仲義在點評于堅的詩歌時指出:“于堅的《事件》系列,在事件的進程中,通過切片方式,于單位時間內放慢時速,進而凸顯事物的紋理:一次《翹起的地板》,一次《啤酒瓶蓋》的下行過程,對一個雨點的觀察,一次殺魚的展開……通過過程的切片放大,讓人感受事件的表象,也由此走進事件的真相。”3于堅在詩歌創作中力圖打破時間的線性規律,他將現在的時間無限擴展,使事件的發生和發展變得無限緩慢。在時距上話語時間無限大、故事時間接近于零的停頓,聚焦了事件過程中他想要強調的細節,并加以最大限度地放大,賦予它一種場景的充實感。在《鐵路附近的一堆油桶》這首詩中,于堅對火車經過汽油桶的瞬間進行了非常細致的描述:
看不見任何內部 火車途經此地
只是十多秒 目擊一個表面的時間
在此之前 我的眼睛正像火車一樣盲目
沿著固定的路線 向著已知的車站
后面的那一節 是悶罐子車廂
一群前往漢口的豬 與我同行
在京漢鐵路干線的附近 我的視覺被某種表面挽救
仿佛是歷史上的今日 文森特梵高
抵達 阿爾附近的農場
我意識到那不過是一堆汽油桶 是在后來1
火車經過這堆汽油桶,只用時短短十多秒,但是詩人卻把這十多秒的事件無限延伸,連接起了過去和未來。“在此之前”,“我”的眼睛是盲目的,對火車途經的景物毫不關心;在此之后,“我”才意識到,剛剛經過了那堆油桶。這個事件的發展過程非常具有連貫性,詩人以一種緩慢的方式敘述出來,在具體的細節中把握事物的存在。在另一首詩《下午一位在陰影中走過的同事》中,于堅在刻畫事件細節時所體現的過程意識和時間意識也表現得淋漓盡致。這首詩由詩人偶然看到同事的一個動作細節所引發的過程,時間相較于上一首詩更短,全程只有五秒:
這天下午我在舊房間里讀一封俄勒崗的來信
當我站在唯一的窗子前倒水時看見了他
這個黑發男子 我的同事 一份期刊的編輯
正從兩幢白水泥和馬牙石砌成的墻之間經過
他一生中的一個時辰 在下午三點和四點之間
陰影從晴朗的天空投下
把白色建筑剪成奇怪的兩半
在它的一半里是報紙和文件柜 而另一半是寓所
這個男子當時就在那狹長灰暗的口子里
他在那兒移動了大約三步或者四步
他有些遲疑不決 皮鞋跟還撥響了什么
我注意到這個禿頂者毫無理由的躊躇
陽光 安靜 充滿和平的時間
這個穿著紅襯衫的矮個子男人
匆匆走過兩幢建筑物之間的陰影
手中的信 差點兒掉到地上
這次事件把他的一生向我移近了大約五秒
他不知道 我也從未提及2
這首詩開題用兩句詩簡單交代了時間地點和事件起因,從第三句開始事無巨細地交代同事的外貌細節和動作細節、所經過的地點細節和時間細節。于堅通過個人精微的生命體驗將五秒鐘的事件拉長、擴張,男人“躊躇”和“匆匆走過”的細微轉換中有進一步將時間拆分揉碎之感,再加之以細節的填充,時間的密度被極大地增強。在這條“狹長灰暗的口子”里,詩人在客觀呆板的物理時間序列之外生成意趣盎然的情態與體驗,時間的延宕生成與擴大了詩歌之境。
于堅在詩歌創作中重視展現自然的連續性、延展性、現實性、關聯性以及外在性,并通過對“正在發生的事件”的描述,使詩句暗含了時間量度。他將細微事件之間的邏輯關聯用動態的流動體現出來,詩歌中的時態交錯、時距和空白設計、時間意象的重復、閱讀時長的效應等表征使敘事時間呈現多樣化特征。因此,事件敘述所體現的日常性,也可以稱之為“正式的現實性”,就是由時間流動和綿延所構成的現實過程。從時間上說,它既不在過去,也不在未來,它在當下也即“此時”;而從空間上說,它既不在前面,也不在后面,或左邊、右邊,總之它就在眼前、腳下或者“此地”。3
二、敘述空間的轉換
懷特海認為,事件是最具體的終極事實,在時間的側面上是綿延而非瞬間,在空間的側面上是體非點,從而使“事件”的時空體系更加直觀、具體。事件的發生離不開場景,因此空間也是事件敘述的一個重要載體。在進行空間敘事時,不可能脫離時間這一重要維度,同樣的,時間也不可能脫離空間而存在于敘事之中,時間和空間不可分割,時空一體性是所有敘事的底線。在于堅看來,“‘詩是動詞,是“語言自身的運動,詩人操作與控制的過程。”1他在敘述事件時講究時空并重,通過具體事物的位移搭建一個立體的空間,將時間邏輯和時間框架隱于空間之后,呈現出動態化的客觀事件。詩歌中所描繪的事件同時在時間和空間中延展,空間的凝聚、擴展和轉換展現了事件的狀態轉變過程,時間在空間的變換中流動,造成了一種四維的動態效果。
1.敘述空間與心理
空間敘事中的心理,總是與知覺、感覺聯系在一起的。空間與心理的橋梁,是認知。“心理空間”是指“一個內部、主觀的空間,也是人的內心對外部世界的投射”2。于堅在進行詩歌的空間建構時,善于從小處著筆,將詩歌的畫面由近及遠地移動,在這個過程中放大敘述者的知覺和感受,搭建起空間和心理的橋梁,打通現實空間和心理空間的邊界,從而使詩歌的空間得以無限地擴展和綿延。在《事件:停電》中,于堅強調“我們熟知一切 停電之前 停電之后 一樣的”,并在黑暗的環境中再現房間的布局:
頂上吊燈 腳下地板 左手左邊 右手右邊
床在房間深處 靠窗放著 旁邊是梳妝臺和鏡子
箱子放得最高 鞋最矮 食物在櫥柜里 電視報告新聞3
詩人的視覺在黑暗中喪失,只能通過記憶呈現出心理空間事物,隨后他開始嘗試用觸覺感知現實空間,將物體存放的地點與自身存在進行了聯結:
伸出左手 可拿到止痛片和熱水瓶 水杯和香煙
伸出右手 能碰到桔子 糖缸和雜志 再伸直些 有火柴
跨前半步 這個長物件必是沙發 順勢而下就安抵軟墊
后退一點 墻根的空處 位于一米八高度的是相框4
詩人用“伸、拿、碰、跨、抵、退”等動詞夸張了事件發生的全過程,小心地測量心理虛幻距離與實際物理空間的差距,記憶和觸覺的一致性打通了心理空間和現實空間的壁壘。作者后半部分把敘事對象集中在斷電之后的內心世界,使其空間的想象力得到了極大的拓展。詩人的心理空間逐漸延伸到房間內較遠的地方,最后抵達“掛歷上八月的公狼”,當詩人由于黑暗無法確定公狼的位置和存在而感到錯覺和恐懼時,時間和空間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綿延,由現實世界擴延到了詩人的精神世界。而在詩歌《在深夜 云南遙遠的一角》中,詩人同樣用大量的筆墨詳細地描繪了事件發生的過程。
在深夜 云南遙遠的一角
黑暗中的國家公路 忽然被汽車的光
照亮 一只野兔或者松鼠
在雪地上倉皇而過 像是逃犯
越過了柏林墻 或者
停下來 張開紅嘴巴 詭秘的一笑
……
在公路邊 幽靈般的一晃
從此便沒有下文5
詩人借助空間的透視原理展現了一只兔子在雪地上倉皇逃離的過程,兔子從眼前逃跑直至消失的一點,指向一個未知的空間。兔子的突然出現和消失,制造出虛實交融的蒙太奇。詩人控制兔子和敘述者之間的距離,對讀者心理空間的構建情況進行預判,隨著兔子的快速移動,詩歌時空的縱深感得以加強,讀者在閱讀時會根據個人體驗自動彌補時間和空間的空白,從而建構出一個無限延展的時空。
2.敘述空間與敘述視角
懷特海曾提到,自然以一個連綿不斷的整體存在于時空之中,知覺者在感知事件時,并非以一個全知者的姿態從高處審視,也并不能以主觀意識進行干擾,而是與所知覺的事物平等地存在于同一個時空范圍中。這種敘述視角被熱奈特稱為“外聚焦”,敘述者的視野具有局限性,像一臺攝影機一樣,以一種相對客觀的角度呈現每一個事件,從外部提供人物的行蹤和周圍環境。1于堅說“一首好詩必然創造出一個場”,事件呈現出了一個“場”的空間,在對這個空間進行觀照時,于堅時常呈現出的是一個旁觀者的姿態,客觀化的敘述事件。比如在《事件·裝修》中,“從這道門到那道門 要經過洗臉架和痰盂/在筆筒和花瓶之間 依次是墨水、硯臺、文竹”2,詩人對空間內的陳設始終保持著客觀的態度,而至于“黃櫥柜為什么要放在這里 為什么有一只腳是斷的”,詩人沒有揣摩物象的內涵和意義,也沒有對此發表自己的主觀看法,只是說“只有睡在郊外青山中穿馬褂的外公知道”3。同樣的,在長詩《0檔案》中,詩人放棄全知敘述者的視角,作為事件外的第三人稱敘述者,旁觀“他”的上班環境,冷靜地呈現情景的轉變,詩句不帶有任何情感傾向:
建筑物的五樓 鎖和鎖后面 密室里 他的那一份
裝在文件袋里 它作為一個人的證據 隔著他本人兩層樓
他在二樓上班 那一袋 距離他50米過道 30級臺階
與眾不同的房間 6面鋼筋水泥灌注 3道門 沒有窗子
一盞日光燈 四個紅色消防瓶 200平方米 一千多把鎖
明鎖 暗鎖 抽屜鎖 最大的一把是‘永固牌掛在外面
上樓 往左 上樓 往右 再往左 再往右 開鎖 開鎖
通過一個密碼 最終打入內部 檔案柜靠著檔案柜 這個在那個旁邊
那個在這個高上 這個在那個底下 那個在這個前面 這個在那個后面4
詩人用大量的動詞和極其精細的數字描繪了檔案室的位置,事件的呈現從存在轉向了過程,空間隨著視角的移動逐漸展開,呈現了一個壓抑窒息的環境。這種鏡頭感能夠使讀者依照詩歌敘述的順序在頭腦中想象、勾畫,并隨之進入詩歌空間,從而給讀者以極強的代入感,進而更易調控讀者的情緒。
在詩歌《兵馬俑博物館》中,于堅同樣使用了攝像式外視角的空間敘事,前半部分羅列了幾十位歷史和現實中的人物魚貫進入秦始皇陵兵馬俑博物館,然后用短語呈現了現場的狀態,“指指點點 交頭接耳 搖唇鼓舌/手機 解說詞 麥克風 外國語/旁白 秦腔 普通話 呼風喚雨/激揚文字 制造出巨大的喧囂/那些秦俑閉著嘴 目不斜視/沉默著/三萬大軍 沒有一塊舌頭”5,下半部分設置了無邊際的沉默,通過獨特的斷句和分行方式來表達特殊的空間特征,“沉默者 沉默著沉默著 沉默著”整齊排列,最后“我們張口結舌 解散”。“沉默者 沉默著”的語言排列形式猶如整齊劃一的兵馬俑,由語詞物質層面所編織出的“圖像”的視覺沖擊力躍居首位,在視覺上帶來強烈的空間感受。懷特海說,“事件是二元關系的場地”1,在時空一體的場域里,于堅將事件從“魚貫而入”一直描寫到“解散”,空間的轉換過程也隱含了時間的流動。
“任何一個事件都既是時間維度的存在,又是空間維度的存在。如果僅強調前者而忽視了后者,無疑是對事實的歪曲,對真實性的遮蔽。”2于堅的空間敘事就是在“事件”的參照下,通過對時空的變化來傳遞自己的過程思想。空間的轉換是一個載體,通過心理空間的建構、敘述視角的客觀化呈現,承載詩人思考的過程和自我表達的投射,從而形成了于堅詩歌獨特的空間敘事節奏。正如于堅所說,“詩是為了讓世界在語言的意義上重返真實(存在)的努力,在這里,‘返的過程就是詩被澄明的過程……存在,就是在途中。詩就是在途中,途中就是能指或命名呈現的過程。”3
三、“事件”敘述中的時空意味
朦朧詩及之前的詩人熱衷于對宏大歷史的隱喻性發掘,這也必然導向對過去或者未來的向往與憧憬,于是,個體生命深陷于對過去與未來的雙重幻覺之中,呈現出一種非存在的狀態。這種歷史循環的時間或現代主義線性的時間觀正是第三代詩人努力反叛的。第三代詩人往往描寫“正在發生的事件”,立足此時此地的生命體驗,質疑過去(歷史)與未來(理想)那種循環或線性時間,體現出一種注重現在時的瞬時狀態的后現代時空觀:時間壓縮于“現在性”的“此在”,具有了空間的特性;它告別傳統、歷史的規定性與連續性,不再是一種縱向的時間延展,而是一種具有多維度的、充滿斷裂與裂縫的空間存在。因此,后現代時空意識往往表現為“此在性”,即“‘現時的‘在與‘現地的‘在”,只有“抓住眼下每一個可供感覺棲息的時刻,才能真正去體驗‘此時此地的生命過程和漫長而又短暫的人生之旅”。4
于堅認為“當代詩歌寫作真正的現代性是對‘無的重建,對時間的重建”。面對非永恒的線性時間帶來的種種弊端,面對“新的經驗”,“我們必須再造時間”5。于堅的詩向我們呈現的時間觀不再是面向未來、前進、斷裂、急速的線性時間,而是面向自然、當下、后退、緩慢的非線性時間,不再是單向度的、一維的時間維度,而是多向度、立體化的時間維度。事件作為于堅對日常生活的“閃存”,儲存著太多日常生活碎片,觀察一個雨點的一生、在牙科病室寫詩、林中漫步、早晨刷牙、公園晨練等等,向我們展現一個多面立體的于堅生活思想全貌的同時,也向我們呈現了日常自然時間觀視角下生活的多種形態,悲傷、快樂、虛無、矛盾、緩慢、平靜等,它們都是真實存在于我們生活的當下。于堅在事件敘述中對時間進行各種暫停、轉換、延伸、變速,在日常生活的瑣碎和庸常中發現當下和瞬間的詩意,時間也因此轉化成有內涵、有形態、有意義的審美對象,由此尋繹出時間的多種向度和可能性。
空間是事物存在、事件發生的又一根本體坐標,與時間一起為事件定位。與缺少歷史與理想關聯的、當下的“現在性”時間相照應的是“此在”空間中的事、物、人。空間作為一種文學建構的方式,是由主體參與建構的實在與想象的復合。由于自身聽力上的一些異狀,于堅對于非聲音系統的時空更為敏感,現實世界通過感官投射到他的內心,超過了形體的障礙和約束。現實空間和心理空間的連接與融合,搭建了一個可以無限延伸的時空場域,“當下”“瞬間”的日常在空間形式的聚合中成為一個整體,構成了具有詩性的存在語境。“時間的空間化”和“空間的時間化”是于堅強調事件“現在性”狀態的手段,他企圖通過客觀的事件呈現“重建日常生活的尊嚴”,建立起時間和空間縱向的深度和橫向的廣度。
于堅作為第三代詩歌的代表人物,他關注的主要是個體生命體驗當下的行為動作和瞬時感受,用事件本身來傳達某種思想、情感或者理念。事件與其一切的過程、脈絡有關,與其一切具體的細節有關,因為在許多微小的事件之間均有著邏輯上的關聯性,這種關聯性是需要動態的流動體現出來的。然而在另外的很多詩人那里,在他們通過詩歌語言來傳達自己的宇宙觀的時候,容易忽視流動性,往往用一種穩定的、靜態的視角去描寫事物。比如臧棣的《詠物詩》描寫松塔:“窗臺上擺放著三個松塔/每個松塔的大小/幾乎完全相同/不過/顏色卻有深有淺”1。我們難以明晰地看到這些詩句中有一種“時間量度”和“空間向度”,它們更傾向于用一種穩定性來表現事物的永恒屬性。而于堅則突破了這一點,他把某種存在即使永恒性置于不可逃脫的流動性之中,也就是說,在時間和空間的流變中發現永恒。相對于現代主義詩歌所倡導的宏大歷史或者理想主義線性時間,日常生活所固有的零碎、斷裂、凡俗與當下性等特性,使得于堅詩歌對日常生活中的人、事、物的時間和空間書寫顯得尤為真實、恰切而多維。
阿格妮絲·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指出:“日常生活在其中進展的時間,同它在其中發生的空間一樣是以人類為中心的。正如日常生活總是同個人的‘此地相聯,它也同個人的‘此時相聯。現在是日常生活發生的參照系。”2于堅要解構的是在現代主義線性時間觀基礎上的隱喻文化,而要建構的是以日常生活形態出現的此時此地的存在。因此,于堅的詩總是在敘寫局部、具體、細節,或者直接呈現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本身。于堅曾經在《棕皮手記》中表達過,詩不思考,詩本身就是一切。他主張還原,不想讓詩歌承載本不屬于它的東西,但是他把權力交給了讀者,從他的“事件化”敘述中,讀者能夠看到時間與空間的無限延展性,從而完成詩歌對存在本身的還原。
于堅在《拒絕隱喻》一書中說:詩歌所歌詠的“不是蘭波們所謂的‘生活在別處,而是大地上詩人們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3。事件的詩性敘述是一個于日常事物中體驗、發現和呈現的藝術,也是于堅“回歸事物本身”的主要手段,呈現了他獨特的詩學觀念。時間性在敘述詩學研究中占據著主導地位,但同時敘述研究中也存在一個空間維度,詩歌敘述中的時間性和空間性形態,共同形構了敘述詩學的時空思想和過程哲學。
此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詩歌敘述學的中國傳統、西方資源與當代詩歌寫作生態研究”的階段性成果(21YJA751021 )。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山東大學詩學高等研究中心
1 于堅、陶乃侃:《抱著一塊石頭沉到底》,《當代作家評論》,1999年第3期。
2 孫基林:《有關事件與事件的詩學:當代詩歌的一種面相與屬性》,《文藝評論》,2016年第6期。
1 于堅、陶乃侃:《抱著一塊石頭沉到底》,《當代作家評論》,1999年第3期。
2 [英]阿爾弗雷德·諾思·懷特海:《自然的概念》,張桂權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頁。
3 [荷]米克·巴爾:《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譚君強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頁。
4 [美]喬治·赫伯特·米德:《現在的哲學》,李猛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頁。
1 于堅:《于堅的詩》,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頁。
2 于堅:《我述說你所見:于堅集》,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頁。
3 陳仲義:《中國前言詩歌聚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頁。
1 鄭觀竹:《現代詩300首箋注》,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346頁。
2 于堅:《我述說你所見:于堅集》,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頁。
3 孫基林:《有關事件與事件的詩學:當代詩歌的一種面相與屬性》,《文藝評論》,2016年第6期
1 于堅:《拒絕隱喻:于堅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頁。
2 方英:《小說空間敘事論》,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20頁。
3 于堅:《我述說你所見:于堅集》,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頁。
4 于堅:《我述說你所見:于堅集》,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頁。
5 于堅:《于堅的詩》,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頁。
1 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頁。
2 于堅:《我述說你所見:于堅集》,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頁。
3 于堅:《于堅的詩》,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頁。
4 于堅:《我述說你所見:于堅集》,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頁。
5 于堅:《我述說你所見:于堅集》,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頁。
1 [英]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著,張桂權譯:《自然的概念》,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頁。
2 龍迪勇:《敘事學研究的空間轉向》,《江西社會科學》,2006年第10期。
3 于堅:《于堅詩學隨筆》,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44頁。
4 孫基林:《中國第三代詩歌后現代傾向的觀察》,《文史哲》,1994年第2期。
5 于堅:《為世界文身》,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頁。
1 臧棣:《騎手和豆漿:臧棣集1991-2014》,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頁。
2 [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258頁。
3 于堅:《拒絕隱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