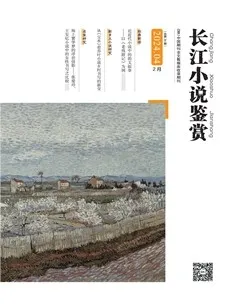春陽下的人性悲劇
黃歡
[摘? 要] 施蟄存的短篇小說《春陽》,描寫了一位鄉下中年寡婦嬋阿姨在大都市上海經歷的欲望萌生—膨脹幻想—沖動嘗試—重回封閉的一系列心理變化過程,暴露了其內在人格的各種矛盾,展現了施蟄存對女性生存處境、人性悲劇根源等問題的思考。嬋阿姨作為在現代文學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的女性代表,她的身上體現了兩種文明的碰撞與沖突,并以一系列內在矛盾展現出來:現代都市消費觀念與傳統封建倫理道德的矛盾、人性欲望追求與金錢主義持守的爭斗、都市空間與鄉鎮空間的對立、情感與道德的抵牾、幻想與現實的落差等。在各種矛盾中,面對種種枷鎖與教條,嬋阿姨也曾作出突破和抗爭,可她并沒有實現個人的解放,這更加彰顯與印證了她人生的悲劇性。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悲劇不是個例,而是當時時代洪流中的普遍產物。本文試圖對《春陽》進行文本細讀,探究施蟄存是如何呈現與揭示這一女性悲劇的。
[關鍵詞] 《春陽》? 施蟄存? 文本細讀
[中圖分類號] I207.4?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4-0011-05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思想的大解放與對現代主義思潮的重新接受和認識,施蟄存作品的文學價值被重新認識。施蟄存的文學創作集中活躍于20世紀20、30年代,其作品的一個主要特色就是對人物心理的分析,描寫人物意識的流動和心理情感的變化,深入刻畫人性。本文選取了施蟄存創作于1929年的一篇短篇小說《春陽》進行文本細讀。
《春陽》講述了一個被抹殺正常欲求的中年鄉下寡婦,在上海準備放縱欲望,但最終幻想在現實中破滅,灰溜溜地回到原來的狀態中的故事。小說細致呈現了主人公嬋阿姨的心理變化過程:封閉-欲望覺醒-膨脹幻想-沖動嘗試-失敗后重回封閉,在這一心理變化的過程中,通過具體細致的文本解讀,讀者可以更深刻地把握人物身上存在的多重矛盾性格,體會出作者通過嬋阿姨這一文學史上罕見的女性形象所傳達出的悲劇意識。
一、外來女性“都市漫游者”的欲望覺醒與種種不適
標題“春陽”顧名思義是春天的太陽,揭示了故事開展的環境特點,也隱喻著主人公的懷春心理。標題的色彩是明亮溫暖的,可是在這個標題之下講述的故事卻是一個關于女性欲望與存在的悲劇。故事的開篇是嬋阿姨鎖上保管箱,走出庫門,看見那個年輕的銀行工作人員正在對著她瞧,她心里一動。這“一動”是因為一個年輕男人正在對著自己瞧,但這觸動只一瞬間。對這觸動的反應是,她不由得回過頭看了一眼保管箱,接著往懷里一掏,剛才提出來的一百五十四元息金好好地在內衣袋里,于是她走出了上海銀行的大門。“好好地”“于是走出”等可看出此時她心里的一動已經得到安定。男性的注視激起了嬋阿姨心中的漣漪,而嬋阿姨緩解這一漣漪的方式卻是尋求金錢的安慰,愛欲與金錢在嬋阿姨的身上一開始就是交織在一起的。不容置疑的是,嬋阿姨緊閉的心門開始出現了松動的跡象。
“好天氣,太陽那么大。這是她今天第一次感覺到的。”[1]直接回應標題“春陽”的由來,“第一次”這個表述是值得注意的。嬋阿姨一早從昆山來上海,取完錢了,這時候才第一次注意到“春陽”的天氣。不是她之前沒注意,而是這好天氣就是她當前心情的反映。因為那位年輕的銀行工作人員的注視,從走出銀行大門開始她便開始了回味、享受,性幻想的苗頭在潛意識中已經冒出,但是她的意識并沒有覺知到,反而著重于對“春陽”天氣的強調。春陽的“陽”,也是“陰陽”的“陽”,象征著男性,對“春天”“暖和”天氣的強調,暗示著嬋阿姨對異性的渴望。此時,敘述者跳了出來,直接對讀者說:“這二月下旬的,好久不照到上海來的太陽,你別忽略了,倒真有一些魅力呢。”[1]這魅力正在于春陽改變了嬋阿姨固定的行程:從銀行出來后坐黃包車到火車站,回到昆山——穩定、一成不變的鄉鎮中年寡婦的生活中去。而今天卻“平空添出許多興致”“還好在馬路上走走呢”[1]。敘述者的現身雖然有些突兀,但直接提醒我們注意在春陽下嬋阿姨異于往日的心緒和行為。于是,嬋阿姨成為一位特殊的“都市漫游者”,在行走與觀看中,欲望不斷被喚醒和釋放。
一般的都市漫游者都是男性,而且是浪蕩子,是都市本地人,而嬋阿姨是一名女性,來自昆山一個傳統的鄉鎮,此時卻漫游在現代都市上海最繁華的路段南京路上。壓抑沉寂的小鄉鎮與活躍放縱的大都市兩種異質空間的錯位,在行走的嬋阿姨身上以各種不適感呈現出來。首先是著裝的差異。她看到的男男女女都“穿得那么輕”“那么樣美麗”“那么樣小玲玲的”,感覺到“自己的絨線圍巾和駝絨旗袍的累贅”,開始后悔沒預料到天氣太熱,不然“可就穿了那件雁翎縐襯絨旗袍了”[1]。這種累贅表面上看來是因為天氣熱,穿著臃腫顯老,實際上卻折射出傳統城鎮生活方式給人強加的各種束縛,尤其在一個抱牌位成親的寡婦身上有更多的道德規范和苛刻的自我克制,透露出濃重的封建道德色彩,所有這些在現代化新潮的都市環境中,就顯得極其格格不入。然而,嬋阿姨卻下意識地做出了把絨線圍巾除下來的舉動,或許可以將之理解為她已經在無意識中開始了對身體的解禁。身體的欲望與激情被喚醒,并開始膨脹,但是此時當事人并沒有意識到,因為此時她還在努力自制。雖然受到各式各樣商品的誘惑,內心卻在“堅守”著所謂的自制力:“沒有必需,她不會買什么東西。”[1]但是這自制力不久便開始捉襟見肘,她一路走,走得出汗了,這是正常的生理現象,同時也是身體欲望的一種象征(體液常常暗示欲望)。她卻沒摸出手帕來,此時,“她覺得有必需了”[1]。實際上,這算必需嗎?非得用手帕擦汗嗎?其實這也不算必需,但這卻給了她一個去消費的借口,因此,她去買了一塊手帕,消費的欲望得到了一定的滿足。
在購物后的休憩時,她又感受到了自己與其他都市男女在體力上的差別。“愈看人家矯健,愈感覺到自己的孱弱”[1],與之前著裝的差異所引發的不適感相同,其實質是兩種異質空間的對立。但在都市中行走得越久,都市空間對其熟悉鄉鎮空間的身體的介入程度就越深,兩種空間的矛盾對立在嬋阿姨身體上體現的不適感也就越強,使之“害怕走出門去,將怎樣擠進這些人的狂流中去呢?”[1]此時,嬋阿姨開始有意識地去覺察、思索這種不適感的來源,“在昆山的時候,天天上大街,可并不覺得累,一到上海,走不了一條馬路,立刻就像個老年人了。這是為什么呢?”[1]但她的思索也就停留在了這個疑問的層面上,而且立刻開始了逃避,“同時就埋怨自己,不應該高興逛馬路玩,那是毫無意思的”[1],她不可能認識到自己身上矛盾的根源。
二、欲望消費中的矛盾彰顯
“意料不到的卻是,當她往永安公司那邊走了幾步路,忽然讓她覺得身上又恢復了一種好像久已消失了的精力,讓她混合在許多呈著喜悅的容顏的年輕人的狂流中,一樣輕快地走……走。”[1]何以出門前還害怕擠進這些人的狂流中去,出門后就能在狂流中輕快地走呢?下一段敘述者做出了回答:“這春日的太陽光,無疑的。”[1]或許可以直接將之轉換為覺醒后不斷膨脹的欲望,那就不能忽視上一段出現的永安公司。是因為往永安公司那邊走了幾步路,忽然才生出的精力。永安公司有這么大的魔力?永安公司是當時四大百貨公司之一①,“對外地游客而言,在南京路的百貨公司里購買現代的奢華品是必要而令人神往的儀式”[1],因此,嬋阿姨的消費欲望不斷膨脹也在情理之中。另一個原因是其身體中兩種空間的沖突不斷磨合后,開始取得了一個平衡,都市的力量占據了上風,嬋阿姨心中對都市生活方式的渴望沖動不斷上浮,并且在群眾力量的裹挾中,她終于決定順流而下,準備在上海好好享受一下,畢竟天氣這樣好!城市的一個代名詞是“光電聲色”,在好天氣的照射下,城市“光”的特征不斷強化,“一切都呈現著明亮和活躍的氣象”,除了先施公司對面的點心店,“還呈現著一種抑郁的煙煤的顏色”[1],因為那是嬋阿姨回昆山必經的一個場所。在春陽之下,上海的都市魅力對嬋阿姨的吸引力得到空前加強,欲望被不斷膨脹并得到了嬋阿姨的感知和回應:她要在上海好好玩一玩,首先是要舒舒服服吃一頓飯,甚至考慮住一晚。但她一切欲望的源頭:對男人的渴望,還未被她有效覺知。
于是,嬋阿姨開始考慮在哪里去吃一頓舒服的飯了。雖然她是個富婆,內衣袋里還揣著一大筆錢,然而她還是有意考慮著節省,“不敢闖進任何一家沒有經驗過的餐館”[1]。最后終于決定去冠生園,“給自己斟酌了兩個菜,一共一塊錢”[1]。可以看出嬋阿姨就算是在放縱欲望的過程中,也始終不放松對金錢的把控。這樣的心理、行為似乎令人發笑,一個有錢人竟然連花錢都放不開手腳,這顯示了她身上的另一對矛盾:對欲望的追求與對金錢的把控,新舊兩個時代的弊病在她身上集中。她看到了鄰桌的丈夫、一個和自己年齡差不多大的妻子,還有一個孩子。她下意識地把自己置換到那個妻子的位置上,在觀看他人的同時,也觀照著自己,但她的身邊并沒有丈夫與孩子。她對家庭的欲望被牽引出來,這在根本上卻是對丈夫、對男人的渴望,而這一欲望卻是她從未被滿足過的。她本可以避免這一悲劇的發生,但因為“有著被人家所稱贊為卓見的美德”,和“大宗財產的合法繼承權”,她主動選擇了“犧牲”[1]。傳統封建倫理道德的束縛與物質主義的計算,甚至讓她以為自己的選擇是有勇氣的犧牲,實際上,她的選擇是一次交換,用愛欲換取了財富。但在這不可逆的交易之后,嬋阿姨陷入了悖論之中:財富是用被犧牲的幸福換來的,那就必須抓緊這些產業,但自己并沒有有血緣關系的繼承人,只是財產的暫時經管人而已,如果要享受,去追求欲望的滿足,那就必須花費自己犧牲幸福換來的財富,這樣又對不起自己的犧牲了。因而嬋阿姨始終保持吝嗇,陷于自我選擇的悖論中,并導致其矛盾的人格和各種矛盾的行為。隨著年歲的增長,容顏老去,對寡婦身份的適應,她換來的財富不僅成了一個包袱,也是內心尋求安穩的一個依靠。一開始藏在內衣袋里的一百五十四元六角的息金(這還只是利息,不是本金),使她在面對陌生的年輕男人曖昧眼光時感受到的震動得以緩解,并鼓勵自己去消費“現在,有的是錢,雖然還要做兩個月的家用,可是就使花完了,大不了再去提一百塊來。”[1]但在具體的消費行為中,節儉的心理始終占著主導,經濟上的節儉是其欲望自我抑制的外在表征,現代的消費享樂觀念與傳統的貞節道德的矛盾在嬋阿姨的身體內激蕩不息。
現在再回到嬋阿姨的飯桌上,畢竟她已經點好了菜,開始了自己的欲望“放縱”。在對鄰桌一家三口的觀看和轉換到他們的位置上對自己的觀看中,她“覺得難堪”“怕接觸那三雙眼睛”“害怕一個否決的回答”[1],在與幸福家庭的對照中,她感覺到自卑,對男人的欲望更加強烈,因而她開始了一場“性幻想”。她看見一個單身男人在尋找空座位,于是幻想他坐在自己對面,微笑、點頭、攀談。甚至就算他不坐下來,也是因為他是一個靦腆的人。嬋阿姨在幻想中越來越大膽,因為她能夠意識到自己是在上海,“在上海,這是普通的事。”[1]但在其潛意識中,始終有一個昆山的語境作為對照。嬋阿姨后悔自己沒有擦粉,強調自己忘記化妝的疏漏,刻意避免注意自己年老色衰的事實,在期待中,她對自己的稱呼是“小姐”而不是符合自己實際年齡身份的“太太”。于是,在幻想中,她是以“小姐”的稱呼被搭訕的,或者是主動去搭訕,“冥想一位新交的男朋友陪著在馬路上走,手挽著手”[1]。“在上海。這樣好的天氣。沒有遇到一個熟人”[1]的環境中,她得以進行一場年輕男女式的浪漫幻想,刻意想忘記昆山既定的生活方式,拒絕熟悉的人和事,努力將自己融入陌生的上海這個都市語境中,當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上海小姐,只是過著小姐先生們普通的交往生活。但實際上,昆山的陰影始終在她的潛意識中存在,在潛意識的影響下,嬋阿姨的幻想是一種放縱,也是一種出格的行為方式。嬋阿姨的思想斗爭無聲無息,卻進行得難解難分。
三、欲望斗爭的落敗與從城市的狼狽逃離
幻想結束于“鄙姓張,我是在上海銀行做事的”[1]。嬋阿姨的思緒又回到了故事開頭那個銀行男職員,“特別清晰地看見了他站在保管庫門邊凝看她的神情”[1]。之前那一瞧,帶給嬋阿姨的可不是“心里一動”那么簡單。在嬋阿姨的自我暗示和強化下,“一道好像要說出話來的眼光,一個躍躍欲動的嘴唇,一副充滿著熱情的臉”[1],普通的服務性禮儀被強加上了情欲信號的釋放,甚至他們幻想之間可能還存在著更加曖昧的肢體接觸,“他的下頜曾經碰著了她的頭發”“她還疑心她的肩膀也曾經碰著了她的頭發”[1]。此刻,嬋阿姨內心最深層的欲望一覽無余,她今天一切反常舉動的出發點都在這里,她壓抑十多年的性欲被這個年輕的男職員喚醒,并在商品景觀和消費行為的刺激下達到了頂點。因此,此時嬋阿姨在膨脹的欲望的鼓動下,做出了一個沖動的舉動——回去銀行再見那個年輕的男職員。她依然給自己找了一個托詞——有沒有把保管箱鎖上?必須回去看一眼!
回去銀行之后,如愿見到了那個年輕的男職員,職員臉上呈現出詫異的神氣,似乎有點不耐煩,但隨即就消失了,因為行長對職員的工作要求是要對主顧客氣,因而他立刻又變得殷勤起來。敘述者告訴我們職員對嬋阿姨的神情、表現都是出于工作服務的需要,只是被嬋阿姨誤解了,或者說是有意忽視了,此時嬋阿姨又處于欲望膨脹的沖動嘗試中,更不能覺察事實的真相,因而職員的一個微笑和注視,又使她陶醉于幻想中,并歡喜地期待職員按自己的幻想行事。然而,一句“太太”打破了她所有的幻想,她立馬從云端墜回了冷冰冰的現實中,被打回刻意忘記的鄉下中年寡婦身份中,而年輕職員對另一個女人更親切的“密斯”稱呼,更對照出自己的衰老落伍。由此,嬋阿姨意識到了自己浪漫幻想的可笑,興致從頂點一下降落到最低點,膨脹的欲望驟縮,重新回到封閉的狀態中。因而,春陽不見了。“一陣冷。眼前陰沉沉的,天色又變壞了。”[1]天氣實際上是嬋阿姨情感狀態的反映,她好不容易有所解禁的身體又被重新加上了束縛,“她遲疑了一下,終于披上了圍巾”[1]。嬋阿姨狼狽地直奔北站,去趕那趟以往固定路線的三點鐘的快車,回到熟悉又固定的昆山生活中去。也許此后嬋阿姨的“套子”再也不會有所松動了,這次失敗的嘗試耗盡了她所有的勇氣。
在小說的結尾,嬋阿姨在回昆山的車上從衣袋里帶出了在冠生園吃的那頓飯的發票。“她困難地,但是專心地核算著:菜,茶,白飯,堂彩,付兩塊錢,找出六角,還有幾個銅元呢?”[1]關于這頓飯賬目的計算,照理說應該在嬋阿姨離開冠生園的時候進行,可是卻被敘述者有意安排到了故事的結尾,可見敘事的安排是隨著嬋阿姨的情緒發展進行的。嬋阿姨離開冠生園的時候正是欲望高漲的時刻,她暫時放松了對金錢的掌控,而在心情跌落谷底,欲望收縮之后,她回歸了金錢意識,又開始對幾角、幾個銅元精打細算,側面反映出她欲望熱情的消弭。金錢與欲望之間的矛盾爭斗,以欲望的消失黯然退場。
四、結語
嬋阿姨的形象填補了現代小說女性人物譜系的空白,她不是都市中的尤物,也不是墮落的妖魔,而是以一個良家婦女的形象出現在現代都市的語境中,后來這篇小說也被施蟄存收入一部名為《善女人行品》的集子,嬋阿姨可以說是“善女人”的一個代表。此外,她也不像一般的女性人物成為被凝視的對象,反而成為觀看動作的發出者。然而,她擺脫不了的鄉下中年寡婦的身份注定了她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都市漫游者,她不能真正適應都市的生活方式,在都市的行走中,她內在的各種矛盾不斷暴露出來,遭遇了各種各樣的不適與尷尬。她的悲劇性更在于,被抹殺壓制十多年的欲望好不容易在春陽下得到覺醒,在商品景觀和消費機制的刺激下,做出的一次勇敢嘗試最終卻被證實為一場可笑又可悲的烏龍,摧毀了她此后踏出“禁地”的所有信心。表面看來,她的身份、年紀等客觀條件堵死了她追求幸福的道路,深層的原因卻在于她實際上是兩種文明沖突與雙重壓迫的一個犧牲品:現代都市消費觀念與傳統封建倫理道德的矛盾、人性欲望追求與金錢主義持守的爭斗、都市空間與鄉鎮空間的對立、情感與道德的抵牾、幻想與現實的落差等象征性地集中于嬋阿姨這一女性人物形象之上。況且,都市空間對女性更不寬容,嬋阿姨最終灰溜溜地逃離回昆山,何嘗不是都市對一個傳統舊式女子的拒絕。
值得深思的是,社會在不斷解放,人性得到了空前的強調,最現代最包容的都市對嬋阿姨出于人性解放的要求卻呈現出了一種拒絕的姿態,那么,如嬋阿姨這樣的女子該如何獲得自我的解放、人性的成長呢?嬋阿姨沒有名字,只是一個符號化的敘事設置,作者有意模糊處理主人公的個性特點,他想提醒我們的是,像嬋阿姨這樣的女性還有很多,嬋阿姨式的人性悲劇也是具有時代性的社會悲劇,可能她們一生都難以覺察到自我悲劇的根源,而社會也沒有提供足夠的條件讓她們尋找到正確的解決方式。通過嬋阿姨這一人物形象,我們可以對施蟄存的悲劇意識有所體會。通過對《春陽》進行文本細讀,也可以對其人物心理分析的創作特色有更多把握,盡管施蟄存以人物的心理變化和意識流動展開敘事,但筆觸刻畫深入、描寫面向廣泛、思考的問題獨到且深刻,遠超同時代的其他作家。
注釋
① 據李歐梵著《上海摩登 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 修訂版》第16頁的內容,在20世紀20、30年代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多層百貨大樓吸引了大量的中國人,尤其是“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
參考文獻
[1] 施蟄存.施蟄存全集 第1卷 十年創作集[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2] 李歐梵.上海摩登 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修訂版)[M].毛尖,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責任編輯:羅?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