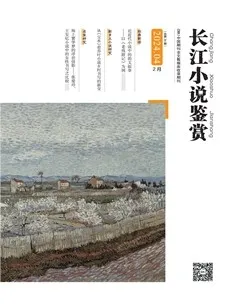愛倫·坡短篇小說中的幽靈侵擾
黃丹欽
[摘? 要] 美國短篇小說之父愛倫·坡創作的作品以恐怖和驚悚聞名,經常講述荒誕離奇的鬼怪故事。興起于20世紀80、90年代的幽靈批評為解讀愛倫·坡小說中的鬼魂提供了新的視角。本文在此理論基礎上聚焦愛倫·坡短篇小說中的死亡與復活,探究幽靈對19世紀美國個人、家庭和社會的侵擾現象,挖掘隱藏在幽靈背后的心理機制和文化歷史成因,揭示愛倫·坡思想的復雜性、深刻性和前瞻性。
[關鍵詞] 愛倫·坡? 短篇小說? 幽靈批評
[中圖分類號] I06?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4-0103-04
埃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年)是19世紀著名的美國詩人、小說家和文學評論家。愛倫·坡一生窮困潦倒、命運多舛、飽經滄桑。在美國浪漫主義盛行時期,他的作品以死亡、驚悚和恐怖聞名,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因此外界評價褒貶不一。但在歐美現代主義浪潮席卷而來時,坡以不可阻遏之勢幾乎成為現代主義各個流派的高祖[1],他使短篇小說達到了可以作為獨立文體存在的水平,并且擺脫了歐洲長篇小說的束縛,在美國創立了健全的短篇小說傳統。2006年,復旦大學的張瓊提出從幽靈批評的視角重讀愛倫·坡[2],為研究愛倫·坡的小說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簡而言之,幽靈批評旨在和死者進行一種令人恐怖而又渴望的交流[3],通過揭示文本中隱藏的社會和歷史痕跡,結合作者的個人經歷,來更全面地理解文學作品。本文在此基礎上,試圖與愛倫·坡短篇小說中的死者“對話”,解讀侵擾人物內心的幻象,傾聽來自19世紀美國社會的幽靈之聲。
一、本我的幽靈:個人精神危機
愛倫·坡的短篇小說常用第一人稱內心獨白的敘事方式,講述荒誕離奇的死亡故事。在《泄密的心》(1833年)中,敘述者的聽力異常敏感,甚至可以聽到來自天堂和地獄的聲音。敘述者的不可靠敘述讓我們不禁懷疑他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他的殺人動機僅僅是因為老人長了一雙禿鷲式的眼睛,在英語中,眼睛(eye)的讀音和我(I)同音,因此有學者認為從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小說中的老人是“另一個自我”,“我”殺死老人是因為死亡恐懼,想通過毀滅自己的身體來躲避死亡[4]。從精神分析的視角分析較符合敘述者的心理,老人是超我的象征,本我的快樂原則和超我的道德原則難以協調,導致“我”人格分裂,飽受死亡幽靈侵擾之苦。在《提前埋葬》(1844年)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坡筆下精神病患者對死亡的恐懼與擔憂。“我”不再歇斯底里地辯解,而是以一種心平氣和的語氣講述患病時的腦海幻象。在“我”看來,被活埋是人類有史以來遭受的最極端、最可怕的命運之一。但這種聽起來匪夷所思的事情竟然頻頻發生、屢屢出現,有必要的話可以馬上列舉出上百個證據確鑿的例子[5]。這看似有悖常理的念頭在患有強直性昏厥的病人身上似乎真的有可能發生。這種怪病會讓患者僅在一天或更短的時間內陷入一種反常的嗜睡狀態,持續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只有依靠朋友們的經驗和肉身毫無腐爛跡象的事實才能免遭被提前埋葬的厄運[5]。這種狀態常人難以想象,因為“我”時時刻刻提心吊膽,生怕遭到朋友的厭棄和陌生人的誤解,在墳墓里無助地醒來,在無邊的黑暗中苦苦掙扎。“我”的想象力已經變成停放尸骨的場所,熱衷于談論蟲豸、墳墓和墓志銘,終日沉湎于對死亡的幻象。在小說最后,“我”也意識到恐懼也許是發病的原因,不讀鬼怪故事,活在現實世界里,努力讓靈魂獲得安寧[5]。除了恐懼的幽靈,復仇的幽靈也經常在坡的世界里出沒。《泄密的心》中的謀殺沒有正當的動機,而在《一桶白葡萄酒》(1846年)和《跳蛙》(1849年)中,主人公則有著明確而強烈的復仇執念。《一桶白葡萄酒》中,“我”因為福吐納托一再的羞辱而發誓要報仇,在復仇的過程中雖有過恐懼和猶豫,完成計劃后也會從生理上覺得“惡心”,但是家族格言的警訓“凡傷我者,必遭懲罰”就像幽靈一樣,推著“我”一步一步泯滅良知,犯下殺人的罪行。“我”沒有接受法律的懲罰,但也在50年后懺悔,希望逝者安息。而《跳蛙》中的復仇則是弱者對暴君的反抗,盡管復仇的手段很殘忍,但是復仇者脫離苦海卻大快人心。從《泄密的心》到《一桶白色葡萄酒》再到《跳蛙》,復仇的動機似乎越來越正當,復仇者也逐漸逃脫法律和良知的雙重懲罰。有學者考證,坡是在作品中發泄對生活中仇敵的痛恨。1846年,坡與昔日朋友英格利希反目成仇展開筆戰,向法庭控告其誹謗罪卻慘遭敗訴。坡因此產生復仇之心,甚至動員朋友幫他反擊。1849年,坡對英格利希的報復心有增無減,從他給朋友的求助信中可以看到,他因患病等原因認為自己完全無法捍衛自己。小說也許是愛倫·坡真實狀態的寫照,他反復遭受親人離世的打擊,生活中多有不如意,文學之路也并非坦途,加上酗酒和染上鴉片,深受各種幽靈幻象侵擾,精神狀態不堪重負,因此在生命的盡頭,坡連續幾天處于譫妄的狀態,大呼“上帝保佑我”,就此含恨而終[5]。
二、女神的幽靈:家庭天使幻滅
坡在《創作哲學》中斷言從悼念亡者的戀人口中表達美麗女性的死亡無疑是最具詩意的主題[6]。陳良廷在《愛倫·坡短篇小說集》的前言中寫到,坡本人和注定要死或已經亡故的母親或妻子是坡大部分作品的中心人物[5]。盡管這種論斷可能有失偏頗,但毋庸置疑的是,美麗女性之死是坡創作的重要主題,這與他的生平經歷有很大關系。坡的生母和妻子均在24歲時患肺結核而香消玉殞,疼愛他的養母也體弱多病,年紀輕輕就撒手人寰。生命中摯愛女性因病早逝使得愛倫·坡對于美麗女性的死亡有了一種近乎偏執的熱愛,他不相信死亡是人生的終點,認為死去的親人在冥冥之際可以和活著的人進行交流,因此她們常常幻化成女神般的幽靈出沒在坡的小說中。《麗姬婭》(1838年)講述的是“我”的愛妻麗姬婭借尸還魂的奇異故事。麗姬婭可與土耳其神話中的火麗仙女相媲美,她有著“純白象牙相仿的皮膚、寬闊而飽滿的天庭,熠亮、濃密的蓬松烏絲”。然而,她“來去無蹤,像幽靈”[5],“我”無法記住與她相識的時間和確切地點, 甚至不知曉她的姓氏。由此可見,麗姬婭是坡幻想中理想的女神形象,有著具體的樣貌。而《艾蕾奧瑙拉》中,艾蕾奧瑙拉則化身為自然萬物,無處不在、純潔無瑕,美得像六翼天使撒拉弗,清澈的河水不如她的眼睛,潺潺的流水不及她的嗓音,光滑的光斑不及她的臉蛋。即使她離世后,靈魂也要來照顧“我”,也要在“我”呼吸的空氣中灑滿仙鼎散發的香氣[5]。從有形到無形,坡對女神的想念與日俱增,伴隨著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坡對女性的崇拜可能受到19世紀30、40年代美國普遍流行的“家庭崇拜”意識形態的影響。這種思想最初起源于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共和母權思想,強調母親向兒子傳遞的各種價值觀至關重要。女性被社會貼上了“虔誠、純潔、順從、愛家”的標簽[7],以道德榜樣的名義桎梏在小小的家庭中。然而,這樣的價值觀受到歐洲政治革命和工業革命的沖擊。隨著女性解放運動蓬勃發展,女性終于有機會沖破枷鎖,走下神壇。也許由于坡自身家庭中女性的缺位,天使幻象本就虛無縹緲,坡反而可以更清醒地旁觀這一現象,因此在小說中揭露了傳統女性所受的壓迫,預言了舊式家庭模式的崩潰。《麗姬婭》中的替身新娘羅維娜是形式婚姻的犧牲品。與麗姬婭的雍容華貴相比,羅維娜只是有碧發秀眼[5],這反而說明她是現實中普通女子的寫照。羅維娜的娘家因貪圖錢財而枉顧她的終身幸福,讓她住進五個角上都豎著一口巨大的黑花崗巖石棺的鬼屋,這暗示傳統的婚姻是禁錮女性的墳墓,羅維娜的郁結而亡是她必然的結局。《鄂謝府崩潰記》(1839年)中,妹妹常年在陰森黑暗的古屋內閉門不出,忍受著家族遺傳病的折磨,身子一分一分地消瘦,時不時要發一陣的身體局部僵硬癥[5]。她從未說過一句話,就像一具僅剩下軀殼的游魂,哥哥則陷入異樣的恐懼中惶惶不可終日。妹妹在“我” 抵達當日的傍晚突然去世,被停放在主樓的一間地窖中,但在一個狂風大作的夜晚,卻掙扎著破棺而出, 穿著血跡斑斑的白衾,拉著孿生哥哥一同倒地而死,鄂謝府也隨之崩塌。就像傳統封閉的家庭模式必然衰敗,這座表面安然無損而實際脆弱不堪的古宅注定要走向滅亡。
三、歷史的幽靈:社會現代反思
坡所處的時代,美國正經歷第一次工業革命,經濟迅猛發展、科技日新月異。1820年,退伍軍人西姆斯提出“地球中空說”,勾起人們對海洋和南極探險的無限向往,民間有人自發組建探險隊想一探究竟。1823 年,美國改變建國初期的孤立政策,轉而走向對外擴張的殖民之路[8]。正是在這樣的創作背景下,《瓶中手稿》(1833年)講述了一個靈異的航海故事,廣受讀者好評,也讓坡一夜成名。坡將小說主人公設定為一個滿腹經綸的美國探險者,與英國船長的冥頑不靈形成鮮明對比,借此暗示了美國人有別于英國人的責任與擔當。但是坡也在諸多細節中表達了自己內心深處的憂慮。主人公登船的地點巴達維亞是幽靈聚集之地,無論是歷史上在“巴達維亞號”輪船失事的亡魂,還是在巴達維亞城因洪水和地震喪生的怨靈,似乎都化作了航行途中的巨浪、風暴和漩渦,向野心勃勃的探險者頻頻發出死亡預警。由于當時美國有意染指南太平洋地區,而小說中的英國商船正好是在南太平洋海域失事,坡實際上是希望通過這一情節提醒美國政府不要重蹈英國的覆轍。“我”在英國商船覆滅時僥幸逃脫,被卷到一艘神秘莫測的幽靈船上,飛速地向南極方向駛去。小說中的荷蘭幽靈船來源于東印度公司中“飛翔的荷蘭人”的傳說,因受到詛咒永遠只能在海上漂泊。這艘船及船上所有元素都散發出古老的氣息。船上蒼老的船員是早期殖民者的幽靈,他們沉迷于研究探索海洋的古老儀器,急迫不安的眼神寫滿征服領土、掠奪資源的野心。船上的幽靈預示毀滅是探險和殖民最后的歸宿。坡在審視美國對外擴張政策的同時,也在反思美國對待本土印第安人的殘酷態度。1829年,以征伐印第安人起家的將軍安德魯·杰克遜入主白宮,對印第安人的迫害愈演愈烈,強制東部印第安人遷至西部荒涼的保留地,鑄就了美國歷史上殘酷無情的“血淚之路”。《凹凸山的故事》(1844年)是一則時空穿越的故事,借18世紀印度人民的幽靈向19世紀美國人貝德羅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警告。小說中,貝德羅穿越到1780年,親身經歷切特·辛帶領印度人民揭竿而起,英勇反抗英國殖民者的歷史事件。貝德羅深受精神困擾,離開瑪咖便不能生存,最終也和當年的英國軍官那樣死于非命。坡以此暗示印第安人終將奮起反抗,而美國政府終會自食惡果。在原始資本的積累下,美國社會蒸蒸日上,但是坡看到了隱藏在浮華表面下的社會問題。《同木乃伊的談話》(1844年)中,沉睡了5000年的木乃伊被美國科學家用電流治療法強行復活,兩者神奇地共處一室,進行了一番唇槍舌劍。“我”旁聽后發現19世紀美國人因科學的迅猛發展而一葉障目,自詡創造了前無古人的輝煌成就,而事實上歷史并非總是線性前進的,科學的進步在給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災難。比如所謂的顱相學和進化論以科學之名成為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幫兇。木乃伊聽完美國人夸夸其談后,說當時埃及的十三個省與其他十五或二十個省合而為一,成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令人厭憎和無法忍受的專制制度。而這一專制制度的暴君便是“烏合之眾”[5]。古埃及作為一個奴隸制國家,一直奉行君主專制政體,根本不存在這樣的民主。木乃伊提到的“十三個省”實際上指的是美國建國初期的十三個殖民地,而“合并”則指的是在安德魯·杰克遜執政期間,隨著美國的西進運動,新的州被設立并加入美國聯邦。在這個大背景下,為了贏得民心,杰克遜實施了民主制度改革,將政治利益以“分贓”的方式分配給對他忠心耿耿的部下,引發了許多不滿[8]。難怪“我從心底厭棄了19世紀美國的生活,希望被制成木乃伊,就此沉睡兩三百年”[5]。坡借古埃及文明的幽靈反觀19世紀美國的現代文明,對當時的科技發展和政治改革進行了無情鞭撻。
四、結語
愛倫·坡的短篇小說聚焦死亡,常有幽靈出沒,造成恐怖的效果。結合坡的個人生平和時代背景,我們發現幽靈其實是來自個人、家庭和社會方方面面的幻象總和。坡借助幽靈訴說自己遭受的精神危機之苦,寄托對母親和妻子女神般的愛慕,預判傳統家庭模式的衰敗,同時為美國19世紀現代社會鳴鐘示警。坡的黑暗浪漫主義思想曾為時代所不解,但其對社會的批判是深刻的、犀利的、富有前瞻性的,時至今日依然在歷史的長河中熠熠閃光。正如保羅·瓊斯所說,坡并非漠不關心政治的浪漫主義者,而是一個深切關注時代重大問題的作家。同樣,貝特西·厄基拉認為,坡的美學作品是歷史的產物,而非獨立于歷史之外[10]。在筆者看來,坡生動地踐行了詩歌求美,而小說求真的創作理念。他的偉大和影響力不僅僅屬于19世紀的美國,也屬于全世界的所有人。在當今社會,民主與霸權、科學與自然、孤獨與異化等諸多議題依然存在,深入研究坡作品中潛伏的幽靈,也許能從中找到應對現代人困境的靈感。
參考文獻
[1] 王齊建.試論愛倫·坡[M]//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集刊(第六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2] 張瓊.幽靈批評之洞察:重讀愛倫·坡[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6(6).
[3] 沃爾弗雷斯.21世紀批評述介[M].張瓊,張沖,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4] Canario J W.The Dream in “Tell-Tale Heart”[J].English Language Notes,1970(7).
[5] 坡.愛倫·坡短篇小說集[M].陳良廷,徐汝椿,馬愛農,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6] 張丹丹,劉立輝.矛盾的女性觀:愛倫·坡短篇小說中的女性身體敘事研究[J].文學界(理論版),2011(3).
[7] 盧敏.19世紀美國家庭小說與現代社會價值建構[J].外國文學評論,2009(2).
[8] 張運愷.用異域想象反思十九世紀的美國[D].鄭州:戰略支援部隊信息工程大學,2020.
[9] CHRISTIAN J P.The Danger of Sympathy:Edgar Allan Poes“Hop-Frog”and the Abolitionist Rhetoric of Pathos[J].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2001(2).
[10] Erkkila B.The Poetics of Whiteness:Poe and the Racial Imaginary[M]//Kennedy G J,Weissberg L.Romancing the Shadow:Poe and Race.Oxford:Oxford UP,2001.
(特約編輯 張?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