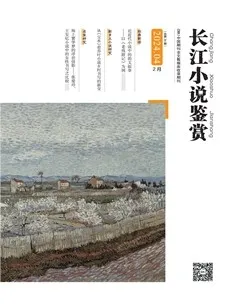石舒清小說的內傾化書寫研究
李春雨
[摘? 要] 寧夏回族作家石舒清以故鄉西海固為背景,書寫著這片土地上人們的生活狀態和心理感受,其小說在情節上也注重生活流和意識流的描寫,表現出鮮明的內傾特征,展現出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向內轉”趨勢一致的流向性。石舒清的內傾型現實主義小說寫作開辟了一個嶄新的寫作路徑,他以深度的內心體驗和抒情性的寫作,為西部文學和中國當代鄉土小說創作提供了新的書寫經驗。
[關鍵詞] 石舒清? 內傾書寫? 心理小說
[中圖分類號] I207.4?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4-0041-04
21世紀以來,一批西部作家始終筆耕不輟,創作出一批又一批優秀的文學作品,他們以自己獨特的文學書寫表達著對故鄉的熱愛,獲得了學界的關注與認可,寧夏回族作家石舒清是其中一位,他的風格沉靜、內斂,注重人內心感受。石舒清自1987年公開發表文學作品至今,已出版中短篇小說集10部、長篇小說2部,多篇小說獲全國性大獎。石舒清扎根于寧夏西海固這片土地上,執著地描寫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的生活狀態和心理感受,向讀者展示了當地人豐富細膩的精神世界。同時,他的小說選取不易察覺的細節為切入口,向深處挖掘人們內心的細微感受與變化,呈現出強烈的內傾化特征。
一、“內傾”概念與內傾書寫
“內傾”原是一個心理學概念,最早由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提出。榮格根據人的心理活動傾向,把人的性格分為內傾型和外傾型兩類。內傾型性格的人喜靜不喜鬧、好沉思,注意力的方向和活動的興趣點總是朝著自己的內部世界,擅長對內在精神世界的細膩感悟。隨著文藝心理學的深入發展,文學和心理學的界限日益被淡化,“內傾”概念逐漸被借用到文學上來,榮格在《論分析心理學與詩歌的關系》一文中用“內傾的”和“外傾的”來區分作家或藝術家的創作方式,指出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創作方式。
19世紀以來,伴隨著西方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巨大變化,現代主義文學迅速崛起,此時期的小說創作,展現出探索與表現人的主觀世界和深層心理的轉向,也就是內傾化的書寫轉向。亨利·詹姆斯最早從內部敘事進行嘗試,試圖在小說中展現內心深處的、類似于潛意識的思想,并指出越成功的小說越應該呈現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特的心靈。羅伯特·漢弗萊把所有意識流作家的目標總結為要揭示人物的心理存在,把表現的重點從客觀物理世界轉向主觀心理世界。在《尤利西斯》《喧嘩與騷動》等典型的內傾書寫作品中,心理、意識、精神是小說表現的中心,作家的寫作意圖在于將意識進行多維度的呈現。
中國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經有作家出現了內傾化書寫的傾向。魯迅自述在創作《不周山》時,就“取了茀羅特說”[1]。作為五四新文學重要形態之一的自剖文學,最顯著的標志就是內傾化,關注個人的內心世界,注重心理分析,敢于自我暴露,以主人公的心理告白來張揚作家自我的主觀情感與價值判斷。郁達夫常以自我殉身的手法在小說中宣泄靈肉分裂的苦痛。此后,施蟄存、穆時英、張愛玲和徐訏等作家同樣注重在小說文本中關注人的心靈世界與情感世界。20世紀80年代,展現內宇宙的小說再次活躍在大眾視野中,許多學者也開始持續關注并將內傾化書寫納入自己的研究視野中,最早對此進行系統論述的是魯樞元。魯樞元指出,“新時期文學與心理學的融會貫通,造成了新時期文學‘向內轉的必然趨勢”,并進一步預判,“這一趨勢將使我們的文學走出多年的積弊,走進一片嶄新的天地”[2]。魯樞元提出的中國文學向內轉趨勢,也就是文學創作內傾化的特征。
事實證明,自20世紀80年代起,隨著經濟發展和物質生活的富足,人的心理構成和精神困境越來越復雜,文學“向內轉”的現象逐漸發展為一種自發自生的趨勢,整個文學界都在尋求最能表現人的內心感受和獨特體驗的寫作,內傾化書寫特征越來越明顯。放眼西部文壇,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許多取材于西部的小說和西部作家的創作都致力在茫茫曠野中尋找理想人格,書寫和展現主體的內心世界與精神世界。張承志書寫的徐華北們的精神世界嘩變,展現了一代人的精神悲劇,在文壇上引起了強烈的精神震動。這一批西部文學創作者,較少有純粹講述故事者,多以抒情為主,給予小說高度的寓言性,借助內傾化書寫來展現西部人民的內心世界,傳達自身的生命體驗。石舒清作為寧夏文壇的杰出代表,自然沿襲了西部文學重抒情、輕情節的書寫傳統,并在作品中表現出新的藝術風格和寫作傾向。石舒清在最初的小說創作中就將視野和興趣投射到了人物的內心世界,對日常生活進行詩意化書寫,并將自己的感受貫注在小說之中。秉持著這一種創作理念,他孜孜不倦地向著心理世界、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深入,并在小說中將自己對于生活的認識、對生命的思考及自身對外在世界的心靈化感受進行充分展現,就像他自己曾說的那樣:“我希望成為一個把我對我那個村子的豐富感受充分寫出來的作家。”[3]
二、展現西海固人的精神世界
石舒清的小說多以鄉村生活為背景,展現故鄉人敏感多情的內心世界,以內在的心理流動和主觀情思來建構本文世界的客觀真實,淡化外部事件構成的情節,以內在的心靈、感覺、思維為主體。不論是書寫日常生活還是宗教生活,小說的主題總是側重于展現西海固人豐富、多情的內心世界和高潔、虔誠的精神世界。
小說《農事詩》展現了西海固農民在日常勞作中的意識流動和內心體驗。他們在日頭里忙碌著,重復著簡單機械的勞動,思維狀態是麻木、呆滯的,“站遠了望去,說不清日頭和人群哪個更孤單些”。休息的時候,放松下來的人們仿佛進入夢境,“在愜意的恍惚中感到一些醉意”[4]。再次進入勞動時,人們仿佛游戲一樣,感到輕快與愉悅。小說《果院》展現了耶爾古拜的女人在自家院子里勞動時的思緒變化與情感滌蕩。園藝站修剪果樹的年輕人作為“誘餌”,勾起了耶爾古拜媳婦的欲望與無限的遐想。她想到了自己與耶爾古拜和諧體面的婚姻,想到了先前那個性格古怪的園藝師,想到了自己與這個小伙子相處時的心猿意馬。小說最后,她猜測、揣度著接下來會是一個怎樣的師傅來剪果樹,“這一份不知道,使她覺得新鮮,隱隱有一絲期待”[4]。小說《浮世》中,哈賽媳婦在得知丈夫出事后,內心被驚慌、擔心、顧慮等種種情緒填滿,石舒清通過細膩的女性心理描寫,表現出了鄉村女性的堅韌與敏感。在得知獲得巨額補償金后,哈賽兩口子感到十分欣喜與滿足,金錢的誘惑使其忘卻了身體與精神的痛苦,最終心靈被扭曲與異化。小說《列車上》以“我”在火車上的所見所聞引起的所思所想為線索,記敘了“我”由車票、同車廂的旅鄰人引起的思緒與思考。
除觀照日常生活中人們的內心世界與情感體驗外,石舒清還將目光投射到精神世界中。小說《紅花綠葉》展現了回族送葬過程中各種人的內心活動。在回族人民的信仰中,今世的“亡”乃是后世的“生”,是精神上的“皈依”與“歸真”,因此他們并不懼怕死亡,也不表現出過度悲傷,而是表現得平靜、安然。小說《旱年》展現了回族村婦與乞丐的內心交流,這種交流是無聲的,是心與心、靈魂與靈魂的交流,薩利哈姨婆也在這一交流即“散乜貼”的過程中獲得了巨大滿足與神圣感。“乜貼”是阿拉伯語的音譯,指有益于他人的意愿,“散乜貼”是一種自愿的、誠心的奉獻行為。石舒清筆下的穆斯林們過著節制清貧的生活,虔誠地進行各種“清潔”儀式,懷著堅定的信念構筑高潔的“內瓤瓤子”。小說《小青驢》中年逾古稀的姑太太充分享受生活的清貧,作者著重寫了姑太太心靈的滿足——人要善于苦中作樂,知足才能長樂。
三、以感性表達理性的敘事策略
石舒清的小說多以思緒和情感作為敘事線索,情節由跳躍的片段構成,敘述中充滿擬想性的情境。許多小說展示了人物內心意識的流動,但這種流動并不是意識流小說的那種“作者退出小說”,而是作者主動化的展現自己思索的過程。小說《果院》以女人的思緒和心理活動為線索行文,耶爾古拜女人在果院里勞動時的思緒是串聯起全文的線索。小說《涼咖啡》以男主人公的內心波動為線索,展現了城市人壓抑的內心世界。小說《暗處的力量》以“我”的膽怯、懷疑、恐懼、不安等情緒推動故事情節發展,“我”在內心經歷的自我搏斗中揭示了人性中丑陋的一面。
在視角設定方面,石舒清選擇將全知視角與限知視角靈活交替運用,且鐘情于內聚焦敘事。全知全能的全知視角能夠幫助敘述者隨時進入與抽離人物心理,對人物內心活動進行自由透視與觀察,通過人物的想法傳達自身的生活態度和悲憫情懷。小說《趕山》中,敘述者自由進出9個人物內心,敘事者眼光與人物眼光來回切換,穿插運用。敘事者時而跳出的聲音和對人物的評價,都在加深讀者對文本中涉及的婚姻、生命等問題的思考。小說《恩典》開頭便寫道“馬八斤越想越覺得自己活得窩囊”[4]。這一“想”和“覺”,既是主人公馬八斤的心理感受,也是敘述者的價值判斷,全知敘述者直接進入人物心理,帶我們走進了馬八斤的內心世界,同時也傳達了作者對于自尊的態度。人物有限視角敘述則能夠更準確、更強烈地表達人物的主觀意識。石舒清的小說創作一直致力于人物有限視角的嘗試與創新,特別是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視角,長篇小說《底片》和短篇小說集《三岔河》是熟練運用這一視角的典范,以“我”的有限視角回顧,講述發生在故鄉西海固的過往人事。《風過林》一類的“內聚焦”作品,更是完全沉浸在自我的思緒與幻覺中,以“我”的聲音敘述“我”看到的世界在“我”內心引起的反應與體驗,專注于對恐懼、迷茫等主觀感受的強烈表達。
內傾型的小說視角聚焦于主體的內心世界,由此建構起獨特的心理意義上的時間。石舒清的大部分內傾作品中都存在著時間的倒錯,即故事時間或心理時間和故事時間或現實時間是錯亂的,而小說則隨著人物的感受、心情、幻想和夢境進行故事,如短篇小說《節日》《歇牛》《空宅》等,故事的時間可以隨意翻轉,而文本的時間藝術也因此變得豐富多彩。小說《娘家》中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真實時間與心理時間交疊纏繞,女主人公微妙復雜的心理變化推動著故事時序的變換,今昔對比之間產生強烈的懸念與張力。小說《農事詩》中夢境與現實交替出現,當“站遠了望”時,就好像進入夢境;“站近了看”就又回到當下現實中。夢給枯燥的生活賦予了別樣的意義,日復一日地繁雜勞作并沒有使人豐富的情感消磨殆盡,貧困的環境也并不能困住人們幽遠縹緲的思緒。石舒清很少順著故事的開展時間敘述故事,他喜歡經時間過濾后,重新審視記憶中的事件,采取回顧性敘述,尤其鐘愛倒敘,《殘片童年》《羊的故事》《小學教師》《奇怪的午后》等記人記事的小說都是以童年記憶來行文的,帶有敘述者自身深刻的情感體驗。大部分倒敘的作品也存在現在時的故事,起到襯托、對比或評價過去事件的作用。小說《二爺》以“我”的二爺被打成右派為線索,追憶了二爺的一生。開篇第二段,敘述者就按耐不住進行了評價,講述二爺在生產隊參加勞動時,敘述者多次插敘當下的議論與感慨。小說詳細追憶了二爺被打成右派后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對于他平反后、現在的生活狀態則一筆帶過,這就使得這篇短篇小說在有限的篇幅內,截取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生活片段,并加以延伸形成了生命的厚度。
石舒清的小說多是短篇,作品篇幅短小,語言節制,卻能精細地傳達出人物心境與敘述者的情感。小說《花開時節》在對話中表現人物心理,少女宰乃拜與養蜂人一來一回的對話充分展現了二人的心理變化。穿插在對話中的心理分析與人物心理狀態并置,使人物的心理活動呈現出更具有戲劇化的緊張感與情感張力。小說《眼歡喜》借人物獨白、自述來表現人物深層的心理活動。阿旦女人看到老人喝湯時的那段獨白,是以向另一個人講述的口吻呈現的,設問的句子層層深入,不僅展現了阿旦女人的心酸與心憐,更凸顯了老人的凄苦處境。美文式的敘述語言與其情節上的生活流和意識流交相輝映。對意境的有意營造使他的小說在不自覺中形成了詩化、散文化的文風,幾乎看不到刻畫情節的痕跡,“讓人看到一部分,但還有很重要的一部分讓讀者能感知卻不能清晰地看見與說出”[5]。小說《一個女人的斷記》中的主人公郝麗身患殘疾,不幸的婚姻只給她留下了一個有智力障礙的兒子。她的兒子來“我”家果園搗亂后,作者寫到“院子里給人一種塌陷感,陽光散發出一種經久不息的虛無的聲音”[6],寫出了“我”與母親的復雜心境。
四、結語
石舒清小說創作中的內傾特征肯定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表現人的內心感受與體驗的創作傾向,他將自己對于生活的認識、對生命的思考、對外在世界的心靈化感受在小說中進行充分展現,并對筆下人物的內心世界深入發掘。“內傾”并不意味著與“外部”的完全脫離,更不是對“客觀”的全然忽視,相反,石舒清小說的現實主義色彩是十分鮮明的。正是作家的心靈與他筆下西海固廣大民眾的心靈相同,在創作中關注社會問題引發的精神問題,并主動尋求超越與療救的方式,才能以洞悉的姿態,在作品中呈現對社會、對人生的深邃看法與獨到思考。
石舒清專注挖掘內心,以素樸和詩性的語言進行內傾化書寫,是在全球化背景和現代化進程中對民族文化與地域文化的價值堅守,在喚起人們對現代文明的反思、重構當代文學精神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石舒清忠誠地書寫著西海固大地上人們的凡常生活和人世冷暖。寫他們在農事勞作、飲食起居、宗教儀式中的內心百態與情感體驗,寫他們在生存與道義面前的掙扎與困惑。石舒清將自身對外在世界的心靈化感受充分展現在作品中,其內傾化書寫為當代文壇提供了一種新的敘事方式和書寫范式。
參考文獻
[1] 魯迅.魯迅全集 2[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2] 梁光弟,等.中外文藝理論概覽[M]//魯樞元.新時期文學與心理學.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6.
[3] 石舒清,舒晉瑜.留心日常生活里的漩渦和浪花[J].上海文學,2023(5).
[4] 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
[5] 石舒清.隨筆兩則(代創作談)[J].朔方,1997(4).
[6] 石舒清.伏天[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
(特約編輯 劉夢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