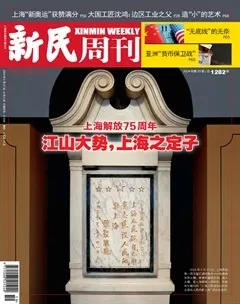傳統(tǒng)水墨與“實驗水墨”
喻軍

姚逸之作品《無題》。
傳統(tǒng)水墨與“實驗水墨”其實構(gòu)不成什么學(xué)術(shù)邊界,后者甚至還算不上一個成熟的概念。
傳統(tǒng)水墨當(dāng)然是指根植于中國本土文化、歷經(jīng)數(shù)千年演化而生成的藝術(shù)形態(tài)。20世紀(jì)以來,它經(jīng)歷了三次沖擊:一是世紀(jì)之初,西風(fēng)東漸所帶來的觀念、風(fēng)格裂變,形成所謂中西融合或中西對峙;二是建國后以適應(yīng)“新形勢”為任務(wù)的、對于所謂“舊國畫”的改造;三是“八五思潮”所帶來的水墨觀念的轉(zhuǎn)型,試圖擯棄條條框框,建立水墨的當(dāng)代話語。且隨自身的運作,不斷衍生新的概念、新的形態(tài)和新的訴求。
比如“觀念水墨”:上世紀(jì)90年代出現(xiàn)的一種提法,或說是建立在超越地域和學(xué)院建制以上的一種文化審視形態(tài)。把中國畫視為動態(tài)的審美系統(tǒng)而非固化的模式,有別于80年代極具叛逆性的思維方式。既尋求“文化身份”的認(rèn)同,又把水墨置于全球化語境下加以重構(gòu)。“觀念水墨”正是“觀念藝術(shù)”的延伸,試圖挖掘傳統(tǒng)水墨中隱藏的現(xiàn)代因子,通過觀照現(xiàn)代西方人文哲學(xué)、藝術(shù)觀念實現(xiàn)對當(dāng)下處境的關(guān)切。20世紀(jì)80年代,當(dāng)觀念藝術(shù)通過裝置和行為藝術(shù)進入中國時,實際上已經(jīng)成為繪畫、雕塑之外的新的媒介,更注重思想觀念的植入,而非繪畫的形式語言。可問題是,傳統(tǒng)水墨即便吸收了西方現(xiàn)代元素,自身的“根性”依然牢固,既不可能移栽,也不可能重塑。觀念藝術(shù)或者當(dāng)代藝術(shù)的出現(xiàn),對于傳統(tǒng)水墨只是提供了一種“可能”,并不具有“改造中國畫”的顛覆性作用。
“實驗水墨”差不多出現(xiàn)在八九十年代,有人認(rèn)為它就是抽象水墨,屬于表現(xiàn)型的水墨形態(tài)。其實西方繪畫在19世紀(jì)也曾出現(xiàn)與自身傳統(tǒng)背離的現(xiàn)象,凡高、馬蒂斯繪畫中那種強烈的東方印記和大量抽象性繪畫的出現(xiàn),對于古典寫實傳統(tǒng)也構(gòu)成觀念的沖擊。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名目繁多的“概念”對畫家的創(chuàng)作并無多大的指導(dǎo)意義,因為創(chuàng)造的天性,只服膺內(nèi)心的自由,思維的跳躍、理論的發(fā)明和學(xué)術(shù)的探究,只能在事后或事中尋求邏輯自恰,對路徑的延伸作出預(yù)見。
這些年,我們還注意到“都市水墨”的出現(xiàn),與“傳統(tǒng)水墨”或“抽象水墨”相比,無疑具有更為清晰的辨識度。傳統(tǒng)水墨的花鳥蟲魚、仕女古賢和山水亭臺,顯然不在“都市水墨”的取材范圍。而直面都市、反映都市,直指當(dāng)下城市生態(tài),反映城市化進程,無疑構(gòu)成新的視覺體驗。
同時我們也須看到,大多數(shù)都市題材的創(chuàng)作,仍須借助傳統(tǒng)水墨的技法和“線性藝術(shù)”的手段達(dá)致效果,也不乏素描、色彩的運用。甚至有些描繪高樓大廈的都市建筑畫,可以視作“三遠(yuǎn)式”山水畫的變體,多少反映了某種形式借鑒。我們對“都市水墨”有所肯定的同時,不能不說此類創(chuàng)作還處在起始或摸索階段,還不具表達(dá)的深刻性。倘僅為題材而題材,則很可能墮入換一種方式的“墨戲”。
“水墨”這一概念,唐朝即有,而“中國畫”這一提法,直到明清之際才出現(xiàn)。今冠以“現(xiàn)代水墨”“實驗水墨”的種種形態(tài),究竟成果如何?我以為還遠(yuǎn)沒有到下結(jié)論的時候。一方面我們欣賞那些探索的勇者,試圖掙脫傳統(tǒng)水墨的“銅墻鐵壁”和觀念束縛,創(chuàng)出與全球化背景相適應(yīng)的“當(dāng)代水墨”。同時仍須注意到,大多的“實驗”“探索”根基薄弱,無法自圓其說,而且?guī)资旯怅幃吘苟檀伲湓u價體系大體未備,更無法與很多畫家心心念念的“當(dāng)代藝術(shù)”取得共振效應(yīng),這是不爭的事實。
信息
東方既白——賴少其與長三角美術(shù)事業(yè)作品文獻展
近日,“東方既白——賴少其與長三角美術(shù)事業(yè)作品文獻展”在中華藝術(shù)宮舉辦。展覽用大量藝術(shù)作品與相關(guān)文獻資料,系統(tǒng)地梳理了著名美術(shù)活動家,畫家賴少其數(shù)十年來在江蘇、上海、安徽和浙江領(lǐng)導(dǎo)文藝工作,進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波瀾經(jīng)歷,彰顯其為新時代美術(shù)工作做出的杰出成就與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