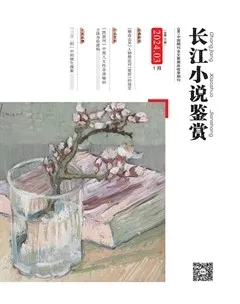后殖民女性主義視域下《雪花秘扇》中被邊緣化的女性
李雅雪
[摘? 要] 《雪花秘扇》是由美籍華裔女作家鄺麗莎創作的長篇小說,小說在書寫“女書”與“老同”這一已經近乎消逝了的中國傳統女性文化中,展示了19世紀的封建中國、閉塞的瑤族村落、奇特的社會習俗、神秘的女書文字、有著終生誓約的老同、小腳的東方女性等種種異域風情。這部小說試圖刻畫和呈現當時的女性命運、心理特征和時代價值觀,展示了女性在父權制社會中被視為邊緣化的“他者”的悲慘遭遇。本文擬從后殖民女性主義的視角出發解讀《雪花秘扇》,揭示在此作品中所體現的在父權話語下被邊緣化的女性境遇及成因以及邊緣化女性社會身份的重構。
[關鍵詞] 后殖民女性主義? 邊緣化? 女性形象? 身份構建
[中圖分類號] I247.5[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3-0032-04
一、被邊緣化的“他者”女性形象
1.女性遭受的身體上的傷害
在父權制思想的支配下,婦女被看作是男人的附屬物,受到家族和社會觀念的雙重壓力。作為封建時代的深閨婦女,百合的母親和嬸嬸堅守著傳統觀念,從女兒五六歲的時候便開始為女兒纏足,來塑造女性的美麗和纖細。她們相信,只有通過束縛女性的腳部,才能使其表現出嬌小、柔弱和優雅的特質。這種傳統做法在當時被廣為接受,雖然現在已被視為殘忍和剝奪自由的做法。當時的母親都希望借此為自己的女兒尋找一個好夫婿。但是,要想得到“三寸金蓮”,就必須要承受纏足之苦。雖然百合努力地克制著自己,想要裝出一副堅強的模樣,然而雙腳傳來的疼痛還是讓她難以忍受,她還被母親趕著在地上走來走去。久而久之,她的腳趾骨折,肌肉潰爛、化膿。纏足不但會帶來身體上的痛苦,還會造成殘疾,嚴重時會危及生命,書中的三妹就是這樣死的。這是令人嘆息的遭遇。女性在這樣的社會中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和不公。女性生來的意義好像就是為了嫁人,身體的掌控權也不在自己,完全在于男性的審美和喜好,那個時代的女性的地位低下,生命的存在也是沒有價值的。
在當時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中,生育子嗣對于家族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孩子可以傳承祖先的香火,同時也給予母親社會地位和榮耀的認可。甚至當百合聽說雪花在婚姻中受到虐待時,她的家人鼓勵她再生一個孩子,安撫她的情緒,希望以此來提升她在婚姻中的地位。可是,在意外流產的時候,從她體內流出的血,卻是黑色的,黏稠的,還帶著腐臭的味道。雪花最終淪為了封建大家族的生育工具,無休止地孕育子嗣,正是因為當時對于“母憑子貴”這種荒謬思想的盲目追捧,這給雪花帶來了巨大的痛苦,由于她的身體負荷過重,最終導致她病重并去世。把自己的身體當作容器孕育家族的接班人,可見女性受封建禮教思想的荼毒之深,讓自己的身體承受了不可逆轉的傷害。
2.女性忍受的心理上的折磨
在這部作品中,描述了一個脫離了時代的落后村莊,那里的人們有著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女人們沒有愛情和婚姻的自由,還會用纏足、結老同等方式來滿足男人的審美需求。小說中,“婚姻,是傳統觀念和封建社會賦予女性的一種宿命”[1]這種觀點多次體現。男性和女性都沒有權利自主選擇婚姻,因此夫妻間的感情和默契難以達成。男性隨時可以丟棄妻子,納妾,而女性則可能因不幸的婚姻而遭受毀滅性打擊,無法彌合一生的傷痛。
小說中,相較于身體上的傷害,雪花遭受了更多心理上的折磨。雪花原本是富有家庭的小姐,博學多才,舉止優雅,憑借這些優勢,她完全可以同另外一家門當戶對的公子結婚。但是,因為她的父親做生意失敗,又吸毒,所以她的家庭受到了很大的沖擊,逐漸沒落,雪花也從大家閨秀變成了連一般人家的閨女都不如的落魄小姐,這給她帶來了巨大的心理沖擊。她被迫放棄大小姐的身份,學習家務勞動,還去侍奉他人,這令人悲哀又心疼。更令人震驚和同情的是,媒人告知雪花,她將要嫁給一個屠夫,從此以后,她將過上卑微又貧窮的生活。平時,雪花受盡了婆婆的白眼和丈夫的打罵。她只能用自己的身體當容器,以免被遺棄,她把自己的尊嚴踩在腳下,拼命生育,讓自己淪為生育機器。在雪花的身上,體現了舊社會女性遭遇的不公,婦女完全喪失做人的權利和追求,完全淪為家族和男人的附庸。正如雪花母親所說:“命運是無法改變的,這就是命。”婚姻、性別和權力結構的不對等,造成女性處于社會邊緣,導致了無數女性的悲劇命運[2] 。
3.女性話語權的缺失
婦女在社會中的生存是一種困境,這種困境主要表現在婦女的話語權缺失。小說開篇就寫道:“時代變了,我也可以把這些都說出來了,以前我是靠父母把我撫養長大,后來是靠婆家養活,因此,我也不好說什么。如今,我想要把我這一生的遭遇都吐露出來。我已經一無所有,也不會得罪任何人了”[1]。這折射出在男權社會中,女性在男性統治話語權的社會中處于弱勢并缺乏話語權。話語權,就是說話的權力,說話人話語的地位。誰有話語權,誰就能掌控輿論。男性主導的社會就是通過對話語權力的支配來實現對社會權力的支配。福柯“話語權力”理論指出,話語權與權力密不可分,只要有話語權,就會產生權力,而權力又是一種無所不在的統治力量,對話語的支配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長期以來,婦女話語權的缺失導致了婦女社會地位處于“缺失”狀態,作為被男性操控的客體,婦女的沉默和容忍既是話語權的缺失,也是婦女權益的喪失。
在封建時代,女人依賴男人生存,一言一行都要小心翼翼,沒有任何話語基礎,處于話語權無根狀態,最終被男權話語體系所吞沒。在男權價值系統中,婦女總是處于次要地位,是一種被異化的自然物,是男性欲望的客體。“裹小腳”是由男性主導的社會文化所決定的,它決定了女性的美學特點和行為準則。男人視自己為“主體”,并根據自己的審美標準和對女人的期待,將其塑造為擁有“善解人意”“謙恭溫順”“相夫教子”等人格特質的客體觀賞物,甚至連后世的婦女都認為這些特性是與生俱來的。作為被壓制的婦女,在男權統治下,婦女話語權的缺失,使得婦女被置于社會邊緣,沒有一位真正的獨立女性。小說中的百合成為八十歲的寡婦的時候才敢說出這段往事,這象征著女性開始覺醒并對自己的話語權做出反思。但要注意的是,這種覺醒和反思是在百合社會地位提高的基礎上發生的。當時,大多數女性仍然處于男權話語的統治下,一直被邊緣化并成為被動的“他者”。
二、女性身份被邊緣化的原因
1.父權制對封建女性的壓迫
在父權制文化中,男性的社會地位很高,有著支配女性的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女性則成為了被支配、被剝削、被壓迫的對象,成為了“他者”。后殖民女權主義認為,在第三世界中,婦女不僅僅是性別的“他者”,同時也是文化的“他者”,處于被雙重邊緣化的地位。身處男權文化之中的婦女,始終不能完全擺脫由兩性差別所造成的歧視、偏見與不公。19世紀中國婦女深受封建倫理思想的毒害,為了取悅異性不斷改變自己的心理和行為,這一點可以從“女為悅己者容”這句話中看出來。女性纏足正是對這一觀念的深刻體現。但是,由于受中國古代傳統儒學的熏陶,男尊女卑、重禮輕愛、三從四德、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等思想已深入人心。
百合成為地位崇高的盧夫人之后,她就已然變成了以男性凝視為中心的理想女性。她躍升成為那個時代婦女的標桿和榜樣,也是男人心目中最理想的馴服模范。她以男性為中心,以男性主導的文化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規范和馴化自己以及身邊的女性,即便這些都是她以前最深惡痛絕的。百合的思維早已被男性主導的社會所同化,所以她對于自己,對于其他女性,都有著與男性對于女性同樣的要求。她既要讓自己順從于社會對婦女的期待,又要讓其他婦女順從,把這當作評價女性是否稱職以及衡量女性價值的尺度。時間久了,百合就失去了心靈上的知音,與昔日的好姐妹們也有了隔閡。
2.家庭內部的隱形傷害
女性在家庭之中被賦予了理所應當的責任,這種責任則變成了對女性無聲的壓迫。百合渴望著愛,但對她來說,愛是如此遙不可及。甚至當她的母親給她一個耳光時,雖然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她都不會感到憤怒,因為百合認為這就是母愛。她的心靈已經變得扭曲,她覺得母親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好。然而,在和母親的分歧和爭吵中,她忽然想起了自己被裹腳的那段日子,那種痛讓她撕心裂肺,一直無法忘懷。她忽然清醒地發現母親從來沒有對她有過哪怕一丁點的愛,只有無盡的要求和無盡的責備。這令百合非常失望,她不能原諒和釋懷母親對她所做的一切,包括她的自私行為。她試圖將母親從自己的生活中剝離,卻使自己陷入深深的悲傷中,永遠無法忘卻。這就是家庭對百合造成的隱形傷害,使她一輩子生活在陰影之中。
雪花一直向往著自由,也曾借助女書給他人寫信訴說自己的悲慘遭遇,渴望得到同情和關注。但她的好友百合首先向她施壓,要她遵守家規,當個乖乖聽話讓夫家滿意的合格媳婦,“順從,順從再順從”,要靠生個男孩來提高家庭地位,從而改變命運。作為女性的典范,百合的婆婆盧夫人因為雪花家族的衰落以及其殺豬丈夫的緣故,嫌棄雪花的身份,斷絕了百合與雪花的交往。那些恪守婦道和三從四德的女子,已經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封建制度對自己的殘害和壓迫,并將之前自己棄之如敝履的規定作為自己現在的行為準則。她們淪為了舊習俗的受害者,最終也成為了壓迫別人的人,作為曾經傷害自己的人的幫兇,她們把他人也變成了犧牲品。這都是家庭內部對于女性的隱形傷害,女性并沒有從自己的家人和姐妹那里得到安慰與支撐,無處訴說自己的無奈與苦悶,相反受到最親近的人的背叛以及不信任[3]。
三、邊緣化女性社會身份的重構
小說中的女性從老同的姐妹情誼中獲得精神慰藉以反抗父權壓迫;構建以女書為核心的女性話語系統來打破父權壓抑下“緘默”的失語境況;以“雙性同體”的形象來顛覆父權社會所建立的不平等的兩性關系。
1.老同的姐妹情誼
“老同”是中國南部一種古老的風俗,有這樣一種傳說,即年齡相仿、相貌相似、性情相近的姑娘會對彼此發誓,互相愛護,永遠不分開。結“老同”是一種神圣、吉祥的喜事。這是女人與女人間最親近的感情,比丈夫與妻子、姊妹之情更甚。她們使用一種名為“女書”的獨特女性語言進行溝通。這不是同性之間的戀愛關系,更像是心靈上的伙伴,生活上的朋友。“老同”與歐美文學史上的“姐妹情誼”有很多相似之處。“姊妹情”是一種由婦女聯合起來的力量,它是由被男權社會所排斥的女性力量組成的反抗勢力。與此類似,“老同”也是“婦女們在共同被壓制的情況下所形成的一種感情聯系,是對婦女感情世界的一種溫柔的救贖”。“百合”與“雪花”是經媒人介紹而結成“老同”的,并以獨特的女性文字——“女書”的形式“互訴衷腸”。在困境中,她們分享彼此的情感,鼓勵對方勇敢地面對不公平的命運;在幸福中,她們分享彼此的喜悅,為對方的快樂而感到開心,共同分享喜怒哀樂。
小說中的義姐妹也如此,性格相合的幾個女孩會自動結成義姐妹。在女性遭受壓迫、迫害的情況下,婦女的命運、人身自由都會被種種條條框框所制約,身心俱受摧殘。因此,女性們會尋求可以信賴和依靠的人結盟,彼此幫扶鼓勵,一起直面艱難的人生。根據《道縣志·社交習俗》所載:“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年間,在鄉村中的未婚女性中已經形成了一種新的風俗習慣。她們大多是正值青春妙齡的大家閨秀,由于對傳統的包辦婚姻感到不滿,又懼怕自由戀愛,不敢與異性交往,結果就是同性相愛,結為姐妹。”[4]義姐妹處于同一生活層面,共同的經歷和情感讓她們彼此靠近,惺惺相惜。這是一種淳樸的人際關系,不摻雜利益關系,給予對方日常生活中的陪伴以及苦難中的精神慰藉。
父權制社會中,女人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但是她們也在極度壓抑、身不由己的處境中結成了老同和義姐妹關系,這是獨立于男性之外的人際關系,她們成為了彼此生命中的一束光,陪伴彼此,給對方重獲新生的力量。
2.用女書文化構建女性話語權
江永女書是湖南省西南地區的一種具有神秘色彩的文字。它在女性中間流傳了上千年,是世界上唯一基于性別的書面文字。在男權社會中,女性常常陷入“失語”的境地。但是,女書卻為女性提供了一種特殊的溝通方式。女書既是女性的智慧,又是一種文化的聯系。仔細閱讀女書中的故事,我們能更好地理解當時女性的人生境遇。
百合與雪花之間有許多書信都是用女書所寫,其中一封這樣寫道:“我的丈夫對我很好。我從來不知道我家的那些地在什么地方。我每天都要非常努力地工作。婆婆一直在旁邊監督。我們家的女人對女書都很有研究。我婆婆也教會了我很多關于女書的新字體。回頭我再寫給你。我每天都要縫補衣服,做針線活計,做鞋子,還要紡織,做飯。如今,我有個兒子了。我向上蒼祈禱,希望有一天能讓我生下另一個兒子。你也得聽我說,要聽你老公的話,聽你婆婆的話……”[4]這封女書簡單明了地描述了女性生活的日常情況。從女性的勞動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她們的勤奮、能干;她們對公婆、丈夫百依百順,并以自己有個男孩而自豪,表現了婦女社會地位的卑微與她們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我從來不知道我家的那些地在什么地方”揭示了女性生活的封閉,認為男人是這個世界的主角,女人是圍繞著她的丈夫,從丈夫那里獲得生活來源。
“女書”是一種以女人為載體的象征代碼,傳達著女性的訊息,對女性有著特殊的意義。以男性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對女性施加了種種限制與約束,舊時代女性只有借助女書來表達她們內心深處的苦悶與壓抑,她們的情緒借此得到了短暫的釋放。在女書中,女性在解放自身的同時,也獲得了自身特有的個性魅力。女書有其獨特的書寫規律,“每一種女書字體都要回到原文中去解讀”,這既體現了女性對女書的獨特運用,又體現了女性獨特的感情世界,以及女性建構自身世界的方法[5]。
四、結論
在壓迫和失語的狀態下,寫作行為承擔著巨大的責任。《雪花秘扇》通過獨特的敘述話語,讓讀者了解生活在父權社會中女性的悲劇處境,刻畫了被邊緣化的女性形象,體現了作者對受苦受難的女性的關愛。鄺麗莎對男權意識和男性主義的解構與重構使女性敘事主體成為敘事的主要聲音、女性角色成為了故事情節的創造者和推動者,而男性角色被描繪成敘述者的對象。
總有一天,被壓迫、被邊緣化的女性和人們將重新書寫自己的社會身份,不會被視為“他者”。在全球化背景下,女性書寫也意味著一種新的女性身份,即“強調尊重女性個體的差異,不再有削弱、國家、民族和階級的界限”。
參考文獻
[1] 鄺麗莎.雪花和秘密的扇子[M].忻元潔,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2] 林樹明.多維視野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3] 張艷.論《雪花與秘密扇子》中百合的多重身份與焦慮[J].山花,2013(2).
[4] 范若恩.全球姐妹情誼的幻與滅——《雪花秘扇》的后殖民女性主義與新歷史主義解讀[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2(2).
[5] 莫秀云.《雪花秘扇》的女性獨立意識解讀[J].電影文學,2013(1).
(特約編輯 范? 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