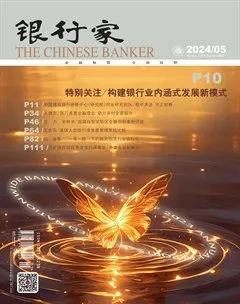金融機構提供投資顧問服務的信義義務
柏高原 湯杰 戎晨


隨著金融市場不斷發展創新,金融機構與客戶間的法律關系及相應的爭議類型也不斷變化。金融機構為普通客戶提供投資顧問服務時,雙方在金融信息、經驗、知識等方面不對稱,如果僵硬地遵從“契約自由”,普通投資者難以就合同條款實現“自由協商”,其合法權益或難以保障。為此,對金融機構賦以信義義務應作為我國深化金融改革的內容,并在金融監管和金融司法審判中予以落實,實現金融協同治理。本文以大陸法系國家德國的一起案件為由頭,就信義義務的引入方式、義務基本內涵進行探討。
一個德國金融衍生品交易訴訟案例
2011年12月,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就一起涉及利率互換的案件作出判決①,判令被告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對原告(一家德國企業,Ille Papier-Service GmbH)的損失進行賠償。該案中,被告德意志銀行于2005年初預測兩年期利率與十年期利率之間的利差在未來可能會大幅擴大,因此在兩次投資咨詢中向該德國企業推介CMS價差階梯互換合約(CMS Spread Ladder Swap),即“利率掉期”(interest-rate swap)。此類交易中,交易雙方約定在未來的某一個期限內,根據兩筆同種貨幣、金額相同、期限相同的本金,交換利息現金流。根據雙方的衍生品交易合同:前者同意在五年內為200萬歐元支付3%的利息,以換取后者在第一年支付1.5%的利息,之后則按可變利率支付利息;合同三年期滿后,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單方面終止合同,但必須基于彼時市場價格向另外一方進行補償。自2005年秋季開始,利差持續下降,原告遭受重大損失。2007年1月,原告支付賠償金后,利率掉期交易終止,后向法院提起訴訟,2011年聯邦最高法院就該案作出最終判決。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事實上早在設計合同之時,銀行就將自己風險損失設定得很窄。在互換合約中,一方的利潤為另一方的損失。德意志銀行在此次事件中扮演著雙重角色,這種雙重身份帶來了嚴重的利益沖突。一方面,其作為投資顧問,理應將客戶的利益置于自己之上;另一方面其又作為互換合約的“對賭”方,有追求利潤的動機,這就導致其并不會完全為了客戶的利益而作出投資建議。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判定,本案存在嚴重的利益沖突,被告與客戶之間存在“對賭”關系,同時又向客戶提供投資建議;為獲取利益,銀行故意通過結構化設計,將產品設計得與客戶的利益相悖。法院認定該利率互換合同本質上是一種“賭博”。一方所贏的,正是另一方所虧的,而這種利益沖突必須得到披露。銀行在投資咨詢過程中僅向客戶披露了統計模型,告知損失風險“在理論上是無限的”,并未向客戶披露合同不利于其的具體風險。銀行向客戶提供了交易結束時可能的價值區間,包括一份對所涉風險進行分析的《條款說明書》。同時,銀行還向客戶提供了一張用于在現有利率數據基礎上計算任一付款日到期凈額的數據表。但是,銀行并未向買方提供其內部的估值情況。
對于CMS利差階梯互換合同這樣高度復雜的金融產品,銀行作為投資顧問,必須基于客戶的投資目標和風險承受能力,推薦真正符合客戶投資目標的產品。如果并未在投資建議之前詢問客戶的風險承受能力,銀行必須通過確保客戶在做出投資決定之前已經了解其所描述的金融產品在各方面的風險,從而作出有利于投資者的建議。否則,投資顧問不能假設其建議與客戶的風險意愿相一致。本案中,通過投資咨詢合同,銀行僅承擔了向客戶提供建議的責任,并未向原告說明其故意設計的風險結構,不利于保護原告的利益,而這對原告決定是否購買該金融產品具有決定性意義。因此,原告請求的損失補償是無可爭議的。
該案在沒有專門的信義立法的情況下,通過司法裁判,認定雙方存在投資顧問事實合同關系,進而對金融機構賦以信義義務,創造性地解決了因投資顧問信義義務立法制度的缺失而無法有效保護投資者的難題。不同國家和地區在信義立法方面的具體路徑各有不同。
投資顧問信義義務引入的路徑比較
信義義務的概念起源于英美法系,后通過司法裁判和立法植入大陸法系。英美法獨特的“法官造法”孕育了信托制度,并通過判例法使信義義務的適用領域進一步擴張,也通過頒布立法、行業規范軟法等方式實現了信義義務的成文法化。大陸法系雖無“法官造法”的傳統,但引入信義義務的做法值得研究。
英美法下投資顧問的信義義務
在英美法系,信義義務源于衡平法最偉大的創造——信托。“受托人—受益人”關系,一直是信義關系的基礎范式。信托被認為是基于當事人之間的信任而產生的一種信義關系,這種關系的核心內容就是受托人的信義義務。時至今日,英美法下的信義義務已經不再局限于信托,而是向多個法域擴張。可以說,以信義義務為核心的信義法,已經構成了普通法系國家法律體系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信義法主要適用于委托人將自己享有重要利益的事務委托給受托人,受托人因此享有對受托事項較為寬泛的自由裁量權的法律關系。之所以在此前契約社會形式平等的“天平”上,對受托人賦以更重的義務,毫無疑問是基于立法者對信義法律關系中委托人和受托人實力、信息不對稱的基本狀況的考慮。20世紀以來,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此類司法實踐愈加頻發,以至于出現了寬泛的“信義法”(fiduciary law)的稱謂,更有學者呼吁制定統一的信義法。英美法系下信義義務呈現擴張態勢,與裁判方法不無關系。在信義義務的適用中,通常首先采用類推(analogy)的方法,法官會從先前判例所認定的信義關系入手,類比此前判例法律關系與本案的相似性,從已知的類型推出未知的類型,進而將新的關系認定為信義關系,這樣就使得信義義務的適用范圍從先前判例擴展到另一案的法律關系中。摩根大通銀行起訴Springwell Navigation Company & Ors案②中的爭議焦點即為Springwell與摩根大通銀行之間是否構成信義關系。法官指出,謹慎義務的存在始終是基于特定事實的,法院通常不愿意在以前判例法沒有確立的情況下確認這種義務,或者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武斷地判定信義義務。同樣,投資者是否真的依賴于建議的問題也始終是基于具體事實的。可見,投資顧問與客戶間是否必然構成信義關系,需要以個案判斷。而Smith起訴 Frame案③則闡明何種情形下可以認定信義關系存在——如果脆弱性因素上升、受托人自由裁量權會損害受益人利益且沒有任何其他立法或實踐救濟的可能,可以對信義義務進行擴大適用。該案中,法官特別強調脆弱的重要性,即當一方能夠使用自由裁量權(如投資顧問的投資建議權)單方面地去影響他人法定利益的情況,會產生信義義務。
與此同時,英美法系的國家和地區也將信義義務進行成文法化,或者制定于行業規范等軟法之中。例如,2016年4月,為了保護向退休儲蓄者提供財務建議的正當性,美國勞工部(DOL)頒布了一項規則,要求在《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The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以下簡稱“ERISA”)之下,向退休計劃受益人提供投資方案和建議的機構均應當負有信義義務。ERISA規范之下,受信人的信義義務包括忠實義務和謹慎義務。此外,信托法理下的審慎投資者規則也適用于退休儲蓄者的財務顧問。投資顧問為退休計劃投資組合提供的投資方案和建議中,需要滿足審慎的投資組合要求。北美證券管理機構協會(NASAA)通過制定行業標準的方式確定了投資顧問的信義義務標準,投資顧問的受托責任要求投資顧問將客戶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前,并避免利益沖突。當利益沖突發生時,投資顧問必須清楚而準確地進行披露,并向客戶解釋其將如何保持公正。
大陸法系國家信義義務的引入
大陸法系通過司法裁判和立法引入信義義務的具體做法值得研究。前述德國案例即為通過司法裁判引入信義義務。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定原告企業與被告銀行間既成立金融衍生品交易合同法律關系,同時因被告銀行向原告企業提供咨詢服務也成立投資咨詢合同法律關系;但前一合同關系有書面合同佐證,而后一合同關系是法院認定存在“事實契約”。在金融衍生品交易合同中,雙方權利義務依據書面合同確定,雙方的經濟利益關系是典型的“零和游戲”;而在投資咨詢合同法律關系中,被告銀行并未充分告知原告企業產品風險結構出自被告銀行的有意設計,倘若如實相告,或許原告企業不會做出購買決策。
有趣的是,事實契約理論正源于德國。1941年,德國學者豪普特(Haupt)發表《論事實上之契約關系》,提出了事實契約的概念和較為完整的事實契約理論。依據傳統的民法理論,合同關系的成立必須有意思表示的一致,且須通過“要約—承諾”的程式為之,但在現實生活中大量的合法交易無須當事人有真正的意思表示,只要有符合社會觀念的事實行為即可創立合同關系。傳統民法理論以意思的擬制理論解釋這一現象,既與現實相脫離,也不敷生活之所需,應當勇敢地承認合同關系在一定情況下可以因事實過程而成立這樣一項新理論,即事實契約理論。所謂事實契約,即平等主體之間不以意思一致為要素,基于一定事實過程而成立的債權債務關系。事實契約理論是對逐漸演進的社會關系的客觀價值判斷,恰恰表現了私法制度社會功能的演變,將契約的成立方式從擬制當中解放出來,能夠更加妥適地解決實際問題。事實契約理論體現了日益豐富復雜的私法生活的現實需要,在傳統的合同關系和侵權關系之外,創造性地解決了現實生活中廣泛存在的通過事實行為所成立之法律關系的法律適用問題,為合同法上新興的默示條款、附隨義務等地位尚不明確的新動向提供了一種清晰的理論分析框架,簡化了法律的適用,提升了私法生活的規范性和清晰度④。前述案例中,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無論何時,只要作為賣方的銀行與其客戶討論一筆投資問題時,銀行的顧問義務隨即產生。投資顧問義務的產生與誰先發起討論無關。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雙方簽訂的合同中,并無明示的咨詢條款,咨詢合同也會被推定成立。
也有大陸法系的國家通過頒布成文法,對提供投資顧問服務的金融機構賦以信義義務。2006年6月,以金融商品的規范整合及投資人保護為宗旨的《金融商品交易法》獲日本國會通過,2007年9月得以實施。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被定位為“金融商品銷售與勸誘的一般法”,就涉及金融商品的行為而言,是不分業務形態、適用統一的銷售和勸誘規則。忠實義務與善管注意義務是《金融商品交易法》對金融業者要求的最基本的一般性行為規制,該法很多具體規定就是對這兩大基本義務的具體化。例如金融業者在推介金融商品給客戶時負有的適當性義務;金融業者的最佳執行方針義務要求金融業者對其客戶秉持公平、誠信且適當的處理模式,在為其客戶進行金融商品交易和投資時,都以上述模式為指導方針。
投資顧問信義義務的內容
投資顧問的信義義務主要包括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和謹慎義務(Duty of Care)。
忠實義務
現代投資顧問的忠實義務源于英美普通法的信托和代理中的忠實義務。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投資顧問法》規定了“最佳利益”原則⑤。根據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證券商在向顧客提供建議時受制于“適合性”標準,他們須確保其提供的投資建議對于顧客需求而言是適合的,而投資顧問則要受《投資顧問法》的約束,投資顧問須受制于更高的信義義務標準。在信義義務標準下,投資顧問的建議不能僅僅是“適合的”,還必須符合顧客利益至上原則⑥。投資顧問對客戶負有忠實義務,須以客戶利益為重。投資顧問必須避免偷盜、欺詐和自我交易。在忠實義務下,投資顧問必須避免利益沖突,至少要向客戶披露利益沖突。投資顧問不應不公平地利用客戶的信任和信心。此外,投資顧問在不披露信息的情況下,不得將有利可圖的交易分配給其青睞的客戶或投資顧問本人。在美國的判例實踐中,法院認為,投資顧問對于每筆交易都必須獲得投資人的披露和同意⑦,僅取得投資者“一攬子”的同意(blanket consent)是不夠的。
前述德國判例中,如果銀行僅披露統計模型,說明相關的潛在風險在“理論上是無限的”,即使投資者接受,也無法免除銀行作為投資顧問的信義義務和責任。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由于市場波動頻繁,投資顧問在最后一刻做出交易決定時,很難提前取得投資者同意。因此,實踐中,投資顧問出于忠實義務的考慮,通常會避免自身作為對手方進行交易⑧。
謹慎義務
投資顧問還應履行謹慎義務(Duty of Care),該義務衍生自信托法的“謹慎投資者規則”,現已被廣泛作為投資顧問的謹慎標準。謹慎義務要求投資顧問收集信息,評估客戶的成熟度和風險承受能力。該義務要求投資顧問必須選擇合適的投資,并監控投資組合;必須盡合理的努力向客戶提供其所知道的或有理由知道的客戶想要的信息;必須在研究和監督投資方面盡職盡責。同時,投資顧問還必須跟蹤表明可能存在風險的危險信號⑨。
前述摩根大通銀行一案中法官論述的標準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該案的核心焦點是被告摩根大通銀行(JP Morgan Chase Bank)對于原告(Springwell Navigation Company)所遭受的損失應當負責的程度,以及其作為原告的投資顧問與客戶之間是否構成了信義關系。盡管本案最終法官判定信義關系并不存在,但法官指出了如果信義關系存在,投資顧問作為受信人所負有的注意義務的具體要求。法官在判詞中對于投資顧問在高風險咨詢投資組合中,對相對有投資經驗的客戶的職責以及謹慎義務的具體標準進行了經典描述。就謹慎義務的內涵,法官認為,受信人義務包括:合理謹慎地了解客戶的投資目標和風險承受能力;合理謹慎地向客戶提供與其投資目標和風險承受能力相符的投資機會;采取合理的謹慎措施,解釋提供該投資機會的原因,并提供適當和有幫助的信息,使客戶作出知情的選擇;采取合理的謹慎措施,提供準確的價格,以便客戶能夠自行決定何時出售;根據客戶的投資目標和風險承受能力,采取合理的謹慎措施,使投資組合在新興市場內適當分散。從法官的判詞,我們不難體會:謹慎投資義務對投資顧問施加了高度注意義務要求,這一義務貫穿投資的全流程——從投資前對施信人的合理謹慎了解、對投資機會合理謹慎的分析研判、向施信人充分披露信息、在出售問題上提供合理謹慎的建議以及投資的分散化等。
完善我國投資顧問信義義務規制的思考
我國金融市場發展迅速,金融機構與客戶間的糾紛也在不斷變化。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劉貴祥指出,當前金融民商事審判呈現出法律適用的復雜性特征,銀行糾紛從傳統的借款合同開始向服務收費、產品代銷、銀行理財等領域延伸。筆者認為,對金融機構為客戶提供投資顧問服務時,課以信義義務應作為我國金融改革的重要內容。
投資顧問信義義務是我國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傳統金融業務中,金融機構主要充當交易和支付中介,金融機構與客戶所建立的關系主要為賬戶關系或委托執行交易關系。隨著金融市場的變遷,各種新型金融商品和服務不斷涌現,金融服務也從單純事務處理延伸至金融產品推介和銷售、投資咨詢、代客理財等領域,金融監管和立法需要回應金融市場變化。對金融機構課以信義義務,是“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轉變的需要。信義義務規制著眼于金融機構的行為,而非簡單著眼于金融產品,對金融機構課以信義義務,有助于金融機構提升經營管理能力和競爭力。
投資顧問信義義務是行政監管和司法裁判的金融治理協同結合點。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是深化金融改革、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同時金融審判中依法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也是捍衛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新型金融交易產品層出不窮,金融交易結構更為復雜,使金融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適用面臨極大挑戰。相應地,金融民商事審判也呈現復雜性特征,信義義務可以成為金融監管和金融司法裁判的共同標準。金融監管所確定的信義義務標準,即便因其立法層級較低而不能直接作為裁判依據,但可以作為裁判機構說理的參考,從而實現行政與司法的金融治理協同。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既是金融監管和金融司法的共同追求,也是金融治理協同的“結合之點”。
金融市場發展需要投資顧問信義義務的橫斷性立法。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機構向其客戶提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呈現多樣化特點。例如,銀行協助客戶搭建家族信托,銀行因不具備信托牌照,必須引入信托公司作為財產的受托人。但銀行可以在信托財產投資管理方面向信托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金融機構投資顧問業務呈現出與傳統金融業務不同的特點,投資顧問業務中,金融機構并非必然與客戶直接建立賬戶關系,甚至并非直接建立合同關系。此時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出現跨市場的特點,組合投資可能涉及多類金融產品,如果采用分市場立法,即根據金融產品分別確立監管規則或立法,就會出現立法分散或沖突等問題。而信義義務立法是橫斷性立法,它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對各種金融產品或服務都有規制力,是從行為規范的角度對投資顧問課以義務。
(作者柏高原系特華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法學博士后、
京都律師事務所金融法高級顧問,湯杰、戎晨的
工作單位為京都家族信托法律事務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