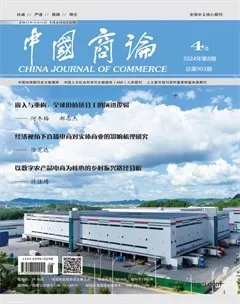江蘇省勞動者參與零工經濟意愿的驅動因素研究
陳雨露 宗美怡 張凱
摘 要:近年來,隨著數字技術對人們生產和生活的滲透,基于數字平臺的“零工經濟”在國內外迅速興起。零工經濟的興起為我國的就業壓力起到了一定緩解作用。本次調查圍繞零工就業者的基本信息以及收入、工作形式和幸福感,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對江蘇省勞動者參與零工經濟意愿程度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并提出相關建議。包括政府完善“守門人”角色,加強零工經濟市場建設與監管加大零工平臺企業支持;社會企業平臺堅守“護航員”角色,為零工就業者提供優質的權益保障;零工就業者做好“主人公”角色,在參與零工經濟時提升自我素質水平、職業道德水平與技能水平得到自我提升實現自我價值。
關鍵詞:零工經濟;就業民生;結構方程模型;收入;幸福感
本文索引:陳雨露,宗美怡,張凱.<變量 2>[J].中國商論,2024(08):-163.
中圖分類號:F24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4)04(b)--04
1 引言
隨著大數據、移動支付以及其他技術的發展,共享經濟以及數字經濟的迅猛崛起,已深深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并且推動了一個嶄新的、更加便捷的就業形態——零工經濟結構的出現。目前,日本和美國的靈活用工模式已經相對成熟,而我國靈活勞動者占人力資源行業的比例不到10%,并且獲取經濟報酬仍然是靈活勞動者追求的主要目標,這不同于日本和美國的靈活勞動者大部分以工作的靈活性和打發閑暇時光為追求,這也說明中國的互聯網經濟能帶動靈活用工群體的數量還有很大上升空間。零工經濟模式的出現,既為個體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也為企業和組織提供了更多的靈活性和效率。短短數年內,即時出行、即時送餐、互聯網家政服務、按需軟件開發、在線勞動眾包等新興行業就已發展成為經濟的重要新生力量。目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接近9億人,在城鎮就業的新成長勞動力近1600萬人,城鎮登記失業人員近1036萬人,零工經濟的興起為我國就業的壓力起到了一定的緩解作用。零工經濟為高技能勞動者和兼職勞動者提供了更靈活的工作機會和較高的總收入,但低技能全職零工勞動者則迫于生活和競爭的壓力主動選擇工作時間的延長和工作強度的增大。在如今全新的經濟環境中,怎樣更好地提升零工經濟的參與度以此體現零工經濟價值值得進一步探索。本文基于江蘇省勞動者的社會調查,通過分析調查結果,建立回歸模型發現影響零工經濟參與意愿的關鍵因素,同時檢驗其對零工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探討零工經濟幸福感的中介效應,并就所發現的問題總結提出相應建議。
2 理論基礎與分析框架
世界的技術發展使人們消費和生活成本增加,就業變化和信貸約束等促使共享和租賃的誕生,全球經濟不穩定造成工作崗位供不應求的現象,失業率顯著提高勞動力閑置,更多人渴望以勞動力換取收入,因而形成大量的“零工”。移動互聯網技術快速匹配勞動力供需方的新模式,產生了按需性和眾包性動態匹配勞動力的新供需方式,催生了零工經濟[1-2]。
零工經濟的靈活性和自由度是其最大優勢,對于許多勞動者而言,選擇零工經濟是為了逃離傳統工作的束縛和限制。勞動者收入是影響零工經濟參與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參與零工經濟可能帶來更高的工作滿意度和靈活性,但也可能面臨更大的不穩定性和風險[3-4]。近年來,學者通過對勞動者的調查發現,收入水平與零工經濟參與意愿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3],[5-6]。對于勞動者而言,參與零工經濟可以提高自由度、增加收入和改善工作體驗。對于江蘇省的勞動者而言,收入更是影響其參與零工經濟的重要因素之一,2022年江蘇居民人均消費水平位于全國人均消費支出排行榜第四位近3.3萬元,高額的消費使得勞動者對收入需求劇增。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參與零工經濟所獲收入直接對參與零工經濟意愿程度有正向影響。
工作形式是影響零工經濟參與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寧(2022)[7]、王文舉(2022)[8]等研究發現,截至2021年,我國零工經濟的人口規模達到2億人次,大部分從業人員主要從事直播帶貨、餐飲、網約車、美容美發等行業,此類型行業往往較其他行業收益獲得率更高,且對勞動者的學歷、經驗、技術要求相對較低,由此更多勞動者在閑暇之余更愿意參與此類零工工作。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2:工作形式調節了零工收入與幸福感之間的中介作用。
除了勞動者收入與零工經濟的工作形式外,勞動者幸福感體驗也是影響零工經濟參與度的重要因素之一[9]。零工經濟中的工作內容相對單一,工作強度和壓力相對較小,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調查結果,有近60%的勞動者表示參與零工經濟能夠給其帶來更多的工作樂趣和滿足感,提高其幸福感。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3:參與零工經濟所獲收入將通過幸福感對參與零工經濟意愿程度有正向影響。
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3 模型設定與數據來源
3.1 模型設定
依據前文假設,本文建立如下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其中,被解釋變量Happiness表示個體幸福感,選項設置為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分別賦值為1-5。核心解釋變量Income為勞動者從事零工所獲收入,中介變量Willingness為勞動者零工參與意愿,調節變量Work_Form表示勞動者參與零工經濟的工作形式,分別為自給自足和多勞多得。
3.2 數據來源
本次研究在江蘇省發放調查問卷共1238份,其中無效問卷206份,有效問卷1032份。無效問卷的評定標準為:在“您是否愿意參加零工經濟?”和“您參與零工經濟的意愿程度?”這兩個問題中選擇的選項邏輯相反。本次問卷的Cronbach.α系數為0.886,大于0.7,即問卷內部一致性比較好;KMO值為0.924,大于0.9,顯著性P=0.000,小于0.05,即問卷的結構效度良好。
4 實證結果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分析
問卷受訪者包含43%的女性和57%的男性,24歲以下人群占比12%,25~35歲的人群占比64%,45~60歲的人群占比21%,61歲以上人群占3%。33%的人月收入在6001~8000元,32%的人月收入在4001~6000元,共有28%的人月收入低于4000元,月收入高于8000元的受訪者僅占總人數的7%。民營企業職員占比最大,有360名;外企職員緊隨其后,有243名;有157名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參與本次的問卷調查;學生、農民、退休或無業人員以及其他職業的人員共有272名。學歷比例最高的是本科或大專,占樣本總數量的52.30%,而研究生及以上的群體僅占少數部分,占比在9.30%左右。調查結果顯示,在社會人群中其學歷以大學本科或大專為主,此次調查符合學歷分布的狀況。
4.2 勞動者參與零工經濟意愿程度影響因素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由于本研究僅采用問卷法收集數據,可能會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探索因子分析來進行檢驗。探索性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3個,第一個因子的變異解釋率為39.913%<40%,因此本研究問卷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及其相關系數如表1所示。將收入、幸福和意愿三者的總均分做相關分析,結果表明,三者之間均存在顯著正相關。各變量間存在的關系支持進一步假設檢驗。
本文運用結構方程模型探究參與零工經濟意愿程度、參與零工經濟所獲收入和從事零工經濟產生的幸福感3個變量之間的關系。其中,參與零工經濟意愿程度、參與零工經濟所獲收入、從事零工經濟產生的幸福感3個因子均為潛變量,其對應的14個觀測變量為顯變量。文章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法進行估計,用多種方法來考量模型的擬合優度。
基于勞動者參與零工經濟意愿影響因素概念框架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模型適配度檢驗結果見表2。根據模型檢驗與擬合優度可知,模型中卡方統計量(CMIN)為119.721,其對應的P值為0.001,小于0.05,表現不顯著。卡方與自由度(CMIN/DF)之比小于2。此外,CFI、NFI、TLT的值均大于0.9,RMSEA值為0.024,小于0.05。以上指標均滿足模型檢驗與擬合優度的要求,說明模型的擬合效果非常好。
基于建立的結構方程模型,通過AMOS軟件得到表3的結果。零工收入→幸福感、幸福感→參與意愿和零工收入→參與意愿三條路徑均在P<0.01水平顯著。
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法檢驗中介效應,結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中介作用的置信區間為[0.128,0.276],不包含0,即幸福感的中介作用顯著,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量為37%,即中介效應的效應量通過幸福感這一中介路徑起作用。
根據路徑分析結果可知,幸福感顯著正向預測意愿(β=0.321,SE=0.046,t=6.918,p=0.000);收入顯著正向預測幸福感(β=0.606,SE=0.042,t=14.474,p=0.000),在加入幸福感后,仍顯著正向預測意愿(β=0.330,SE=0.048,t=6.946,p=0.000)。這表明在收入對意愿的影響中,幸福感起部分中介效應,因此,研究假設H3部分成立。
4.3 工作形式對勞動者參與零工經濟意愿程度的調節效應分析
本文采用多群組分析的方法來考察工作形式的調節作用,將中介模型在工作形式變量上進行分析,檢驗自給自足和多勞多得模型每條路徑系數上的工作形式差異,若模型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則說明工作形式存在調節作用。結果表明,中介模型在工作形式變量上存在顯著差異,工作形式在收入→幸福感→意愿的前半路徑上起調節作用,置信區間為[-0.244,-0.040]。工作形式在收入→幸福感→意愿的后半路徑中置信區間為[-0.058,0.236],置信區間包含0,因此在收入→幸福感→意愿的后半路徑中工作形式的調節效應不顯著。具體而言,在自給自足、多勞多得模型中,收入→幸福感的路徑系數分別為0.511、0.653。進一步檢驗自給自足、多勞多得類型幸福感的中介效應,在自給自足模型中,幸福感的中介效應量為38.0%;在多勞多得模型中,幸福感的中介效應量為34.3%。研究假設H3部分成立。具體而言,相比自給自足的工作形式所獲得的收入,多勞多得的工作形式所獲得的收入對勞動者產生幸福感的預測作用更大,這一結果反映出多勞多得的工作形式受從事零工經濟所獲收入的影響更大。
5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調查問卷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利用結構方程模型來分析零工收入對勞動者參與零工經濟意愿的影響,結果表明:(1)零工經濟新業態的蓬勃發展下,不同的零工工作形式對勞動者的吸引程度不同,因此勞動者參與零工經濟開始越來越重視工作形式。(2)當零工就業與幸福感聯系不斷加強時,勞動者會更加傾向參與零工工作。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分析,人們會不斷追求更高層次的自我滿足與需要,這也包括對幸福感的更高要求。因此,本文預測未來幾年靈活用工市場將會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本文提出以下提升居民零工參與意愿,緩解就業壓力,助推新就業形態發展的政策建議。
政府要采取“助推型”規制手段,明確勞動關系的認定。政府的立法部門要不斷完善法制法規,讓靈活就業的勞動者在實際工作中有法可依、無后顧之憂。政府要不斷增加對共享平臺企業的政策扶持與幫助,可以為包含靈活用工模式的企業提供一定的稅費減免政策,主動去優化企業事物的審批程序,相應的增加對該類企業的貸款金額力度,緩解當下零工平臺企業融資難的壓力,鼓勵企業發展靈活用工模式,支持勞務派遣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企業要積極轉變人力資源體系,根據自身發展狀況,不斷創新用工模式,以最大程度為企業自身減負,減少勞務成本支出。我國的共享平臺企業具有多而雜的特點,企業要主動對自身進行分類與定位,讓人才招募對接更加精準。為了更加規范靈活就業者的準入程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部門還需要提高勞動者的入職要求,以尋求更加高質量的勞動者,確保靈活就業者的綜合能力。在當前的嚴峻就業形勢下,勞動者應積極轉變傳統的就業觀念,從求高質量強穩定的要求向工作沒有優劣之分,先工作不挑剔方向轉變。同時,勞動者要深入了解就業市場,依據自身情況謹慎選擇就業模式。
參考文獻
劉子龍,李曉涵,唐加福.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及其防控政策對互聯網零工經濟平臺勞動生產率的影響: 以外賣騎手為例[J].中國管理科學,2023,31(3):81-91.
許弘智,王天夫.勞動的零工化:數字時代的勞動形態變遷及其形成機制探究[J].經濟學家,2022(12):25-34.
張志朋,李朋波,朱麗,等.知識型零工職業轉換自主動機及其形成機理的扎根研究[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22,39(5):95-114.
陳嘉茜,趙曙明,丁晨,等.零工工作者體面勞動感知對其工作投入的影響: 一個被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J].經濟與管理研究,2022,43(10):81-95.
張藝,明娟.數字金融會帶來更高的零工工資嗎?來自網絡兼職招聘大數據的證據[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22,39(6):39-51.
謝富勝,江楠,匡曉璐.零工經濟如何改變性別工資差距: 基于家庭與市場的雙重視角[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22,42 (11):10-25.
王寧.從雇員到零工:勞動者個體化中的勞動價值[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8):33-43.
王文舉,魏巍,劉貝妮.樂在其中還是權宜之計: 數字零工勞動者工作意愿研究[J].經濟與管理研究,2022,43(10):96-112.
劉蘋,熊子悅,張一,等.基于數字平臺的零工經濟研究:多學科多視角的文獻評述[J].西部論壇,2020(6):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