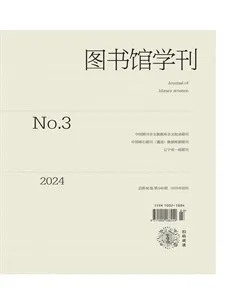圖書館信息網絡傳播服務例外權利限制問題的立法研究
[摘 要]在網絡環境中,為了保障圖書館服務功能的發揮,通過立法對信息網絡傳播權進行限制具有正當性。然而,我國立法對圖書館行使信息網絡傳播權例外權利的反限制條件較多而且嚴格,適用范圍狹窄,同時存在規定模糊等問題,極不利于圖書館開展網絡信息服務。為此,應進一步健全版權立法,探討完善例外權利行使制度、引入版權法定許可制度、建立網絡版權窮竭制度等策略。
[關鍵詞]圖書館 版權 信息網絡傳播權 合理使用
[分類號]D923.4
盡量滿足讀者對知識信息的需求是圖書館擔負的一項重要社會職責,由于其中涉及對大量的、類型復雜的版權客體的收集、整理、儲存、傳播,所以圖書館服務功能的發揮受到版權制度的必然影響。國內外解決圖書館版權問題的總體取向是“大圓圈+小方塊”,即在賦予權利人擁有壟斷性質的版權的同時,對版權進行限制,通過立法使圖書館具備行使版權的“例外權利”。在網絡環境中,版權呈現出對信息網絡傳播權立法并強勢保護的擴張趨勢,而圖書館利用數字版權的例外權利卻沒有得到合理的安排,造成圖書館行為受到極大束縛,加之法律規范的邊界存在模糊性,影響了基于新技術的圖書館服務功能的彰顯。若想改變這種狀況,筆者認為主要是創新版權制度,在圖書館工作領域重構新的版權利益平衡關系。
1 信息網絡傳播權立法及其在圖書館的適用限制
1.1 國內外對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立法
版權制度發展史表明,技術變革是版權擴張的直接動因。正如《伯爾尼公約》第11條內含的“受作品傳播技術的影響,條約修訂不斷賦予權利人更廣泛的傳播權[1]。”與模擬技術環境相比,在網絡環境中作品的創作模式、傳播速度、受眾范圍、使用頻率都發生了新的變化,加之侵權具有多樣化、隱蔽化、難查證等特征,對權利人的利益構成更大的沖擊和威脅,因而賦予權利人享有一種新的控制作品傳播利用的權利就有了正當性,這就是對信息網絡傳播權立法的背景。1996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管理的《版權條約》第8條和《表演與錄音制品條約》第2條率先以“向公眾提供權”的形式賦予權利人享有作品網絡傳播的壟斷權,并提出“傘形解決方案”,即由各成員國自行決定為這種權利進行立法的模式[2]。此后,歐盟《信息社會版權指令》,以及中國、德國、日本等國家修訂后的版權制度都采取設置新權利的策略,為信息網絡傳播權提供保護。雖然美國沒有為信息網絡傳播權立法,但是通過擴大發行權的適用范圍以及司法判例導向,使其版權制度的效力范圍覆蓋信息網絡傳播領域。
1.2 信息網絡傳播權行使限制與圖書館
法律之所以賦予權利人享有版權,并不是為了使其獨享智力勞動帶來的利益,而是在保障其得到合理的激勵回報的同時,更好地創造公共福利,使版權能夠為社會的文化、經濟、科技、教育等事業發展服務。于是,既賦予權利人享有版權,又對版權進行限制,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維系謹慎的利益平衡關系就成為一項基本而重要的版權立法技術。就信息網絡傳播權在圖書館適用的限制問題,可以在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法律法規中找到具體的規范。如,按照2019年修訂后的澳大利亞《版權法》的規定,適格的圖書館出于非營利目的,在不違反“商業供應檢驗法”的前提下,可以通過網絡按比例傳播作品。又如,按照2019年歐盟《單一數字市場版權指令》的規定,適格圖書館在法定條件下提供網絡作品可以免責[1]。我國針對圖書館開展網絡信息服務,制定了專門的信息網絡傳播權限制政策,即《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7條,但是無論是理論研究成果,還是圖書館實踐都證明,該項規定沒有起到應有的利益平衡功能,圖書館在該條款下行使例外權利,不僅無法對抗強大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反而種種限制行使例外權利的條件給圖書館開展網絡信息服務加上了一道無形的“緊箍咒”。
2 我國圖書館信息網絡傳播權例外權利限制的體現
2.1 適用作品的類型較狹窄
按照《條例》第7條的要求,圖書館行使例外權利傳播的作品只能是“本館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數字作品”和“依法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數字化形式復制的作品”,從而將大量的“本館收藏的合法出版的非數字作品”與“非陳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復制的作品”排除在適用范圍之外[3]。不僅如此,在圖書館行使例外權利針對的作品范圍極有其限的情況下,《條例》第7條又對圖書館傳播作品的“地域”進行了限制,即“本館館舍內服務對象”,該項規定是對美國《跨世紀千年版權法》相關條款的立法借鑒,指的是“圖書館物理建筑內的服務對象”。也就是說,在未有更明確的法律規定或者權利人授權的條件下,圖書館對作品的網絡傳播范圍必須局限于“圖書館物理館舍的局域網中”,從而否定了超出此范圍的在線遠程網絡信息服務的合法性。
2.2 圖書館承擔的義務過重
《條例》第7條規定,“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數字化形式復制的作品,應當是已經損毀或者瀕臨損毀、丟換或者失竊,或者其存儲格式已經過時,并且在市場上無法購買或者只能以明顯高于標定的價格購買的作品”。這是“商業供應檢驗法”第一次在我國版權制度中的體現,具有里程碑意義。但是,有學者認為,“商業供應檢驗法”的標準過高,要求圖書館證明圖書脫銷比取得權利人許可還困難[4]。因為,我國并沒有圖書銷售的統一平臺可供檢索查詢,而圖書館本身又不具備市場調查的能力,無法掌握圖書是否脫銷的準確信息。所以,《條例》第7條的這項規定,事實上是排除了圖書館通過行使例外權利“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使用作品的情況,圖書館在無依據判斷某作品是否脫銷的前提下,對作品進行數字化復制并開展網絡傳播,無疑具有明顯侵權風險。
2.3 合同對例外權利的克減
與在模擬技術環境中不同,許多國家對網絡環境中圖書館例外權利的立法采取了“任意法模式”,而非“強制法模式”。如,按照德國《版權法》第52條b款的規定,圖書館出于非營利目的可以在物理館舍內的局域網通過終端向讀者提供作品,并由版權集體管理組織向權利人轉移支付報酬,但是前提條件是圖書館不違反與權利人簽訂的合同[3]。也就是說,權利人可以通過合同排除圖書館的例外權利。我國《條例》第7條關于“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的規定,同德國《版權法》第52條b款“不違反合同約定”的規定的法律含義沒有實質性區別。國際圖書館協會(IFLA)對權利人利用合同克減甚至排除圖書館例外權利的做法持明確的反對態度,呼吁各國立法否定這類合同的合法性[5]。
2.4 有關規定法律邊界不清
法律規定越明晰,圖書館就越能判斷自己行為的合法性,對于可能存在的侵權風險,采取事先的防范措施。反之,如果法律規定模棱兩可,或者標準不明,界限不易把握,就會給圖書館的版權管理實踐造成障礙,或者使圖書館面臨不可預知的責任風險,而這正是《條例》第7條存在的突出問題之一。如,《條例》第7條“依法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數字化形式復制的作品”的規定中的“依法”是何含義,圖書館自行開展的“陳列服務”或者“保存版本業務”是否是“依法”呢?又如,《條例》第7條沒有對“存儲格式已經過時”進行具體解釋,而美國《版權法》第108條c款對該問題有確切的判斷標準[3]。再如,圖書館如何考量《條例》中規定的“明顯高于標定的價格”呢?圖書館擬購買的作品的價格是高于標定價格一倍算是高還是高于兩倍算是高呢?另外,《條例》第7條對“直接經濟利益”“間接經濟利益”的內涵同樣沒有界定。
3 健全我國圖書館信息網絡傳播權例外制度的立法思考
3.1 完善例外權利行使制度
在國際上,對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主要采取3種模式,即以“因素主義”為特征的“開放立法”、以“規則主義”為特征的“封閉立法”和結合二者優點的“混合立法”[6]。網絡環境中,我國對圖書館合理使用制度立法的不足,除了價值取向外,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立法的封閉性和僵化性,使圖書館許多具有合理性的利用作品的行為無法及時得到法律法規的認可。即便是在2020年修訂后的《著作權法》第13條設置了版權限制的“兜底條款”,但是封閉式立法模式并未徹底改觀[7]。鑒于我國2020年修訂后的《著作權法》已經吸納了由《伯爾尼公約》提出的設置權利限制“三步檢驗法”的重要元素,所以建議以此作為衡量網絡環境中合理使用的最重要法律依據,重構權利配置體系,完善圖書館例外權利制度。如,將圖書館權利延伸到非數字載體作品,并取消關于“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目的之限制。又如,取消“本館館舍”的制約,允許圖書館向所有“本圖書館服務對象”遠程提供作品。當然,要求圖書館采取技術措施,防止“不合理并發用戶數”的增加,控制讀者對作品非經授權的下載、修改和進一步傳播。另外,采取“強制性立法”,防范權利人利用合同或者采取技術措施擠壓圖書館的權利空間。
3.2 引入版權法定許可制度
權利人之所以反對擴大網絡環境中圖書館享有的例外權利,是因為擔心大范圍傳播作品會造成并發用戶數激增,由此形成的聚合版權使用效應,會萎縮作品銷售市場,減少其經濟收益。因此,如果能夠通過制度設計對權利人的經濟利益進行合理補償,那么就會為擴大圖書館享有的例外權利創造有利的條件。另外,制度的安排應當避免“意定授權”的弊端,維護圖書館的利益。綜合考量,符合這些條件的制度就是“法定許可”。有學者認為,即使不把圖書館的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納入合理使用范疇,也應納入準合理使用范圍[8]。這個“準合理使用”指的就是“法定許可”。目前,在國際上針對圖書館通過網絡傳播作品進行法定許可制度立法已經有了先例,如德國《版權法》第52條b款規定的實質就是法定許可。我國雖然還沒有針對圖書館的法定許可規定,但是《著作權法》已經有多項涉及相關主體利用作品的法定許可規定,而《條例》第9條更是一種嚴格的網絡傳播作品法定許可制度[9]。法定許可與合理使用相比的優點在于,不割裂作品非經授權使用與權利人經濟利益之間的聯系,有利于維護利益關系的平衡。法定許可與意定許可相比的優點在于,防止權利人利用合同模式對圖書館享有和行使權利的限制。
3.3 建立網絡版權窮竭制度
“首次銷售原則”(the first sale doctrine)是指合法制作的作品原件及復制件經權利人(作者、出版商或者其他版權主體)授權進入市場之后,對于該原件、復制件后續的銷售、收藏、轉讓等流轉行為,無須再征得權利人的同意[10]。在模擬技術環境中,首次銷售原則較好地解決了版權和物權之間的矛盾,因而成為版權制度的一項重要法則。然而,在網絡環境中,由于存在法理方面的障礙,使得首次銷售原則迄今未能得到版權立法的認可,而司法實踐中,國內外法院對于網絡適用該原則的訴求或者判決結果大相徑庭,或者完成不予支持,這在我國司法審判中尤其如此。如,在“丹東法信法律咨詢服務有限公司訴費縣圖書館等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案”中,法院對被告圖書館提出的首次銷售原則抗辯,沒有給予認同[11]。有學者建議,應突破法理障礙,擴大首次銷售原則的適用范圍,建立網絡權利窮竭制度[7]。與合理使用制度相比,網絡首次銷售原則或許更有利于對圖書館權利的保護,因為網絡環境中圖書館對作品的傳播與模擬技術環境中取得合法物權并予以處置并無本質的不同,但是必須通過立法,要求圖書館履行技術措施義務,在傳播作品的同時,銷毀合法取得的作品的原件或者復制件,保證并發用戶數不致不合理地增加,即與傳統圖書借閱模式的理念相契合。
參考文獻:
[1] 柴會明.圖書館信息網絡傳播權限制與例外研究:緣起、現狀與走向[J].山東圖書館學刊,2021(6):53-59,84.
[2] 吉宇寬.數字圖書館信息網絡傳播合理使用的規制、困境與訴求[J].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4(7):9-13.
[3] 周剛志,王星星.圖書館信息網絡傳播權研究[J].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8(5):5-10.
[4] 梁欣.解讀《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對圖書館的影響[J].情報資料工作,2007(6):69-72.
[5] 徐軒,孫益武.論國際圖聯關于圖書館版權限制與例外的立場及其啟示[J].圖書館論壇,2014(12):36-41,57.
[6] 秦珂.2006年以來我國圖書館合理使用數字版權立法研究綜述[J].圖書館論壇,2015(8):72-83.
[7] 姚志偉,詠絮.論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權利限制[J].電子知識產權,2020(12):4-16.
[8] 梅術文.信息網絡傳播權合理使用的立法完善[J].法學,2008(6):103-112.
[9] 韓慶揚,譚云鵬.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法定許可研究[J].福建警察學院學報,2016(5):51-57.
[10] 唐艷.數字化作品與首次銷售原則[J].知識產權,2012(1):46-52.
[11] 張健,陳琳.圖書館著作權侵權分析及應對策略[J].數字圖書館論壇,2021(10):47-53.
蘇 偉 女,1977年生。本科學歷,館員。研究方向:知識產權。
(收稿日期:2023-12-10;責編:婁明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