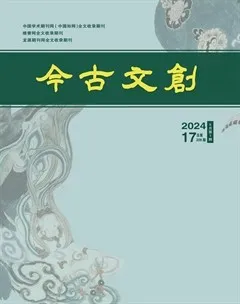從《太平狗》看跨場域的底層生存狀況
【摘要】陳應松作為新世紀“底層文學”的代表作家,其小說創作秉承著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擔當,始終關注著城鄉社會底層的現實生存。《太平狗》作為系列小說中獨具特色的一部,將底層人民在城鄉不同場域下的生存現狀利用程大種與趕山狗太平的生存經歷連接起來。小說超越了地理局限和主題局限,在跨場域之下,有意將城鄉關系緊張化,揭示了底層人民跨場域的生存焦慮,以及苦難生存中的現實思考和精神救贖。
【關鍵詞】《太平狗》;跨場域;底層生存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17-002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7.007
“底層”的誕生,弱化了長久以來的“階級”概念。隨著時代的發展,底層被看作“在社會分層結構中處于社會結構底端;從經濟收入上看,收入較平均水平低,生活比較困難;從文化話語權上看,社會公共話語權較少的一類社會人群,甚至還包括一些老弱病殘等。”[1]4作家陳應松自登上文壇開始就一直關注著最底層人們的現實生存,始終致力于對鄉村苦難生存的書寫,其鄉村小說創作碩果累累。《太平狗》作為其中篇小說的代表作,文字更是針砭時弊,有力度地敘說了城鄉之間生存的緊張關系。小說采用非常態化的動物視角,展現了底層人們在城鄉不同場域之下的生存方式,在對比交錯中反映出城鄉社會的種種矛盾,成功地引發了社會對底層苦難生存和城鄉和諧發展的現實思考。
一、非常態化敘事視角
新時期以來,非常態化“動物敘事”作為特殊的敘述方式開始介入“底層文學”中,為底層文學創作融入了新的文學生命力。小說《太平狗》利用獨特的動物敘事方式,賦予趕山狗人的思維,采用了人和狗雙線并行的敘述模式,以狗的視角來感受城鄉不同生存模式下復雜的現實社會和人性的善惡。
首先,以動物的視角來感受城市生存環境的殘酷和人情的冷漠。“動物沒有語言,卻能發聲,發聲就是語言,就是文學。”[2]115動物能夠用其獨特的話語方式準確傳達它們的歡喜與憤怒。這只來自神農架的純種趕山狗“太平”,跟隨主人來到城市的第一個晚上就感受到了城市的寒冷和饑餓。太平僅僅只在垃圾堆里翻到了兩塊骨頭吃下了,“那骨頭戳著它的胃,戳著肚皮,用爪子一摸就能摸到,可難受了。太平真想把那骨頭抽出來重新咀嚼一遍,沒什么危險嘛,何必這么慌張呢?”[3]5初入城市,丫鵲坳意氣風發的太平忍受著饑餓和寒冷的同時,竟然產生了慌張和害怕的感覺。城市里怪味刺鼻的黑水溝、殘酷無情的冷風、冰窖般的水泥地、亂糟糟的集貿市場……陌生的環境讓太平感到小心翼翼。這里借太平的視角來觀察著城市最底層的生存環境,看似是太平在暗暗發聲,實則也有著程大種的幾分影子。程大種的姑媽見到太平的第一眼時,就產生了嫌棄,主人只好將它垃圾一樣的扔出了門外。在城市里,太平失去了溫馨的家園。就如太平自己所言:“神農架再大的風,它也有一個草垛呀,有個狗窩呀。在城里卻沒有。”[3]5而太平見到另一個像垃圾一樣被拒之門外的則是主人程大種。程大種帶著太平在城市的街頭四處流浪,被人指指點點,只剩下滿街冷漠的眼神。圍繞在程大種和太平身邊的城市人被類型化,似乎性格永遠是扁平的。太平深刻地感受到了城市的冷漠,“可它已經來到城市,它已經誤入城市。它的眼里滾出了大顆大顆的淚珠,沒讓主人看見。”[3]46由此,小說以太平的視角來看底層生存,看似有夸張的成分,實則正是這非常態化的呈現,才使得小說反映現實的力度更為深刻。
其次,從動物視角中透視了城鄉社會的隔閡與排斥。在城市里,一條溫順熱情的蘇格蘭牧羊犬跟太平打過招呼,太平也禮貌地回應以示友好,結果城市狗的主人卻無比用力地將自己的狗迅速拉走了。主人表面上是不想要兩只狗聚在一起,其實也是在嫌棄著從鄉村來的農民工程大種,不想和鄉下人沾上邊兒。這無比滑稽的一幕曝光在城市生存場域之下,借用太平的身份折射出了城里人對底層打工者無聲的歧視與疏離。正是本地人高高在上的姿態,才使得太平和主人無論走到哪里都無法獲得安身之所,“城里容不下一條狗!”[3]42當太平被主人賣給剮狗市場后,在鐵籠里看見了上百只形形色色的城市狗,有巨人一樣的“蘇格蘭牧羊犬”,有西施“八格牙魯”,有“黃毛懶犬”等等。長期在山野里生活的太平初見這群狗時便看到了他們華麗外表下虛弱的部分。為了爭奪食物和躲避死亡,太平和這群城市狗們進行了頑強的搏斗,并最終以神農架獵狗靈活矯健的優勢取勝。鄉下狗與城市狗的搏斗,亦可窺見作者別具匠心的寓言化敘事。這既是動物們之間爭食的矛盾沖突,也映射了城鄉之間無言的隔閡與排斥。作者有意讓太平在這一場搏斗中勝出,暗含的是作者對底層堅韌頑強精神的贊頌。
“自進入新世紀以來,諸多‘底層文學作品中融入了‘動物敘事的表現形式與敘述成分,有關動物的想象與敘述,豐富和拓寬了‘底層創作的意義空間與思考維度。”[4]62陳應松利用太平的視角洞察了農村人在城市的生存現狀,盡管有夸張和變形的成分,但卻將更深層次的現實社會矛盾隱喻其中,激發了社會對底層的關注。由此,陳應松非常態化“動物敘事”的社會文化效力也在此彰顯無疑。
二、跨場域底層生存
小說《太平狗》是陳應松“神農架系列”小說中少有的一部當地村民走出神農架的故事,小說反映出了城鄉發展不平衡的情形下農民的生存走向。神農架物質的極度貧瘠構成了底層農民逃離鄉村的重要原因,經濟繁榮的城市又自然而然成了他們心中理想的生存出路。
鄉村生存資源的稀缺使本地人被迫逃離鄉村。小說《太平狗》中主人公程大種的進城,反映的正是神農架村民向外謀生的狀態。在閉塞的神農架地區,村民靠著種地和打獵獲取最基本的生存資料和經濟收入。對于程大種來說,“不出來又咋辦呢?娃子要上學,老母親好在死了,可自癱瘓之后,加上辦喪事,虧了一筆債,收成少,人又沒什么本事,不出來找點事干怎么辦呢?”[3]12靠地吃飯的農民,沒有糧食收成就沒有充足的物質資料,就失去了生存的經濟支撐。程大種的這段內心獨白背后有著萬千中國農民的影子,也是農村人走出鄉村的現實因素,物質生存資料的匱乏催促著農村人逃離鄉村,向外發展。對于小說中的太平來說,它的鄉村世界里沒有現實的物質生存焦慮,小說中的太平就像是程大種另一生存狀態的精神化身。它本可以在丫鵲坳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跑遍山野的每一寸土地,曬著最舒服的太陽,但他和主人還有一個家徒四壁的屋子、黑黢黢的火籠屋、長期害著鼻炎的女主人……在寫太平丫鵲坳無憂無慮的生活時,旁敲側擊地點出了程大種一家惡劣的生存環境和捉襟見肘的生存現實,實則也從側面反映出了貧苦鄉村的生存常態。因此,程大種的走出昭示著新時期的農民不是沒地種了,而是單純地種地已難以獲得理想的經濟收入,難以支撐現實生活所需。他們的逃離并非自愿,而是被迫謀生的手段。像程大種一樣,世代在土地里謀生的農民,土地就是他們的根,面對根的價值的跌落,他們顯得無所適從。
以諷刺的手法揭露底層農民工城市生存的艱難。程大種拋棄自己的趕山狗太平,開始在雜亂的武圣路勞務市場找工作時,小說所關注的正是農民工跨場域后城市生存。“《太平狗》依然繼續民工文學‘控訴的主題,作者直接切入生與死的層面,直白而生動,簡潔而震撼,可以說是民工文學的又一部優秀之作。”[5]60程大種作為一名農民工在城市有兩處打工場所。一處是建筑工地,生存環境極為惡劣,農民工們被施工的塑料布嚴嚴實實地圍著,工人的吃喝拉撒都在圍著的塑料布里,毫無溫馨或隱私可言。而塑料布的外圍卻寫著為城市增光添彩的標語,極盡地諷刺了城市的虛偽。程大種能找到這一份工作也僅僅是因為頭一天泥土塌方壓死了民工,從而空出了位置。這種荒謬殘酷的招工方式展露的正是底層在城市生存的艱辛。不出五天,工地又塌方,又埋進了一個河南人。對于這樣的工傷,城里的老板竟然罵罵咧咧不愿意花錢給工人治病,而這些陰暗、污濁、臟亂又無勞動保障的工地,依舊是進城農民工首選的工作場地。作為程大種第二處工作地點的城市郊區工廠,更是將城市的道德失范體現得淋漓盡致。程大種和工友們被封閉在臟亂的工廠里工作,廠子里怪味刺鼻,每天還有帶著防毒面罩形似“野獸”的監工看守他們,農民工們完全失去了勞動保障和生命保障,飽受著肉體的折磨和精神的摧殘。程大種在置身于嚴重污染的工作環境后,最終病倒了。病了三天,程大種開始皮膚瘙癢,流出化膿的黃水,開始惡心、嘔吐,最終慘死在了工廠里。程大種在城市的苦難生存并非單獨個例的呈現,他的背后有著中國集體農民工的影子。由鄉村到城市,他們經歷著完全不同的生存模式,但底層人民苦難的生存本質從未改變。陳應松的本部小說有意突出城市復雜環境背景對人性惡的影響,以諷刺的筆法和陌生化的效果凸顯底層跨場域生存的現狀,從而直擊讀者的心靈。
中華民族作為有著幾千年農業史的民族,農民是生活于這片土地上的主要群體。而在進入現代化社會之后,鄉村失去了原初的話語權,農民身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和顛覆。“貧窮”和“落后”成為鄉村的身份標識,城市反而成了高踞在上任鄉村仰視的對象。與傳統的鄉土敘事或城市寫作相比,陳應松利用一部短篇小說容納了不同場域環境下底層的現實生存,將城鄉的對立在小說中表現得劍拔弩張。
三、現實性生存思考
作家以平民的姿態深入底層人民的內心世界,以文學的筆墨書寫跨場域生存的現實狀況。作為城市“異鄉人”的程大種以及趕山狗“太平”正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形成的特殊城市漂泊者的縮影。但作家沒有停留于書寫底層群體表層的生存苦難,而是以這些漂泊的靈魂來引發人們對社會發展的思考和對苦難生存的出路探尋。
首先,《太平狗》以人和狗雙線并行的敘述模式深刻地表現了農民工跨場域生存的社會問題,以引起社會對城鄉發展的現實思考。由市場經濟應運而生的“打工仔”在80年代里潮涌般的出現,成了新時期新的社會熱點。數以萬計的農民們離開土地,呼朋引伴,南下、北上、東進,叩響了城市的大門,他們想要在城市謀求更好的生存機會,這是中國農民的集體意識和奮斗主題。社會經濟的主流涌動讓處于偏遠地帶的神農架林區同樣受到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從而像程大種一樣的農民工開始活躍于城市的各個角落,幾乎所有苦活、累活、險活、臟活由他們承擔。在社會轉型的初期,農民工的城市生存承受著巨大的苦難,卻無法獲得最基本的物質保障、經濟保障甚至是生命保障。陳應松這一深刻的寫實,讓底層農民工艱難的生存狀態直接呈現在讀者面前,真實到讓讀者顫抖。也正是因為程大種城市生存的艱難和生命的逝去凸顯出了強烈的社會寫實性,才激發了世人對當下城鄉發展的深入思考。從社會學的意義上看,大量農民工的進城毫不亞于一場社會變革,它的產生已經占據了深厚的社會資源導向。中國正處于發展的上升期,城鄉和諧發展和社會民生問題是主要內容。特別是近年來主流價值觀對底層生存和人民性問題更加關注,更加倡導鄉村的振興和城鄉和諧式發展。陳應松的底層寫作恰恰是對社會民生問題的回饋和城鄉和諧式發展的思考,以利用文學作品來引發社會的關注,更好地促進社會向好向善發展。
其次,《太平狗》中無法融入城市的太平最后神化返鄉,是文化層面的城鄉對立和故鄉對農民工的精神召喚。對于底層農民工來說,城市始終是陌生的,農民工作為城市的“異鄉人”始終都是要返回故鄉的。小說中的多處細節也都為太平最后的返鄉埋下了伏筆。在城里的公交車上,為了向城市人證明太平沒有狂犬病,程大種只能將自己的手塞進太平的嘴里;城里的姑媽不讓程大種和太平借宿;蘇格蘭犬的主人慌張地拉開自己的狗不讓接近太平;在勞動力市場程大種和太平被人指點;在建筑工地,包工頭對程大種下最后通牒“有你無狗,有狗無你”等等。這些情節所反映的是城鄉不同場域下生存經驗、思維方式、文化認可的不相融合,這是鄉村人無法融進城市的文化根源。雖然這些情節也暴露出了作者對城市激烈批判下的極端化書寫,但正是這些極為深刻的事例才足以構成強烈的現實反思。
當下的城鄉和諧發展、鄉村振興規劃,若只有物質層面的縫合是難以完善的,還需要城鄉之間文化層和精神層的引導。城鄉之間的文化隔閡讓故鄉對打工者們產生了強烈的精神召喚,幾乎所有的城市打工群體都有著難以割舍的鄉土情結。他們因家鄉的貧困被迫走出鄉村,又因城市的殘酷而回望溫情的故鄉。他們雖身處城市,卻“精神返鄉,尋找屬于自己的話語”[6]17。小說中的程大種和太平在城市不止一次地懷念自己的故鄉,太平想念著丫鵲坳的山崗、太陽、晚風、森林、溫暖的火籠屋、憨憨豬……程大種想念著自己的老婆、孩子,他們通過回憶達到精神的返鄉,在記憶中獲取精神的救贖,獲取城市生存的動力與勇氣。太平和程大種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體的,對土地和家鄉的眷戀讓他們無法在城市找到安放靈魂的地方。太平最后拖著一身殘骨回到了丫鵲坳,回到了女主人陶花子的身邊,實則也是程大種的精神返鄉,透射的是美好親情對苦難人生的精神救贖。結尾的返鄉安排也反映出了作家的情感偏向,讓我們不得不承認作家受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家文化”“故鄉情結”“安土重遷”觀念的深遠影響,這是陳應松神化太平的內生文化因素。太平的返鄉暗含著故鄉和美好親情對苦難人生的救贖,使人在苦難中看到故鄉和親情對人的巨大精神支撐,給人以戰勝苦難的信念。
文學是人學,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應該對人們的現實生存產生深刻的啟發意義。陳應松以一部短篇小說介入深層現實,在人與狗雙線并行的敘事基礎上,通過太平的視角反觀人性,通過程大種的跨場域生存經歷反思現實,再現了城鄉經濟發展對底層人民的生存影響。于非常態化的敘事視角和生動的故事情節中,展露出了底層人民不同場域下的生存狀態,一定程度上推動著世人對社會和諧發展的深入思考和對底層人們的深情關懷,成功地發揮了小說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
參考文獻:
[1]李新.新世紀底層敘事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2]陳應松.我們需要文學嗎?[J].文藝爭鳴,2009,(02).
[3]陳應松.太平狗[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4]程佳冀.“底層寫作”中的“動物敘事”——新世紀“底層文學”的一個考查維度[J].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02):38.
[5]許貴重,莊金寶,程金友.劃破城市邊緣人的生存面具關于《太平狗》的社會學想象[J].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04).
[6]聶運偉.最后的守望者(陳應松論)[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簡介:
譚彩霞,女,長江大學人文與新媒體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