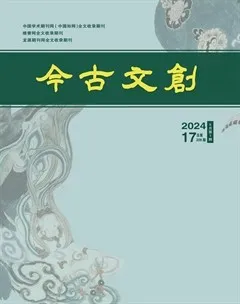比喻義派生機制研究
李佳蓉



【摘要】本文首先對《現代漢語詞典》中聲母為“j”的漢語詞匯的比喻義進行梳理,并從語音、語法以及語義方面進行整理,并對相關現象分析解釋,力求通過對聲母為“j”的漢語詞匯的整理,尋找漢語比喻義背后的規律,為比喻義派生機制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和參考。
【關鍵詞】比喻義;中觀分析;描述性語義
【中圖分類號】H173?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標號】2096-8264(2024)17-012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7.037
詞義是人們通過詞的形式反映客觀世界、主觀世界的事物、現象及其關系的意義內容。邵敬敏先生在《現代漢語通論》中將詞義分為客觀概念義、時間空間義、主觀色彩義、固定修辭義、臨時語境義等五類。其中語言使用者通過某種修辭手段改變語義,且凝固成為詞典義項之后可稱為固定修辭義,比喻義便是其中之一。《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中以“j”做聲母的詞匯約4076個,其中有比喻義的190個。(以釋義中明確提出“比喻”為標準,且將“又稱”“也說”以及組詞構成的詞匯也記入。)
一、比喻義基本情況梳理
(一)語音
190個詞中單音詞有5個,雙音節詞共83個,三音節詞22個,四音節詞組高達69個,多音節詞11個。總的來看雙音節在比喻義中占比最多,高達43.5%,四音節占比達35.6%。從絕對數量上看,具有比喻義的詞主要集中在雙音節詞和四音節詞中,三音節詞較少,多音節詞依次減少,單音節詞數量最少。我們綜合考慮所有4076個詞匯,并判斷占比。綜合數據見下表。
從表格中我們可以看出,雙音節詞絕對數量和占比都位列第一。將各個音節詞內部具有比喻義的詞縱向比較,我們發現,四音節詞中具有比喻義的詞占比達16.5%,單音節詞占比為13.6%,其次是三音節詞,單音節詞占比為3.5%,而絕對數量最多的雙音節詞占比最少,只有2.7%的雙音節詞存在比喻義。我們可以繪制下面的表格,在判斷中不能只考慮“分子”絕對數量的比較,而應該以“分子/分母”為考量標準,從音節本身的集合群中進行數據判斷。
總之,所有具有比喻義的詞語中,雙音節詞占比最大,數量最多。而四音節詞最易產生比喻義,對比而言,雙音節本身語義比較固定,語義引申產生比喻義的可能性較小。
(二)語法
從詞類來看,比喻義詞匯中個別詞詞性比較復雜,例如“教條”有4個義項,其中3個普通意義為名詞,但其用作比喻義時為形容詞。有5個雙音節詞是這種比較復雜的情況。我們這里不考慮其所有義項的詞性,主要考慮其基本義(多個義項時將第一個作為基本義)的詞性。此外,部分多音節詞的詞性也無法判斷。所以,整理分類后的數量總和低于190。
從絕對數量上看,具有比喻義的詞匯中名詞、動詞數量都很多,且基本義為動詞和名詞的詞匯產生比喻義的可能性相比其他詞性要大得多。從可判斷的詞匯的語法結構來看,偏正類詞匯最多,動賓結構、并列結構數量也較多,主謂結構、動補結構數量很少。
組成結構的數量應該結合詞性來看。名詞在整體具有比喻義詞匯中占比較多,且大多為偏正結構。動賓結構的數量較多也受比喻義詞語中動詞較多這一因素的影響。所以語法結構的數量及占比并不能證明詞匯結構本身是否對形成比喻義有影響。
雙音節詞匯語法結構的判斷比較明確,不存在矛盾或無法判斷的情況。
雙音節(83) 有比喻義“j”開頭詞語個數 占比 所有“j”開頭詞語 占比
從語體上看。190個具有比喻義的詞語中,22個為明確標識的書面語,占全部551個書面語的4%。明確標注的方言有1個——節骨眼,占全部116個方言的0.9%。書面語詞匯語義發展,具有比喻義的可能性較大。
(三)語義
首先,我們需要明確,《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中明確提出具有比喻義的詞語共190個,但是這些詞匯并非全部都有兩個及以上的義項。5個詞語釋義中只提到可以用于比喻,但是并未將其具體的比喻義用法單列作一個義項。67個詞語釋義中直接為比喻義,未列其本義,這些詞語大多為多音節詞語。我們具體分析語義的對象是118個既有本義,也有比喻義的詞語。
研究詞義有多種方法,本文對語義的分析主要是從功能角度分析語義結構,將語義分為兩大類:關涉性語義成分和描述性語義成分。關涉性語義成分起介紹、指別、涉及等作用,如類屬(領屬)、構造、工具、材料、用途、物件、時間、空間、數量、性別等,可看作廣義的指稱內容,顯現出關涉性語義特征。描述性語義成分指在語義內部起描寫、修飾、陳述等作用的內容,是語義結構中表特性的部分,如屬性、特征、關系、動程、特定表現等,可看作廣義的述謂內容,顯現出描述性語義特征。筆者首先對既有本義,又有比喻義的118個詞匯的基本義進行結構分析,并對其比喻義的來源進行判斷。118個詞語的語義分析中,有7個詞語筆者未能進行準確的關涉性、描述性語義的區分。有4個詞語筆者未能準確判斷其比喻義與描述或關涉性語義的關系。為了保證數據的準確,筆者對于結構分析不明確、比喻義與描述或關涉性語義關系不確定的詞語11個詞語不計入最后的數據統計。總結如下表。
107個可以判斷的詞語語義中,有19個詞只有關涉性語義(肌體:指身體),有5個詞語的語義成分只有描述性語義(踐踏:①踩②比喻摧殘)。既有關涉性語義,又有描述性語義的詞語有83個。其中比喻義來自關涉性語義成分的詞語有13個。來自描述性語義成分的詞語數量最多,有49個。比喻義既與描述性成分有關,也與關涉性語義相關的詞語有21個。但是,如果以語義成分中既包括關涉性又有描述性成分的詞語為比照對象,即以83為“分母”進行判斷時,數據占比有較大變化。比喻義來自描述性語義成分占比高達59%,涉及關涉性語義的為15.7%,兩者成分都有的占比較多,為25.3%。
“比喻釋義時往往都將用來作比的事物的特征揭示了出來”,描述性語義成分無論是絕對數量還是相對占比中都占據絕對的地位,足以說明比喻義成分與描述義成分的密切關系。
二、比喻義派生規律
從語音表現形式上看,雙音節詞語數量很大,但是四音節詞語確實最易產生比喻義的。首先,比喻義雙音節詞語的絕對數量很大與漢語詞匯雙音節化發展有密切聯系。漢語詞匯雙音節化是漢語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趨勢,也是漢語發展的必經之路。目前漢語詞匯中雙音節詞匯占比最多,基數大,所以“j”做聲母的詞語中雙音節詞匯以及具有比喻義的詞匯中也是雙音節詞占比最大。第二,具有比喻義的四音節共69個,全部為成語,涉及歷史故事或者典故,或者是選自古文書籍。成語的選擇和形成有明顯的民族特點,所表達的概念外延的大小也有著民族的特點。這些詞語本身就包含一定的民族意味和文化意味,皆帶有某種感情色彩,也為其語義引申產生比喻義奠定了基礎。
從語法角度看,具有比喻義的詞語中名詞數量最多,其次是動詞。語言里每一個詞都是客觀現實的一部分的概括反映。組成這個大千世界的要素有三個:事物與概念、動作與行為、性質和狀態,分別由名詞、動詞和形容詞來指稱。張永言先生在《詞匯學簡論》中提道:人的思維從具體到抽象、從特殊到一般的發展都反映在語言里,反映在詞義的變化里。思維從具體到抽象的發展和從特殊到一半的發展是緊密聯系的,抽象化的過程往往同時就是一般化的過程。而比喻義是抽象化、一般化的某一種最終結果。反推之,如果有出現比喻義的可能性,則這個詞某一意義是偏具體的,偏特殊的,且在人的認知中具有可抽象、可一般的可能性和基礎。從詞類看,名詞通常表示人或事物或時地的名稱,動詞表示動作、行為、心理活動或存現。兩者語義比較明確,而且通常指代具體事物,客觀性較強。相比于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介詞等其他詞模糊性較大,產生比喻義的語義基礎比較薄弱。所以,名詞、動詞兩類詞產生比喻義的幾率更大。詞匯中各個語義之間基本上是有聯系的,而相關詞匯比喻義這種修辭義的產生更需要基于詞匯本身的意義。從語義內部來看,我們采取詞匯語義的中觀分析,相比基本義中關涉性成分,我們發現詞匯比喻意義的產生與詞語基本義的描述義成分有密切關系。
詞義變化的影響因素很多,包括物質文化的變化、人對客觀世界的認知等等,從歷時角度看,“人的思維的發展變化和詞義的發展變化有著直接的聯系”。某一特殊意義的產生也與人的思維有很大的關系,比喻義的產生便是如此。描述義成分是語義中起描寫、修飾、陳述等作用的內容,是語義結構中表特性的部分。施春宏教授在說明描述性語義和關涉性語義時曾提出“關涉成分的類型并不復雜,可以看成是對各種語義成分進行歸類后得到的一些大類”。我們認為相比關涉性的基礎語義,描述性成分是某一詞匯語義中的“區別性特征”,這一區別特征的存在一方面是這個詞語存在的基礎,另一方面也是人們認知和區別的重要手段,所以相比于關涉性語義,描述性語義在實際交流和使用中更為突出。此外,世界萬物之間具有相關性,“關涉成分是相對封閉的,而描述成分有相對開放性”,這一“開放性”也為人們充分聯想并利用提供了可能。所以,人們在對某一詞語利用比喻產生相關修辭義時會選擇更明確,更具有特性的成分,也就是描述性成分。
三、結語
總之,比喻義的產生是語義發展的一種表現形式,比喻義的產生有一定的規律和特點。從語音表現形式上看,雙音節詞語數量很大,但是四音節詞語確實最易產生比喻義的。從語法角度看,具有比喻義的詞語中名詞數量最多,其次是動詞,且兩者產生比喻義的可能性相比其他詞性要大得多。從語法結構看,偏正類詞匯容易產生比喻義,但筆者認為詞語結構類型與詞性息息相關,這種趨勢與名詞數量多有很大關系。除此之外,相比方言詞語,書面語詞語產生比喻義的可能性更大。從語義內部來看,可以發現詞匯比喻意義的產生與詞語基本義的描述義成分有密切關系,在語義既有關涉性成分和描述性成分即情況下,59%的詞語的比喻義成分來自描述性成分。這一規律無論是絕對數量還是相對比例都是符合趨勢的。這一規律施春宏也有明確提出,即“最能體現描述性語義特征的是名詞的比喻義。比喻義揭示的是本體和喻體之間共同的描述性語義特征”。
當然,受材料本身的限制,并沒有做到漢語所有詞語的窮盡性研究和數據統計,且以“j”開頭的詞語統計中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語義判斷也存在一定的主觀性,這些因素都影響著結論具體數字的準確性,但是正如張永言先生所說:“詞匯學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對語言中具體的詞匯現象加以全面深入的研究來闡明關于詞和詞匯的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j”開頭的詞語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數量較多,占比相對也比較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數據及規律的可信度也較高,可以為比喻義派生機制的研究,乃至漢語詞匯語義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和可參考的研究方向。希望以此文“拋轉”,引起更多學者的關注和研究,為語義學、詞匯學乃至語言學的發展提供微薄之力。
參考文獻:
[1]王力.漢語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80.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張永言.詞匯學簡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5.
[4]邵敬敏.現代漢語通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6.
[5]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6]施春宏.名詞的描述性語義特征與副名組合的可能性[J].中國語文,2001,(03).
[7]施春宏.試析名詞的語義結構[J].世界漢語教學, 20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