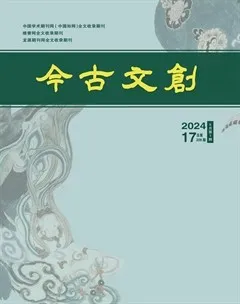聶元松散文中湘西民俗書寫的審美特征
【摘要】湘西作家聶元松的散文創作立足于湘西這一片奇崛而神秘的土地,以湘西民俗為主要創作內容,用詩性的筆調對湘西古老民俗進行生動的還原,飽含深情對湘西民俗進行現代性的反思。聶元松散文的民俗書寫不僅僅停留于湘西民俗的簡單羅列,而是真正實現了民俗與文學的融合,使得散文具有了文化和審美的雙重價值。
【關鍵詞】湘西文學;聶元松;《湘西敘事》;《湘西記憶》;民俗書寫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17-005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7.015
湘西文學自發展伊始,經歷了三次浪潮,第一次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以前,沈從文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一個神奇的湘西世界,描摹出一個自然而準乎人性的生命群體,構筑了一個詩性的精神家園;第二次浪潮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以后至90年代,孫建忠、蔡測海等人緊貼時代脈搏、反映社會變革,開創了湘西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第三次浪潮劃分在新世紀,田耳、于懷岸等湘西第三代作家在接續發展中為湘西文學的發展添磚加瓦。第三次浪潮中雖然缺乏傳世力作,但是一些富有特色的文學作品仍然根植于湘西大地,與湘西大地血脈相連,續寫著沈從文等湘西文學開創者的湘西風格,執著于復活古老的湘西記憶和書寫著新時代的湘西敘事,難掩其文學價值和文化意義的光輝。
鐘敬文在《民俗學概論》中說:“民俗,即民間風俗,指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廣大民眾所創作、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 ①湘西地區深受巫楚文化的影響,又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數民族的聚居地。巫楚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中滋養的這片土地,生長著歌謠、傳說、舞蹈等異彩紛呈又玄奇鬼魅的民俗資源。從湘西文學第一代作家沈從文開始,就在文學作品中自然本能地融入了湘西民俗。當代湘西作家在湘西自然、文化環境的滋養和前輩作家的影響下,接續對地域文化的書寫。
湘西作家聶元松即是不遺余力書寫“湘西之書”的代表性作家,她的散文集《湘西敘事》和《湘西記憶》兩部作品立足于湘西這一片奇崛的沃土,以湘西民俗為主要展現內容,以散文的文體、行走的方式、詩性的筆調詳盡地書寫湘西。她選取鳳凰、茶峒、王村、酉水等湘西富有代表性的地方作為背景,描寫民眾生產生活中所產生的民俗事象,并對其形成進行歷史性的追溯和深層內蘊的挖掘。從其內容來看,其筆下民俗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是豐富絢爛、滲透著湘西人民智慧和心血的物質生活民俗。如華美精致的苗族銀飾,湘西特有的甑子飯、臘肉、菜豆腐、酸蘿卜等,鱗次櫛比的吊腳樓、古老的石板街、古樸明快的馬頭墻、精雕細刻的窗根、曲折幽深的宅院等。二是在歷史的悠悠歲月中生長出的一些與外界特異的歲時節日民俗。如每年農歷的正月初三的為春天祈福的“春會”,土家族“過趕年”等習俗。三是穿越了時間的長河至今仍然在湘西文化的圖譜里鮮活生動的湘西民間口頭文學。如透露出遠古人類文明信息的盤瓠辛女的傳說,一唱三嘆、詳細記述苗族先民遷徙悲壯圖景的史詩《鵂巴鵂瑪》,與土家織錦結合在一起的“織女歌”等。四是異彩紛呈的民間藝術,如講述人類起源、民族遷徙、英雄傳奇的擺手舞,將音樂與舞蹈完美結合的湘西苗鼓舞,還有璀璨的湘西戲曲和絢麗的湘西織錦藝術等。
聶元松散文中包含了湘西民俗的方方面面,她用自己的腳力、筆力保存古老民俗的來龍去脈,再現了湘西民俗的耀眼神光,追問著湘西民俗的命運走向。本文立足文本細讀,結合民俗學的相關方法研究文本,來探尋聶元松散文中民俗與文學文本之間的關系,進而總結其民俗書寫的審美特征、發掘其民俗書寫的審美價值。
一、第一人稱旅人視角的審美蘊含
視角在敘述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不同的敘述視角會產生不同的效果。聶元松運用第一人稱的旅人視角,在散文中,這樣的視角“既可捕捉片段的鏡頭,又能也可以連綴許多鏡頭把畫面串聯起來。” ②聶元松帶著相機跑遍湘西的山山水水,集中書寫仍然存活于湘西民間的物質、精神生活民俗等。十分巧妙地將作者探尋的足跡、文字的記錄、和照片的捕捉交織在一起的,在行走的動態中展示著自己所見所聞所認識的湘西世界,產生了獨特的審美蘊含。
一方面,旅人眼中所見,民俗著作者之眼光。聶元松返回故鄉,以一個尋訪者的姿態行走在湘西的山山水水之間,以一支絢爛之筆和一個多彩的鏡頭為人們展現了湘西世界豐富的民俗畫卷。大家在聶元松的文字中很少看到五四時期鄉土作家筆下所鐘情選取的落后、野蠻的民俗,相反,隨處可見的是美好、詩意的民俗事象。作為湘西之子,她對故土有深厚真摯的情感,她眼中所見、筆下所寫的民俗,實際上滲透了作者真摯強烈的情感。寫到某種民俗的時候,作者總是情不自禁地抒發自己的感慨,或者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將古老民俗的淵源拉到讀者面前。大家從聶元松散文中看到的是經過作家主觀心靈美化的民俗,其間包含著對湘西民俗深刻的認同和熱愛、真誠的保存和守護,以及對民俗不可避免逝去的憂慮和悵然。
另一方面,旅人耳中所聞,民俗更全面而立體。作者在湘西州、吉首市相關領導的支持下,擁有得天獨厚的采訪便利,她尋訪了許多具有代表性的民俗傳承人和堅守者,手藝精湛、重義輕利的銀匠麻茂庭,在錦中織入了自己的生命的土家織錦傳承人劉代娥,癡心不改、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辰河高腔傳承人向榮等等。作者親聞這些傳承人講述民俗文化及他們與民俗文化的故事。因此,除了第一人稱的陳述視角,隨著作者的尋訪足跡的展開,散文中的人物視角也非常豐富。“所謂人物視角就是散文中出現的人物,可以透過他自己的視角來觀物描摹、發言,等等。” ③文章中除了極具作者主觀意識的民俗書寫以外,在作者與傳承人的一問一答之間,第一人稱陳述視角和第三人稱人物視角相遇合,民俗的古往今來和民俗傳承者過去現在的故事交織在一起,使得湘西民俗更加詳盡、清晰、立體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補充了作者第一人稱視角對湘西民俗所見、所感的局限性。
二、民俗空間的美學色彩
民俗與文學不能夠僅僅停留于被承載與承載的關系之上,民俗不只是被羅列的事象,它在文學文本中還能承擔推動情節發展,塑造人物形象,背景的營造、氛圍的渲染等等功能性作用。比如“五四”時期一些鄉土文學作品中寫到水葬、械斗等封建野蠻的陋俗,通過在這些民俗中人們的態度和表現,呈現出愚昧、麻木國民形象;還有沈從文的《邊城》中三次寫到端午節,不僅將湘西地區端午節的具體場景和民俗風貌濃墨重彩地描寫出來了,而且三次端午節也發揮了重要的敘事功能,仿佛串聯起翠翠的整個愛情故事。因為是散文作品,所以許多功能性的作用在聶元松的作品中體現得并不鮮明。但本文把聶元松筆下的湘西世界看作一個民俗文化交匯的空間,這一民俗空間無形中發揮著作用,賦予了聶元松散文無可替代的美學色彩。
一是原始樸野、朦朧神秘的地域色彩。巫楚文化和湘西本土原有的土蠻文化的匯合,使得崇神信巫是湘西各少數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在湘西的許多民俗都是從巫鬼文化中來的。毛古斯的粗獷豪放,梯瑪閃現的神光,鼓舞撼天動地的節奏,辰河高腔所包羅的鄉土狂歡……許多仍然鮮活存在于湘西人民生活中的民俗背后都隱現著人類童年時期的生產生活的投影,涌動著湘西神秘文化的底蘊,作者的呈現將讀者一下拉回原始蒙昧時代中的狂歡氛圍中,給作者的文字蒙上了一層神秘、詭異的面紗。
二是自由浪漫、和諧寧靜的地域色彩。湘西山環水繞、復雜封閉的自然環境孕育著獨特的湘西民俗文化,也成就著特異的文本基調和底色。跟隨者聶元松的足跡,一幅風光旖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水墨丹青徐徐展開:九百里酉水滋潤著兩岸湘西人民的自在生活,也涂抹著豐富的民族畫卷,依山而建的村寨、依山傍水的吊腳樓、悠悠的石板街,河谷里回蕩著或雄奇粗獷、或舒緩多情的酉水號子,山間蕩漾著攜帶著泥土芬芳的苗家山歌……這些文學景觀出現在散文的字里行間,也連同湘西的山山水水、亭臺樓閣,一同浸潤著聶元松的文字,呈現著自由浪漫、和諧寧靜的地域色彩。
民俗滲透在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為地域文化中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反映著特定地域、特定時代的人文風尚和社會面貌。聶元松散文不遺余力地書寫湘西民俗,一方面起到了保存和延續湘西民俗的作用,另一方面這一民俗空間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聶元松散文特異的地域色彩。
三、民俗風情與自然人性的審美呈現
湘西文學發展的三次浪潮層次分明、特點各異,但是也具有一定內在的連續性和核心特質的恒常性。湘西文學中,自以啟山林的沈從文開始,他“繼承和代表的是古代湘楚尊重自然人性、歌頌原始的旺盛生命力、崇尚傳統道德境界的浪漫主義文學傳統。”潛心構筑了人性的“希臘小廟”,塑造了一大批至真、至善,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態。《邊城》中天真淳樸的翠翠,重利輕義、樂于助人的老船工,樂善好施、通情達理的船總順順,《柏子》《龍朱》《虎雛》中一個個充滿原始野性、生機勃勃的生命等等。到了湘西文學第三次浪潮的聶元松這里,她的創作深受沈從文所開創的浪漫主義文學傳統的化育,將湘西民俗風情的書寫與自然人性的描摹緊密結合在一起,也呈現出一些寧靜淳樸生活中躍動的美好人性。
一方面,作者書寫的湘西傳統民俗映射著湘西人的本色與品格。聶元松在展示民俗的同時,試圖通過民俗的表象去追尋其背后涌動的深層民族精神、心理特征。費孝通在《鄉土中國》寫道:“文化是依賴象征體系和個人記憶而維持著的社會共同體驗,這樣說來,每個人的‘當前,不單包括他個人‘過去的投影,而且是整個民族的‘過去的投影,歷史對于個人不是點綴的飾物,而是實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礎。” ④聶元松從湘西人在艱險的山水環境中創造出來的干欄式建筑“吊腳樓”這一民俗中,發掘到了湘西人民的智慧和勤勞;從擺手舞、毛古斯、梯瑪等早期的民俗文化遺存中看到了土家人民高揚的生命意識,自由、雄健的性格和執著的生命追求;從震天的“八合鼓”鼓聲中聽到了“湘西苗家人靈魂深處自然而質樸的生命本性” ⑤;從歷史遺留的點將臺、射擊場等地名中找尋到了湘西人民勃勃的生命強力和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
“作為人類邁向文明的伴生物和人類生活的永恒伴侶,民俗從人類童年時代即開始構建,歷經漫長歲月,在那些大量的具象背后,早已層層疊疊累加著人類心理、情感的積淀,從而成為‘民族精神的標記。” ⑥在聶元松看來,湘西民俗不僅僅是民俗,更是千百年來湘西人民坎坷歷史的隱喻,是湘西人民一脈相承的精神、性格的承載,民俗連同民俗背后的隱喻和承載穿越了時間與空間而經年不息、世代相襲。
另一方面,與民俗息息相關的傳承人身上看到了自然人性的光輝。聶元松寫到的傳承人大都經歷過動亂歲月的磨洗與歷練,都面臨著發展艱難的困境,以及傳統技藝后繼無人的現狀。但他們仍然執著追求手藝的精湛,孜孜以求探尋古老民俗和融入當代精神的最好銜接。藍印花布手藝人劉大炮為人爽朗、剛直,擁有天才的印染絕技和絕佳的創意。碰到真心喜歡自己作品但不寬裕的大學生,劉大炮連賣帶送將作品給了遠方的顧客。對于想學手藝的外人,他從來都是免費。在唱苗歌的人越來越少,價值越來越高的市場上,丹青苗歌傳人陳千鈞仍然堅持一天只收100元,平時比賽拿了獎金也是多半請同去的人吃飯了。因為歌藝好,人隨和,被大家尊稱為“歌王”。梯瑪的傳承人彭繼龍說梯瑪不僅要給四里八鄉的人治病,還要解決鄰里糾紛,他認為“做一個梯瑪,首先要做一個好人,只要有人來請,不管有錢沒錢,不論地位高低,都要去。”我們從這些執著堅守、講情誼、重利輕義的傳承人身上似乎嗅到一絲熟悉的氣息,他們仿佛是《邊城》的里老船工、船總順順,也是《長河》里的果園主,然而最主要的,他們身上都是隱現著健康、淳樸、自然的湘西文化血脈和人性基因。
四、結語
湘西相對封閉的環境,被時代遺忘的落寞,使得民俗文化的碩果在湘西這片土地上得到良好的呵護并仍然蓬勃鮮活。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湘西一些古老的民俗在人們生活中退居其后,其重要的文化意義也逐漸消減,聶元松的足跡和筆力卻能夠返回家鄉奇崛的土地,耕耘在湘西民俗的田野,她用豐厚的人文情懷,豐富、詳盡的民俗文化知識,打開了一個向世界展示湘西的窗口,對世界認識真正的湘西起到積極作用。并向時代發問:當在物質文明強勢入侵的時代,民俗應該走向何處?這是難能可貴的。因此,不僅僅是文章中提到的一個又一個用生命堅守的傳承人,實際上,聶元松也用自己的方式守護著湘西的民俗文化。她用散文的方式,保存著湘西民俗的古往今來、制作過程,連同民俗背后的可貴精神一同凝結成文字的琥珀,她的書寫必將超越民俗和文學本身而具有經久流傳的價值。同時,作者將湘西的民俗畫卷和自我的審美情感融為了一體,為我們留下一個歷史悠久、風情獨特,又注入了時代內涵的新湘西形象,為“文學湘西”“文化湘西”的構筑貢獻出散文力量。
總之,聶元松散文中既全面豐富、頗具針對性地描寫了湘西民俗,又巧妙地將民俗與文學相融合,用詩意的筆調展現民俗,多彩的民俗又成就著聶元松散文特異的藝術風格,使得聶元松散文的民俗書寫兼具了審美和文化的雙重價值和意義而獨樹一幟。
注釋:
①鐘敬文:《民俗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
②鄭明娳:《現代散文理論墊腳石》,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5頁。
③鄭明娳:《現代散文理論墊腳石》,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9頁。
④費孝通:《鄉土中國》,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頁。
⑤聶元松:《湘西記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9頁。
⑥聶元松:《湘西敘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頁。
參考文獻:
[1]鐘敬文.民俗學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2]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張永.民俗學與中國現代鄉土小說[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
[4]聶元松.湘西敘事[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5]聶元松.湘西記憶[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
[6]鄭明娳.現代散文理論墊腳石[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7]段建軍,李偉.新散文思維[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6.
[8]烏蘭其木格.喧嘩中的諦聽[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9.
[9]吳正鋒,申艷琴.湘西文學的“第三次文學浪潮”[N].湖南日報,2012-12-04(02).
[10]張創弘粹.新世紀以來湘西作家小說創作研究[D].廣西大學,2022.
[11]楊倩雯.湘西青年作家群創作特征研究[D].長沙理工大學,2016.
[12]彭文海.繼承與探索:湘西青年作家群創作考察[D].吉首大學,2014.
[13]吳正鋒.民族民間藝術的堅守與傳承——讀聶元松《湘西記憶》[J].創作與評論,2015,(16):53-56.
[14]梁瑞郴.用真情詮釋山水人文經典——聶元松《湘西敘事》觀后[J].民族論壇,2011,(23):62-63.
作者簡介:
姜文臣,土家族,湖南湘西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現當代多民族作家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