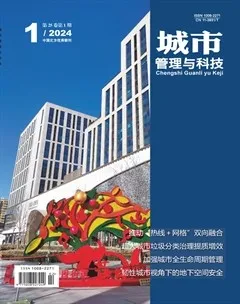生活源廢玻璃產生與回收情況分析
黃家慶?趙長驍?肖勇之?李歡
一、引言
玻璃一般被認為可以百分百回收而不損及質量或純度,因此玻璃的循環利用對于碳中和具有重要價值。在全球范圍內,玻璃制造業每年至少排放8600萬噸二氧化碳。然而,當廢玻璃被回收時,可以抵消其中大部分碳排放,現有技術可以將玻璃制造變成一個近零碳的過程。廢玻璃的來源包括生活源和工業源。生活源廢玻璃產生分散,收集成本高,其回收利用相對工業源廢玻璃難度更大。我國是玻璃生產大國,出口了全球28.7%的玻璃和玻璃制品;同時,廢玻璃也是我國十大再生資源品種之一。根據商務部再生資源統計數據,2019年全國廢玻璃產生量約2123萬噸,廢玻璃回收量約984萬噸,回收利用率為46.4%。根據《中國再生資源回收行業發展報告2022》中的數據,2021年全國生活源廢玻璃產量為1006萬噸,占廢玻璃總產量的44.2%;廢玻璃回收量為273萬噸,回收利用率為27%,顯著低于工業源廢玻璃的回收利用率。然而,在瑞典、德國等發達國家,生活源廢玻璃回收率接近90%。因此,我國生活源廢玻璃的回收亟待加強。
深圳市作為我國開展垃圾分類的領先城市之一,目前已建立了生活垃圾的八大分流分類體系。深圳市將生活垃圾中的可回收物進一步分為廢玻璃、廢金屬、廢塑料、廢紙四類。近年來,深圳市的玻璃回收量逐年增長,但仍然面臨一些挑戰。本研究對深圳市不同場所的生活源廢玻璃產生規律進行了調研,構建了近幾年生活源廢玻璃的物質流,分析了廢玻璃資源化的現狀、潛力、目標和實現路徑,以期為制定配套法規、政策和制度提供參考。
二、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2019—2022年,本研究課題組對深圳市6個物業小區、5個城中村以及多個企事業單位、商業場所和公共區域的生活垃圾產生情況進行了多次調研,分析了不同源頭的廢玻璃產生規律,同時收集了城管部門、商務部門對廢玻璃回收量的統計數據。其中,生活垃圾組分參照《生活垃圾采樣和分析方法》(CJ/T 313—2009)進行分析。
(二)物質流分析
物質流分析可通過系統集成和全過程優化實現管理協同,支持資源循環利用和再生利用相關政策的制定,還可以用于系統資源利用效率評估、實質性資源替代潛力預測、資源利用途徑選擇等方面。生活源廢玻璃主要有三個流向,一是經再生資源系統收集并進行利用,二是作為“可回收物”中的一類組分經環衛作業系統收集并進行利用,三是在“其他垃圾”類別中與其他垃圾一起經環衛作業系統收集并送入焚燒廠或填埋場。本研究采用物質流分析了生活源廢玻璃經再生資源系統與環衛作業系統收集后的流向。首先,計算廢玻璃從垃圾桶流向環衛作業系統“可回收物”和作為“其他垃圾”轉運站的廢玻璃數量;其次,統計從住宅區和辦公區流入再生資源行業的廢玻璃數量;最后,分析焚燒廠和回收廠接收的廢玻璃數量。
三、結果與討論
(一)廢玻璃在生活垃圾中的占比
根據實地調查,綜合各類源頭的生活垃圾產生量占比和組分情況(垃圾排放的情況,而不是分類投放的情況),可以獲得2022年全市垃圾的總體組成;根據各焚燒處理廠進廠垃圾(車輛進廠后直接檢測,非儲坑存放后的垃圾組分)的組分調查,可以獲得末端設施的生活垃圾組成,結果如圖1所示。可以看出,在源頭,廚余垃圾占比最高(包括家庭廚余垃圾、餐飲垃圾和果蔬垃圾等),為37%。可回收物占比較高,其中廢玻璃約為4%。在末端處理設施(焚燒廠)的進廠垃圾中,廚余垃圾比例為41%,這說明在廚余垃圾分流的同時,還有更多的可回收物進入再生資源系統或被環衛系統分類收集。在可回收物中,紙類、金屬、家具的占比明顯減少,這是因為這些可回收物更容易識別,而且市場價值相對更高,容易在投放、收運過程中分類分流。相對地,織物、橡塑的比重增加,說明這些低值可回收物或者污損的可回收物會留在“其他垃圾”中,進入末端處理設施。在廚余垃圾、其他可回收物被分流的前提下,進廠垃圾中玻璃的占比仍略有降低,說明有部分生活源廢玻璃已經被回收,這與深圳市持續加強廢玻璃回收工作有關。
(二)不同源頭廢玻璃產生量與分出量
在調研區域,近幾年各垃圾產生源頭的廢玻璃產生與回收情況如圖2所示。其中,居住區的廢玻璃回收量為居民分類投放量;辦公區和商業區的廢玻璃回收量為環衛作業系統與再生資源系統各自收集量之和;“其他垃圾”桶中的廢玻璃為未分出量,回收量與未分出量之和為廢玻璃的產生量。根據這一結果,不同源頭廢玻璃的產生量與回收情況波動很大。總體來看,辦公區廢玻璃產生量不高,但回收率最高,平均為51%(各調研地點回收率的平均值,下同),其原因是辦公區的廢玻璃通常由物業保潔人員直接管理,可以集中送給回收商。居住區的廢玻璃產生量最多,但回收利用率波動很大,平均為30%,主要依靠環衛工人回收。在公共區,主要人口為流動人口,基本沒有開展玻璃回收工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醫院這類公共區域會產生較多的廢玻璃,除部分屬于醫療垃圾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屬于生活垃圾,也未分類收集,而是進入了生活垃圾焚燒廠。

(三)深圳市生活源廢玻璃物質流
根據上述結果可以推算2019—2022年深圳市生活源廢玻璃的物質流。生活區不區分環衛作業系統與再生資源系統收集的廢玻璃。辦公區和公共區再生資源回收總量經測算分別為408 噸/天和72 噸/天。根據深圳市統計數據,工作區就業人口為1 193.4萬,居住區常住人口為1 766.2萬,公共區估算得到平均流量1 052.9萬人次/天。如表1所示,深圳市居住區廢玻璃每天產生總量為380.26噸,辦公區廢玻璃每天產生量為467.67噸,公共區廢玻璃每天產生總量為236.88噸,深圳市生活源廢玻璃每天產生量為1084.81噸。

深圳市日均生活源廢玻璃物質流如圖3所示。目前,深圳市已實現生活垃圾全量焚燒。生活源廢玻璃中通過再生資源與環衛作業分出的部分直接回收利用,余下的和生活垃圾協同焚燒。由物質流分析可知,深圳市整體廢玻璃回收率為62.50%,廢玻璃回收量主要來源于再生資源回收系統,再生系統回收量占整體回收量的70.79%。其中,辦公區回收情況最佳,回收率為92.24%,每日408噸廢玻璃由再生資源直接回收,23.39噸流入環衛作業,36.28噸流入焚燒。居住區回收情況其次,整體回收率為42.68%,余下217.95噸流入焚燒。商業區回收潛力最大回收率為35.60%,152.59噸廢玻璃進入焚燒,12.32噸流入環衛作業,72噸流入再生資源。全市廢玻璃回收潛力為406.79噸。
(四)生活源廢玻璃管理建議
生活源廢玻璃的回收不僅可以提升資源的循環利用效率,還可以降低焚燒處理負擔、減少灰渣產生量,因此對于生活垃圾管理具有兩方面的效益。

玻璃容器回收率高的國家,廢玻璃回收大多被納入城市固廢回收的相關立法中,并通過押金制度等強制執行。以德國為例,德國政府早在1991年就頒布了《避免和利用包裝廢棄物法》,規定對使用不可再生材料制成的礦泉水瓶、啤酒瓶和軟飲料瓶實行押金制度。深圳市可以借鑒德國的經驗在居住區試點實施飲料瓶押金制度,針對不同類型的飲料瓶制定不同的押金標準。在試點區域設置自動回收機,居民可以直接使用回收機退還飲料瓶,獲取押金退款。

對于使用玻璃容器的消費品生產企業,深圳市可以通過實施生產者責任延伸制來減輕政府的回收負擔,讓生產企業承擔一定的責任。生產企業可以利用押金制自建或者委托第三方建立玻璃容器回收網絡,并給回收企業提供一定的資助。由于生活源廢玻璃回收成本較高而銷售價值較低,針對開展廢玻璃回收的企業或組織,政府也可以給予一定的補貼。在上述體系下,消費者、生產企業、回收企業和政府鏈接起來,共同構成了廢玻璃回收的網絡。同時,還需要明確監督機制,確保回收企業真正履行責任。還應繼續加大宣傳力度,如在學校和社區持續開展分類回收的宣傳活動,提高居民對玻璃回收的認知。
四、結論
深圳市生活垃圾中廢玻璃約占4%,在進入末端焚燒廠的垃圾中約占3%。辦公區廢玻璃回收較好,而公共區相對薄弱,居住區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深圳市每天產生1 084.81噸生活源廢玻璃,其中通過環衛作業系統和再生資源系統回收了678.02噸,廢玻璃的整體回收率達到了62.5%,處于較高水平。為了進一步促進廢玻璃的回收,關鍵在于提高居住區廢玻璃回收率,可以試點實施飲料瓶押金制度,落實生產者責任延伸制,給予廢玻璃回收企業適當補貼,構建四方協作的回收網絡。
參考文獻
[1]EID J. Glass is the hidden gem in a carbon-neutral future[J]. Nature, 2021, 599: 7.
[2]中國物資再生協會. 2020年中國再生資源回收行業發展報告[R]. 2022.
[3]中國物資再生協會. 2022年中國再生資源回收行業發展報告[R]. 2022.
[4]HUANG C L, VAUSE J, MA H W, et al. Using material/substance flow analysis to suppor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sessment: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outlook[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12, 68: 104-116.
[5]GUO D F, HOU H M, LONG J, et al. Underestimate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tailings resource utilization: Evidence from a life cycle perspective[J].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2022, 96: 106832.
[6]AZEVEDO B D, SCAVARDA L F, CAIADO R G, et al. Improving urban household solid waste manag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ased on the German experience[J]. Waste management, 2021, 120: 772-783.
(責任編輯:張秋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