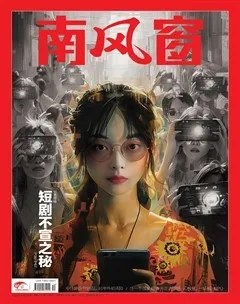短劇出海,叫板網飛?
譚伊妮

羅馬尼亞時間3時55分,短劇制片人梁蘭所在的劇組終于收工。她打開微信,群里爸媽正在曬自己的早飯,問她:下工沒?
在這三個月里,這樣的問候幾乎每一天都會發生,尤其是5月份。那時,梁蘭手頭三個海外短劇項目開機,選角、勘景、找服裝,她忙得腳不沾地,可以與父母聯絡的時間少之又少。
累是累,但看到銀行卡里不斷增長的數字,以及項目上線后評論區里海外觀眾的夸贊,梁蘭又覺得“很值”。
“很值”背后指向的,是這場從去年開始席卷全球的短劇浪潮。SensorTower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2月底,已有40多款短劇應用試水海外市場。單是短劇平臺ReelShort,就在去年11月一度超越TikTok,登上美國iOS娛樂榜首。
人海潮涌中,30歲的投資人高祥晨也離開了老本行,一頭扎進短劇賽道,在去年成為美股上市公司Mega Metrix Corp.(NYSE:MPU)的首席運營官,并主導了短劇平臺FlexTV項目的并購整合。
賽道很重要,高祥晨預測,3年內短劇賽道或將產生百億美元平臺。
就像拼多多之于亞馬遜,TikTok之于Facebook,人們熱切希望下一個成功出海的商業項目從短劇賽道誕生,成為短劇界的網飛(Netflix),挑戰網飛。
但問題在于,現有的短劇生產運營模式,能滿足一個全球性的短劇平臺的饕餮胃口嗎?
短劇平臺,爭相出海
落座五分鐘了,對面的高祥晨身穿灰色T恤,依舊低頭回復著工作消息。
為什么會想到打出“拼多多版網飛”的旗號?
聽到我的問題,他抬起頭,反應略顯遲鈍,有種大腦被強制開機的滯澀感。可以理解,今年1月成功收購FlexTV后,高祥晨和團隊重點發力北美市場,提出今年至少做100部原創劇的計劃,這意味著每個月他們平均要出9部短劇。
整個上半年,高祥晨和團隊忙著上項目,各地跑,想趁著市場早期把量堆上來。也因此,我跟他約時間變得分外艱難,溝通時間花了一周多,本定在周二 上午,卻因臨時突發會議被推遲到了周四下午。
這樣的狀況放在海外短劇人身上似乎是常態。時間就是金錢,所有人都在高速運轉,就像自轉永不停歇的陀螺。高祥晨告訴我,近半年他幾乎沒有怎么休息過。
而撥動陀螺的鞭子,是海外用戶“熱情”的反饋。SensorTower數據顯示,2022年頭部短劇出海平臺下載量/凈流水僅4.4萬次/2.0萬美元,到了2023年,數據膨脹為2823萬次/5671萬美元,實現爆發式增長。

進入2024年后,中國短劇平臺在海外的最佳成績不斷被刷新,多點開花,有的在中國臺灣地區連續七天霸榜iOS娛樂榜第一,有的在日本iOS娛樂類目暢銷榜超過網飛,還有的同時拿下美國iOS和谷歌商店免費總榜的桂冠。
超越網飛是短暫的事實,而把短暫變成常態是短劇出海平臺們熱切的期望。與市場增速放緩、競爭格局基本穩定的國際長視頻相比,短劇出海市場規模增長迅猛,市場潛力空間也更大。
SensorTower數據顯示,短劇出海市場近半年熱度驟增,相比2023年9月,2024年2月內購收入和下載量分別增長280%和220%。
今年3月,在微短劇創新發展與國際傳播論壇上,點眾科技海外業務負責人吳克雷公開表露對短劇行業未來發展的看好態度,認為中國微短劇將成為全球第五個文化現象,并預測2027年海外微短劇市場規模能突破100億美元。
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何天平看來,短劇的內容形態既碎片化又有一定的故事完整性,其強敘事情節很容易跨越文化障礙,給海外觀眾提供直觀而充分的情緒價值,比如打臉、逆襲、浪漫愛情等“爽”感元素。
這種情緒價值是人類共通的需求,在過往的長視頻敘事中未能被充分滿足。具體而言,網飛、迪士尼等平臺拍攝了很多講律師、醫生的行業劇,面向的是中產以上的群體。
而短劇平臺的用戶群體更下沉,口味需求更細分,觀看目的性更強,平臺的任務應該是讓用戶不用思考就覺得很爽。這也是高祥晨把MPU旗下短劇平臺FlexTV定位為“影視界拼多多”的原因。
以北美市場為例,數據顯示ReelShort在美國市場擁有與網飛不同的核心用戶群。
兩者在用戶畫像、熱衷的移動應用和喜愛的廣告類別上差異顯著,ReelShort的中老年女性用戶占比較高,尤其是美國安卓用戶中女性用戶高達70%。
自去年11月ReelShort數據迎來爆發式增長,海外短劇行業的這一波熱度,迄今也才半年左右的時間。
今年1月成功收購FlexTV后,高祥晨和團隊重點發力北美市場,提出今年至少做100部原創劇的計劃。
整體來看,除了頭部的幾款產品開始探索產出進一步的本土化內容外,大部分入局者仍然處在搬運和簡單加工國內現有作品的初級階段,產出的內容數量也無法與國內相比。
FlexTV的CEO曹振軍認為,海外短劇賽道已經邁過試錯階段,進入快速增長階段,后面還將分為兩個階段:找到全球不同國家用戶對內容需求的共同性,和挑戰網飛,或者起碼占領網飛的一部分市場。

打造下一個網飛
縱觀歷史上多數行業巨頭的崛起,都離不開客觀的時代條件,都免不了市場競爭格局從分散走向集中的演變,網飛如此,短劇也應如此。
何天平表示,網飛的崛起和模式都很特殊,短劇賽道誕生全球性平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要像網飛這樣在全球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都產生潛在影響,幾乎無解。
辯證來看,依托長視頻的網飛和依托短劇的FlexTV,兩者在內容和商業模式上有一定的相似之處,比如都是講故事,都要做用戶的長線留存,都是走訂閱制付費,但兩者的底層邏輯完全不同,不具備一起討論的條件。
“短劇的播出效果取決于內容質量和投流,很難靠內容本身贏得口碑,從而獲取流量,”中國青年劇作家、導演向凱說,“長視頻則不然,內容力更強。”
因此,比起短劇賽道是否能出現下一個網飛的問題,討論短劇賽道是否能出現一個持續性吸引觀眾的全球性流媒體平臺,更為合適。
何天平認為,微短劇在行業中已確立其與傳統連續劇不同的業態獨立性,但更多效果是建立在對底層欲望的撩撥上,沒有構成相對完整的文化審美、市場和政策規范,內容生態暫且不是很成熟,很難現在給出行業巨頭誕生可能性的定論。
此外,海外市場廣闊,有60多億人口,但它有190多個國家,人口分散,語言和文化差異都很大,眾口難調。
從這點來看,短劇似乎很難做到像長視頻那樣輻射更大的圈層,至少看慣長視頻的用戶多數難以接受短劇的無厘頭和快節奏。
微短劇更多效果是建立在對底層欲望的撩撥上,沒有構成相對完整的文化審美、市場和政策規范,內容生態暫且不是很成熟,很難現在給出行業巨頭誕生可能性的定論。
但機會是存在的,一位有著十多年宣發與投資經驗的影視從業人員告訴南風窗,他們正在開發類似的出海項目。
生態的不成熟直觀體現在用戶留存上。比起長視頻,短劇短板明顯,隨著“刺激模式”的不斷重復,受眾的認知敏感度將逐步呈現邊際遞減的趨勢。
就像你我下班回家后,刷一部霸總劇尚且能被刺激,但刷了十部類似套路的短劇后,我們能獲得的快感越來越有限,但又沒有新的刺激補上,APP就會在浩瀚的手機應用商場中被遺忘。
根據點點數據,TikTok的30日留存率為29.8%,網飛為14.4%,網文平臺GoodNovel為7.5%,而ReelShort的30日留存率僅為2.4%。對此,ReelShort北京公司總經理南亞鵬曾回應:“是產品起步階段的正常情況,現在成本高,量不夠大。”
上新速度是一方面,內容題材同質化又是另一方面。由于短劇的爽感很大程度來源于“逆襲—打臉”的敘事,大框架不能變,而探索新敘事風險高,攝制團隊就只好在細節方面做微創新,但這樣刺激不夠,難以留住用戶。
稱霸全球前的三道坎
放眼長遠,何天平教授洞察到,要在短劇領域打造出一個全球性平臺,關鍵在于大幅提升內容產量和豐富度,這無疑對平臺的資金實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高祥晨對南風窗表示:“未來一兩年內,短劇平臺間差距或將變得顯著,屆時進入市場的壁壘將大幅提升。無論是APP產品運營、內容質量還是市場投放,都不能有任何短板。每年數千萬美元的內容投入,是參與競爭的基本門檻。”
這種判斷源于內容行業最底層的邏輯,即生產優質內容,吸引消費者付費訂閱。無論網飛還是諸多短劇平臺,都基本遵循這個模式。
盡管與網飛這樣制作成本動輒幾千萬美元的長視頻劇集相比,海外短劇成本更為低廉,只需要10萬到20萬美元,但由于海外短劇市場尚未成熟,整體爆款率低,且短劇本身一次性精神消耗品屬性明顯,為了留住用戶,前期燒錢大肆鋪量是平臺不可避免要做的事情,多數制作方仍處于“戰略性虧損”階段,難以獲得豐厚的回報。
而目前國內短劇行業面臨的成本水漲船高、投流效果越來越不理想、爆款率在變低的疲弱狀態,已成為海外短劇平臺的前車之鑒。
以ReelShort所屬的楓葉互動為例,盡管去年營收同比增長87%,達到6.86億元,但凈利潤僅為24.42萬元,總負債高達3億元。
不堆量的后果是,在手機下載榜單的排名忽上忽下,流水并不穩定,畢竟當平臺短劇庫存過少時,用戶刷完所有感興趣的內容,自然不會打開APP和續費。
現在海外短劇市場的監管環境很寬松,但考慮到地緣政治等問題,平臺做大后或許也將難以避免相關風險。
也因此,短劇平臺的爭奪戰,也是資金實力的比拼戰。提效降本成為業內最迫切的需求。梁蘭回憶,在出海的早期,很多短劇平臺由于不敢激進冒險,無法下定決心砸錢創作更多海外本地內容,大多通過AI換臉、國產短劇翻譯等方式試水,畢竟海外短劇攝制成本更高,且回報未知。
其中,AI技術是大家討論較多的策略,例如 AI換臉、AI翻譯等,也可以通過大數據的分析,讓平臺更精確捕捉受眾的收看習慣和偏好,以此來對其進行改進,提高其黏性。
高祥晨覺得這是一個趨勢,但現在AI還不能直接應用到短劇的拍攝,因為海外觀眾對作品質量還是有比較高的要求。“后續如果它的技術更加成熟,或者有一些更好的應用場景,它肯定可以替代一部分的拍攝需求,或者說在對質量要求沒那么高的情況下,它可以補充一部分產量。”
另一點值得探討的是短劇內容本身的提高。目前的豎屏微短劇有很固定的模式,一集1~2分鐘,結構是“開頭吸睛、兩三個沖突、一個鉤子”,敘事上也多承襲“逆襲—打臉”的套路。
這種形式固然可以最大效率促進用戶的付費轉化,但也限制了內容創作本身,容易造成同質化,那么是否可以拓展更多元講故事的方式?比如延長一集的時間,讓敘事更加飽滿。
人工智能技術加速發展的背景下,何天平認為,IP作為微短劇產業鏈核心資源的重要性將日益突出。打通微短劇同網文、長視頻等跨類型內容深度融合的產業鏈,納入游戲、文創等全模式開發衍生形態,對培育微短劇“出海”具有現實的促進作用。在國內,短劇+互動、短劇+文旅近年已經有一定成果。
短劇出海還需要構建一個健康的生態系統,與當地的內容創作者、制作公司、發行渠道以及廣告商等建立合作關系,實現共贏。這不僅有助于短劇平臺獲得更多資源和支持,還能更好地融入當地市場,實現本土化發展。
不過,與全球各地優秀的本土化團隊合作,也涉及當地的平臺和內容監管等問題,現在海外短劇市場的監管環境很寬松,但考慮到地緣政治等問題,平臺做大后或許也將難以避免相關風險。
整體來說,短劇出海,道阻且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