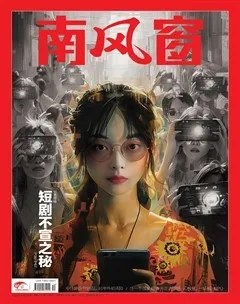高學歷的年輕人,自愿“下放”農村
張渝

在英國讀完碩士,蘇喬回來北京實習,她用壓抑來形容這段經歷。
在她看來,匯集了許多“大廠”的北京,每天的上下高峰時期地鐵都超負荷運載。她形容,到了晚上10時,海淀區的寫字樓上燈火通明,每一棟樓的樓下都排滿出租車,等待著下班趕不上地鐵的白領們。
在北京,高學歷高技術人才太多了,蘇喬只是他們當中的一員。蘇喬在體驗了這樣的生活之后感嘆:“我讀那么多書,賺那么多錢,就是為了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
蘇喬在求學階段,參加過一些鄉村類公益項目與組織,在北京實習之后她選擇了參加廣州銀林生態農場實習生項目,去到一個跟自己完全沒有關系的村莊學習種地。
選擇回去的原因有很多:其一是彼時的蘇喬已經走向獨立,她只希望有收留她的地方;其二則是學習人類學的蘇喬認為,自己從本科以來一直對鄉村問題的關注與實踐太過于淺薄,她想真正進入田野從事生產。
銀林村位于廣州市接近清遠的邊郊從化區,距離市區天河區有50公里遠。在這個地方,有大量的外來村民聚集務農。蘇喬粗略統計有40—50戶。這些“新村民”有的在銀林農場做實習生,有的在獨立農場務農,有的單純在此定居。他們過著社區化的生活,經常聚餐或進行羽毛球等體育活動。
蘇喬形容,他們想要過一種集體化生活,在追求心目中的大同社會。
實習農民
真正把腳踩進泥土里后,蘇喬意識到,她之前農村工作經驗是完全脫離生產的、不管用的。
在來到銀林農場的那些日子里,蘇喬過著朝六晚六的生活。銀林生態農場主要運營模式為種植生態農產品并發到線上售賣。蘇喬的工作內容就是負責種植這些農產品。
最初,蘇喬形容自己的工作狀態不能用手生形容,簡直就是眼生。當農場指導的農民吩咐她拔掉一根雜草,蘇喬卻把菜苗給拔掉了。在往后的一個月里,蘇喬都經歷著一個適應的過程。而農場里鬧出這樣笑話的遠不止蘇喬。
自然與鄉土不會給城市知識分子們慢慢適應的機會。
同樣是來到銀林農場工作的張華,也曾鬧出失誤,即使在此之前他已經在其他農場實習過。
沒有經驗的蘇喬失誤在生產端上,而已有經驗的張華則失誤在銷售端上。
張華在銀林農場工作期間,農場試種很多不同品種的番茄,從質感上分有硬果番茄和軟果番茄,前者適合快遞,后者只能活動采摘或現場購買。
有一次需要打包番茄發售時,由于正常用于發貨的硬果番茄數量不夠,所以張華錯把軟果番茄發給客戶,番茄在途中相互擠壓爛掉了,后來才知道這個品種不能用于快遞。
后來,銀林農場就再沒種這種軟果番茄了。
在銀林農場時期的張華,已經在農業生產上有一定經驗,但他在第一份農場實習經歷里,也會鬧出蘇喬這種失誤。
當時,初來乍到的張華,并不能分清楚什么是除草劑,什么是除蟲劑。當農場里同事讓張華使用殺蟲藥時,他卻把這些除草劑錯當成殺蟲藥噴在了瓜田上,最終換來了農場的損失與農夫們的斥責。
從城市來到田野的實習生們,對土地抱有美好的幻想,但是其生活經歷并不能支撐他們很快上手農業生產生活。
談到適應期的經歷,銀林村的新村民們大都一笑帶過,正如張華所說,“成長嘛,總需要代價”。
銀林村新村民
在結束銀林生態農場的工作后,一心進入鄉土的張華,決定要在銀林村租房子創造自己的農業生活。朋友給他介紹一間家具齊全、價格公道的房子,但是對于手上拮據的張華來說,房子的租金仍然顯得昂貴。
這個群體里,大家的交易往往跳過了貨幣,選擇用最原始的一物換一物。張華經常用他種植的番石榴換取面包和大米,這種交易形式能夠減少對他自身能量的損耗。
張華站在房子門口的樹木底下猶豫著,彼時,一只紅嘴藍鵲飛到了他頭上的樹木嘰嘰喳喳地叫著。張華看見紅嘴藍鵲后馬上打電話給房東,定下了這個房子,開始他的銀林生活。
這是張華第二次在銀林村見到紅嘴藍鵲了。他自小就喜歡與昆蟲、小動物接觸,第一次是在當實習生晚上夜觀時候。當時他看到一大群飛起來,從此他認定了這就是他想要的生態生活。時至今天,一些平常的夜晚里,張華有時候都會夢見紅嘴藍鵲,這是他的幸運鳥。
從那之后,張華便在銀林村定居,并租下一塊地與合伙人經營自己的農場。后來經過商量合伙人轉行,這個農場自然屬于張華自己經營了。在最初定居期間,他也面臨著如何融入銀林村的問題。
鄉土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當陌生人突然闖入這片都是近親老友的土地時,總需要面對與本地人理念、生活習性等方面上的不統一。
張華極度推崇原生態的理念,這使得他的農場雜草叢生。不理解他的觀念的本地人,可能認為他是一位懶人。
張華的農場與一位本地人的農場相鄰,他的農場過道長滿了草,使那位本地人難以行走。后來一天,張華去打理農場時發現,雜草很整齊地消失了。
張華猜測,這是對過道使用了除草劑,這對于他來說完全觸碰到了底線。當天他馬上找到村民理論,挑明“割草這些分外事可以,但是他不能接受有除草劑出現在他的農場里”。
事實上,這種公共空間與私空間的界限之爭,更像是兩種觀念的碰撞。它也不只是在張華身上發生。
在銀林村定居初期,蘇喬狀態不好,想出去遛狗放松心情。但是一打開門,她發現門口的路被鄰居家因下雨而回收后暫時堆放的香水檸檬鋪滿了;好不容易騰出一些空間走出去,蘇喬隨即去找鄰居要求其收回香水檸檬。在鄰居答應的半個小時后,蘇喬再次回家發現自己路上的香水檸檬仍然在那。現在回憶起,她覺得“挺欺負人的”。
“這個地方是我的,我讓你們放這里了你不謝謝我沒關系,但是最起碼得打聲招呼吧?”蘇喬在電話里對著她的房東發火。最終,由于這批香水檸檬是附近很多本地人一起晾著的,蘇喬與本地人之間鬧得不歡而散。
這樣私人空間被無故霸占的事例不少,有時候,村民會把車停在她的家門口。遇到這些事情,蘇喬都選擇在公共空間里直接用嗓門向鄰居討要說法。
最讓蘇喬受不了的是,當她大門開著的時候,有時村民就來串門社交。她還是希望互相擁有私人空間,進門前應該得到對方的邀請。
在這種爭吵中,原村民們逐漸理解了張華的種地理念以及蘇喬對于私人空間的看重。“有沖突蠻好,就會有交集,大家就會認識到我。最怕大家不認識,在心里猜忌,那到時候有什么問題才是真問題。”張華說。
不過,事實另一面是,雖然與本地人關系可以改善,但張華與此地更緊密的聯系,依然是銀林村的“新村民們”。
這個群體里,大家的交易往往跳過了貨幣,選擇用最原始的一物換一物。張華經常用他種植的番石榴換取面包和大米,他很喜歡這種人際交往的感覺。他形容說,相比于貨幣需要宣傳、需要定價等流程,這種交易形式能夠減少對他自身能量的損耗。
“大家都很互相信任,我覺得里面也有種惺惺相惜的感覺。”張華說。
面對現實
2023年9月,當時的廣東連續下雨。張華的農場沒有扛過這個秋天。這次下雨直接讓他損失一兩百斤的番石榴。“下雨果子不甜,人家吃了肯定不會再買,我自己也不想降價去賣,然后果子就爛掉了。”張華說。
新村民們終究會意識到,農民這個職業充滿了不確定性,并不是天然地比城市生活穩定。
在一開始,張華并不會感受到這樣的壓力。當時,他對于田園生活的想象僅僅在于這是一份比較看重體力的工作,而他健碩的身體足以克服。當真正面對一系列的壓力時,張華開始感到后悔想要放棄了。不過,他并不是想回到城市里工作,而是想進入一個其他的農場打工。
在想要放棄的那段日子里,張華看著自己所種植的一草一木,回憶起了自己做獨立農場甚至是進入鄉土的初衷。他也曾經在城市里做過兼職,也在其他農場給人打工,但是這些日子他并沒有完全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在農場里也僅僅是滿足了自己回歸生態的欲望。
他真正想要的是一種收獲感,是每天看著自己種植的果實一步一步茁壯成長給到的反饋,這種反饋讓張華覺得勞動是令人愉悅的。
他真正想要的是一種收獲感,是每天看著自己種植的果實一步一步茁壯成長給到的反饋,這種反饋讓張華覺得勞動是令人愉悅的。
“在城市里,我感覺到工作與生活是分開的,而有了自己的農場后,我開始享受這種在工作里生活,在生活里工作的松弛感。”
張華目前每個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他靠給村里的人打零工來賺錢。他說,這已經夠解決養活自己和一貓一狗了。在村里的一些糧食問題,基本能用自己的農產品與其他人交換柴米油鹽。女朋友與父母不認可、但是理解他目前的生活狀態,他覺得,這些不確定性都是“田園”足以對抗的。
嵌入田園
路邊的草又長到馬路上了,蘇喬認為這是獨屬于鄉村的自由。
受訪時,蘇喬在鄉間道路上散步,她非常享受這種放松的感覺。對她來說,這就是在城里生活給不到的,也是她愛上田園生活的原因之一。
“就像這里的草,永遠都不會有人管它,沒有人會去問這個時候這個地方該出現什么樣的草,這是一種沒有秩序的舒服感。”游歷了中國、外國的大城市后,她最終選擇了鄉土的簡單與自由。
現代社會分工明確的特點,讓城市交際網絡多了一份效率、少了一份人情。“在城市里,如果跟鄰居鬧了矛盾,可能需要隔幾環去找物業,把一件事情變得冰冷,但是在鄉村里只需要找鄰居說上幾句或者給點建議,大家的問題就此解決了。”
在蘇喬眼里,城市里的溝通只有與一個抽象的理性系統“對接”,而鄉村里的溝通卻是跟一個個真實、具象的人來溝通。
所以,這種簡單自由的感覺,把蘇喬們“鎖”在了鄉村。但他們依然是需要給家人一個交代的。
面對家里的擔憂,無論蘇喬還是張華,他們都盡可能地在銀林村營造更好的生活狀態,以向父母展示自己如何均衡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當父母覺得蘇喬在銀林村的生活過于簡陋時,蘇喬決定未來要在銀林村租下更大的房子。而張華則是展現健康開朗的自己。“有一個健康的身體能夠對抗未來很多不確定性嘛,對吧?”
在采訪時,張華家門口的紅嘴藍鵲又開始叫了。張華始終相信,這是給他一直帶來好運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