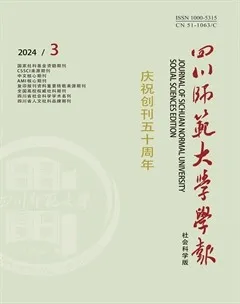兼容與迭代:數字訴訟的三種形態
左衛民 沈思竹
摘要:當下,司法領域已經或者可能出現三種形態的數字訴訟。1.0形態的數字訴訟是數字技術與傳統訴訟結合的初級形態,訴訟的基本機制和規則并未發生根本性變化;2.0形態的數字訴訟旨在通過數字技術方式處理依托于數字技術的數字糾紛,并在一定程度上開始脫離傳統訴訟原理的束縛;在3.0形態的數字訴訟中,數字技術廣泛運用于證據的形成及其審查判斷,糾紛與訴訟程序的展開亦與數字技術密不可分,訴訟理念、原則以及具體的訴訟規則也與傳統訴訟明顯區分開來。三種形態的數字訴訟不同而兼容,交替并迭代。在數字訴訟形態迭代的過程中,司法正義實現的方式以及司法正義概念本身也在變化。
關鍵詞:數字訴訟;司法正義;訴訟形態;兼容;迭代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4.0307
收稿日期:2024-02-28
基金項目:本文系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實驗室“實證法學與智慧法治實驗室(2023)”研究項目(2022sksys-03)、四川省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糾紛解決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項目(jdpt-2022法學0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左衛民,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學杰出教授,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第四屆全國十大杰出青年法學家,E-mail: zuowm@scu.edu.cn;
沈思竹,女,四川內江人,四川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隨著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深刻地影響了傳統的法律體系和訴訟方式。作為新技術與法律相結合的產物,數字訴訟無疑是法律領域數字變革的核心。然而,何為數字訴訟,這是一個在理論界尚未達成一致認識的問題。筆者認為,數字訴訟本質上是指使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型數字化技術開展訴訟行為的訴訟形態。與之相對應,數字訴訟法是規制數字訴訟行為且不同于傳統訴訟法的訴訟規則與機制,主要表現為與數字訴訟行為相關的系列法律規范。當下,數字訴訟由于與部分傳統訴訟原則相悖而受到質疑【理查德·薩斯坎德《線上法院與未來司法》,何廣越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88-243頁。】。因而,是否繼續推進數字訴訟發展以及如何推進數字訴訟發展等問題都需要繼續研究。
一 數字訴訟的不同形態
對于數字時代中司法演進的劃分,目前已有若干討論。如:劉哲瑋依據法規的通過將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的通過認定為在線訴訟1.0的開端,將2021年《人民法院在線訴訟規則》的通過認定為在線訴訟2.0的開端【劉哲瑋《邁入2.0時代的在線訴訟》,《人民法院報》2021年7月3日,第2版。】 ;姜偉依據技術是否影響訴訟模式將其籠統劃分為了為不受技術影響的傳統模式和受技術影響的新模式【姜偉《數字時代的法治模式》,《數字法治》2023年第1期,第32頁。】;域外,理查德·薩斯坎德將目前已經出現的線上裁判和拓展法院劃分為第一代線上法院,將未來引入虛擬現實技術、人工智能法官等技術的法院劃分為第二代線上法院【理查德·薩斯坎德《線上法院與未來司法》,第142-151、255-298頁。】 。在《邁向數字訴訟法:一種新趨勢?》一文中,筆者初步論析了以在線庭審為代表的1.0形態的數字訴訟【左衛民《邁向數字訴訟法:一種新趨勢?》,《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3年第3期,第53頁。】。縱觀數字技術在訴訟中的應用狀況,參考上述學者的劃分,筆者認為世界范圍內已經或者可能出現了三種形態的數字訴訟。
(一)1.0形態的數字訴訟:線下訴訟線上化
1.0形態的數字訴訟是數字技術與傳統訴訟結合的初級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在傳統訴訟框架內引入了數字技術,使得原本的一些訴訟環節在形式上數字化,但訴訟的基本機制和規則并未發生根本性變化。例如,視頻審理便是將傳統線下庭審數字化,將實體法庭中的“面對面”變為云端“面對面”【郭豐璐《論在線訴訟的功能定位》,《法律適用》2023年第5期,第85頁。】。從某種意義上講,當訴訟參與人拋棄紙筆轉而使用電子系統制作、存儲、管理、傳輸訴訟文件時,1.0形態的數字訴訟便開始萌芽。這不僅是數字技術在法律實踐中的初步應用,也是法律流程數字化轉型的開始。在這之后陸續出現的各種電子系統、線上平臺,如電子擔保書系統、法院對外委托鑒定平臺、一站式多元解紛平臺、線上普法平臺、線上法律援助平臺等,不論架構如何復雜、功能多么豐富,只要其最終目的還是作為傳統訴訟的一種線上替代方案,發揮“例外性的保障”功能【郭豐璐《論在線訴訟的功能定位》,《法律適用》2023年第5期,第85頁。】,都屬于1.0形態的數字訴訟組成部分。
(二)2.0形態的數字訴訟:數字化糾紛數字化處理
如果說1.0形態的數字訴訟是數字技術在訴訟領域中的初級應用所呈現的一種訴訟形態,那么2.0形態的數字訴訟源自數字時代糾紛本身的數字化。從某種意義上講,通過數字方式處理與數字技術相關的數字糾紛,反映了訴訟制度對數字時代法律需求的積極響應。相較于1.0形態的基礎性數字化轉換,2.0形態的數字訴訟開始逐步脫離傳統訴訟原理的束縛,推動了訴訟主體間法律交往方式的線上再造【張興美《電子訴訟制度建設的觀念基礎與適用路徑》,《政法論壇》2019年第5期,第118頁。】。這一階段的數字訴訟具有原生性,問題發生于線上,審判行為與規則均實施于云端【劉哲瑋《邁入2.0時代的在線訴訟》,《人民法院報》2021年7月3日,第2版。】。自此,訴訟已經開始發生本質性變化。例如,《人民法院在線訴訟規則》第十六條至第十九條確立的區塊鏈存證的效力及審核規則、第二十條確立的非同步審理模式已不再是簡單地移植或復制線下訴訟規則,而是發端于線上生活的新型訴訟模式的行為基準【劉哲瑋《邁入2.0時代的在線訴訟》,《人民法院報》2021年7月3日,第2版。】,是數字技術對審理程序改造的成果【謝登科、趙航《論互聯網法院在線訴訟“異步審理”模式》,《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第78-82頁。】。
需要指出的是,互聯網法院的創設可能是2.0形態數字訴訟的集中體現。一方面,互聯網法院管轄案件的事實和證據均產生和存儲于網上,且訴訟行為均在線完成,因而互聯網法院在處理與互聯網相關糾紛時展現出了明顯的效率優勢。例如,杭州互聯網法院通過對接糾紛多發的電子商務平臺,合并當事人舉證與法院調取證據的環節,實現在線證據的自動提取、引入訴訟:只要輸入相關的訂單號碼,系統會自動連接電子商務平臺,提取當事人身份信息、訂單、聊天記錄、物流信息、借款合同等數據,并利用第三方技術平臺,對全部數據進行保全固定,自動轉換為證據【李占國《互聯網司法的概念、特征及發展前瞻》,《法律適用》2021年第3期,第9頁。】。同樣,北京互聯網法院可以一鍵調取北京版權保護中心存檔的版權登記材料,打通了著作權登記信息與司法審判數據的壁壘,確保版權信息真實可靠,大大降低了權利人舉證和法官驗證難度【《“互聯網+司法”:如何讓明天在今天實現》,中國法院網,2021年2月25日發布,2024年2月4日訪問,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1/02/id/5821559.shtml。】。另一方面,發生在互聯網上的行為或糾紛,與線下行為或糾紛有很大不同,其訴訟管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都打上了深刻的互聯網烙印,需要建立一整套全新的行為規則、訴訟規則和裁判標準【李占國《互聯網司法的概念、特征及發展前瞻》,《法律適用》2021年第3期,第5頁。】。三家互聯網法院均制定了在線訴訟庭審規則,創新了送達機制,并依托司法區塊鏈平臺探索了電子證據規則【時建中《互聯網法院的核心使命、時代挑戰和發展建議》,《人民法院報》2020年10月10日,第2版。】。例如,以區塊鏈為代表的數字技術為電子證據的取證、存證帶來了全新的變革【肖建國、丁金鈺《論我國在線“斯圖加特模式”的建構——以互聯網法院異步審理模式為對象的研究》,《法律適用》2020年第15期,第109頁。】,故而需要明確電子證據效力認定規則。在杭州華泰一媒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華泰公司)訴深圳市道同科技發展有限公司(道同公司)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一案中,華泰公司通過第三方存證平臺對道同公司的侵權網頁進行了區塊鏈存證【《互聯網十大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報》2021年6月1日,第3版。】。杭州互聯網法院通過審查存證平臺的資格、侵權網頁取證技術手段可信度和區塊鏈電子證據保存的完整性,認為“區塊鏈有難以篡改、刪除的特點,其作為一種保持內容完整性的方法具有可靠性”【盧憶純《區塊鏈電子存證的法律效力認定——杭州華泰一媒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訴深圳市道同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搜狐網,2018年8月17日發布,2024年2月4日訪問, https://www.sohu.com/a/248626935_221481。】,明確了區塊鏈這一新型電子證據的認定效力,并根據電子簽名法的規定總結了這類電子證據認定效力的基本規則【《互聯網十大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報》2021年6月1日,第3版。】。
(三)3.0形態的數字訴訟:數字技術深度創新應用
3.0形態是數字訴訟的顛覆性、革命性階段。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充斥于糾紛發生的過程,整個訴訟機制、理念與規則亦如此。糾紛與訴訟程序的展開包括證據的表現形式及其審查、判斷機制均與數字技術密不可分。從審判主體的角度看,人工智能運用和大數據管理將成為這一階段的重要特征,目標是提升判決的精準度和效率。法官在審判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人工智能的影響,甚至可能出現AI法官。
從實踐來看,體現3.0版本訴訟形態的現象已經出現。例如,深圳市羅湖區法院上線的智能裁判輔助辦案系統能自動提取案件要素,以“類案裁判結果評估”為主、“基于裁判規則計算”為輔的方式自動生成判決文書【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智能裁判輔助辦案系統上線,智慧法院建設再上新臺階!》,新浪微博,2022年1月10日發布,2024年2月4日訪問,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724030510072178。】。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研發的勞動爭議大數據智能輔助平臺可建立勞動人事爭議虛假訴訟分析模型,智能甄別并預警勞動爭議虛假訴訟【江蘇高院《深挖審判數據價值 巧解勞動爭議難題 江蘇法院建設勞動爭議大數據智能輔助平臺》,“數字法院進行時”微信公眾號,2024年2月20日發布,2024年2月26日訪問,https://mp.weixin.qq.com/s/ujd1NDclRsL57LcIF9PLPA。】。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推出的“鳳凰智審”可以對金融、道路交通事故、知識產權、行政非訴等案由進行除文書確認外的全程無人工干預的智能審判【浙江高院《浙江法院“鳳凰智審”——為智慧司法激活新動能》,“數字法院進行時”微信公眾號,2024年2月22日發布,2024年2月26日訪問,https://mp.weixin.qq.com/s/wv2sydRcGczwnwa7LZFuwQ。】。
需要指出的是,法律的生命力源于其對社會變遷和技術進步的適應能力。隨著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法律實踐亦在演變,數字訴訟形態從1.0、2.0到3.0的發展,不僅展現了技術對法律的持續影響,更體現了訴訟為滿足社會需求、提升效率和公正性所進行的不懈努力。當下,1.0與2.0形態的數字訴訟已然存在,似乎開始占據主流。相較之下,3.0形態的數字訴訟方才嶄露頭角,尚處于萌芽階段,表現還不突出,但其發展潛力巨大。隨著技術的進步和法律體系的適應,未來可能出現更多依賴高級數字技術的訴訟形態。目前,以ChatGPT為典型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已經開始在1.0和2.0形態的數字訴訟中試探性發揮作用,如提供文書自動生成、案例研究等服務。但隨著技術的進一步成熟,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很可能成為3.0形態數字訴訟的重要支柱,具體應用將包括但不限于通過人工智能發現事實、分析證據,甚至是自動判決。
二 不同形態數字訴訟之間的關系
數字訴訟的三種形態及其之間的迭代進程,既是技術進步的產物,也體現了訴訟體系自身為適應數字社會的演化而進行的不懈努力,反映了法律體系對于新技術的適應與整合。每種數字訴訟形態在特定時期都有其應用價值,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兼容和迭代的,而不是簡單的前后替代。
(一)不同而兼容
所謂不同,是指三種數字訴訟涉及到的基本技術存在差異。1.0形態的數字訴訟主要使用基礎的數字通信技術,是傳統訴訟的線上展開形態,其糾紛內容與相關證據往往是傳統的;2.0形態的數字訴訟則引入了一系列互聯網技術,旨在通過數字技術的方式來處理依托于數字技術的數字糾紛;3.0形態的數字訴訟更多是采取全新的司法技術來解決本質上依托于最新數字技術(如人工智能等)、帶有濃厚數字因素的社會行為帶來的相應糾紛。與傳統訴訟相比,數字訴訟的1.0形態最接近傳統訴訟,2.0形態對傳統訴訟開始有所脫離,3.0形態可能完全不同于傳統訴訟。所謂兼容,是指三種數字訴訟可以在當下、未來的同一時空并存、互補,對不同、相似糾紛分別或者共同處理。即使在未來,也不會出現某一種數字訴訟(包括3.0形態的數字訴訟)“獨霸天下”的情形。在實踐中,三種形態的訴訟也的確“和平共處”于當下。
一方面,三種數字訴訟所針對的不同糾紛場景會長期并存。1.0形態的數字訴訟主要針對傳統糾紛場景下的數字化處理,適用于所有傳統的、線下發生的糾紛場景,包括但不限于傳統合同糾紛、不動產財產爭議等。2.0形態的數字訴訟適合處理產生于互聯網和相關數字技術的糾紛,包括網絡侵權、電子商務交易爭議、網絡版權問題等。3.0形態的數字訴訟所針對的糾紛場景更加廣泛和復雜,不僅包括相對于2.0形態而言更加復雜的數字化糾紛,如基于數據分析的商業糾紛、智能合約引起的法律問題等,還包括通過利用人工智能輔助或自動完成某些傳統的訴訟行為,如證據的智能分析和量刑的智能建議等。由于人工智能難以習得人類的情感與思維,因而涉及價值判斷和倫理問題的訴訟場景難以充分體現在3.0形態之中。概言之,法律生態復雜而多元,三種數字訴訟形態分別針對不同糾紛場景,從傳統訴訟的數字化處理到網絡時代糾紛的在線解決,再到利用先進技術應對復雜多變的糾紛類型,每一種形態都有其獨特的適用范圍和價值。
另一方面,三種數字訴訟涉及的技術方法存在一定共性。三種訴訟形態的技術基礎都是互聯網與其他數字技術。不管是2.0形態的數字訴訟所使用的區塊鏈技術,還是3.0形態數字訴訟的主要驅動力——人工智能技術,都需要基本的互聯網技術為其提供通信和數據傳輸的基礎。這些互聯網技術也是1.0形態數字訴訟所使用的基礎性技術。同時,不同技術之間相輔相成、互相促進,而非割裂。例如,區塊鏈和人工智能可以說是技術領域的兩個面相:一個是在封閉數據平臺上培育中心化的智能;另一個則是在開放數據環境下促進去中心化的應用【王耀羚《區塊鏈與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官網,2019年11月5日發布,2024年2月4日訪問,https://www.iii.tsinghua.edu.cn/info/1060/2038.htm。】。但是,區塊鏈可以為人工智能提供安全數據,提高人工智能的計算能力,進而解決人工智能信息不透明、計算能力不足等問題。使用區塊鏈存儲人工智能所使用的數據,可以防止數據丟失或被篡改,在保證數據準確性、安全性的同時,也提高了人工智能的可解釋性【《區塊鏈與人工智能(AI)》,IBM官網,2023年11月5日發布,2024年2月4日訪問,https://www.ibm.com/cn-zh/topics/blockchain-ai。】。區塊鏈中的分布式計算可以允許多個計算機同時對數據進行計算,從而提高人工智能的計算能力。
(二)交替與迭代
三種數字訴訟形態在某種程度上存在先后、交替關系,甚至存在一定的迭代關系。隨著技術的變革,數字訴訟不同形態的迭代反映了法律適應技術發展的過程,法律的適應性機制使得法律能夠不斷滿足技術進步和社會變遷的需要,并成為法律生命力的源泉【周少華《適應性:變動社會中的法律命題》,《法制與社會發展》2010年第6期,第105頁。】。與世界信息化三次浪潮以及我國電子政務發展相適應,最早出現的是1.0形態的數字訴訟,其后出現2.0形態的數字訴訟,然后出現3.0形態的數字訴訟。從發展趨勢來看,1.0形態的作用領域正在被2.0形態所占據,1.0與2.0形態逐漸為3.0形態讓路,但并非完全取代。
首先,新技術的出現與擴張使用使得糾紛本身發生變化。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的涌現,使得諸如數據泄露、智能合約爭議等新型糾紛不斷涌現,并帶來了更復雜的交易和合作模式,從而導致糾紛變得更加多樣和復雜。同時,新技術的應用極大地加快了社會交往的速度,擴大了社會交往的范圍,糾紛的形態也因此變化,導致影響范圍擴大和處理難度增加。例如,在浙江溫州市甌海區公安分局破獲全國首例利用區塊鏈“智能合約”(Smart contract)【
是一種旨在以信息化方式傳播、驗證或執行合同的計算機協議。智能合約允許在沒有第三方的情況下進行可信交易,這些交易可追蹤且不可逆轉。】犯罪的案件中,陳某等人利用區塊鏈“智能合約”技術非法獲取大量的以太幣【葛熔金、虞一峰、金一劍《利用區塊鏈“智能合約”,3名95后詐騙1300余人上億元》,澎湃網,2020年7月10日發布,2024年2月4日訪問,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209019。】。區塊鏈技術所帶來的隱蔽性和跨區域性,加上各國監管政策差異所帶來的影響,使得偵辦虛擬貨幣相關案件時線索發現難、鏈上鏈下身份信息關聯難、調證取證難、涉案贓款追繳處置難等問題【徐賜豪《流水4000億!“虛擬貨幣第一案”告破,洗錢成為最常見的虛擬貨幣犯罪》,“元宇宙NEWS”微信公眾號,2023年7月21日發布,2024年2月4日訪問,https://mp.weixin.qq.com/s/2VlGF8jnhxYpgMckZStQyg。】。
其次,技術進步為糾紛解決機制的迭代創造了新條件。新技術為糾紛的預防、分析及解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從而為現有機制的迭代與創新提供了條件。大數據技術能夠幫助分析歷史糾紛數據,識別可能引起糾紛的因素和模式,從而采取預防措施。人工智能通過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和機器學習技術可以快速篩選、處理和分析大量的通訊記錄、金融交易記錄、合同文檔、訴狀、裁決書等,揭示案件的關鍵線索和模式,發現潛在的法律問題。在實踐中,針對虛擬貨幣相關犯罪,在傳統的偵查手段難以奏效時,執法機關開始利用智能溯源歸集等大數據技術,深度挖掘、提取偵查線索【《高科技防范打擊虛擬貨幣犯罪,區塊鏈技術可發揮哪些作用?》,中國新聞網,2023年3月1日發布,2024年2月4日訪問,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3/03-01/9963346.shtml。】。對電子化證據材料的認證,線下肉眼“直觀”感受已無法準確地辨識是否侵權時,杭州互聯網法院可以通過線上智能證據分析,對于視頻類證據通過對視頻幀寬度、幀高度、數據速率、比特率、幀速率等參數進行比對,對圖片類證據通過修改時間、地點、相機型號、像素、分辨率等參數的比對,綜合判斷多維度相似性。技術不僅是工具,更是塑造訴訟程序和參與者互動方式的關鍵因素。因此,在原本的糾紛解決機制難以應對新技術的出現與擴張引發的問題時,法律專業人士和政策制定者開始尋求借助新技術為糾紛解決提供新的手段,從而促進了糾紛解決機制的迭代。例如,針對上文提到的虛擬貨幣犯罪問題,有論者提出了“由鏈到案到人”的大數據偵查模式【夏炳楠《論互聯網金融洗錢犯罪的偵查對策——以區塊鏈為視角》,《上海法學研究》2020年第2期,第51-64頁。】;還有學者提出要運用存證技術和補強佐證措施突破電子取證難點,嘗試虛擬貨幣司法會計評估和等價沒收制度完善追贓挽損機制【胡德葳《區塊鏈技術下智能合約詐騙犯罪偵查》,《中國刑警學院學報》2021年第6期,第14-20頁。】。
最后,科技人員在糾紛解決中地位的逐步提升促進了糾紛解決機制的迭代。傳統糾紛解決機制主要依賴于法律專業人士,然而,新型糾紛中涉及的技術問題越來越復雜,超出了傳統法律專業人士的專業范疇。科技人員因其掌握特定技術領域的專業知識,逐漸成為糾紛解決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科技人員可以提供可能的技術解決方案以及技術評估報告,幫助法律專業人士更好地理解案件的技術維度。在處理涉及大量電子數據的案件時,科技人員運用專業技能進行數據挖掘和分析,可以確保證據的有效收集和正確解讀。以算法的潛在歧視問題為例,其中涉及到復雜的數據選擇和處理過程,需要科技領域的專家為法律人提供必要的技術培訓和支持,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和處理涉及新技術的案件,或者直接參與到糾紛解決過程中。通過提供專業意見、技術分析等形式,為糾紛解決部門提供決策支持。這要求現有糾紛解決機制吸收更多的科技人員,并加強與科技團體之間的合作,強化科技人員在糾紛解決機制中的作用,將科技人員的角色從僅僅作為專家輔助人擴展到糾紛解決過程的核心參與者。這勢必引發糾紛解決機制權力結構的重大變化,糾紛解決的過程將不再由傳統法律專業人士絕對主導。
事實上,迭代過程在軟件開發和技術設計領域非常常見。在訴訟領域,每一次迭代都是對現有系統的重新思考,通過不斷的反饋循環和改進,逐步完善訴訟服務,打造既高效又公正的訴訟體系。這個過程不僅涉及技術的升級和應用,還包括對法律原則、倫理和社會公正的深刻反思。同時,技術并非單方面影響社會,社會需求、價值觀和制度框架同樣塑造技術的發展方向,數字訴訟的設計和實施需要考慮司法公正、可觸達性和效率等多重價值。
三 數字訴訟形態變遷與司法正義的再反思
(一)正視數字訴訟對傳統司法正義的沖擊
數字訴訟通過引入數字技術提高司法效率、降低成本、擴大司法服務的覆蓋范圍,但數字訴訟也無可避免地對審判獨立、實體公正、程序公正等傳統的訴訟原則與理念帶來了一定的沖擊【蔣惠嶺《論傳統司法規律在數字時代的發展》,《現代法學》2023年第5期,第125頁。】。正視這些沖擊,不僅是對現有司法體系的一種審慎評估,更是確保司法正義在新時代背景下得以維系和發展的必要步驟。
一方面,數字訴訟的虛擬性和非現場性對程序正義構成了顯著挑戰。程序正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的形象公正和當事人以及社會公眾對訴訟程序的體驗感【蔣惠嶺《論傳統司法規律在數字時代的發展》,《現代法學》2023年第5期,第135頁。】。庭審的莊嚴感和“劇場效應”是傳統司法程序非常重要的心理和文化元素,體現了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是維護法律尊嚴的重要手段。在數字訴訟中,在線庭審的虛擬性、非現場性會消解甚至嚴重影響庭審的莊嚴感和“劇場效應”,使訴訟程序的親歷性、對抗性、規范性、嚴密性等特質受到削弱,因此,異步審理機制會加劇庭審虛化問題【趙青航《數字時代下協同主義訴訟模式的建構》,《北方法學》2024年第1期,第42頁。】。而法庭程序的形式化和簡化,會削弱公眾對法律及其執行過程的敬畏感,影響法院形象的權威性,從而妨害程序正義的實現。
另一方面,數字訴訟帶來的“算法黑箱”、“數字鴻溝”、訴訟結構失衡等諸多問題對實體公正造成了沖擊。實現正義依靠的是實質判斷,而不是體現相關性的概率計算【馬長山《司法人工智能的重塑效應及其限度》,《法學研究》2020年第4期,第36頁。】。人工智能算法統計的相關性并不代表因果關系,這意味著算法即便在統計學上準確,也不能保證其結論在每個案件中都適用,這種情況可能會放大“同案不同判”的缺陷,削弱“同案同判”原則的合理性。而算法決策邏輯和過程的“算法黑箱”會導致訴訟過程的不透明性,進而損害當事人質證權、知情權、參與權等基本訴訟權利【牛犁耘《人工智能的司法應用與法理審視》,《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第5期,第60頁。】。同時,在傳統的訴訟體系中,法官應保持獨立性,自主進行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享有對案件的法律解釋、法律適用、事實查證和案件裁決等方面的決定權,如果法官在不完全理解算法邏輯和過程的情況下參考人工智能提供的類案或建議,其獨立審判權可能受到沖擊,從而影響實質正義【葛金芬《司法人工智能應用中法官的瀆職風險及其刑事責任》,《湖南社會科學》2023年第3期,第96頁;牛犁耘《人工智能的司法應用與法理審視》,《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5期,第60頁。】。同時,數字技術可能加劇“數字鴻溝”,影響訴訟參與的平等性。“數字精英”和普通民眾之間存在信息及資源獲取的巨大差距。例如,“數字精英”可以利用數據分析技術,如“法官畫像”來深入分析法院和法官的裁判傾向,據此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管轄法院提起訴訟,從而在訴訟策略上取得優勢。這種技術手段的應用,雖然從表面上增加了訴訟的透明度,但實際上加大了信息不對稱性,使得那些無法獲取或使用這些技術的當事人處于不利地位。同樣地,數字技術會大大提升公權力機關的訴訟能力,導致訴訟結構失衡,進而破壞實體公正【胡銘、張傳璽《人工智能裁判與審判中心主義的沖突及其消解》,《東南學術》2020年第1期,第216頁。】。
(二)數字訴訟中司法正義的變化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正義呈現出一種無形的、流動的、多元的主觀判斷狀態【馬長山《司法人工智能的重塑效應及其限度》,《法學研究》2020年第4期,第35頁。】,在某種程度上,數字技術在訴訟領域的實踐應用同傳統的司法公平正義觀所體現的公平正義原則和機理已經有所背離。但這種背離并不意味著否定或替代傳統正義觀念,而是在數字化社會背景下的適應性演化,是在傳統司法正義觀的基礎上針對數字化社會的特點和需求進行的必要補充和調整,是傳統司法正義觀在數字社會轉型升級的結果【姜偉《數字時代的法治模式》,《數字法治》2023年第1期,第30頁。】。在數字訴訟迭代過程中,公平、公正、公開這些正義的核心價值未曾改變,而是司法正義實現的方式發生了變化,司法正義概念在數字時代得到擴展和深化。
關于司法正義實現方式的變化。訴訟原則的迭代推動司法正義實現方式的調整。訴訟原則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時代背景、社會需求和技術發展而不斷進行適應性調整。數字訴訟不可避免地沖擊和重新界定了訴訟的親歷性原則、直接言詞原則、訴訟對等原則,也給管轄規則、身份認證規則、證據認定規則、庭審規則等訴訟規則帶來了全方位挑戰【時建中《互聯網法院的核心使命、時代挑戰和發展建議》,《人民法院報》2020年10月10日,第2版。】。這種新的訴訟實踐帶來的與傳統訴訟原則的背離是對正義實現方式的適應和調整,是為更好地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而對傳統訴訟原則現代化的解釋和應用。只要這種調整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公眾利益,促進社會公正與和諧,那么它就是在推動正義實現方式的調整。
關于司法正義概念的擴展和深化。司法正義在數字時代需要新的定義。傳統正義的實現側重于正確性(真實維度)的評價,而數字訴訟時代要求我們將評價體系擴展為正確性(公正維度)、效率性(時間維度)及適宜性(成本維度)的多維度考量【阿德里安A·S·朱克曼主編《危機中的民事司法——民事訴訟程序的比較視角》,傅郁林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這種變化響應了數字化社會對司法高效率和經濟適宜性的期待。“在數字社會中,自由、平等、民主以及法律、秩序和正義都將被重新定義,數字正義將是更高的正義”【周強《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 不斷推進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人民司法》2020年第1期,第5頁。】。在數字社會中,數據成為了社會運行的核心元素。這種變革不僅重塑了我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對司法正義的概念和實現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要求。因此,對數據信息的控制、依托算法推薦進行的誘導控制、通過算法系統進行直接控制和數字人權,成為了數字正義的焦點【馬長山《算法治理的正義尺度》,《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第10期,第71-73頁。】。這要求法律從以人為中心轉向更多地考慮技術的作用和限制,重新審視和定義公正、平等和透明度等核心法律價值與訴訟原理在數字環境中的含義和應用。以公正為例,在數字環境中,公正不僅涉及到案件審理的公正性,還包括技術應用的公正性。后者包含兩部分內容:一是技術應用的公開正義,實現司法正義的過程需要得到社會見證【理查德·薩斯坎德《線上法院與未來司法》,第193-201頁;王福華《互聯網司法的正義體系》,《中國法學》2024年第1期,第141頁。】,數字技術的公開正義要求增強了算法決策的透明度,從而使當事人和公眾能夠理解并信任技術決策的過程,這包括對算法的設計、應用及其決策依據進行充分公開;二是技術應用的分配正義,即要確保技術應用不加劇或產生新的不平等【王福華《互聯網司法的正義體系》,《中國法學》2024年第1期,第126-131頁。】,例如,確保算法不對特定群體產生偏見,保障所有當事人都能平等地訪問和使用數字訴訟服務。
數字時代的司法正義致力于在數字化環境中實現公平、透明和包容。其與傳統正義在實現正義的目標上是一致的,只是在方法和途徑上進行了創新和發展。通過對數字時代司法正義觀的不斷探索和構建,不僅可以推動法律體系更好地適應數字化社會的發展,也能促進對傳統正義原則的深入思考和實踐創新。為實現數字時代的司法正義,需要在程序機制上進行創新,包括建立算法決策的透明度標準、確保數據處理的公正性、制定個人隱私和數據保護的嚴格規范,以及提高公眾參與度和審判的互動性。
四 簡短的結語
隨著時代的洪流奔騰向前,數字技術正在全方位而又深刻地重塑著社會的運行方式與人類的行為模式。法律與司法作為維護社會秩序和正義的基石,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數字技術不僅重塑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深刻地挑戰和擴展了我們對公平正義的傳統理解。這種變化迫使我們跳出傳統的思維框架,重新審視法律與司法的運行方式以及司法正義。法律規范的更新、訴訟原則的迭代,乃至對司法正義本身概念的深度反思,成為了這個時代法律人所面臨的新課題。站在數字時代的十字路口的我們既是觀察者也是參與者,在享受技術帶來的便利與效率的同時,也不得不面對算法偏見、數據隱私侵犯等一系列新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是技術層面的挑戰,更是法律理論與實踐需要解答的問題。對此,我們不僅要總結過去的經驗,更要預見與規劃可能的未來,通過更新法律規范,創設新的訴訟原則,讓法律與司法體系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時代感。
致謝:感謝官勝男博士、莫皓博士、郭松教授對本文寫作提出修改意見。
[責任編輯:蘇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