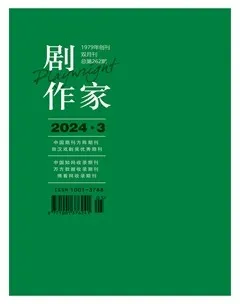傳奇經典在當下昆劇舞臺重塑的典范
韓郁濤
摘 要:《浣紗記》是昆山當代昆劇院與羅周合作的第三部作品,旨在紀念與致敬昆劇的“開山鼻祖”梁辰魚。不同于以往的專題致敬作品,該劇沒有選擇原創與縮編,而是對梁辰魚的原作進行了整合與改編,是一部傳承經典與融合現代意識的作品。集中表現在編劇對劇本的解構與重塑,將范蠡與西施改為劇情主線,進而思想主題亦由家國政治轉向了女性關懷。改編之后的《浣紗記》一經搬演,便受到了學界與昆曲愛好者的關注,其古雅詩意的舞臺風格廣受好評,并開啟了全國巡演的計劃。顯然,這是一部可演可傳的優秀劇目,對于當下昆劇新編與改編創排劇目所面臨的傳演困境提供了借鑒與解決路徑。
關鍵詞:《浣紗記》;羅周;昆劇
一、劇本的解構與重塑
此次昆山昆劇院排演的《浣紗記》對原作進行了大刀闊斧式的改革,不同于以折子戲集錦串演的縮編,編劇羅周選取了原本十余出關目情節,將原作散珠碎玉式所敘述的范蠡與西施的故事脈絡進行了集中凝練,聚焦歷史人物的私人情感空間,以突出在歷史大背景下生旦悲歡離合的個人命運,來映射封建王朝興亡的歷史規律。
羅周用其所擅長的“新雜劇”的創作手法,以“四折三楔子”的結構將原作這一鴻篇巨著進行了全新的編創。四折分別為《盟紗》《分紗》《辨紗》《合紗》,三楔子為《別越》《進姝》《賜劍》,保留了原作中的雙線結構,將范蠡與西施個人命運的悲歡離合,置于社會動蕩的國家背景之中,以“小家”的傷痕累累,折射出“家國”在兵燹之后的滿目瘡痍。與原本不同的是,全劇側重于表現生旦的私人情感表達,而吳、越兩國的政治博弈則作為楔子部分,串聯起生旦個人命運在波詭云譎、風云變幻政局下的起伏,“以情鑒史”成為了此次改編最大的特色,也為今后的昆劇舞臺復蘇與改編傳統戲中的長篇傳奇樹立了典范。
羅周對于《浣紗記》劇本的解構與重塑,是從劇作本身結構所存在的問題及昆曲發展到今日舞臺審美意趣的變化與需求兩方面考慮的。梁辰魚的《浣紗記》雖甫一問世便被爭相搬演,開了文人清唱的昆曲被搬上舞臺的先河,但其戲劇結構所存在的問題,也被同時代與后世的戲曲評論家所指摘。王世貞《曲藻》:“梁伯龍《吳越春秋》,滿而妥,間流冗長。”[1]P37徐復祚《曲論》又言:“梁伯龍,辰魚作《浣紗記》,無論其關目散緩、無骨無筋,全無收攝,即其詞亦出口便俗,一過后便不耐再咀……”[2]P239從兩位戲劇大家的評論來看,梁辰魚《浣紗記》所存在的最大問題便是結構松散,頭緒繁多,全戲幾乎找不到一個高潮,只是按照情節發展鋪敘,給人冗長雜亂之感。“減頭緒”與“密針線”恰是該劇在重新整理與改編時需要解決的問題。
《浣紗記》以群場戲見長,占據全篇半數以上,多以合唱、對唱、遞唱的形式展現。但不可否認的是,昆劇發展到后期,以突出生旦為主的角色制傳奇結構成為了舞臺上演出的主流形式。進入新世紀以來,《浣紗記》折子戲常演出劇目僅剩《打圍》《寄子》《合紗》《泛舟》四出,其中有三出為對子戲,半數為生旦戲,皆以曲唱佳而見長。可見昆劇發展至今日,以生旦為主體結構的演出形態居于主體地位。
基于上述兩點,羅周便以她嫻熟的創作技法對《浣紗記》進行了全新的改編。她將原劇中散落于宏篇敘事中范蠡與西施二人的離合提煉為全劇的主線,即為傳奇先立主腦,并在此基礎之上刪減頭緒,綿密針線。不同于原本《浣紗記》中范蠡秉持著“想國家事體重大,豈宜吝一婦人”,只身勸說西施赴吳。羅周在第二折《分紗》中,借鑒原作《迎施》《演舞》《別施》三出,巧妙設計了雅魚、勾踐、眾文官“三拜紅顏”的關目,這屬于編劇創作技法上的“三番四轉”。西施每接受一次跪拜,便將其置于道德綁架的困境中推重一步,前兩拜屬于統治者階層遞進式的逼迫,最后一拜則蘊含了天下蒼生與心愛之人的祈求,可以說是令其最終下定決心犧牲小我而為國獻身的根源。羅周的藝術加工,可謂是一次“點鐵成金”,在將原作零亂的頭緒集中凝練與刪減的同時,加強了生旦離合為主線的“主腦”,并巧妙地解決了歷史長期遺留的“范蠡勸獻”這一被后世難以從心理情感所逾越的同理心的障礙。
如果說《盟紗》《分紗》《合紗》還是羅周基于原作的串聯與改編,那《辨紗》一折則屬于原創。結構松散、劇無高潮是原本《浣紗記》在結構上所面臨的重要問題,而羅周所慣用的“新雜劇”模式,實則是對元雜劇四折在戲劇敘事結構上所表現出的“起承轉合”方式的一種繼承。第三折居于全劇的高潮,原作既無合適的高潮出目可選,那便要重新創作。《辨紗》一折可謂是情節推進與情感迸發的雙線高潮。一縷輕紗是范蠡與西施二人分屬兩地卻彼此心意相連的媒介,更是他們無論在何種險象環生的環境中負重前行、茍且偷安的精神支柱。這樣的私密之物卻因伍子胥的揭發而令西施處于前所未有的兇險境地。戲劇發展到此刻,張力十足,矛盾沖突的外在表現與人物情感的復雜交織被推到了頂峰——別國離鄉的西施第一次面臨了生死存亡的危機,她的生,必然會導致角力另一方的死,她以背叛情感的方式獲取了肉體的生,而另一方卻以犧牲肉體的方式,完成了死諫的臣子使命。生者雖生,卻再也回不到最初生死契闊的誓言;死者雖逝,卻早已在預知結局的前提下,無愧忠君報國之心。此折所表現出的歷史興替的經驗總結全部凝結于西施與伍子胥二人的“辨紗”之中。
二、家國情懷下的女性關照
梁辰魚的《浣紗記》以宏觀的政治高度來涵蓋這一規模龐大的歷史題材,作者站在縱向的歷史長河的高度,以政治家的目光來俯瞰國家的興廢之道,探尋其盛衰之因,是一部名副其實的政治戲,與李開先的《寶劍記》、王世貞的《鳴鳳記》一樣,是代表傳奇繁興的著名的政治戲,合稱明代“三大傳奇”。
羅周所改《浣紗記》在戲劇結構做出顯著調整之后,全劇的思想主題亦隨之發生了變化。作者以她細膩的筆觸,書寫了家國興亡背景下女性所面臨的生存困境及個人命運軌跡的顛覆。對于在歷史長河中,人們贊美卻難以共情的這樣一位女性,羅周予以了她極具溫柔的寫實關照。作品依然在遵循歷史的情況下,圍繞戲劇人物的人生重大抉擇而展開。西施自第二折起便被置于難以承受的殘酷沖突之中,最大限度地探索與觸摸人性的底線,構筑出劇烈的情感沖突。而在這一過程中,編劇巧妙地以稱呼的變化來訴說西施無常命運下的成長與妥協。在首折《盟紗》中,她是范蠡口中的“好姐姐”“神仙姐姐”,此時的西施是一個不諳世事、天真無邪的少女,純凈如紙。至二折《分紗》,她已是眾人口中的“姑娘”,她純真的少女時代與對美好愛情的憧憬在這一稱呼中戛然而止,此時的她在面對無可抗拒的壓迫后,瞬間成長,肩負起了為國獻身的使命。《辨紗》里,西施的稱呼尤為復雜,她是夫差口中的“美人”“寶貝”,伯嚭口中的“娘娘”,伍子胥口中的“奸妃”“賤人”。多種稱呼的交織,折射出的是西施入吳之后所面臨的人格撕裂。最后《合紗》中,已是身心俱疲、千瘡百孔的西施與范蠡遇合時,說出了“哪來的姐姐,再沒個姑娘”,經歷過這場長達十三年的桎梏后,她已不是自己,是世人口中稱頌的“娘娘”了,面對愛情已不敢再奢望與重拾了。
如果說稱謂的不斷變換所展現的是女性人物在家國動蕩下命運被裹挾的真實寫照,那關于西施美貌濃墨重筆式的反復強調,則表達了編劇對其悲劇命運根源所進行的深刻挖掘。“越國之美人,莫若諸暨。諸暨之美人,莫若苧蘿。苧蘿之美人,莫若西施!”在全劇之中出現了三次,分別在《盟紗》《分紗》《進姝》中,美貌是西施悲劇命運的溯源,何其無辜又何其諷刺。因為美貌她的愛情是缺陷的,命運是曲折的,人生是悲劇的,而這些都是她所不能抉擇的。面對因美貌而招致種種磨難的西施,羅周以其細膩溫潤的筆體對她予以了深切的體貼與關懷。在《合紗》一折中,范蠡問詢西施:“東南西北,意欲何往?”西施淡然反問:“今日所起何風?”當得知梅雨將至,南風向北時,便決定面北而去。這看似延宕的一筆,卻飽含了編劇對女性人物在家國巨變后的人性關照。二人此刻的泛舟絕非是大團圓式的收煞,而是一種身感浮萍、四處漂泊的落寞。看似以超脫的感悟與曠達面對現實所帶來的種種被動與恩怨,在閱盡離合與興亡之后選擇釋然與接受,實則如張弘老師所言,不過是“兩個畸零人的漂泊”。殘缺的兩個人,拼不成一個完滿的圓。當他們想要選擇回歸人性、做回常人時,卻發現選擇的權利早已在昔日的吳宮里被剝奪了,注定不會是一個圓滿的結局。他們的個人命運就如同最后隨水而流卻再也無法愈合的兩片薄紗,在鼎革興亡的歷史潮流中,被淹沒與吞噬,無助與渺小。
對于女性的人文關懷是羅周戲劇作品中所表現出的重要特征。她筆下的女性形象不同于李莉筆下的“剛毅”,亦不同于羅懷臻筆下的“扭曲”,同樣在經歷極具張力的戲劇沖突與情感折磨后,羅周對她們發出的更多的是跨越時空與歷史局限、站在現代角度的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關懷。戲劇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從不缺乏“撕裂”,卻鮮有被以溫柔的筆觸照拂與關懷,這一點是羅周塑造女性人物的獨到之處。
三、古雅詩意的舞臺呈現
深厚的文學功底與嫻熟的曲牌寫作是羅周昆劇創作的主要特征。她的作品將當下的昆劇創作回歸到了曲牌體乃至“劇詩”的古典戲曲文學的傳統之中。
在宮調與曲牌的選擇上,編劇羅周最大限度地選擇尊重原著,新作曲子不到三分之一。原作《浣紗記》作為昆山腔劇曲的開山之作,風采風流,用曲規范,是其聲名在外與舞臺傳承流傳至今的重要緣由。編劇在改編過程中,大量保留了原作套曲與曲牌,并以新曲過渡銜接,做到了交融無礙,基本呈現出了原劇的曲辭風貌,這是對傳統的致敬與回歸。曲辭基本遵照原作,念白則是羅周此次改編過程中改動最大之處,差不多有八成以上是新寫。中國古典戲曲的文學性具有“劇詩”的傳統,唱詞具有濃郁的抒情性,而念白往往推動劇情的發展。羅周此次的改編,以新作的念白串聯起原作中相對散亂的故事情節,以最大限度保留原作曲辭的手法使得作品延續了之前典雅綺麗的曲唱風格,可謂匠心獨運,使得原本卷帙浩繁的《浣紗記》凝練為適宜當下舞臺演出與觀演習慣的《浣紗記》,同時還留存了原著文學與曲學的整體風貌。
在角色的設置分配上,分別有小官生、閨門旦、末、正旦、副末、凈、外、丑、付。“四折三楔子”的劇情下,生、旦、凈、末、丑五個行當俱全,同時編劇還注意到大行當之下類型差異性角色的分配,并在單折之中設計了生旦對子戲、多角色群場戲、凈旦外鼎足戲、外行獨角戲,形式豐富,以示戲劇勻稱之美。注重舞臺展呈與冷熱場交替的對稱性,是羅周此次改編的精心設計。全劇以范蠡、西施生旦對子戲《盟紗》而起,又以二人《合紗》泛舟而去的對子戲收束。東施作為全劇付丑的角色,分別出現在第二折與第四折,安置在表現悲涼氣氛的西施“別國”與“歸越”之前,以插科打諢的方式,調劑冷熱場之間的過渡,同時交代了作者很多難以讓主人公說出的話與交代的事,滿足了調節氣氛的同時,也是作者乃至觀眾心中想言卻難言的代言人。三個楔子里,第二個楔子《進姝》與第三個楔子《賜劍》安置在劇目高潮第三折《辨紗》前后,起到串聯情節與調節戲劇節奏的作用。故事情節分別為伯嚭受賄與伍員自刎,表現出了對稱的“忠奸”關系;在舞臺呈現上,則體現出了滑稽調笑與悲涼抒情的對比,形成了喜與悲的舞臺節奏方面的對稱。
改編之后的《浣紗記》從文本特色與戲劇結構上,堅守了中國古典戲曲古雅詩意的風格,而舞臺的二次創作也遵循文本所流露出的特色,進行了詩意化的編排。中國傳統戲曲的舞臺同樣是“劇詩”的舞臺,講求寫意性,留給演員充分表演與發揮的空間。“昆昆”(昆山當代昆劇院)版《浣紗記》在舞臺設計上采用了意象化的戲劇舞臺造型,追求空靈與意境的視覺傳達。這點秉持了中國傳統戲曲舞臺美學的內在精神,戲曲舞臺的核心是演員的表演而非舞美。
大幕拉開,舞臺后方設置一道白紗藝術幕布,作為前后臺的分割區,白幕右下方嵌有篆體“浣紗記”三字,整體效果就像一幅徐徐展開的畫卷,演員在這幅素白的畫卷里演繹著一幕幕悲歡離合。這層白紗背景極具飄逸雋秀的視覺美感,同時透視的特征還可成為不同出目的置景底版。首折《盟紗》中,白紗的左后方放置著一葉篷船,伴隨著四周漫起的干冰,小船若隱若現的效果反而有湖中飄蕩之感。此時的西施走上前臺浣紗,使得舞美與故事情境、演員表演自然貼合,三位一體。同理,在之后的《辨紗》一折,白紗后面置景了一排荷葉,此時的白紗又成了夫差與西施賞荷的宮苑,而白紗幕布本身的質地又與此版《浣紗記》中的核心道具“紗”相暗合。這顯然是舞美的精心設計,可謂精巧、簡潔卻充滿詩意,在不干擾演員表演的同時,又與場次的置景巧妙融合,一改新編古裝戲置景繁雜或喧賓奪主的亂象,是對中國傳統戲曲舞臺寫意性的回歸與創造。
在昆劇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不乏優秀的作品,很多作品在戲曲自身的發展與變遷中,漸漸退出了舞臺,停留于案頭。羅周正以她高超的編劇技法與成熟的普世價值逐步將這些作品一一恢復,使其重新在舞臺之上煥發光彩。從《梧桐雨》再到此次的《浣紗記》,她為當下如何恢復與喚醒那些曾經在舞臺上馳名一時卻湮沒于戲曲前進車輪中的作品樹立了正確的示范。同時,對中國古典戲曲舞臺寫意與“劇詩”風格的回歸,也是為這些復排作品在舞臺之上重返高峰而保駕護航的重要手段。這或許是此次《浣紗記》的改編所帶給人們的最大驚喜。
參考文獻:
[1](明)王世貞:《曲藻》,《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四)》,中國戲曲研究院編,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2](明)徐復祚:《曲論》,《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四)》,中國戲曲研究院編,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本文為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新世紀以來昆劇編創研究”,項目編號:21YJC760024;2021年度南京信息工程大學人才啟動經費項目“新世紀以來江蘇省新編昆劇研究”,項目編號:2021r059;2022年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藝術與科技融創發展研究中心項目,項目編號:YS2022-06。作者單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藝術學院)
責任編輯 姜藝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