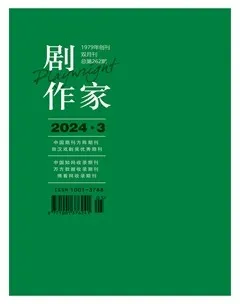以情感體驗完成革命講述,讓主旋律作品更好看
孫紅俠
摘 要:革命歷史題材劇作不應滿足于對歷史事件的講述,而應將藝術感染力置于革命歷史題材創作與表達的重要位置。安徽省安慶市黃梅藝術劇院推出的原創革命歷史題材現代戲《太陽山上》,以“小人物”個人命運的書寫、個人情感的表達來折射戰爭的宏闊,展示歷史的風云,在歷史敘事中重視個體敘事,以人物的日常情感體驗完成革命講述,讓主旋律作品更好看。這個戲的創作和演出為革命歷史題材創作這個話題提供了一個全新而有益的觀察視角。
關鍵詞:黃梅戲《太陽山上》;黃梅戲;革命歷史題材創作
在當下戲曲創作的格局中,革命歷史題材作品數量眾多,影響甚廣。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那些壯烈的故事是革命歷史題材劇作創作的源泉和動力,這些故事中的價值與精神是民族復興和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同時,觀眾和時代對革命歷史題材的創作也相應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品不應滿足于對歷史事件的講述,而應將藝術感染力置于革命歷史題材生命力表達的最重要位置,以藝術的方式感動觀眾,完成講述,才是革命歷史題材作品應有的創作原則和宗旨。
安徽省安慶市黃梅藝術劇院推出的原創革命歷史題材現代戲《太陽山上》,以人物的日常情感體驗完成革命講述,讓主旋律作品更好看。這個戲的創作和演出為革命歷史題材創作這個話題提供了一個全新而有益的觀察視角。黃梅戲現代戲《太陽山上》首演以來,收獲了眾多榮譽,2023年代表安徽省參加文化和旅游部舉辦的第三屆全國戲曲(南方片)會演;2023年獲得安徽省第十六屆精神文明“五個一工程獎”;2023年入選安徽省舞臺藝術精品劇目展演、“新時代新徽班新氣象”安徽省精品劇目展演的劇目;2020年、2021年入選安徽省委宣傳部重點文藝項目;2021年參加文化和旅游部主辦的第九屆中國黃梅戲藝術節展演、安徽省委宣傳部主辦的“安徽省建黨一百周年優秀劇目展演”……《太陽山上》以抗日戰爭中具有真實人物原型的小人物李安本為主角兒,在繼承革命歷史題材的創作傳統和紅色氣質的同時又在視角的選擇和表現的方式等方面體現了戲曲的特質,在大與小、情與理、生與死的沖突與架構之間展現了創作的能力,更因為以人物的日常情感體驗完成革命講述這一視角而增強了作品的感染力。這些都為革命歷史題材作品提供了有益的積累和探索。從這些角度看,《太陽山上》是近年以來革命歷史題材劇作中非常值得關注的作品。
黃梅戲《太陽山上》改編自人民文學獎獲得者、安徽作家季宇的中篇小說《最后的電波》。這是一部優秀的小說作品,是作家為自己的父母親一輩所做的記錄和懷念,更是在母親的遺物中發現《新四軍、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通信兵史料回憶選編》后因閱讀而產生的震撼。1941年1月,新四軍主力遭到國民黨突襲,血戰與重圍使得這支鐵流般的部隊到了最危險的邊緣。葉挺在和顧祝同談判時被扣押;項英與周子昆被叛徒殺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率部突圍中被打到血肉模糊,他因傷勢太重不想讓士兵們抬著他走而舉槍自殺,這位黃埔四期出身的年輕將軍犧牲時只有三十五歲……這是中國軍史上沉重暗淡的一刻。從《最后的電波》到《太陽山上》講的正是這段時期在安徽肥東縣白馬山中被切斷了與主力部隊聯系的新四軍戰士們如何在等待和希望中堅守、如何突圍東進的故事。這個故事里,實在有太多壯烈。這樣的書寫因立足于歷史的真實而準確、生動、真誠。
這樣真誠感人的故事,改編并立足于黃梅戲舞臺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戰爭場景無論多么波瀾壯闊、激蕩人心,舞臺作品和電影電視劇作品表現起來則完全不同。影視劇作品可以全景式或者藝術角度記錄式展示歷史;同樣的創作策略用于舞臺作品卻只能破壞藝術表現規律,尤其是以抒情性見長的戲曲很難直接表現戰爭場面,更不可能以電影那樣切換自如的手段來講述兩個以上的可以平行推進的故事。黃梅戲《太陽山上》將故事的戰爭背景切換到抗日戰爭,更增加了家國情懷,也更有利于高潮的推進,同時將原著中相對龐雜的人物關系做以簡化,突出主要人物和主要情節,為戲曲舞臺作品的創作和表現而服務。創作者選擇以李安本這個傳統農村最底層最普通的老百姓的經歷為主線,貼著地面行走,貼著心窩寫戲,以“小人物”個人命運的書寫、個人情感的表達來折射戰爭的宏闊,展示歷史的風云。縱觀全劇,由于沒有正面表現戰爭場面和相關情節,因此并沒有出現領袖人物,也沒有相關場面的呈現,而是更多地選取能讓所有基層觀眾感同身受的微觀視角和敘事語境,用平實和生活化的語言以及生存的真實狀態來產生戲劇的能量。
《太陽山上》成功塑造了“小人物”李安本的形象。“小人物”形象塑造屬于革命歷史敘事中個體敘事的一種,常見的手段就是將人物的命運與精神發展歷程與“家國”“戰爭”“時代”等宏大背景相聯系,但目的并不在于單純表現大背景中的小個體,而是以“小人物”的人生為切入點、為視角來賦予歷史的講述以微觀的體驗。《太陽山上》中的李安本屬于這一類敘事。李安本是一個“小人物”,還帶著做逃兵的不光彩歷史,被時代裹挾而卷入了戰爭卻因為對死亡的恐懼而做了逃兵。身為小人物,除了寄居于一個他無法左右的大時代,還能做什么呢?大時代里的小人物,為了生存,也無可厚非。
這個人物是有鮮明的成長軌跡的,他的成長軌跡和《太陽山上》整體的起承轉合節奏相一致。劇作一共六場戲,前半程氣氛相對輕松,而后半程則激越慘烈。整體節奏與李安本的心理轉換不僅一致,也是由他的轉變所帶動的。李安本的轉變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從大鵬為了將他的母親安全護送到蕪湖的那一刻開始的。活生生的一個人走了,只留下了一把刀,那一刻的李安本“手捧大刀重千斤,救母之恩似海深。耳邊忽聞離別語,句句敲打我的心”。大鵬的死,撞擊到了李安本的內心,使他潛藏于人性深處的善良得以蘇醒。滴水之恩,涌泉相報。性命相托,結草銜環。這是中華民族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底色,是復刻于我們民族文化基因與人性深處的美好。
如果說是新四軍戰士大鵬的死讓他選擇留在軍中,完成了“小人物”放棄“小”的自我的第一步,那接下來逐漸推進的情節設置則最終促使他成為了一名真正的戰士和英雄。新四軍是一支什么樣的隊伍?李安本心中是看成“四老爺”的。打動他的是這支隊伍里的人,他們各具性格,各有人生故事,最后都把年輕的生命留在了歷史滾滾向前的鐵流之中。他面對的是一支隊伍,但對他而言,更重要的是把他當人看待的人,給他以尊重的人,給他溫暖和友誼的人,為他獻出生命的人。這個群體,用人際的情感踏踏實實打動著李安本,感染著他、打動他的是恒久的人性,是日常情感中的革命啟蒙。在一次次、一回回的接觸中,他不僅感受到了這支人民軍隊給予他的溫暖和情義,更深刻認識到“誰人拿命不當命,誰人沒有弟兄姐妹和親娘”。在犧牲面前,他終于找到了“為什么他們這般鐵血剛強”的答案。
最后時刻的太陽山,是共赴國難的英雄地。那一刻的李安本,更是和觀眾一起解答了心中所有的疑問。“為了泱泱中華不再受劫難,為了天下百姓不再遭禍殃。為了中國人活出個人模樣,為了中國人從此可以挺脊梁。為了繼往開來重整河山,為了華夏大地民主富強,為了紅旗招展萬民敬仰,為了太陽山上日出東方。這就是新四軍,這就是共產黨。”這一大段演唱不僅酣暢淋漓,徹底推進了李安本由小人物到革命者的身份與精神的雙重轉換,將劇情推向了最終的高潮,也以戲曲獨特的方式表達了劇作的價值主題。
劇作除了表現出一個只想過好自己小日子的普通人到革命者的轉變,更表現出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群眾路線對勞苦大眾完成的感召與啟蒙,既是個人敘事,更是對黨的群眾路線與優秀作風的禮贊。這都屬于用情感話語表達政治話語,以微觀視角與時代對話,這遠遠比單純表現小人物的轉變更有意義。
面對革命歷史題材劇作創作更高的要求,創作者如何精深挖掘,讓主旋律作品更好看,而非停留在題材選擇的層面之上?如何沿著淮海戰役如此深厚宏大的歷史背景,去深入其中挖掘和觸摸人物的生命軌跡和心靈空間?從什么樣的創作視角切入才能不停留于一般層面的戰爭故事的表現而挖掘出更深沉動人的細節?又如何解決歷史性與現實性的統一,藝術性與真實性的統一?這些永遠需要創作實踐來回答的理論問題,值得持續關注。革命歷史題材的生命力在于其藝術感染力。也就是說,無論其表現的內容是什么,都需要以藝術的形式來對其進行呈現。內容和價值是作品的靈魂,但一個優美的靈魂仍然需要優美的形式。能讓藝術作品以藝術的方式得到承認和留存的也一定是其中藝術的部分。遺憾的是,很多作品誤解了內容與形式的關系與意義,以為題材的選擇可以成為作品成功的尚方寶劍和免死金牌,從而疏忽了形式和技巧上的精雕細刻與深耕細作,假大空的作品就是在這樣錯誤的創作觀念之下產生的。
《太陽山上》一劇沒有依靠題材優勢而忽略藝術的形式。不僅沒有吃題材的老本,這部劇作在藝術呈現上還表現出高度的準確性,這體現為題材與劇種氣質和演員特色的結合。而這兩點對于戲曲作品,是避開宏大敘事和場面鋪排而走向精細化、抒情化、人性化和詩意化的一種策略,是放棄歷史場面的簡單還原,走向生動和藝術感染力的一種路徑。這樣的創作模式,是對以往優秀創作傳統的一種繼承,同時也是推進和提高。也只有這樣不違背歷史真實、也不以宣講和教育面孔出現的作品才能做到誠懇地面對觀眾,做到對歷史革命題材的真誠表達,做到發揮創作者的使命感,使革命歷史題材避免因宏大而虛假。題材的莊嚴性也因其“小視角”而能得到確立,做到貼著地面行走,貼著觀眾創作。從這樣的角度思考,《太陽山上》一劇帶給我們的啟發還應該更多,更深入,我們也因此有理由相信,在思考的基礎上會有更多革命歷史題材的優秀作品以真誠的面目出現。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
責任編輯 姜藝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