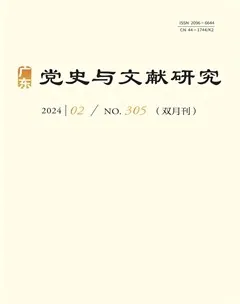皖籍進步青年的思想轉變與身份轉換
王久高?吳雨眠
【摘 要】1919—1923年,安徽相繼爆發了五四運動、六二學潮、反對第三屆省議會賄選等十數次影響較大的青年運動。作為青年運動的主體,部分皖籍青年在此過程中逐漸認識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無產階級力量的強大,思想開始由改良轉向革命,站到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上來。隨著運動目標從爭取學生權益發展到反對當局,皖籍青年進而加入政黨以尋求政治力量,在思想轉變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了身份轉換。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環節并不是單一的線性過程,也不是皖籍青年個人發展的唯一路徑。但對這一發展路徑的內在邏輯進行探析,可以回溯一代皖籍革命青年的成長軌跡,也可從中映照出安徽馬克思主義傳播和中共黨組織發展的歷史進路。
【關鍵詞】青年運動;皖籍青年;思想轉變;政治參與
【中圖分類號】K26;D2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6-6644(2024)02-0026-16
青年運動的興起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一大現象,有關于此的研究成果亦頗豐富,但多基于整體視角,即在全國范圍、全時段中闡述其發展過程,基于詳實史料的區域研究和具體個案探討仍較缺乏。在五四運動中,安徽被視為全國最活躍的地區之一。1919—1923年間,安徽影響較大的青年運動更是多達十數次。然而,既有關于安徽青年運動的研究可謂只有零星幾筆,且均微觀聚焦于狹義上的五四運動在安徽的具體開展情況、某個皖籍人物在運動中的作為與貢獻,未宏觀把握1919—1923年間安徽地區青年運動的發展軌跡,亦未考察皖籍進步青年在運動中的思想轉變和身份轉換,及其與安徽馬克思主義傳播、中共黨組織建立的內在關聯。
革命青年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鮮活體”,也是無產階級政黨在中國創建發展的實踐者。故而,本文以皖籍進步青年為主體,基于《白話書信》《五四》等一手地方材料靜態考察青年思想發展與認知進步;以安徽青年運動為窺點,動態考察青年在運動中的決策與行動以及由此帶來的自身轉變,探討一代青年在復雜時局中主動作為的“前沖力”和“后坐力”,并以此嘗試分析安徽青年運動與當地馬克思主義傳播、中共黨組織建立的內在互動關系,以期描繪這一時段安徽青年運動進退升降之全貌及運動中皖籍進步青年的群體畫像與個體面相。
一、五四運動:學生主體力量的發軔
清末民初,新式學校和班級授課的出現使學生脫離了農村私塾教育的分散狀態,聚集到城市中來,成為一種群體存在。作為五四運動早期階段的斗爭主力,青年學生通過向上請愿申訴和向下發起群眾,與社會各階級產生交集與碰撞,其作為群體存在的主體力量由此脫胎而出,五四運動也就成了這股力量形成的歷史場域。各地在響應五四運動的過程中,基于學生主體的實踐差異均呈現出鮮明的地域特征,如廣東、上海的集會游行規模之大,江西的運動秩序之井然。安徽對北京五四運動的響應極快,且持續了很長時間,皖籍青年在運動中表現出十分強硬的斗爭姿態。
1913年安徽二次革命失敗,北洋軍閥倪嗣沖踞皖,擴編兵匪、絞殺革命、克扣教育經費。同時,英、美等國在安慶、蕪湖等地創辦了多所教會學校,奴化青年思想。皖籍青年內受軍閥官僚壓制,外受帝國主義侵凌。1919年5月6日,北京五四游行的消息傳到安徽。翌日,蕪湖各校學生2000余人走上街頭,喊出“廢除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等口號,并向鎮守使署遞交請愿書,要求支持運動,電請北京政府釋放被捕學生、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等。5月8日,安慶各中等學校全體學生3000余人在黃家操場集會,結隊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北洋軍閥政府!”到5月19日,北京學聯發出全國大罷課號召。蕪湖學聯會得到消息,立即決定響應,并派代表前往安慶聯絡,以采取一致行動。安徽全省學生團還致電北京大學等校,表示“此次義舉,敝省各校學生極表同意,已電致政府力爭,務望堅持到底,敝省全體學生愿為后盾”。可見,在五四后的兩波全國性學生運動熱潮中,安徽的響應都是極快的。
當時在安慶、蕪湖、合肥求學的外地青年主要來自壽縣、金寨、六安等地,均位于長江以北、淮河以南。江北地區位置偏遠,經濟落后,故外出求學者較少。學生中,江北青年性格多剛烈倔強。而安徽青年運動中的學生領袖亦多來自這些地區,如合肥學生會會長喻石泉、安徽學聯會會長舒傳賢均是霍山縣人。青年學生,尤其是學運領袖強硬剛烈的性格特點使安徽青年運動相應展現出較強的斗爭性,這在學生群體與各方的交涉中可見一斑。
學生“鬧事”,校方必先介入管治。合肥學生籌組學聯時,到會的三個中學校長均“勸大家緩行”。當安慶學生準備上街游行時,教育廳長親自趕到學校“訓話”,認為中國積貧積弱,若據理力爭,必節外生枝影響談判。蕪湖二女師學監反對女生參加學聯,即使加入學聯也不應上街游行。如此反對之聲,不一而足。然而,“家長們”的指揮都失靈了。蕪湖萃文學校校長在學生第一次整隊游行時出面壓制,言稱“你們愛國行動,在我的學校里,我就要管”,學生齊呼“你管不了”而去。一些校長甚至請來軍警在學校附近巡邏,監視學生行動,許多運動中的中堅分子都被暗中記下名字。這是青年學生在運動中首先遭遇的反對力量,而當他們走出校門、踏上街頭時,面對的則是更為復雜的社會勢力。
各校學生開展反帝反封建斗爭最直接的行動就是抵制日貨,其中以蕪湖為首。蕪湖早于1876年即被開為商埠,作為屯轉基地,蕪湖設有三個專運碼頭,每日都有三到五只日貨輪進港,日貨充斥市場。蕪湖學聯在第一次示威游行后,積極開展抵制日貨運動,要求商家停進日貨,然毫無效果,往后幾月里日貨仍大宗涌進。學聯繼而向上要求行業工會、商會保證“全市商家不再購進日貨,如有再進,立即焚毀”,結果遭到蕪湖商會會長湯善福反對,學生代表與其多次談判無果,引起全體學生憤怒,遂搗毀商會,痛打會長,最終逼迫商會簽字同意。其實,校方和商界的行動多取向于封建軍閥勢力。當學生運動深入發展起來時,軍閥丟掉了“愛護青年前途”的幌子,對運動采取更強硬的鎮壓手段。例如,倪嗣沖在復內務部密電中指出,“各校學生亦有全體罷課情事。……如果始終違抗,即將為首各生立予革除”。安徽省長呂調元并令警廳立發布告:“如有糾眾滋事紊亂秩序之行動,依法逮懲……遇有學生發布傳單違法紀而不服取締者,一經查出,即行依法嚴辦,絕不姑寬。”但此威脅恐嚇并不奏效,“傳單密布,且益加多”,可見安徽學生運動斗爭之剛強。
當青年學生組織起來以主體力量沖擊社會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后坐力”。這一時期的青年“大都受過‘五四時代的教育和訓練,而且多因參加這次運動才開展他們一生的事業。這次經驗一直影響他們的思想和心理”,皖籍進步青年亦如此。五四運動前,安徽青年學生“只是埋頭讀書,追求知識,希望學得一些本領,將來升學找事,還有可靠的本錢。因之,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群眾關系、‘集體觀念。……那些問題怎樣產生,該應怎樣去解決,那里有什么出路,什么才是真正的出路,思想上都是模模糊糊的”。周新民也認為自己在五四運動前的思想很落后,對于該走什么樣的政治道路也不清楚。而在運動中,部分學生直觀地見識了社會各階層的反應和態度,這才真切明白軍閥政治之黑暗腐朽,資產階級之軟弱動搖,更改變了對群眾的認識。例如,1919年6月3日,反動政府逮捕學生達2000人以上,激起全國憤怒。上海實行罷課、罷市、罷工,表示抗議。對于響應“六三”運動,安徽各界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封建買辦集團,寧肯出賣祖國,也不肯損失自身利益;中小商人,有一定愛國行為,但動搖性大;店員學徒,大多具有愛國熱情和民族正義感,積極配合學聯響應運動,在商店內部組織活動。面對商會召開緊急會議制止罷市,店員堅決對抗,任憑解雇也不妥協。其中,最積極的是工人。由于受到愛國宣傳影響,多數工人已自動結合起來。如碼頭工人,協助學生檢查日貨,寧肯失業挨餓,也拒絕為日商運貨;旅棧業工人,不到大阪輪船接客,勸阻旅客不要購買大阪客票;黃包車工人,不拉日本貨,不接外國人。故而,周新民又說:“到了‘五四運動爆發以后,我才為愛國熱情所驅使,走出學校大門,參加了學生運動。在學生運動中,使我不斷受到教育和鍛煉。……如果沒有‘五四運動來引導我,我一定要走不少錯路,絕不能早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
安徽的愛國運動持續了近5年時間,宣傳方式和運動形式也逐漸規整。在抵制日貨運動中,安徽學聯建立起四個組織:設立國貨檢查所,專門查搜到港貨輪,使絕日貨來源;開設國貨販賣部,售賣學生手工制品,以示學生愛國熱忱;創辦義務小學,培育勞動人民子弟,向家長宣傳愛國反日思想;組織街頭宣傳隊,輪流上街演講,以喚起群眾反日。到1923年5月,安徽學生為紀念五九國恥、收回旅大決定開展“五九”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貨運動,“由于這是個有組織有準備的反帝運動,使其超過以往任何一次”。總體觀之,皖籍進步青年在運動中處理各類矛盾、應對各種問題、接觸各式人群,見識得以增長,個人能力素質也發展起來,為在安徽持續發動學生運動奠定了基礎。周新民后來回憶說:“安徽學聯初成立,即能有計劃有步驟地做了上述一系列的工作,主要原因是有一批進步青年如王步文、方樂周等骨干人物。……在先進的思想指導下團結廣大青年,孜孜不倦地進行工作,這就為后來教育革新、‘六二慘案、推翻三屆省議會、驅逐李兆珍等斗爭創造了條件,也為中國共產黨在安徽建立組織打下了基礎。”
二、新文化運動:主義探索與思想轉變
五四運動不僅是學生主體力量的濫觴,亦是新文化運動的轉折點。通常認為,以五四運動為標志,新文化運動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馬克思主義逐步在思想文化領域發揮指導作用。這說明青年學生在初始組織起來時,即面臨著思想上的轉向問題。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1904年《安徽俗話報》的創辦是陳獨秀“開通民智”思想的試水。其中內容所及,大體可歸為四個方面:一是反帝反封建,二是提倡文學改革,三是主張改良國民教育,四是呼吁發展實業,富國強兵。對于《安徽俗話報》的出版,社會評論各別,“同人皆頗歡迎,而局外則多訾議”。少數開明官吏利用它來開啟民智,績溪縣“捐廉購辦,隨同官報發行,聽人采取,并望大家傳閱”。進步青年最為歡迎之,“尤可感者,桐城崇實學堂同學諸君,集資月購本報百余份,以分送其鄉人”。高一涵后來追敘:“起了組織革命和宣傳革命的作用。”
陳獨秀、章谷士、汪孟鄒等人是青年運動的先行者,“那時也是二十幾歲的少年,為革新感情所趨使,寄居在科學圖書社樓上,做《安徽俗話報》,日夜夢想革新大業”。從《安徽俗話報》到《新青年》,從上下求索的少年成長為領導新文化運動的中流砥柱,陳獨秀等人作為在世紀之交中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其思想經歷了由資產階級改良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復雜過程。安徽的新文化運動也隨之經歷了一個由內向外到由外向內的過程,即陳獨秀早年創辦《安徽俗話報》以批評時事、開啟民智,從蕪湖發行至全省而至全國,總體來說還帶有鮮明的本土性,體現的是一代皖籍青年的革新志向;11年后,陳獨秀創辦《新青年》以提倡民主、科學,繼而宣傳馬克思主義,從上海、北京傳至安徽,此時已具備強烈的引導性,體現的是一代思想先驅對青年的指引和推動。
由于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亦是皖籍出身,這使皖籍青年與新文化運動之間平添了一層地緣聯系。如在接觸進步刊物方面,1913年,汪孟鄒到上海開辦亞東圖書館后,將科學圖書社事務交由陳嘯青主持,實際上就是亞東分店。除經售除亞東圖書館、泰東書局出版的新書外,凡上海、北京出版的雜志,幾乎都有,更是《新青年》的第一批“代派處”。諸如《中國魂》《明治維新史》這一類書籍,安徽多數學生均已看過。科學圖書社每到新書雜志,則爭先搶購。此外,陳獨秀與安徽知識分子,尤其是進步教師聯系密切。陳獨秀在離開安徽時,曾對劉希平、高語罕、朱蘊山等人說:“我去搞全國性的運動,你們在安徽搞反軍閥運動。”當時,劉希平和高語罕在蕪湖五中任教,一致認為“當前的任務應該爭取在校機關長期埋頭下去,從改革教育,培養青年入手,通過普及國民知識,提倡新文化,竭力而慎重地介紹新思潮,去提高青年們要有社會責任心的覺悟”。因此,與他省青年主要通過閱讀進步書刊接觸新文化、新思潮不同,皖籍青年在接受新思潮的過程中更多受到進步教師的直接引導。
五四運動前,各種思想、各家學派、各類主義的書籍,都從國外介紹過來,學生辨別能力有限,讀完不免一時思想混亂。例如,在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下,蔣光慈與胡蘇明、吳葆萼、李宗鄴等人組織了無政府主義團體“安社”,并編印社刊《自由之花》,猛烈抨擊軍閥統治,鼓吹無政府主義。蔣光慈還曾一度沉迷于宣傳俄國虛無黨暴力主義的《夜未央》,并寫詩表白書中女主角:“此生不遇蘇維亞,死到黃泉也獨身。”五四運動后,科學圖書社雖積極經銷《共產主義ABC》《辯證唯物論》等馬克思主義書刊,但統治當局對此檢查很嚴。為使學生能直接讀到社會主義書籍,高語罕將河上肇所譯《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入門》和克卡樸所著《社會主義史》等書帶回五中給學生們閱讀。1920年,惲代英到宣城四師任教,親自指導學生閱讀《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剩余價值學說史》等各種進步書刊,并要求學生讀后撰寫心得,定期舉行社員會議分享讀書感想。同時,一些學生也開始主動收集革命書刊,如安慶一師王步文就在宿舍辦了一個秘密圖書組,使《共產黨宣言》《唯物史觀淺說》《湘江評論》等書刊在進步青年中得到廣泛傳播。
此外,高語罕、劉希平還鼓勵指導學生籌款辦義務學校,教師從學生中推選,如“吳葆萼、胡蘇民、蔣光慈等,大家輪流去上課”,學生則多是商店學徒、店員和貧民子弟。蕪湖商業夜校設有國文、英文、數學、商業通論等七門課程,國文選用教材,除《新青年》等進步雜志上刊登的文章外,還有高語罕自編的《白話書信》。高語罕在書中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以通俗易懂的語言介紹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知識。并且,此書對工人貧民的苦難生活著墨較多,認為“要把現在社會的經濟組織從新改造,必須要先使勞動者對于本身的價值和‘階級斗爭的意義有徹底的覺悟。他們一旦覺悟,自然會起來改造不平等的一切社會的組織”。在此影響下,蕪湖商業夜校建立起“學徒聯盟”,聯合向店主提出要求,組織罷工。蕪湖各校學生在開展抵制日貨運動過程中,也曾得到商業夜校學生的幫助。
值得一提的是,《白話書信》輯錄了大量皖籍青年的往來信件,從中或可直觀捕捉其思想動態。如李宗鄴認為“人的一生,必須要發現現象界一椿神秘——真理——這里自然離不去‘奮斗”,不然“決不能探出‘真理”,“馬克思餓病在床上,還在執筆完成他的資本論。……能有敢自殺的魄力,才能做成不容易做的事業”。胡蘇民則言“偽文化運動家是沒有希望的;他的文化運動是他的方法,不是他的目的”。廖天一梳理了社會主義的定義與各派別分異,提出“至于我們中國現在的情形——政治,社會,經濟,哲學等——是否有采行社會主義的必要,另是一個問題;若有采行的必要,那一種社會主義——有產?無產?有政府?無政府?——可以適用,又是一個問題”。蔡戡天也認為研究社會主義“千萬要把里面的派別弄清楚了”,并“要處處以我們所處的社會做印證,看看那一派的社會主義適合我們現在的社會,就是那一派的社會主義,可以醫我們現在社會的病”。
此外,皖籍進步青年創辦宣傳反帝反封建的刊物,是推動安徽新文化運動發展的重要方式,亦可作為了解當時青年思想的一種通道。《蕪湖學生會旬刊》的發刊宣言表明了當時學生對于眾多社會思潮的態度,即對于舊的一切不愿無意識地服從,對于所謂新思潮也不愿盲目信仰,對各類事物都持懷疑態度。第二期中的《青年與新潮》一文表示青年學生對于新舊文化的激戰覺得可喜又可懼,可懼在于青年知識不多,不能辨別各式主義,倡導青年應當平心靜氣地研究,等有把握再做定奪。《安徽第六師范周刊》則以“利用這個周刊做新文化運動的工具”為唯一宗旨,其第21號勞動節專版中闡述了勞動的重要意義和勞動者在階級社會中的困苦生活,指出勞動者必須團結起來以謀求自身解放。專號還指出當前斗爭的具體目標應是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工資和改良待遇,且必須逐步提高勞動者的文化水平和階級覺悟以更好地開展勞動運動。朱蘊山通過創辦《評議報》評議安徽政局,宣傳革命思想,積極推動安徽省反帝反封建愛國主義運動,該報刊后來成為安慶青年團組織的喉舌。
由此可見,五四運動后,皖籍進步青年面對風起云涌的社會思潮尚且缺乏辨別能力,對探尋救國道路在思想上仍有模糊和局限,但對勞動群眾的認識和同情卻著實提高了,開始主動深入到工人和其他勞動群眾中去。在此過程中,一方面,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第一次對華宣言給皖籍青年帶來了巨大沖擊;另一方面,高語罕、劉希平等進步教師為其提供了新的思想資源和實踐引導。一部分皖籍青年逐漸認識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無產階級力量的強大,思想開始由改良轉向革命,站到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上來,進而向外宣傳馬克思主義。
需要指出的是,真正的思想轉變是一個復雜甚至些許漫長的過程,皖籍進步青年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救國的指導理論,并不意味著他們深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原理,而多與當下時局和個人社會實踐經歷相關。例如,皖籍北大學生蔡曉舟、楊亮功與教授陳獨秀、高一涵等交往密切,并深受其影響。五四運動中,蔡曉舟、楊亮功與北大學生一起參加游行示威,并在五四運動爆發兩個月后共同編撰了《五四》一書,詳細記錄了五四運動的經過和各地響應情況。蔡曉舟在《文化運動與理想社會》中有這樣一段論述:“我們理想的社會,凡是具人的性靈,和人的形體,都應該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住一樣的房子;求學和做工的時間,都應該平均一樣多。但是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因為行的是資本制度,就不是這樣了。……達到我們理想的社會,自然要從打破資本制度運動起了。現在這項運動,總括說起來,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項是強權轉移的運動;第二類是同化的運動,即是拿泛勞動主義,無抵抗主義,來同化全人類的。第一類運動,現世界中已有成功而且震動環球的,就是我們北鄰的新俄國。……第二類運動,我國已經發現的:有北京工學互助團;北京工學互助團第一組已經失敗,是因為它的分子,缺乏職業上的技能,并且組織法也未盡善。”顯然,當時蔡曉舟還未能辨別泛勞動主義、無抵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根本差異,對于理想社會的設想也帶有空想主義的色彩。但受到工學互助團實驗失敗及其參與五四運動的實踐經歷影響,蔡曉舟認為“現在想要推翻軍閥財閥,應當先把自己的士大夫架子放下,去與勞動者為伍”,并響應“到民間去”的號召,于1920年秋回到安慶,開辦文化書店,領導群眾運動。
三、反軍閥運動:介入政治與加入政黨
新式學校的學生集聚化是一個自然過程,而五四運動中產生的學生組織化是一個自覺過程。“各校在運動爆發之前,校與校之間,班與班之間都很少往來,甚至有不團結現象。運動開展以后,都站到一起來了,一個學校,結成一個整體。各個學校聯合起來,成為一個戰斗集體。學聯會起了統一指揮的作用。”學生聯合會是五四運動中產生的新型事物,是學生主體力量的組織體。通過學聯,皖籍進步青年與學校、政府交涉,表達訴求,組織發起多次學生運動。從爭取學生權益到尋求政治力量,部分青年在思想轉變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了身份轉換。
1920年,倪嗣沖借口軍費不足,擬辦三種附加,并向省議會提出“鹽斤加價”議案,群情大駭。安徽學聯立即發動群眾堅決反對鹽斤加價,省議會因此最終未通過此議案。當時安徽設有“公益維持會”,地方土豪劣紳、政府公職人員無不視其為爭權奪利的捷徑而競相加入,以至學校校長也多是它的成員,視學校為厘金差缺,公開貪污,壓制學生。反對鹽斤加價的勝利鼓舞了學生斗志,安徽學聯進一步提出教育革新的要求,號召各校學生驅除充當倪氏爪牙的校長。
一年前,安徽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就發起過驅逐校長運動。當時的法專校長張某是個貪污腐化的官僚,辦事只知秉承倪嗣沖意旨。周新民、童漢璋等學生遂發起反張運動,將張某驅逐離校。到1920年秋,繼任校長丁述明仍是個腐敗官僚。法專學生罷課、教員罷教達40多日,一致要求改派光明甫來當校長,安徽旅滬同鄉會又推派張鴻鼎、汪升潛回皖協助,省當局被迫同意。同時,安慶一師學生方樂周等也堅決反對省議會副議長趙繼椿兼任校長,要求調派李光炯來接管該校。法專、一師改組的消息傳到蕪湖,五中學生立即罷課,要求改派劉希平代替潘光祖來任校長,也達目的。
當時,有某教育界人士認為安徽教育不振有兩點主要原因,一是“軍事與教育相混:吾皖督軍屢易,兵事連年。實業學校也、測量學校也,則停歇之;高等學堂也,優級師范也,則縮小之”,二是“政治與教育相混:以一端論之,各議員之兼校長職是也。……既為議員,必不能專心致志,從事教育”。驅逐校長運動即反映了安徽軍事與教育相混、政治與教育相混的特點,這也是六二學潮爆發的導火索。
1921年,安慶學生和教育界人士以必須增加教育經費、提升安徽教育為由,向政府交涉。財政廳長與省議會議員聲稱剩余省款已移墊軍用,拒絕增加教育經費。而實際情況是倪道烺等準備將剩余省款給公益維持會作為三屆省議員賄選之用。6月2日,省會各校學生推舉代表再次前往省議會請愿,副議長趙繼椿出見,盛怒拒絕學生請求,下令軍警毆打學生,當場受傷50余人。慘案發生第二天,安慶學生罷課、教員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一致表示憤怒。省教育會、學生聯合會、學生總會通電全國,將安徽軍閥的丑惡行徑與詭計公之于世,以求各省支援。當時上海《申報》《新聞報》等報刊都以顯要版面刊登六二學潮消息,各省群起多發援助之聲。學潮既已擴大,反動政府若不根本解決學生訴求則難以收場。教育界提出在慘案提交法院判決以前,政府必須維持此次增加教育經費案且省議員不得兼差,政府均予接受。雖倪道烺等人并未立即受到判決處置,但教育會、學生總會等認為最初目的已達,運動至此可暫告一段落,遂宣告復課。
“教育與政治相混”并非安徽教育不振之切要,軍閥政治的腐敗才是其癥結所在。教育作為意識形態統治中的重要環節,自然與政治掛鉤,故而“教育問題仍然是一個政治問題”,“要革新教育,便須同時革新政治”,部分青年學生在六二學潮的潦草收場中逐漸意識到這一點。如有青年直呼“自由之城,建筑在革命流血之上;不是和平的手段所能造成的。為請愿而死,何若為革命而死?愛和平的兄弟姐妹們!經過這一回教訓,到今天還不覺醒嗎?”此外,胡適在為六二學潮中犧牲學生姜高琦所作詩中表達了對死者的致敬與哀悼,但亦更為強調“請愿而死,究竟是可恥的。我們后死的人,盡可以革命而死,盡可以力戰而死。但我們希望將來,永沒有第二人請愿而死”。
六二學潮后,正值倪道烺、馬聯甲所御用的第二屆省議會期滿解散,即將選舉第三屆省議會。倪、馬二人決議把持“公益維持會”為其效命,謀劃賄選活動。安徽省學聯隨即發布通告,表示學聯將組織監視團監督省議會選舉。當時省議會選舉法中有一條規定,即省議員選舉只要有一縣無效,則全部無效。安徽學聯抓住這一點,發動安慶、蕪湖等各地學生利用暑期返鄉時機,搜集各種舞弊證據起訴。各地法院以選舉案太大,一時不敢進行審判。倪道烺逼迫省長聶憲藩召集第三屆省議會,聶憲藩懾于六二學潮余波不敢召集,被迫辭職。倪道烺即以40萬元賄賂國務總理靳云鵬,以使其老師李兆珍做安徽省長,意在召集議會。安徽學生得到消息,立即向群眾宣傳演講,號召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并組織隊伍上街游行,包圍省署,高呼驅李口號,最終逼迫李兆珍逃出安徽。繼任省長許世英為人圓滑,對召集議會兩面敷衍。在許拖延不決之時,無為縣選舉經法院宣布無效,接著桐城、舒城、六安等地也作出同樣決定,安徽政府不得不宣布由賄選產生的第三屆省議會無效。如此將已選出的議員全部算作無效的,“在中國還是第一次”。
不難發現,在經歷了五四運動、六二學潮后,皖籍進步青年在反對第三屆省議會賄選中表現出更強的組織性和斗爭意識,善于運用正確的策略,動員各方力量共同促進運動目的之實現,安徽學聯在發動領導學生斗爭的過程中亦逐漸成熟。在斗爭策略方面,在驅逐李兆珍運動中,學聯推舉專人籌劃并領導運動。在李兆珍到皖前,學聯組織建立“糾察隊”“義勇團”,日夜巡視江岸。在李兆珍喬裝入皖后,學聯立即聯合教員召開緊急會議,制定驅逐李兆珍方案,計劃縝密、行動迅速是這次運動取得勝利的關鍵。在反賄選斗爭中,學聯利用選舉法條例組織學生收集證據起訴,合法有據地成功抵制了第三屆省議會賄選。在斗爭組織方面,在六二學潮后,安慶、蕪湖等地各校增派了一批代表,如一師許繼慎、楊溥泉等,一工舒傳賢、趙唯一等,二農薛卓漢等,二女師沈紹芬等,以加強安徽學聯的領導。同時,改選舒傳賢為會長,周新民為副會長。另外,在各校運動宣言中也可一窺新文化運動對皖籍青年的影響。1919年,蕪湖學聯發布五四運動宣言書,雖“各正襟敬掬誠宣告于我全國父老諸姑伯叔兄弟姊妹之前”,然宣言通篇文言,于普通群眾而言實在晦澀。到1921年,六二學潮的罷課宣言則使用了白話文,文字直白生動,頗具感染力。如在陳述六二慘案過程時連問五個“我們能忍不能忍”,又如“我們亦只得以我們的頭顱和血,同他們周旋,求最后的解決,才無負于學生們為國家根本的教育上流了這么許多血”,再如最后結尾呼喊“諸君啊,快醒醒罷,快起來罷”。
革新教育運動是反對封建軍閥的一個側面,驅逐校長、增加教育經費還停留在爭取學生權益層面,與軍閥在政治上尚未發生直接對抗,而反對賄選則帶有明顯的政黨意味。李大釗認為“因為政治不澄清,使我們不能不犧牲求學之精神,而來干涉政治”,學生應“組織民眾,以為達到大革命之工具”,并“對現政府立于彈劾的地位”。也就是說,與軍閥斗爭,需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實行社會制度的革命。在這一點上,學聯作為學生組織就失去了政治斗爭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這進一步促使部分青年學生加入政黨以尋求政治力量,亦是此后學生運動政治化的重要緣由。
1921年初,安慶社會主義青年團建團籌備會在懷寧縣召開,由蔡曉舟、劉著良主持,到會的有一師學生方樂舟、許繼慎,一工學生舒傳賢,法專學生童漢璋、宋偉年等20余人,其中多為省學聯骨干。同年4月,安慶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在菱湖公園召開,成為全國最早建立的17個地方團組織之一。1922年,安慶地方團定名“安徽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時團員9人組成學生運動委員會,負責組織領導學生運動。周新民回憶說:“由于有了團的組織,加強了安徽學聯的政治領導,所以在‘六二慘案、驅逐李兆珍、推翻三屆省議會的一系列斗爭中,才取得了勝利。”
然而,安徽青年團的發展并不順利。1922年冬,安徽省長許世英為疏解學生運動壓力,決定官方資助一批學生骨干赴日留學。這一舉措實則釜底抽薪,使人數本就不多的安慶團組織陷入渙散。1923年春,陳獨秀派柯慶施回皖開展黨團工作。柯在關于安慶地方團第一次報告中指出,安慶地方團團員“甚消極,而且他們與政治上的關系——保守派——很深”,并決定“從新做起,另找同志”。而到1924年,安慶團組織的情況仍不容樂觀。薛卓俊在給團中央的信中提到,“自去年學潮平靜后,分校隨解散,校長及各職教及多數同學均不能留皖。……在此大力壓迫之下,最近期中,分校難于成立矣”,并感嘆“奈此地青年消沉已極,恐一事不能舉矣!”安慶團組織陷入沉寂固然與周新民、舒傳賢、朱子帆等赴日留學所導致的團員骨干流失有莫大關聯,但這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了這一時期革命青年骨干的稀缺和青年政治立場的搖擺性。
對于安徽地區黨組織的建設情況,1923年11月的中共《中央局報告》指出:“安徽國民黨分兩派,均不得社會的信仰,現需有能力者前往另行組織。”同年冬,在上海大學入黨的薛卓漢、徐夢秋回到壽縣,與曹蘊真等人共同組織成立了安徽第一個黨支部。特支以小甸集小學為活動中心,創辦了幾期農民夜校和識字班,入學者大多為青年農民。到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規定改組國民黨之各項原則,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安徽的中共黨組織和青年團即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動員黨、團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并幫助國民黨在青年群體中發展黨員。根據1923年11月形成的安慶團員調查表,登記在冊的團員22人中,只有柯慶施和許繼慎已加入國民黨。到1924年4月,蕪湖團員調查表登記的46名團員中,則有31人已加入國民黨,未加入國民黨的15人也幾乎都是同年剛入團的新團員。到1926年1月,安徽地區已建立國民黨市黨部有二、縣黨部有三、臨時縣黨部有四,新發展國民黨人數1700有余,且大多為學生黨員。
總體來說,在這一時期青年運動的發展過程中,皖籍進步青年逐漸將參加新式政黨作為革新救國之途徑,雖具有一定的主動性,但這種身份轉換亦存在不可忽視的盲目性,這種盲目性或可歸結于思想認識上的模糊。一是表現為青年在選擇加入何種政黨時,不能厘清各政黨性質和綱領的本質區別;二是如上所言,這一時期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者甚少,有些青年團員、中共黨員對于中國共產黨究竟要做什么也沒有完全弄清楚。故而,待“國共兩黨由合而分,原有加入政治活動的師生,政治立場遂告分化”。
四、青年運動與運動中的青年:群體趨向與個體選擇
縱觀1919—1923年,安徽相繼爆發了反對鹽斤加價運動、易長運動、六二學潮、反對第三屆省議會賄選、驅逐李兆珍、反對曹錕賄選等十數場青年運動。學生青年和知識青年是這一時期青年運動的主要發起者和參與者,運動目標從抵制日貨、增加教育經費發展到打倒反動軍閥、維護群眾利益。陳獨秀在《安徽學界之奮斗》一文中說:“豬仔議員全中國各省都有,獨有安徽學生加以群眾的懲戒,……這一方面當然顯出安徽學界還有點生氣,他方面卻顯出別省的學界太無生氣了”,并高呼“此時安徽學界的生命已放在軍閥的炮口,全國的學界竟始終袖手觀嗎?”可見,當時安徽學界,尤其是青年學生在反軍閥斗爭中尚有一番作為。
參與青年運動,以請愿、游行示威、罷課抗議等方式表達訴求是當時青年的一種群體趨向,這在青年運動的爆發次數和參與人數中可見一斑。而運動平息后,青年學生在自身發展道路的選擇上卻存在較為明顯的個體分異。
筆者共搜集30位曾參與運動的皖籍青年。出生時間集中在1896—1906年間,尤以1899—1902年出生為眾,多達半數。其中年紀稍長的,或入學較早的,幾乎都參加過五四運動。當時,他們多為17~20歲,最大不過23歲,最小者才13歲。出生地較集中于皖西地區,其中壽縣9人、六安縣6人、霍山縣2人、合肥縣1人,另有12名青年來自涇縣、宣城、蕪湖等皖南地區,多數出身于農民家庭。
這些進步青年個人發展道路的初期選擇分異大體有三類:一是升學,如王紹虞、王逸常、薛卓漢、徐夢秋、胡允恭等升入上海大學,楊溥泉、許繼慎、毛正初、曹淵等升入黃埔軍校;二是出國留學,如常萬元赴法留學,湯志先、童漢璋、舒傳賢、周新民、朱子帆、祖晨、王步文等赴日留學,蔣光慈、吳葆萼、王培吾、王稼祥等赴蘇留學;三是返鄉工作,如李克農、喻石泉等在安徽領導開展農民運動,建立根據地,發動起義。大部分人仍處于校園環境中,此間差距尚不明顯。但此后在面對大革命起伏跌宕的洪流時,這些曾經共同參與過學生運動的青年們則做出了差別迥異甚至截然相反的選擇。在所取青年樣本中,除常萬元、湯志先外均已加入中國共產黨,多數青年學生如薛卓漢、徐夢周等在畢業或回國后回到安徽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黨組織工作。其中有半數如喻石泉、祖晨、舒傳賢、楊溥泉、許繼慎、周狷之、王步文等為革命付出生命;部分投身教育研究事業,如吳葆萼、蔣光慈、常萬元等;少數人如王逸常等中途脫離中國共產黨,轉投國民黨。探究個中緣由,可能有以下三點因素:
一是家庭出身,包括家庭經濟情況、家庭成員思想觀念、早年成長經歷和社群環境等,這是遠因。例如,曹蘊真幼年時就讀于鄰村開明人士、同盟會成員張樹候門下,受其影響,曹蘊真心中向往社會改革。薛卓漢則是父輩幾人都加入了同盟會,從小深受愛國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后來,曹蘊真和薛卓漢均回到壽縣,共同創立了安徽第一個黨支部。
二是運動實踐,包括在運動中的負責事項、見聞和人緣際遇等,這是近因。例如,1919年,常萬元作為安徽學生代表前往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大會,當時孫中山正在上海指導學生運動。常萬元通過黃大偉與孫中山取得聯系,孫中山對常萬元說:“中國的未來,中國的命運,這些重大的責任,完全落在你們這一代青年身上了,你們要學科學,要愛國,不學科學,你們雖有愛國之心,但力量不夠,作用也就不大。”在孫中山安排下,常萬元由前往法國勤工儉學,改變從政初衷,立志學農。1925年回國后從事桑蠶、畜牧、煙草業領域的研究教學。而周新民、舒傳賢、朱子帆等人赴日留學則是安徽省政府官僚疏解學生運動壓力的對策,即教育廳以學聯負責人和學運領袖“連年為國事省事奔走犧牲”為由,決定官方資助其赴日留學。
三是思想立場,包括對各種主義的辨別理解、對社會的考察認知、對人民群眾的態度等,這是核心因素。例如,周狷之出生于六安有名的大地主家庭,在校時參與了六二學潮、反賄選等學生運動。他常向佃戶、雇工宣傳“土地歸農,耕者有田”的思想。父親讓他去佃戶家定租收課時,他有意減收或不收。還因此被當地土豪劣紳戲稱為“周家敗家子”,周狷之則批駁“為富不仁的封建家庭必敗之”。1926年,周狷之受黨組織派遣,返回家鄉開展農民運動,創建秘密農民協會和農民夜校,建立縣總工會。1927年,周狷之參加領導六霍起義,為創建皖西根據地和霍山縣蘇維埃政府做出了重要貢獻。1930年,周狷之由于叛徒出賣被捕,面對高官引誘和嚴刑拷打毫不動搖,英勇就義,犧牲時年僅30歲。又如早期推崇無政府主義的蔣光慈到莫斯科大學后,通過深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轉變了思想,認為“來這里學習,就是為了在不久的將來幫助我國人民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原則,同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作斗爭”。1924年蔣光慈回國,中共中央根據其興趣專長與個人志愿,將其分配至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后亦成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主要籌建者。
總體來看,能否始終同工農群眾結合、堅持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是這些青年人生走向的分水嶺。而這一時期,能夠掌握馬克思主義并主張無產階級革命的青年學生還是極少數。能在青年運動中實現思想轉變和身份轉換,與工農群眾結合,走無產階級革命道路,也只是其中一種發展路徑和人生走向。但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對于各類主義及各式政黨的認知偏差和思想曲折,實則是中國革命的客觀復雜性在青年主體認識中的反映,而把握真理本就要經歷一個從實踐到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曲折反復過程。因此,對于此間青年的認知偏差與行為偏向,實則無可厚非。
五、結語
有學者對1919年后十年的學生運動進行了階段劃分,認為1919—1922年為五四式學運時期,1923—1924年為學界與北京政府對抗加劇時期,1924—1927年為政黨運動學生時期,1927—1929年為學運消沉與中挫時期。總體觀之,本文所涉1919—1923年安徽地區的青年運動之發展走向與此大抵相符。在這個意義上,安徽青年運動的確處于全國青年運動發展軌跡的回歸線上,但這并不意味著可將其視為全國青年運動的縮微模式。安徽青年運動在與全國青年運動整體走向趨同的同時,仍呈現出鮮明的地域特點。綜上所言,這具體表現為:一是由于皖籍青年與新文化運動核心人物、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間具有地緣聯系,這使得皖籍青年在接受新思潮、加入政黨的過程中更多受到進步教師、知識分子和中共黨員的直接引導。二是運動斗爭性強,這一方面取決于安徽青年的文化性格,尤其是學運領袖剛強的個性特點;另一方面是由于軍閥倪嗣沖踞皖,克扣教育經費,議員兼任校長、教師,安徽教育頹靡,學生只得強硬抵抗以爭取自身權益。三是運動較早強化政治斗爭,皖籍進步青年于1921年即發起反對第三屆省議會賄選運動,而全國性的反對直系軍閥曹錕賄選運動起于1923年。也就是說,在“學界與北京政府對抗加劇”之前,安徽學界已與當地政府展開了政治斗爭。四是愛國運動持續時間長,到1923年安徽反日貨運動仍在繼續,并設立了國貨檢查所、國貨販賣部等專門部門以更好組織領導運動。
而將其放歸于青年運動的整體視域中去,宏觀視之,皖籍進步青年發起、參與運動或可反映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青年對待社會事件的直觀態度,這是淺層次的。巴黎和會失敗,青年學生爆發五四運動,實則是其對反動政府賣國行為的不滿和愛國情緒的直接表達。但對如何救國這個問題,共同參與五四運動的青年卻有不同的回答,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激進方式在當時也并不流行。第二,青年學生與各社會階級之間的關系,這是中間層次的。比如,反對安徽省議會賄選運動中學生對軍閥親屬官員的抵制;支持黃包車工人大罷工運動中對工人的支持同情和對資產階級剝削的批判;開設工讀學校招收店員以爭取小資產階級。盡管這些關系導向在當時并非全是自覺行為,但一定程度上折射了青年學生的思想進路。第三,青年發展與國家命運之間的關系,這是深層次的。毛澤東后來在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會上提出了判斷青年是否革命的標準,“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并指出延安的青年運動是全國青年運動的模范和方向,因為延安的知識青年、學生青年、工人青年、農民青年都是團結統一的,而且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張太雷在《青年運動的使命》中更是首先將青年運動與中國革命聯系起來,指出青年運動的使命“不僅是以謀青年的福利為中心的目的,乃是以謀全國的福利,當作他任重道遠的事業。簡括言之,他的使命就是革命的事業”。
[王久高,法學博士,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吳雨眠,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葉浩豪)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y and Identity of Progressive Youth of Anhui
——Taking the 1919—1923 Youth Movement in Anhui as the Centre
Wang Jiugao Wu Yumian
Abstract: From 1919 to 1923, several influential youth movements broke out in Anhui, includ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June Second Movement and the opposition movement against bribery of the third provincial council. As a major force of the youth movement, a section of the Anhui youth gradually realized the scientificity of Marxism and the power of the proletarian, which shifted their position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As the goal of the movement developed from fighting for the rights of students to opposing the authorities, some of the youth began to join political parties to seek political power and further transformed their identity on the basis of the change in ideology.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above links are not a single linear process, nor is it the only path for the personal development of the youth of Anhui. However,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is development path can retrace the trajectory of a 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y youth of Anhui and reflect the history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Anhui.
Key words: youth movement; youth of Anhui;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