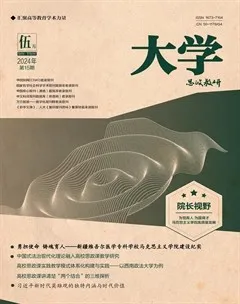感性引導(dǎo)與事實(shí)判斷:情與理何以統(tǒng)攝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體系
基金項(xiàng)目:本文系2023年教育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青年基金項(xiàng)目“艾利斯·揚(yáng)的新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xué)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23YJ C710051);2023年國家民委高等教育教學(xué)改革項(xiàng)目“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全過程融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課程教學(xué)的邏輯與方式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23009);中央民族大學(xué)青年學(xué)術(shù)團(tuán)隊(duì)引領(lǐng)計(jì)劃項(xiàng)目“中國共產(chǎn)黨中華民族觀的觀念建構(gòu)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2023QNYL11)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劉怡婷(1999—),女,碩士在讀,中央民族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研究方向?yàn)轳R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摘" 要:情與理是正確理解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體系的重要維度。情體現(xiàn)著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體系的應(yīng)用與方法,表征著跨越主體的共情能力;理體現(xiàn)著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體系的學(xué)理化,顯現(xiàn)出提升話語解釋力的路徑。共情與說理的內(nèi)涵與外延并非模糊不清乃至分離,而是通過二者有機(jī)融合實(shí)現(xiàn)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體系的進(jìn)一步構(gòu)建,提升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體系的共情力與說理性。以“何以為是”“何以為要”“何以為踐”為指引,通過勾勒共情與說理的概念發(fā)端、內(nèi)在區(qū)別、共生共存,進(jìn)一步厘清了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體系中情與理的向度。堅(jiān)持課程話語內(nèi)容政治性與學(xué)術(shù)性的共生,個(gè)人話語語境宏觀與微觀的重合,教學(xué)話語方式剛性與柔性的并濟(jì),實(shí)現(xiàn)共情與說理的契合,從而實(shí)現(xiàn)了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體系的情理交融,真正達(dá)成教學(xué)目標(biāo)。
關(guān)鍵詞:思政課話語體系;共情與說理;情理交融
中圖分類號(hào):G641"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 文章編號(hào):1673-7164(2024)15-0039-04
馬克思曾經(jīng)在《〈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導(dǎo)言》中首次提出“以理服人”應(yīng)當(dāng)始終貫穿于無產(chǎn)階級(jí)的思想政治工作之中。而面向新的歷史方位,對(duì)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進(jìn)行新的思考,是有效破解內(nèi)化與外化教育困境的前提。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下的一門重要學(xué)科,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話語體系中的情理之維既是相互獨(dú)立的關(guān)系,又是相互交融的整體。然而,在當(dāng)下的思政課教學(xué)實(shí)踐中,存在著共情與說理割裂的現(xiàn)象:過于注重共情而忽視說理,會(huì)使學(xué)生難以在學(xué)術(shù)層面領(lǐng)略思政課話語體系的獨(dú)有理論魅力;過于注重說理而忽視共情,則使學(xué)生出現(xiàn)輕價(jià)值性教學(xué)話語、重事實(shí)性教學(xué)話語的傾向,使得學(xué)生對(duì)思政課內(nèi)容的理解浮于表面,不利于領(lǐng)會(huì)思政課話語體系傳達(dá)的真實(shí)意蘊(yùn)。打破思政課話語體系里的講共情而不論說理,唯說理而不重共情的局面是當(dāng)下亟待解決的難關(guān)。因而,實(shí)現(xiàn)思政課話語體系的情理交融,是學(xué)界面臨的重要問題。
一、何以為是:思政課話語體系中共情與說理的透視
(一)情理之源:共情與說理的概念發(fā)端
共情與說理均由中國哲學(xué)延伸而來,具有濃厚的闡釋學(xué)意義。重情是傳統(tǒng)中國的特質(zhì)之一,以儒學(xué)為甚。《禮記·禮運(yùn)》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xué)而能……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zhēng)奪,舍禮何以治之?”[1]《荀子·樂論》又云:“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yīng)則亂。” “人情”“民情”“萬物之情”以及“天地之情”“古今之情”都體現(xiàn)了重視五官基本欲求的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中國的“情”既包括象征符號(hào)所營造的當(dāng)下情感體驗(yàn),又蘊(yùn)含了文化遺產(chǎn)與歷史記憶中的情感資源。古代中國對(duì)于“理”在伊始之初就有自己獨(dú)特的理解。先秦哲學(xué)中,“理”意為“條理、文理”。《周易》坤卦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2]現(xiàn)代中國繼承了傳統(tǒng)儒家的道德觀、人性論和工夫論,使得情與理不再是二分法的界定。梁漱溟先生認(rèn)為:“所謂理性,要無外父慈子孝的倫理情誼,和好善改過的人生向上。”情與理的關(guān)系近乎于孔子所言“質(zhì)與文”的關(guān)系,即合情理。因此,共情與說理在觀念長河之中并非此起彼伏的正弦曲線。[3]
(二)情理之別:共情與說理的內(nèi)在特征
通情成感,感應(yīng)成通是共情的根與魂,而理一分殊則是說理的勢(shì)與夢(mèng)。感原意為萬物之間的交相攝入,后被延伸為對(duì)“人情之常”的情感調(diào)控。通意為覺,是一切感覺的集合,并非是對(duì)理論經(jīng)驗(yàn)的感觸。感通基于“乾坤天地之相感通”,是以孟子的四端之情為出發(fā)點(diǎn),以貫通的生命感區(qū)別于以理性為基礎(chǔ)的經(jīng)驗(yàn)知識(shí)論,是儒家的體學(xué)之術(shù)。理一分殊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xué)的倫理觀念,而是主張對(duì)共同文化價(jià)值基礎(chǔ)的探尋。將感通之術(shù)應(yīng)用于高校思政課話語體系之中,打破了大學(xué)生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教學(xué)困境,彌合了理論邏輯性與話語體系整體性的裂痕,以情真意切之話語表達(dá)藝術(shù)抑制了情感虛無主義的泛濫。理一分殊以理論邏輯為遵循,以會(huì)講理、善講理為尺度,以講透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學(xué)科為風(fēng)向標(biāo),使大學(xué)生構(gòu)建與客觀規(guī)律相一致的世界觀、人生觀、價(jià)值觀、歷史觀與文化觀。歸根結(jié)底,思政課話語體系中的共情與說理均以情理交融為價(jià)值旨?xì)w。
(三)情理之聯(lián):共情與說理的共生共存
離開共情,說理將會(huì)淪為填鴨式的知識(shí)灌輸性輸出,導(dǎo)致思政課話語體系的庸俗化。具有親和力的思政話語體系側(cè)重一種社會(huì)意義的共在與情緒情感的共識(shí)。在思政課上,通過情感的分享,大學(xué)生在共同的學(xué)習(xí)與交往之中培養(yǎng)對(duì)共同體的意識(shí)和情感,與教師共情、與歷史共情。[4]與之相對(duì)的是,單純的說理會(huì)使學(xué)習(xí)者缺乏同理心,彼此之間的情感交往被削弱。學(xué)習(xí)共同體的情感黑洞造成情感冷漠與疏離,隱含著吞噬社會(huì)關(guān)系黑洞的危險(xiǎn),[5]甚至?xí)淙牖舨妓顾枋龅摹耙磺腥朔磳?duì)一切人”的彌散化狀態(tài)。因此,思政課話語體系中的情感共鳴的缺失不僅無法達(dá)到教—學(xué)貫通的高度,甚至?xí)T發(fā)社會(huì)關(guān)系分裂的隱患。
離開說理,共情的極化將會(huì)扭曲教育精神。對(duì)于如今的高校思政課話語體系而言,淺層次的感官愉悅對(duì)理論知識(shí)體系的統(tǒng)攝將會(huì)掩蓋人們對(duì)高校思政課教育意義的深層次追尋。深度、邏輯、理性無法在思政課話語體系中體現(xiàn),平面化、感性、激情仿佛成為僅有的蒼白印象。大學(xué)生在重情而輕理的高校思政教育中淪為畸形的單面人。正如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靈魂的高級(jí)部分在于理性,主要體現(xiàn)在思維與認(rèn)識(shí)之中。對(duì)理性的脫離將會(huì)使大學(xué)生對(duì)高校思政課的認(rèn)知浮于表面,無法讓新知識(shí)通過分析整合等手段化為已領(lǐng)悟的知識(shí)體系之中。認(rèn)知結(jié)構(gòu)的淺薄化導(dǎo)致教育隱患層出不窮,對(duì)高校思政課話語體系也會(huì)產(chǎn)生不可預(yù)估的摧毀效應(yīng)。因此,思政課話語體系中的理性缺乏將會(huì)使大學(xué)生在熵增狀態(tài)中迷失方向。
共情與說理在思政課話語體系之中是共生共存的。一方面,高校思政課需要通過理論闡述獨(dú)有的知識(shí)體系,但不僅僅是“授人以魚”,而是在各門理論課之中以潤物細(xì)無聲的方式培養(yǎng)大學(xué)生的辯證思維、歷史思維、創(chuàng)新思維、底線思維等必需的理論思維能力。知識(shí)傳授與情感互通的結(jié)合真正做到“授人以漁”。另一方面,高校思政課話語體系中蘊(yùn)含的說理之學(xué)通過嚴(yán)密的推理方式,講透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提升大學(xué)生的理論境界。然而,情之極化會(huì)引發(fā)教育同質(zhì)化隱患,理之極化會(huì)導(dǎo)致教育庸俗化危機(jī)。因此,實(shí)現(xiàn)“情+理”對(duì)話式教學(xué)至關(guān)重要。
二、何以為要:思政課話語體系中情與理的向度
(一)以情感人:共情在思政課話語體系中的意義
共情在思政課話語體系中以跨越主體間裂谷彌補(bǔ)話語親和力的空?qǐng)觥Ec客體自然而然、感同身受的教學(xué)話語方式以情感人、以情動(dòng)人,使傳統(tǒng)的思政話語體系完成了從“主—客”到“主—主”的轉(zhuǎn)變。通過共情,高校思政課教師設(shè)身處地地了解大學(xué)生的情緒與感受,重建了與他人主觀感受的連接。在對(duì)大學(xué)生的言傳身教中,使得“紅色情懷”“傳道情懷”與“仁愛情懷”入腦入心。當(dāng)情感不再被虛化淡化時(shí),你說我聽的“主—客”話語表達(dá)方式逐漸被以交流互動(dòng)為主的“主—主”話語表達(dá)方式所代替。“主—主”的話語表達(dá)方式關(guān)注大學(xué)生的所慮、所思、所求,充分尊重了其話語表達(dá)方式的權(quán)利。話語體系完成了意義的承載工作,以受教育群體——大學(xué)生獲得認(rèn)可為標(biāo)志,使思政課成為大學(xué)生真正喜愛的立德樹人的課程。共情在思政課話語體系的發(fā)展弱化了教學(xué)內(nèi)容的理論性,但不能過分感性化。高校思政課的到課率和抬頭率的增長表現(xiàn)出手段的成功,但這僅是手段上的成功,需警惕背離思政課教學(xué)的最終目的。
(二)以理服人:說理在思政課話語體系中的限度
說理在思政課話語體系中主要表現(xiàn)為話語資源供給呈現(xiàn)出曲高和寡的困境。依據(jù)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話語風(fēng)格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之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說理對(duì)高校思政課教師而言,是以自己對(duì)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學(xué)科的“真懂、真信、真學(xué)”來引領(lǐng)大學(xué)生的“真懂、真信、真學(xué)”的。從“懂、信、學(xué)”,大學(xué)生在曉之以理的氛圍中逐步堅(jiān)定政治自覺、提升道德修養(yǎng)與自覺擔(dān)當(dāng)歷史使命。作為認(rèn)識(shí)最高形式的理論雖有不可替代性,但是理之極化伴隨而來的情感不存抑或是空談情感的現(xiàn)象導(dǎo)致思政課話語體系的隱性滲透力被削弱,重知識(shí)灌輸而輕價(jià)值啟發(fā)的行為并沒有深入大學(xué)生思想本身,更遑論有無情感引導(dǎo)抑或是情感深淺之別,不利于從“經(jīng)師”到“人師”的轉(zhuǎn)變。因此,思政課話語體系打通教與學(xué)的屏障需要情感共鳴與理論邏輯的辯證統(tǒng)一。
(三)通情明理:共情與說理辯證統(tǒng)一的原則
以通情明理之名堅(jiān)持共情與說理的辯證統(tǒng)一為思政課話語體系提供了堅(jiān)實(shí)的實(shí)踐空間。堅(jiān)持價(jià)值性和知識(shí)性相統(tǒng)一:從橫向視角看,情感表達(dá)是思政課話語體系的著力點(diǎn);從縱向視角看,具備嚴(yán)密邏輯論證的理論之學(xué)是連接政治自覺與思想立場(chǎng)的紐帶。堅(jiān)持政治性和學(xué)理性的統(tǒng)一。2019年3月,習(xí)近平總書記在學(xué)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huì)上就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改革創(chuàng)新提出堅(jiān)持八個(gè)統(tǒng)一,其中政治性和學(xué)理性的統(tǒng)一居于首位。政治性毋庸置疑帶有意識(shí)形態(tài)色彩,卻如大廈之巔,不可動(dòng)搖。一方面,兩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約。思政課話語體系中的政治性要解決的是“何為”的問題,是其情感屬性,是學(xué)理性的統(tǒng)帥;學(xué)理性要解決的是“應(yīng)為”的問題,是思政課話語體系的基本屬性。政治性和學(xué)理性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若在思政課話語體系的構(gòu)建中只注重政治性(側(cè)重情感),就會(huì)缺乏學(xué)理支撐,強(qiáng)硬灌輸和空洞闡述則達(dá)不到預(yù)期的效果。當(dāng)一味強(qiáng)調(diào)理性,則會(huì)曲高和寡,最終陷入韋伯所描述的“理性的柵欄”;而只注重學(xué)理性而忽略政治性,就會(huì)迷失道路和旗幟。因此,堅(jiān)持價(jià)值性與知識(shí)性相統(tǒng)一、堅(jiān)持政治性與學(xué)理性相統(tǒng)一是思政課話語體系構(gòu)建的基本原則。
三、何以為踐:思政課話語體系建構(gòu)的情理統(tǒng)一 ——情理交融的現(xiàn)實(shí)路徑
思政課話語體系的建構(gòu)以情理統(tǒng)一為旨?xì)w,通過課程話語內(nèi)容的科學(xué)性與思想性共生、個(gè)人話語語境上的宏觀與微觀重合、教學(xué)話語方式的剛性與柔性并濟(jì),逐步實(shí)現(xiàn)情理交融。
(一)課程話語內(nèi)容:科學(xué)性與思想性共生
在課程話語內(nèi)容上堅(jiān)持科學(xué)性與思想性相統(tǒng)一是構(gòu)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體系的必然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核心任務(wù)是針對(duì)大學(xué)生成長過程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思想理論問題,向大學(xué)生進(jìn)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系統(tǒng)教育,使其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jià)值觀。因此,必須堅(jiān)持說理視閾下的高校思政課的科學(xué)性,把理論講深講透。思政課的關(guān)鍵是講清馬克思主義理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dǎo)的科學(xué)社會(huì)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具有嚴(yán)謹(jǐn)?shù)倪壿嬂砺放c完整的觀念體系,需要通過科學(xué)的知識(shí)形態(tài)表達(dá)出來。此外,思政課的話語親和力亟待提升,堅(jiān)持以共情視閾下的思想性,提升話語體系的話語表達(dá)藝術(shù),是思政課話語體系構(gòu)建的新型目標(biāo)。學(xué)習(xí)借鑒多元多樣的話語藝術(shù),塑造民主式與交流式并行的課程話語,以中國特色話語語境為核心,突出有“根”、有“情”、有“趣”的思想。因此,堅(jiān)持說理之學(xué)的科學(xué)性與共情之術(shù)的思想性相統(tǒng)一是構(gòu)建好高校課思政話語體系的題中之義。
(二)個(gè)人話語語境:宏觀與微觀重合
在個(gè)人話語語境上堅(jiān)持宏觀與微觀相重合是構(gòu)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體系的內(nèi)在要旨。個(gè)人話語語境的宏觀層面是指在高校思政課教學(xué)中,從集體主義、國家利益、人民至上等倫理話語出發(fā),重點(diǎn)關(guān)注個(gè)體如何遵循已有的宏觀規(guī)則,而忽略了個(gè)體自身世界的內(nèi)心話語,蒙上了一層重理輕情的色彩。個(gè)人話語語境的微觀層面是指懸置抽象理性的宏大話語,偏重個(gè)人的微觀話語,輕視理論方面的教化,陷入重情輕理的囹圄之中。高校思政課話語體系中個(gè)人話語語境的創(chuàng)設(shè)既不能失理,也不能失情。因此,在思政課教學(xué)方式上既要秉持學(xué)理嚴(yán)謹(jǐn)?shù)暮暧^敘事,又要秉持體悟與理解并行的微觀敘事。同理,就內(nèi)容而言,既要選擇滿足政治學(xué)習(xí)需求的理論話語,又無法摒棄滿足大學(xué)生個(gè)人需求的生活話語。總之,理之宏觀與情之微觀的重合是實(shí)現(xiàn)高校思政話語體系情理合一的助推器。
(三)教學(xué)話語方式:剛性與柔性共濟(jì)
在教學(xué)話語方式上堅(jiān)持剛?cè)岵?jì),是構(gòu)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體系的合用向度。剛性的教學(xué)話語方式注重話語表達(dá)的邏輯性與嚴(yán)謹(jǐn)性,側(cè)重以理服人,以科學(xué)化與論辯式為特點(diǎn),增強(qiáng)大學(xué)生對(duì)思政課的直觀體驗(yàn)。理之剛性的教學(xué)話語方式對(duì)理論話語片刻不離,容易降低教學(xué)話語方式的溫度,漠視大學(xué)生的話語表達(dá)欲望,從而無法達(dá)到以情感人的效果。柔性的教學(xué)話語表達(dá)方式偏重用情和文化人,注重?cái)⑹碌纳罨凸适禄自斐伤颊n教學(xué)話語體系的散亂無序,不利于思政課教學(xué)效果的真正實(shí)現(xiàn)。歸根結(jié)底,思政課教學(xué)話語體系既需剛性到場(chǎng),又需柔性到場(chǎng)。理之剛性話語與情之柔性話語的共生是實(shí)現(xiàn)高校思政話語體系情理合一的風(fēng)向標(biāo)。
四、結(jié)語
在思政課話語體系中,情理交融的達(dá)成并非最終目的,最重要的在于共情的真正改進(jìn)與說理的真正確立。情感共鳴與邏輯理論的結(jié)合既符合學(xué)科發(fā)展趨向,順應(yīng)時(shí)代潮流,又開啟了思政課教學(xué)的良性循環(huán)之門。因此,思政課話語體系中的共情與說理以其歷史淵源,真正實(shí)現(xiàn)了情理統(tǒng)一,而且以其現(xiàn)實(shí)意義厘清了二者的關(guān)系,明晰了其辯證統(tǒng)一的原則。在情理統(tǒng)一的構(gòu)建路徑上,應(yīng)當(dāng)通過課程話語內(nèi)容的科學(xué)性與思想性共生、個(gè)人話語語境上的宏觀與微觀重合、教學(xué)話語方式的剛性與柔性并濟(jì),逐步實(shí)現(xiàn)情理交融。然而,對(duì)思政課教師而言,教學(xué)話語體系中的“知”與“行”和“情”與“理”的分裂仍在,通術(shù)明學(xué)的情理交融之路仍然漫長,共情與說理的博弈、爭(zhēng)論、發(fā)展、融合也仍將持續(xù)。思政課話語體系的情理交融過程演繹了深入情理反思、抉擇與建構(gòu)的邏輯本質(zhì),以價(jià)值性與知識(shí)性、政治性與學(xué)理性的辯證統(tǒng)一為理論自覺,為教學(xué)話語的表達(dá)提供理論視域與范式指導(dǎo),從而提升思政課教學(xué)效果。
參考文獻(xiàn):
[1] 戴圣. 禮記·禮運(yùn)[M]. 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95:116.
[2] 黃壽祺,張善文. 周易譯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8.
[3] 吳飛. 共情傳播的理論基礎(chǔ)與實(shí)踐路徑探索[J]. 新聞與傳播研究,2019,26(05):59-76+127.
[4] 唐美云. 思政課教學(xué)中的“講理”與“共情”[J]. 中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1,41(09):148-153.
[5] 高奇琦,嚴(yán)文鋒. 知識(shí)革命還是教育異化?ChatGPT與教育的未來[J]. 新疆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3,44(05):2+102-112.
(薦稿人:楚江亭,北京師范大學(xué)學(xué)校特色發(fā)展與實(shí)驗(yàn)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dǎo)師,教授)
(責(zé)任編輯:羅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