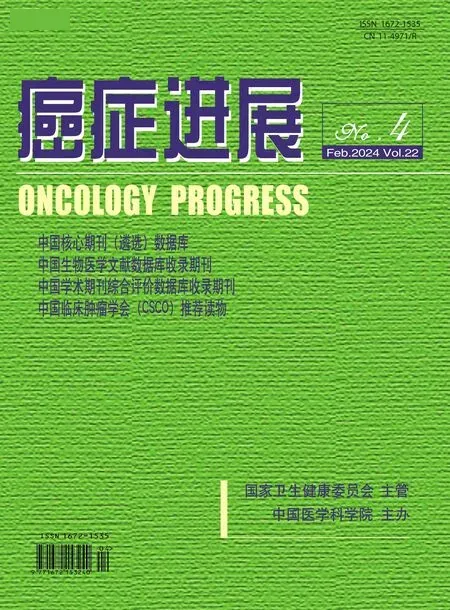晚期肝癌一線治療的研究進展
佘明金 綜述,孫登群 審校
武警安徽省總隊醫院1 腫瘤科,2 普外科,合肥 230041
據統計,全球每年新發肝癌病例約90.57 萬例,死亡病例約83.02 萬例,其病死率居全部惡性腫瘤第3 位[1],中國新發肝癌病例和死亡病例均約占全球病例的一半[2]。中國肝癌患者多具有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肝硬化背景,就診時大多數為中晚期,表現為肝內腫瘤負荷大、合并門靜脈癌栓、肝功能差等。肝癌起病隱匿,進展迅速,大多數患者就診時已失去根治性治療機會,亟需系統藥物治療[3]。化療是晚期肝癌全身治療的主要手段,但療效有限且不良反應明顯。近年來,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迅速發展,使晚期肝癌的一線治療有了更多的選擇[4]。本文就晚期肝癌一線治療的臨床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1 晚期肝癌的一線靶向治療
1.1 索拉非尼(Sorafenib)
索拉非尼是一種口服多靶點受體酪氨酸激酶抑制劑,其可抑制腫瘤細胞增殖,促進腫瘤細胞凋亡。一項多中心、Ⅲ期、雙盲、安慰劑對照試驗SHARP 研究了索拉非尼作為一線治療藥物在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中的應用效果,結果發現,索拉非尼組和安慰劑組患者的中位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分別為10.7 個月和7.9 個月(HR=0.69,95%CI:0.55~0.87,P<0.001);雖然索拉非尼組和安慰劑組患者的中位癥狀進展時間無顯著差異,但中位影像學進展時間分別為5.5 個月和2.8 個月(P<0.001);索拉非尼組和安慰劑組患者的部分緩解率分別為2%和1%;且索拉非尼組患者腹瀉、體重減輕、手足皮膚反應和低磷血癥的發生率更高[5]。2009 年Oriental 試驗結果顯示,在亞太地區肝癌患者中,索拉非尼組和安慰劑組患者的中位OS 分別為6.5 個月和4.2 個月(HR=0.68,95%CI:0.50~0.93,P=0.014)[6]。基于上述研究,2009 年8 月,索拉非尼經過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NMPA)批準在中國上市,用于治療不能手術切除的晚期HCC。索拉非尼的應用開啟了肝癌靶向治療的序幕,但整體療效有限,完全緩解病例罕見報道,有被替代的趨勢。
1.2 侖伐替尼(Lenvatinib)
侖伐替尼是一種針對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1~3、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受體(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FGFR)1~4、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受體(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PDGFR)、RET 和C-Kit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劑。一項開放性、多中心、Ⅲ期臨床試驗REFLECT 比較了侖伐替尼與索拉非尼治療HCC 患者的臨床療效,結果顯示,侖伐替尼組和索拉非尼組患者的中位OS 分別為13.6 個月(95%CI:12.1~14.9)和12.3 個月(95%CI:10.4~13.9),中位無進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分別為7.4 個月與3.7 個月[根據改良實體瘤療效評價標準(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RECIST)評估]。該研究還發現,侖伐替尼在中國人群中的療效較全球人群更佳[7]。侖伐替尼最常見的不良反應是高血壓、腹瀉、食欲下降和體重下降[8]。侖伐替尼作為一種多靶點酪氨酸激酶抑制劑,具有獨特的與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R)、FGFR 結合機制,在肝癌患者的治療中表現出良好的抗腫瘤活性和較高的客觀反應率,為晚期肝癌患者帶來了新的希望[9]。基于侖伐替尼在Ⅲ期臨床試驗REFLECT 中對比索拉非尼具有非劣效性,2018 年9 月,侖伐替尼被NMPA 批準作為HCC 一線治療的一種選擇。
1.3 多納非尼(Donafenib)
多納非尼是中國自主研發的口服、多靶點、多激酶抑制劑類小分子抗腫瘤藥物,是索拉非尼的氘代衍生物。多納非尼主要通過作用于VEGFR、PDGFR 等多種受體酪氨酸激酶,以及多種RAF 激酶和RAF/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的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kinase,MEK)/胞外信號調節激酶(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ERK)信號轉導通路,強效抑制腫瘤細胞增殖和腫瘤新生血管生成,從而發揮雙重抑制、多靶點阻斷的抗腫瘤作用[10]。Qin 等[11]在國內開展的一項開放標簽、隨機、多中心Ⅱ/Ⅲ期臨床研究結果顯示,相比索拉非尼,多納非尼顯示出更好的療效和安全性,入組的668例意向治療HCC患者被隨機分配到多納非尼組和索拉非尼組,全分析集(full analysis set,FAS)分別包括328例和331例患者。FAS中,多納非尼組患者的中位OS明顯長于索拉非尼組(12.1個月vs10.3個月,HR=0.831,95%CI:0.699~0.988,P=0.0245);意向治療人群中,與索拉非尼組相比,多納非尼組表現出更好的OS。FAS中,多納非尼組和索拉非尼組患者的中位PFS 分別為3.7 個月和3.6 個月(P=0.0570),客觀緩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分別為4.6%和2.7%(P=0.2448),疾病控制率分別為30.8%和28.7%(P=0.5532)。與索拉非尼組相比,多納非尼組患者藥物相關3級以上不良事件發生率明顯降低(38%vs50%,P=0.0018)。
2 晚期肝癌的一線免疫治療
2.1 免疫單藥治療
CheckMate 040 的研究結果開啟了肝癌免疫治療的序幕,無論是否接受過索拉非尼治療以及程序性死亡受體配體1(programmed cell death 1 ligand 1,PDCD1LG1,也稱PD-L1)表達高低,晚期HCC 患者均能從納武利尤單抗治療中獲益[12]。基于CheckMate 040 的研究結果,2018 年歐洲腫瘤內科學會(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ESMO)推薦納武利尤單抗用于HCC 的一線治療。
CheckMate 459 是一項隨機、多中心、Ⅲ期臨床試驗,頭對頭比較了納武利尤單抗與索拉非尼在晚期、不可切除的HCC 患者中的療效,且患者之前沒有進行過系統治療,結果顯示,納武利尤單抗組和索拉非尼組患者的中位OS 分別為16.4 個月和14.7 個月,差異無統計學意義(HR=0.85,P=0.075)[13]。
2.2 免疫聯合治療
2.2.1 免疫治療聯合抗血管生成藥物 IMbrave150 研究是一項開放標簽、隨機、平行對照的國際多中心Ⅲ期臨床試驗,共納入501 例既往未接受過系統性治療的不可切除的HCC 患者,按照2∶1的比例隨機接受PD-L1 抑制劑阿替利珠單抗和貝伐珠單抗聯合治療(以下簡稱“T+A”方案)或索拉非尼治療。49.1%的入組患者之前接受過局部治療,47.9%的患者合并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21.6%的患者合并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40.0%的患者合并大血管侵犯[14]。該試驗包括病灶侵犯門靜脈主干或對側一級分支(Vp4)、膽管侵犯或肝癌占全肝比例>50%的高危患者,這些患者在其他試驗中通常被排除在外。“T+A”方案:第1 天,阿替利珠單抗1200 mg,貝伐珠單抗15 mg/kg,靜脈滴注,21 天為1 個周期;索拉非尼治療:口服索拉非尼400 mg,每天2 次。患者接受“T+A”方案或索拉非尼單藥治療,直至出現不可耐受的不良反應或研究者確定無臨床獲益。主要研究終點為獨立審查機構(independent review facility,IRF)根據RECIST 1.1版評估的PFS 和OS,次要研究終點為ORR、疾病進展時間(time to progression,TTP)、緩解持續時間(duration of response,DOR)、患者報告結局(patient-reported outcome,PRO)、安全性和藥代動力學。在經過中位17.6 個月的隨訪后,結果表明,“T+A”方案可將患者的死亡風險降低34%,中位OS 達到19.2 個月,長于索拉非尼治療患者的13.4個月(HR=0.66,95%CI:0.52~0.85);“T+A”方案和索拉非尼治療患者的中位PFS 分別為6.9 個月和4.3 個月(HR=0.65,95%CI:0.53~0.81,P<0.001);與索拉非尼相比,“T+A”方案的獨立評估ORR 也明顯較高(30%vs11%,P<0.001)。值得注意的是,“T+A”方案的完全有效率也高于索拉非尼(8%vs<1%)[15]。“T+A”方案與索拉非尼因任何不良事件導致的停藥率分別為21.9%和11.5%,3~4級治療相關不良事件(treatment-related adverse event,TRAE)發生率分別為43.5%和46.2%,TRAE導致的死亡率分別為1.8%和0.6%。值得一提的是,IMbrave150 試驗及擴展試驗中的中國人群雖然有著更高的HBV 感染率,同時具有大血管侵犯、肝外轉移、甲胎蛋白水平≥400 ng/ml 等多種預后不良因素,但仍然取得了出色的療效,尤其是中位OS 達到24.0 個月[16]。2020 年,基于IMbrave150試驗,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和NMPA 分別于2020 年5 月和10月批準“T+A”方案用于治療既往未接受過系統治療的不可切除的HCC。對于身體狀況良好[肝功能良好、美國東部腫瘤協作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體力狀況評分為0~1 分、Child-Pugh 分級為A 級]且無禁忌證或其他肝病史的HCC 患者,尤其是巴塞羅那臨床肝癌(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BCLC)分期B 期患者,“T+A”方案是首選的一線全身治療方案[17]。
ORIENT-32 研究是國內開展的一項關于晚期肝癌一線治療的隨機、對照、開放、多中心Ⅲ期臨床試驗,571 例符合條件的不可切除的HCC 患者被納入研究,其中27.1%的患者合并微血管侵犯,82.3%的患者既往接受過局部治療,排除門脈主干癌栓的同時累及門脈左右支或腸系膜靜脈[18]。入組的HCC 患者中,BCLC 分期B 期和C 期分別占14.5%和85.5%,多數(96.7%)患者為HBV/HCV 陽性,Child-Pugh 分級主要為A 級,以2∶1 的比例隨機分配接受信迪利單抗(200 mg,靜脈注射,每3周1 次)+貝伐珠單抗(15 mg/kg,靜脈注射,每3 周1 次)治療或單純索拉非尼(400 mg 口服,每日2次)治療,直至疾病進展或發生不可耐受的不良反應。中位隨訪10.0個月,信迪利單抗+貝伐珠單抗組患者的中位PFS 明顯長于索拉非尼組(4.6 個月vs2.8 個月,HR=0.56,95%CI:0.46~0.70,P<0.0001),中位OS 也明顯長于索拉非尼組[未評估(not evaluated,NE)vs10.4 個月,P<0.0001);在所有亞組中,信迪利單抗+貝伐珠單抗治療患者的中位OS和PFS 均長于索拉非尼治療患者。信迪利單抗+貝伐珠單抗使患者的死亡風險降低了43%,信迪利單抗+貝伐珠單抗組和索拉非尼組患者的1 年生存率分別為62.4%vs48.5%。根據RECIST 1.1版獨立療效評估結果顯示,信迪利單抗+貝伐珠單抗組和索拉非尼組患者的ORR 分別為20.5%和4.1%,兩組中均未觀察到完全緩解,疾病控制率分別為72%和64%,因出現不良事件而停止治療的比例分別為13.7%和5.9%,3~4 級TRAE 發生率分別為32.9%和35.7%,TRAE 導致的死亡率分別為1.6%和1.1%。基于該研究,NMPA 于2021 年6 月批準信迪利單抗注射液聯合貝伐珠單抗注射液用于晚期HCC 的一線治療。
2.2.2 免疫治療聯合酪氨酸激酶抑制劑(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 RESCUE 研究是一項非隨機、開放、多中心、Ⅱ期臨床試驗,納入了190 例未經治療(n=70)或一線靶向治療難治(n=120)的晚期HCC 患者,并給予卡瑞利珠單抗聯合阿帕替尼治療[19]。結果顯示,卡瑞利珠單抗聯合阿帕替尼治療晚期HCC 患者具有較高的ORR(34.3%)、疾病控制率(77.0%)和持久緩解,且安全性可控,中位反應時間(time to response,TTR)為1.9 個月。該研究表明,卡瑞利珠單抗聯合阿帕替尼方案系統治療晚期肝癌具有顯著療效,且安全可控。基于RESCUE 的研究結果,隨之開展了SHR-1210-Ⅲ-310 研究,這是一項評估卡瑞利珠單抗聯合阿帕替尼(聯合組)對比索拉非尼(對照組)治療既往未接受過系統治療的不可切除或轉移性HCC 患者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隨機對照、開放性、國際多中心Ⅲ期臨床試驗[20]。中位隨訪14.5 個月,聯合組和對照組患者的中位PFS 分別為5.6 個月和3.7 個月,中位OS 分別為22.1 個月和15.2 個月,ORR 分別25.4%和5.9%,完全緩解率分別為1.1%和0.4%。卡瑞利珠單抗聯合阿帕替尼可將疾病進展風險降低48.0%,死亡風險降低38.0%,使晚期HCC 患者取得明顯的生存獲益。而且,卡瑞利珠單抗聯合阿帕替尼治療的安全性可控,耐受性良好。2023 年1 月31 日NMPA 批準卡瑞利珠單抗聯合阿帕替尼用于晚期HCC的一線治療,這是中國首個獲批的用于治療晚期HCC 的程序性死亡受體1(programmed cell death 1,PDCD1,也稱PD-1)抑制劑與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藥物組合,為晚期肝癌患者帶來了新的用藥選擇。目前,2022 版中國臨床腫瘤學會(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CSCO)原發性肝癌診療指南已將卡瑞利珠單抗聯合阿帕替尼方案列入肝癌的一線治療選擇(1A 類證據,Ⅰ級專家推薦)。
Llovet 等[21]開展的KEYNOTE-524 研究結果顯示,帕博利珠單抗聯合侖伐替尼一線治療HCC 患者具有良好的療效,67 例患者的ORR 為44.8%,中位DOR 為18.7 個月(95%CI:6.9~NE)。Finn 等[22]開展了一項開放、單臂Ⅰb 期臨床研究,旨在評估K藥聯合侖伐替尼一線治療不能局部治療的晚期不可切除的HCC 患者的療效與安全性,結果顯示,患者的中位PFS 和中位OS 分別為9.3 個月和22.0 個月,中位DOR 為8.6 個月(95%CI:6.9~NE)。根據RECIST 1.1 版的獨立評估結果,100 例患者的ORR為46%,完全緩解率為11%,疾病控制率為88%。Sun 等[23]開展一項真實世界研究,旨在評估侖伐替尼聯合K 藥治療晚期HCC 患者的療效和預后影響因素,該研究納入了腫瘤占肝體積≥50%或Vp4 浸潤的患者(這些患者被排除在KEYNOTE-524 研究外)。該研究共納入了84 例HCC 患者(包括31 例腫瘤占肝體積≥50%的患者和30 例Vp4 浸潤的患者),中位PFS 和OS 分別為6.6 個月和11.4 個月,侖伐替尼聯合K 藥可以為Vp4 浸潤的HCC 患者提供生存獲益。表明侖伐替尼聯合帕博利珠單抗的適應證可能進一步擴大。Finn 等[24]開展了一項評估帕博利珠單抗聯合侖伐替尼一線治療晚期HCC的Ⅲ期臨床試驗(LEAP-002),該研究共入組了794 例未經系統治療的HCC 患者,按1∶1 的比例接受帕博利珠單抗聯合侖伐替尼治療或侖伐替尼單藥治療。截至2022 年6 月21 日,中位隨訪32.1 個月,帕博利珠單抗聯合侖伐替尼組和侖伐替尼單藥組患者的中位OS 分別為21.2 個月和19.0 個月(HR=0.840,P=0.0227),中位PFS 分別為8.2 個月和8.0 個月(HR=0.867,P=0.0466)。在次要研究終點方面,帕博利珠單抗聯合侖伐替尼組和侖伐替尼單藥組基于RECIST 1.1 版評估的ORR 分別為26.1%和17.5%,DOR 分別為16.6 個月和10.4 個月;基于改良RECIST 評估的ORR 分別為40.8%和34.1%,DOR 分別為11.2 個月和8.5 個月。在安全性方面,LEAP-002 研究與KEYNOTE-524 研究保持一致,帕博利珠單抗聯合侖伐替尼組并未觀察到新的不良事件。帕博利珠單抗聯合侖伐替尼組和侖伐替尼單藥組患者3~5 級TRAE 發生率分別為62.5%和57.5%,其中5 級TRAE 發生率分別為1.0%和0.8%。期待通過后續的進一步分析,篩選出可從帕博利珠單抗聯合侖伐替尼治療中獲益的優勢人群。LEAP-002 研究的最終分析結果顯示,OS 改善未達到預設的統計學差異,可能是由于對照組生存期的預設值過低,同時這也是唯一將侖伐替尼作為對照組的臨床研究,如果對照組是索拉非尼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結果。Yang 等[25]開展一項侖伐替尼聯合PD-1 抑制劑治療378 例晚期肝癌患者的真實世界研究,結果顯示,中位PFS 和中位OS 分別為6.9 個月和17.8 個月,ORR 和疾病控制率分別為19.6%和73.5%;該研究認為,侖伐替尼聯合PD-1抑制劑在中國不可切除HCC患者中具有較好的療效,聯合治療的耐受性可以接受,但應進行密切監測。
COSMIC-312研究是一項多中心、開放標簽、隨機Ⅲ期臨床試驗,共納入837例HCC患者,按2∶1∶1的比例隨機分配至卡博替尼+阿替利珠單抗組(n=432)、索拉非尼組(n=217)和卡博替尼單藥組(n=188)[26]。該研究按病因(HBV、HCV 和其他)、地區(亞洲和其他)、是否存在肝外疾病或大血管侵犯等因素進行分層,并采用了雙主要終點,由盲態獨立評審委員會(blinded 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BIRC)根據RECIST 1.1 版評估卡博替尼+阿替利珠單抗組和索拉非尼組前372 例患者的PFS(意向治療人群),以及卡博替尼+阿替利珠單抗組和索拉非尼組患者的OS(意向治療人群),次要終點是意向治療人群中卡博替尼單藥組與索拉非尼組的PFS。結果顯示,意向治療人群的中位隨訪時間為13.3 個月,卡博替尼+阿替利珠單抗組和索拉非尼組患者的中位PFS 分別為6.8 個月和4.2 個月(HR=0.63,96%CI:0.44~0.91,P=0.0012),中位OS分別為15.5 個月和5.4 個月(HR=0.90,96%CI:0.69~1.18,P=0.44);卡博替尼+阿替利珠單抗組、卡博替尼單藥組、索拉非尼組患者的ORR 分別為10.8%、6.4%和3.7%,完全緩解率分別為0.2%、0%和0%。安全性方面,卡博替尼+阿替利珠單抗組、卡博替尼單藥組、索拉非尼組患者最常見的3~4 級不良事件是丙氨酸氨基轉移酶升高(9%vs 3%vs 6%)、高血壓(9%vs 8%vs 12%)、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升高(9%vs 4%vs 10%)和掌跖紅腫疼痛(8%vs 8%vs9%),嚴重TRAE 發生率分別為18%、8%、13%。2022 年3 月14 日,美國Exelixis 公司宣布COSMIC-312 研究的最終OS 未顯示出改善,考慮到晚期HCC 治療格局的快速發展,放棄向美國FDA 提交補充新藥的申請。
2.2.3 雙免疫治療 HIMALAYA 研究納入16 個國家190 個中心的1324 例既往未接受過系統治療且不可手術切除的晚期HCC 患者,該研究是一項隨機、開放標簽、多中心臨床試驗[27]。患者按1∶1∶1的比例隨機分配至聯合治療組(替西木單抗300 mg,靜脈注射,第1 天;度伐利尤單抗1500 mg,靜脈注射,第1 天;隨后度伐利尤單抗1500 mg,靜脈注射,每4 周1 次)、度伐利尤單抗組(度伐利尤單抗1500 mg,靜脈注射,每4 周1 次)和索拉非尼組(索拉非尼400 mg,口服,每日2 次)。結果顯示,相較于索拉非尼組,聯合治療組患者的中位OS、ORR均改善(16.4 個月vs 13.8 個月,20.1%vs 5.1%),3年生存率提高10.5%(30.7%vs 20.2%);然而,聯合治療組與索拉非尼組患者的中位PFS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3.8 個月vs 4.1 個月,HR=0.90,95%CI:0.77~1.05)。這是目前已知的HCC 中首次顯示OS顯著改善而PFS 未改善的隨機對照試驗[28]。HIMALAYA 研究顯示,在HBV 亞組中,聯合治療組較索拉非尼組OS 改善(HR=0.64)與FAS 相似(HR=0.78),但在HCV 亞組中并非如此,聯合治療組較索拉非尼組OS 未改善(HR=1.06),與FAS 相似(HR=1.05)[29];在非病毒亞組中,聯合治療組較索拉非尼組OS 改善(HR=0.74)與FAS 相似(HR=0.78)。基于HIMALAYA 研究,2022 年10 月21 日,美國FDA 批準度伐利尤單抗聯合替西木單抗作為HCC 一線治療的另一種選擇,為不適合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VEG)治療的患者提供了一種新的治療選擇。鑒于HIMALAYA 研究的成功,一項評估度伐利尤單抗聯合替西木單抗一線治療不可切除HCC 患者臨床療效的開放標簽、多中心、Ⅲb 期臨床研究(TREMENDOUS 研究)正在進行。
3 晚期肝癌一線治療中存在的問題
3.1 如何選擇一線聯合治療方案
過去20 年,晚期HCC 患者的全身治療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30]。隨著系統治療方案的增加,合理的一線治療選擇對改善HCC 患者的預后至關重要[31]。2023 年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肝膽腫瘤指南已經將“T+A”方案列為晚期HCC 一線治療的首選方案,這證明“免疫治療+靶向治療”模式是目前肝癌患者初治時的“最優解”。有研究表明,“T+A”方案與侖伐替尼相比,能更好地維持患者的肝功能[32]。研究證實,肝癌患者在“T+A”方案治療失敗后,接受TKI(如侖伐替尼、索拉非尼等)治療能夠從中受益[33]。HIMALAYA 研究中的方案因高昂的治療費用限制了其臨床應用[34]。由于缺乏生物標志物指導治療的排序,合理安排HCC 治療藥物是一項重要挑戰。鑒于藥物的可及性以及循證醫學證據,考慮到既往使用TKI 治療的患者中超過一半肝功能惡化無法接受二線治療[35],對于不可切除的HCC 患者來說,接受“T+A”方案后接受TKI(侖伐替尼、索拉非尼或多納非尼)治療,再使用瑞戈非尼、卡博替尼和雷莫蘆單抗進行三線治療,可能是正確的藥物治療順序[36]。美國FDA 建議在未接受過系統治療的晚期HCC 患者中使用阿替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這開創了HCC 系統治療的新時代,但高成本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30,37]。從成本效益的角度考慮,對比阿替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信迪利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可能更適合作為中國肝癌患者的一線治療[38]。ORIENT-32 研究完全是針對中國人群的研究,納入了571 例中國肝癌患者,其中大部分為HBV 感染患者,信迪利單抗+貝伐珠單抗方案可能更適合中國患者,可能也是“T+A”方案的最佳替代[18]。
3.2 重視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的安全性
抗血管生成藥物的不良反應可累及全身多個系統和器官,常見不良反應為手足皮膚反應、腹瀉、高血壓、蛋白尿等。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具有維持免疫平衡的作用,同時,免疫相關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irAE)可累及多個系統和器官,包括皮膚、胃腸道、肝、肺和內分泌器官,疲勞、皮膚毒性和肝臟毒性是最常見的irAE[39]。隨著靶向治療、免疫治療在肝癌中的廣泛應用,臨床醫師越來越重視irAE。irAE 涉及全身多系統,及時發現和處理免疫相關性心肌炎、肺炎及重癥肝炎等具有重要意義,需要不同專科醫師共同協作進行診斷與治療。
4 小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改變了晚期肝癌的一線治療格局,目前不同指南推薦不同的治療方案,選取有效的一線治療方案仍是一項挑戰。進一步探索肝癌的分子和免疫分型以指導優勢人群的選擇、耐藥后應對策略的制訂以及不良反應的管理等,是臨床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免疫聯合治療是治療晚期肝癌的新方法,相信免疫治療將為晚期肝癌患者帶來更多的生存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