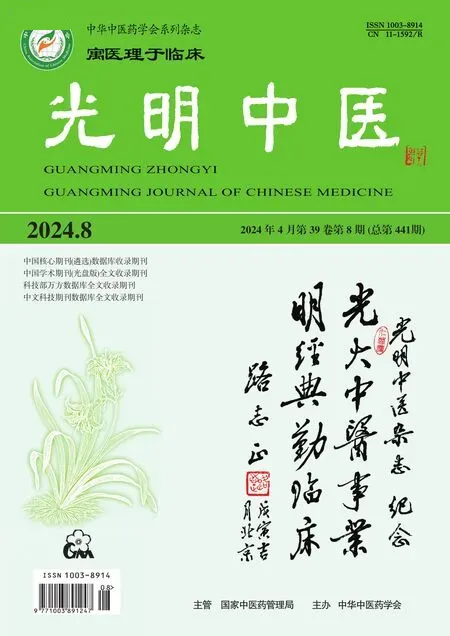朱慶軍主任從神論治小兒多動癥經驗擷菁
汪雅婷 楊夢夢 葉 輝 朱慶軍
小兒多動癥又稱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 常見于兒童時期,是以與年齡、智力水平不相稱的注意力不集中、多動、易沖動為特征的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且可與多種神經精神障礙同時發病,多數患者常伴有精神緊張、脾氣急躁、性格膽小、神經敏感等問題[1]。調查顯示,中國兒童的小兒多動癥患病率為5.7%,男童患病率高于女童[2]。
目前該病的發病機制尚不明確,現代醫學研究普遍認為,小兒多動癥患者存在廣泛多樣的大腦結構及功能異常[3]。現代醫學多采用藥物治療,一線治療藥物可分為中樞興奮劑(如哌甲酯類制劑)和非中樞興奮劑(如鹽酸托莫西汀),主要用于改善患兒的注意力渙散和過度活動癥狀。藥物治療療效尚不確切,療程偏長,且存在胃腸道功能紊亂、生長發育緩慢等不良反應,甚至導致抑郁、自殺和妄想等不良情緒產生[4]。故6歲以下患兒不推薦使用該類藥物治療。中醫學主張治病求本,在治療該病的具體實踐中具有個體化、療效確切、不良反應小等優勢,值得推薦。
導師朱慶軍,安徽省中醫院主任醫師,臨床20余年,經驗豐富,主張“神安則百病消”,擅長調神治療各種疑難雜癥,在小兒多動癥的臨證中獨具特色,朱師以調神養神為治則,運用中藥、針刺、調護等多種方法結合治療該病,療效顯著。
1 病因病機
小兒多動癥在中醫學中并無與對應的病名,根據其多動多語、沖動不安、注意力不易集中等臨床表現,可屬“躁動、臟躁、失聰、健忘”范疇[5]。中醫認為,小兒多動癥多與情志不暢、外傷、飲食不潔、勞倦過度、調護不當等因素有關[6]。明代兒科醫家萬全概括小兒的生理特點為“三有余四不足”,且易產生風、火、痰等病理產物,歷代醫家多重視清心平肝、瀉火豁痰、滋陰潛陽、補益脾胃。但朱慶軍導師認為,小兒多動癥病機總屬氣血陰陽失調,元神失養,神形錯亂。《素問·移精變氣論》中云:“得神者昌,失神者亡”,故神在人體生理、病理中有著關鍵作用,無論是呼吸運動、血液循行、消化吸收,還是津液輸布與排泄、生長發育、生殖功能等,都只有在神的統帥和調節下,才能發揮正常作用。神之為病可體現在兩個方面,一為神本身之病變,可出現躁動、臟躁等情志異常;二為神之所驅使的五臟六腑、精血津液、氣化功能、筋骨肌肉等紊亂。
1.1 氣血失調 神失所養《讀醫隨筆·氣血精神論》記載:“道家以精、氣、神,謂之三寶,是故氣有三:曰宗氣也,榮氣也,衛氣也;精有四:曰精也,血也,津也,液也;神有五:曰神也,魂也,魄也,意與智也,志也,是五臟所藏也”。即精、氣、血、津液是構成人體的基本物質,與人體生命活動密切相關,神主宰人體的生命活動,是其外在總體表現的統稱[7]。“血者,神氣也”“血為神之居”“血氣者,人之神也”,氣血、津液濡養神,是神賴以存在的載體,氣血、津液是神的外在表達與顯現。道家認為,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體用相應,道器不二。氣血調和,則精神乃安。氣血失調,可影響正常的情志活動,表現精神渙散,容易沖動,性格急躁,敏感膽怯等,情志異常也可導致生理代謝的紊亂,從而產生軀體化障礙,如多動、行為異常。
1.2 陽氣失司 神游離合《論衡·論死》云:“陽氣導萬物而生,故謂之神”。又有《景岳全書·中興論》言:“氣為陽,陽主神也”。說明神的功能是否正常運行與陽氣關系密切。陽氣偏盛或偏衰,均可見神的異常。《靈樞·天年》曰:“人生十歲,五臟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動”。說明兒童活潑好動為正常現象,小兒常“陽有余”,若陽氣失司,小兒多動癥患兒皆可表現為多動沖動、多言多語、煩躁不安。
1.3 臟腑嬌嫩 形氣未充 心神易擾小兒臟腑嬌嫩,形氣未充,其臟腑經絡、四肢百骸、精血津液、生理功能都不夠成熟和相對不足。《小兒藥證直訣·小兒脈法》中記載:“五臟六腑,成而未全……乃全而未壯也”。其心神極易受外界的干擾,易出現神志不安、神無所居、心神不寧、多動少靜的異常行為活動。
2 治療特色
2.1 針刺部分 暢達三焦 治神守中《素問·寶命全形論》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朱師結合多年臨床經驗認為,針刺治療小兒多動癥的取效原理在于以氣調神,在整體論治和辨證施治的指導下,常選用董氏奇穴“怪三針”治療該病。“怪三針”是由針灸名家胡光總結、獨創的一種針法,由正會穴及旁穴,鼻翼(左),次白(右)組成。
正會穴即十四正經穴之百會,其定位為頭頂正中,前發際直上5寸凹陷中。旁穴即百會前、左、右旁開1.5寸,朱師認為,該四針對應人體陰神、陽神、元神、本神。又“頭者,元神所聚”,“元神”為先天之神,腦為神藏之處,主五臟之神,百會位于頭頂,歷代醫家治神也多用百會,為調神要穴。其屬督脈而又交于足厥陰肝經,故此穴可通達陰陽,陰陽調和則心神自安。
《靈樞·五味》曰:“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別出兩行,營衛之道”。營氣行于脈內,衛氣行于脈外,一日一夜五十營而大會于手太陰。如環無端。又說:“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咽喉,故呼則出,吸則入”。《靈樞·邪客》中言:“宗氣上出于鼻而為臭,積于胸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根據《靈樞·營衛生會》的論述,營氣出于中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在宗氣的參與下上注于心脈,化而為血,以奉生身。鼻翼穴位于鼻翼上端之溝陷中,在督脈與手足陽明經之間,同時又位于鼻部通于肺經,“肺主一身之氣”,故此穴上中二焦共治,兼有調理宗氣,溝通營衛的功效。營衛和則神安。
次白位于手背,第三掌指關節后5分,第三、四掌骨間凹陷中,屬心包經與三焦經之間,《靈樞》中明確認為三焦上合于少陽,《針灸大成》又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人心湛寂,欲想不興,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脈。及其想念一起,欲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流溢,并與命門輸瀉而出,故號此腑為三焦”。因此該穴不僅可以調理三焦,又可溝通表里。
清代醫家章虛谷言:“凡表里之氣莫不由三焦升降出入”,此三穴配合可統調三焦,調和營衛,和暢表里,近而達到調神的效果,故針刺此三穴能改善小兒多動癥諸癥,頗有療效。
2.2 中藥部分 透轉樞機 暢形達志朱師擅長中藥湯劑治療小兒多動癥,博采眾長,引經據典,經過其多年實踐形成鮮明特色。治療該病擅長將柴胡桂枝湯作為此病的基礎方,隨癥加減。柴胡桂枝湯作為《傷寒論》常用方劑之一,被廣泛應用于治療各種兒科疾病[8]。國醫大師王慶國認為,柴胡桂枝湯可同調少陽、脾胃、少陰三者之樞,和解三焦脾胃,通調營衛利氣血,用于治療情志病常取得良好的療效[9]。
柴胡桂枝湯由小柴胡湯合桂枝湯各用半量而成。其藥物組成為柴胡、人參、黃芩、法半夏、炙甘草、桂枝、白芍、生姜、大棗[10]。方中柴胡味苦性平,《神農本草經》謂:“其主心腹,去腸胃中結氣”,其可調理上中二焦,又入少陽經,可透泄少陽之邪,疏泄少陽經氣機之郁滯;《素問·六節藏象論》中說:“凡十一臟皆取決于膽”,柴胡輕清,升達膽氣,膽氣條達,則十一臟從之宣化。黃芩苦寒,《神農本草經》言:“主諸熱黃疸,腸澼,泄利,逐水,下血閉”。清泄三焦郁熱,二者合用一散一清,能燮理陰陽升降之樞機。桂枝味辛性溫,助衛陽,通經絡;白芍味酸性寒,益陰斂營,斂固外泄之營陰,兩藥同用,營衛自和,溝通陰陽,氣血調和、邪正兼顧。法半夏、生姜降逆和胃。人參味甘,《神農本草經》曰:“主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大棗扶助正氣,俾正氣旺盛,則邪無內向之機,可以直從外解。甘草調和諸藥。桂枝湯為群方之首,可滋陰和陽、調和營衛,小柴胡湯為和解少陽之代表方,可和解少陽、驅邪扶正,樞機得利。縱觀全方,可舒達樞機,調和營衛,氣血調和,暢心志、通血脈。
朱師認為,柴胡桂枝湯可兩解太陽少陽之邪。太陽主開,督脈和足太陽經并行于背、統領諸陽,為一身之藩籬,其陽氣最為旺盛,少陽為一陽,主樞機的開合運轉,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兩方合用,使邪從少陽轉出太陽,隨太陽之開而病解。精神亢奮者,加生地、百合、龍骨、牡蠣;煩躁易怒者,加梔子、淡豆豉;汗多怕熱者,加桑葉、生石膏、知母;多夢寐難者,加白薇、連翹;大便干結者,加酒大黃、枳殼、厚樸、玄參。
2.3 調護部分 多法并舉 形神共調朱師對于多動癥患兒的治療強調從“神”進行整體調攝,采用正念冥想訓練、形體及內功鍛煉等方法,從而達到形與神俱、形神共養。同時認為,孩子深受家庭環境的影響。除了依賴醫生及藥物的調整以外,還需要患兒及家長共同營造良好氛圍,以達到最佳治療效果。
2.3.1 正念引導 以期神效何為正念?正念源于佛教,指的是覺知、專注和意念。《莊子》中記載:“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必靜必清, 無勞汝形,無搖汝精, 無思慮營營, 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視, 耳無所聞, 心無所知, 汝神將守汝形, 形乃生”。即通過正念冥想訓練,保持內心安定,觀察自我呼吸集中注意力,洞察和體會當前的情緒和心境,使神經系統得以充分放松。這與中醫靜功功法強調的調身“以意引氣,灌注周身”,從而達到調息、調心、調神的治療理念不謀而合。因此,正念可緩解慢性疼痛,注意力集中,調節情緒,緩解焦慮,提高身心健康水平,臨床主要應用于精神心理疾病。同時也可幫助醫師精神專注,臨證時神情安定,內守于心,通過自身之正氣去調整病者失調之氣,以達良效。
2.3.2 額葉訓練 調暢情志額葉皮質是負責控制行為和精神活動的重要區域,與注意力、抑制力、執行力、情感調節、運動功能等相關[11]。額葉訓練法是朱師根據臨床總結而出的效法,即通過眼看、口念、神專三者并用以訓練額葉,同時配合眼球訓練、平衡訓練及營養學方面綜合刺激強化恢復其額葉功能,以達到提升注意力、改善注意缺陷、穩定情緒的目的。
2.3.3 家長配合 營造良好家庭環境朱師認為,多動癥兒童的家庭問題通常比一般兒童家庭多,父母關系不和諧、孩子教養理念不完善,會使得多動癥兒童的癥狀變得更為嚴重,對兒童的身心發展不利。同時,兒童的身心健康也影響家長的情緒,加重家長的焦慮,如此長期循環,易致病情加重或綿延。故治療此病當重視調暢情志,需要多方配合。家長需要做到以下幾點:首先,要接受孩子的病情,樹立正確積極的人生觀。其次,作為孩子的榜樣,要注意情緒管理,培養并傳遞樂觀精神,以正面引導患兒。晨起帶患兒進行戶外鍛煉,多陪伴其去戶外放松,如慢跑、八段錦等,可選取樹木多的地方,木主疏泄,可調養形體,暢達情志。合適的喂養方式也必不可少,如孩子偏食,需要督促飲食,營養均衡。
3 驗案舉隅
患兒,男,9歲。2023年3月8日初診。因“好動多言、注意力不集中6個月余”于筆者科室就診。家長述患兒于6個月前出現好動難以安靜,多言多語,寫作業時注意力不集中,未予重視,后患兒出現上課時左顧右盼,離開座位,跑出教室等行為,就診于某兒童醫院神經內科,診斷為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未予藥物治療。現患兒好動多言,注意力不集中,坐立不安,情緒易波動,伴有清嗓等癥狀,智力正常,平素父母較為寵愛,飲食挑食,喜食肉食,夜間難以入睡,寐欠安,易出汗,小便正常,大便干結。舌質紅,邊尖紅,苔微黃膩,脈弦。診斷為小兒多動癥,辨證為心肝火旺證。治以清心瀉火,重鎮安神。治療:針刺:正會及旁穴、鼻翼(左)、次白(右),正會穴沿著頭皮斜刺,傾斜45°~60°,快速進針,針刺0.1~0.3寸,將針輕微刺入穴位即可,不必提插捻轉。鼻翼穴斜刺0.1~0.2寸。次白直刺0.3~0.5寸。留針30 min,1次/d,每周3次,留針30 min。方藥:予以柴胡桂枝湯加減,藥物如下:柴胡9 g,黨參6 g,法半夏6 g,黃芩6 g,炙甘草3 g,桂枝6 g,白芍6 g,酒大黃4 g,梔子6 g,百合12 g,生地黃9 g,大棗6 g。6劑,每天1劑,水煎服,早晚溫服。另囑家長:晨起后帶患兒去戶外適度運動,微微出汗為宜;改變飲食結構,飲食清淡,不要過飽。
2023年3月15日二診:家長訴患兒跑出教室等行為減少,寫作業時注意力不集中較前改善,但仍有好動多言,易煩躁,喜肉食,睡眠欠佳,大便正常。上方已初見成效,首方加減:柴胡9 g,黨參6 g,法半夏6 g,黃芩6 g,炙甘草3 g,桂枝6 g,白芍 6 g,梔子9 g,連翹6 g,百合12 g,大棗6 g。6劑,每天1劑,水煎服,早晚溫服。針刺穴位在原方基礎上加用照海(左)、申脈(右)。余囑不變。
2023年3月18日三診:家長訴患兒已無跑出教室行為,無明顯左顧右盼動作,寫作業時注意力不集中較前好轉,夜寐改善,已安穩,仍有挑食,大便正常。遂效不更方,繼續予以針刺治療,穴位在原方基礎上針刺穴位去照海、申脈,加用腎關(雙)補髓益智。剩余中藥繼續服用。囑患兒家屬督促其配合額葉訓練法訓練。
2023年3月22日四診,家長訴患兒上課可專心聽講,回家可獨立完成作業,飲食睡眠正常,二便調。如此再鞏固治療1周,配合額葉訓練法,隨訪患兒無再發。
按語:本案患兒為學齡期兒童,平素情緒易煩躁,好動多言,注意力不集中,加之飲食不節,喜食肉食,濕熱內生,疾病遷延難愈。朱醫師臨證時重視對“神”進行整體調攝,選以“怪三針”結合柴胡桂枝湯治療,患兒大便干結、寐差、煩躁,故加酒大黃通便,梔子除煩調神,百合改善睡眠,生地黃清熱。二診時患兒睡眠仍欠佳,乃病程日久,損傷氣血,致使機體陰陽失衡而致,故針刺加以照海(左)、申脈(右)調和陰陽,調心養神,大便改善,故中藥去酒大黃、生地黃,但情緒易煩躁,加連翹、梔子加量除煩清熱。三診時夜寐改善,針刺去照海、申脈,加腎關穴補髓益智加強注意力集中,提高療效。四診時患兒情況基本穩定,已能進行正常學習生活。同時囑托患者于太陽初升時輔以導引之術及額葉訓練法,使之心情舒暢,神志暢達,愿意積極配合治療,故顯捷效。
4 小結
小兒多動癥是常見的兒科病,現代醫學多采用興奮劑治療,長期使用不良反應較大,中醫學治療該病具有安全性高的特點。朱師經過多年臨床經驗,認為小兒多動癥的病機在于元神失養,神形失調。治療上以調神養神為原則,多法并用,各得其所宜,拓寬臨床診療思路,臨床療效頗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