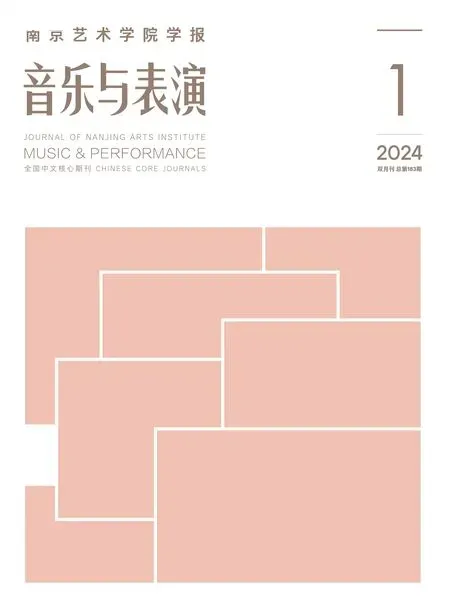論新歷史主義視域下大女主商戰劇的敘事話語轉變與身份認同①
陳 琰 (南京藝術學院 傳媒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3)
高智陽 (南京藝術學院 傳媒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3)
商戰題材電視劇在20世紀90年代成為一種類型,出現了大量表現商業戰爭的風云變化、股市大亨的升落浮沉、金融巨子們鉤心斗角的作品,如《情滿珠江》《中國商人》《商界》《大宅門》《喬家大院》《白銀谷》《龍票》《紅衣坊》《奔騰向海洋》《海之門》等。當商戰題材和女性成長題材碰撞,又催生出新的類型——大女主商戰劇。此類型敘事往往將人物放在兩條敘事線索之下,通過事業線和情感線的并置凸顯女性的成長。事業線是敘事的表層結構,在歷時性向度里,體現女性在男權主導世界中的抗爭與成長;情感線是敘事的深層結構,在共時性向度里,表現人物的情感狀態,包括愛情、友情、親情,及其反映的時代思想和文化背景之間的沖突。
2022年的大女主商戰劇《風吹半夏》,在江蘇衛視和浙江衛視播出后均取得不俗的收視,并引發了觀眾熱議。該劇突破了此前這一類型作品的束縛,在大時代的背景下表現女性角色的成長,將大女主敘事融入宏大敘事,并揭示了大女主商戰劇在身份話語上的轉變,成為大女主商戰劇的典范。
事實上,近年來以《風吹半夏》為代表的大女主的商戰劇的敘事話語和身份認同頗引人注意。本文將從新歷史主義的視角,界定大女主商戰劇的類型特征,分析這一類型電視劇中大女主身份和敘事話語的轉變。
一、大女主商戰劇:一種新歷史主義的雜糅類型
“大女主商戰劇”緣起于商戰題材電視劇與女性題材電視劇的類型互融,以女性為主角,以現代商業體系中的利益沖突為敘事核心,女主角在商戰中起主導作用。此類型敘事往往將人物放在兩條敘事線索之下,事業線和情感線并置凸顯女性的成長。大女主商戰劇幾乎和傳統意義上的商戰劇在同一時期出現。20世紀9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浪潮推動了全國經濟的發展,我國現代商業體系日趨成熟,女性群體在商業中的力量逐漸凸顯。這在影視劇的體現就是女性角色逐漸進入敘事中心,最終主導故事中的商戰行為。然而,最初這類劇作并沒有突出女性在商業體系中的價值,反而將女主角置于情感、事業雙被動的位置。從表面上看是激烈的商業角逐,內里卻是“癡情女子爭奪負心情郎”的所謂“真心”的模式化的愛情故事。比如根據梁鳳儀小說改編的女性商戰劇《醉紅塵》與《今晨無淚》,這兩部作品可以視為前后篇,內容彼此獨立又互相關聯,講述了兩個家族企業為了爭奪房地產開發權而進行的爾虞我詐的商業角逐。其中,女主角的情感糾葛是商戰行為的催化劑,故事內核只是一場癡情女子對負心漢的“復仇傳奇”。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敘事力度,內容單薄,既不能凸顯大女主的主體性,也未能表現出商戰劇的商戰文化,這樣的女主角并不能成為商戰劇“大女主”的典型。對比來看,同一時期出現的比如《情滿珠江》在時代洪流中摸爬滾打、最終成長為企業女強人的梁淑貞,《奔騰向海洋》中果敢有魄力的乳業集團總經理劉丹虹,才是頗具魄力的商戰大女主。
大女主商戰劇是商戰題材電視劇的一個分支,或者也可以說是女性題材電視劇的一種題材延伸。筆者認為,大女主題材電視劇深受新歷史主義影響,以新歷史主義的視角來看,該類型劇可視為獨立于商戰題材電視劇和女性題材電視劇之外的類型。新歷史主義理論是受20世紀80年代“歷史轉向”思潮影響而在西方文學界興起的批評理論。雖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曾經指出,“新歷史主義是一個沒有確切指涉的措辭”[1],學術界對其的解釋也因研究方向不同而錯綜復雜,但所有的相關論述都指向了一個共同點——“拒斥歷史決定論而注重主體的反抗顛覆論”[2],其中主體,也就是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該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左右傳入中國,與改革開放的時代軌跡并行。新歷史主義者認為歷史與現實緊密相連,歷史是發生過的現實,現實也映照出曾經的歷史。“對當下個體生命而言,個體生命只能通過對歷史文本的解釋活動來選擇歷史,改變歷史。在這個意義上,任何對歷史文本的解碼,都離不開解釋者的主體想象,都可能演變為一種符合當下主流意識形態邏輯的歷史清單。中國文化一直具有強烈的歷史情結,文學藝術都有以史為鑒的文化傳統。”[3]大女主商戰劇以史為鑒,秉持著“反抗顛覆論”而非“歷史決定論”的新歷史主義觀點。相較于傳統的商戰題材電視劇,大女主商戰劇除了表現特定時代商戰活動對于傳統經濟模式的顛覆,更是在女創業者、女商人的身份話語認同等主體性的方面展現出強烈的革新意識,且隨著時代的變化迸發出新的能量。如今的大女主商戰劇呈現出“去瑪麗蘇化”的現實主義傾向,在故事背景上,時代性愈發明顯。“人是一個歷史的存在”,大女主商戰走向現實主義本身也是一種時代性的、新歷史主義的傾向。因此可以說,大女主商戰劇從誕生之初發展到如今,正體現著新歷史主義在電視劇領域中的運用,是具有“雙重顛覆性”的雜糅類型。
二、大女主商戰劇敘事話語的現實主義轉向
類似“電視劇中的商戰”和“現實中的商戰”對比的話題在網絡多有探討,甚至成為商家引流的手段。其顯露出的是商戰題材電視劇敘事過于懸浮、脫離現實的問題。大女主商戰劇誕生之初參照傳統商戰劇的形式,在創作手法上追求戲劇化沖突,但仔細推敲,其實這一做法有“為戲劇而戲劇”之嫌,且大女主的性別敘事一直以來都存在爭議,這就使得一些劇作重點在于表現人物的情感糾葛而非商戰活動。推杯換盞的交易、叱咤風云的人物、驚心動魄的商戰等只是大眾的圖解式想象。文學理論家R·韋勒克認為,現實主義的特征可以用“五個排斥”總結,即“排斥虛無縹緲的幻想、排斥神話故事、排斥寓意與象征、排斥高度的風格化、排除純粹的抽象與雕飾”[4]。也就是說,現實主義應該從現實世界中汲取養分,作者風格應該隱藏在真實敘事的背后,而不能為了所謂的戲劇性擾亂敘事節奏。文藝創作不能“僅從恣意馳騁的想象汲取營養”[5]。大女性商戰劇的主體其實是普通人,故事背景也應置于真實的國家歷史之中,其中的矛盾糾葛都應該致力于塑造接地氣的大女主形象、現實主義的典型環境、生活化的戲劇情節。
(一)大女主商戰劇和職場劇的融合
隨著觀眾對現實主義題材電視劇需求的增長,大女主商戰劇也準確把握當下的發展趨勢,對商戰的表現不再流于想象,而是朝著現實主義的方向邁進。職場劇和商戰劇的邊界互融是當前大女主現實主義商戰的一個發展趨勢。
應該說,職場劇與商戰劇邊界并不十分清晰,職場劇也常表現“商業體系中的利益沖突”。大女主商戰劇多設置為商界背景,但對于女商人來說,商界就是職場。不同于早期TVB的豪門情仇或者世紀之交的家族商戰,如今的大女主商戰劇呈現出大眾化、現實化、日常化的特征,這其實也是傾向于職場商戰的表現。如《理想之城》(2021)、《大博弈》(2022)、《風吹半夏》(2022)、《我要逆風去》(2023)、《縱有疾風起》(2023)等電視劇都兼具職場劇和商戰劇的特征,用細致入微的筆觸刻畫有血有肉的大女主形象,關注商業職場的風云變幻,涉及房地產、建筑、民族品牌、網絡電商等諸多當下深刻影響國計民生的行業。當然,并不是所有的職場劇都可以被歸入大女主商戰劇的范疇。21世紀之初的十年里出現過很多側重女性視角的都市職場劇,如《杜拉拉升職記》《丑女無敵》等,這些職場劇讓女主角的部分品質凌駕于專業能力之上,以此獲得男性同伴的幫助,她們和同行的競爭也始終擺脫不了性別的凝視與桎梏。由于敘述重點過于集中于女性的成長,關于職場刻畫則顯得草率。這類職場劇與當前大女主商戰劇的精神內核并不一致。當前大女主商戰充滿“人味兒”,既不陷于“瑪麗蘇”的夢幻沼澤,又把商戰描寫得近日常生活引發觀眾共鳴,究其根本是敘事話語的現實主義轉向。
(二)大女主商戰劇與年代劇的融合
大女主商戰劇的現實主義轉向在一定程度上蘊含著時代要求,也反映了觀眾心理的變遷。面對著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以及充滿機遇和挑戰的全球化局勢,商業秩序有所變革是必然的。觀眾想看的是在時代潮流中勇往直前的普通人,而不是所謂攪弄風云的英雄人物。可以說,英雄商戰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式,描寫普通人的商戰才是當下的主流。一開始,這多出現在一些反映社會改革題材的商戰劇中,意在突出改革開放年代平凡個體的奮斗歷程,贊揚人民群眾的時代力量。
2015年,《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出臺,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創作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聚焦“中國夢”的時代主題。由此,大女主商戰劇與年代劇的融合成為這一類型劇的另一個發展趨勢,出現了諸如表現改革開放的《雞毛飛上天》《溫州一家人》《追夢》等, 表現鄉村脫貧題材的《右玉和她的縣委書記們》《歲歲年年柿柿紅》《麥香》等。這些電視劇不同于以往的大女主商戰,對無往不利的大女主祛魅,轉而描寫時代浪潮下的普通女性。其中無論是故事空間還是人物形象,都極具時代特征合。可以說,女性在商戰中迸發出的力量源自時代,脫胎于生活,發自于內心。就如《風吹半夏》描繪的,鋼廠展現著那個時代老國企獨有的氣象,烈焰紅唇、披著港風大波浪卷的許半夏行走其間,就像時代之風吹進了這個鋼鐵森林,畫面形成強烈的視覺沖擊。許半夏身上所折射出女性力量、時代精神正符合觀眾對新時代巾幗形象的想象和期許。《風吹半夏》的成功在于大女主“內外兼修式”的雙重成長:從事業上來看,女主角許半夏在改革開放中從一名普通女性成長為商業翹楚;從精神上看,她在“心理尋父→精神弒父→成為父親般的存在”這個過程中完成蛻變,逐漸成長為主宰自身命運的精神主體。更重要的是大女主敘事文本背后深刻豐富的人文積淀。女性商人形象的多元和立體,不僅豐富了電視劇中的女性形象,也反映了女性在當下主流話語中的生存現狀。
總的說來,早期商戰劇中的女性形象及其行動均較為單一,甚至有教條化的傾向。在與都市職場劇融合的階段,大女主商戰劇中的女性成長則隱匿著“瑪麗蘇”式的夢幻愛情想象。當前大女主商戰劇扎根于現實,避免塑造雷同的女商人形象:她們可以是堅強的母親,也可以是缺愛的孩子;可以勇敢追逐愛情,也足夠清醒;可以野心在外,也能內修于行。她們和千千萬萬的普通人一樣,有著相似的生活困境,在時代的洪流中摸索前進。這正是她們深受觀眾喜愛之處。
三、剝落無意識的凝視:大女主的身份認同
大女主商戰劇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一直存在著一種模式,那就是從表面上看是爾虞我詐的商業角逐,內里卻是“癡情女子負心郎”的愛情故事。很多作品往往借助偶像劇的套路,敘事視角單一,人物性格缺乏層次,女性角色完美甚至缺乏情節發展邏輯和人物性格邏輯。這種近似“圣人”的大女主總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評判眾人,也就難以迸發出打動人心的情感力量。即使主人公有強大的能力和高尚的品格,但商業權謀過于理想化、重要場景空間缺乏深度和震撼力、“無腦爽文”式情節等設置,均使得主人公的行動難以讓普通觀眾產生情感共鳴,影響了觀影體驗。最終這類作品的問題常常表現在男女主角的關系上。在很多商戰題材的大女主電視劇里,愛情是唯一核心的能指和意義所在,商戰變成了一個富麗堂皇背景。女主角雖然擺脫了早期商戰劇中沒有欲望的被動地位,但依然處于“被凝視”的狀態。女主角通常以道德的絕對純凈感化對手或敵人,并最終在更強大的男性力量的扶持下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在大女主商戰劇中,女主居于核心地位,男性角色的設置是為女性角色的行動服務,處于次要的客體地位。但在有些劇中,大女主崛起只是假象,性別、地位的置換并沒有給女性以平等的啟迪。如《那年花開月正圓》《正陽門下的小女人》雖然展現了商戰中的女性力量,但女主角都是以繼承等得到男性社會認同的方式成長、創業;《杜拉拉升職記》《星辰大海》等電視劇中充斥著大量瑪麗蘇橋段,女主的成功建立在霸道總裁一路扶持之上,跌入了商戰女主劇套路的泥沼。不論是男性解救女性于危難之中,還是男性作為啟蒙者的形象,都說明在這類劇中,男性仍是話語權力的中心,依然在性別秩序中處于主體地位,女性則依然是邊緣化、被動化的被統治者。這類劇作以大女主的外殼、兩性凝視的實質,演繹著“被凝視”的女性故事,而且往往為突出女主角的中心地位,將其他角色工具化,因而呈現出一種奇怪的狀態:所有的人物行動都圍繞著女主展開,女主是故事的中心,卻不是能力的中心,她的成功依賴于周圍男性角色的幫助。
真正的大女主劇,講述的絕不是仙度瑞拉通過愛情實現階級躍升的故事。女性的困境不應等待“王子”的拯救來解決,大女主的成功不應該依靠男性力量實現。反過來說,男性角色以及其他角色也不應該是工具人,更不應該為女主角的成長背書。
近年來一系列大女主商戰題材劇一改陳舊的敘事策略,在女性意識的話語表達上形成了新的敘事策略,使得大女主商戰題材的表現極為亮眼。當前大女主商戰劇更加審慎地對待“凝視”:女性的成長是否具有真正的主體性,男性角色是否淪為女性成長的工具。身份建構伴隨主體自身的成長,往往是大女主類型劇重要的敘事主題。以往的商業領域一直是男性角力的疆場,如今女性角色在商戰中不再從屬于男性權力之下。她們有目標、有野心、有實干精神,是真正意義上的大女主。在家庭中,她們保持著家庭決策的中心地位,敢想敢做,這以《雞毛飛上天》里的駱玉珠、《溫州一家人》中的趙銀花、《姥姥的餃子館》的姜桂芳等人物身為典型代表。在事業上,無論是在都市還是在鄉村,她們都能因地制宜,展現出極強的毅力,如《麥香》中女主角帶領全村脫貧致富,《楓葉紅了》中高娃經歷13次創業失敗最終成功。這些女性角色個性鮮明,人物設置“去瑪麗蘇化”,女性憑借自己的努力實現自我成長,男性角色也并不會一味地為大女主提供幫助。《風吹半夏》表現了女性在男性占有絕對主導地位的鋼鐵行業里闖出一番天地的過程,但并沒有刻畫性別對立:女主角許半夏和所有創業者一樣,縱橫謀劃、獲得資源,對愛情和事業的邊界有清醒的認知。她在創業的過程中經歷了人性和道德的考驗,也敢于承擔責任,勇于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凝視是主體攜帶著權力和欲望以主體意識進行觀看的方法。因此在這層含義下凝視的主體也就是權力和欲望主體的觀者,看向的是被權力和欲望支配的客體。”[6]從“凝視”的角度觀照大女主商戰劇,“大女主”是在展現真正的女性力量還是女性意識崛起的消費主義陷阱,觀眾是能夠判斷的。這也是近年大女主商戰劇擺脫“瑪麗蘇”的陳舊套路束縛的根本原因。大女主商戰劇中,女性角色從早期被規訓的賢妻良母,到兩性相互凝視的“瑪麗蘇”,再到消解凝視的真正意義上的“大女主”,體現了觀眾對影視劇女性形象訴求的變化。觀眾希望看到的是有力量、能決斷、敢負責的大女主商戰,而非糾結于愛情的“瑪麗蘇”或者耽溺于家庭角色的賢妻良母。近年的大女主商戰劇準確把握觀眾的訴求,致力于擺脫兩性凝視,讓女主形象貼近大眾。大女主不是“瑪麗蘇”爽劇架空的人物形象,而是“一個歷史的存在”,她們的行動具有時代的屬性,有特定時代的力量,這也符合新歷史主義。如《雞毛飛上天》是表現浙江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發展史,其中的女主角駱玉珠與丈夫一起精英小商品生意、互相借力、甘苦共度,從最初的零售小攤位到最后成立自己的企業,是典型的市場經濟時期的大女主形象。表現當下鄉村脫貧與振興題材的大女主商戰劇也不在少數,這些劇中的女主角往往是具有過硬專業技能的人才,返回自己的家鄉或者奔赴扶貧一線地區,發揮自己的才能幫助當地村民脫貧致富,這也契合了國家鼓勵大學生下鄉創業就業的時代要求。《我的金山銀山》《鮮花盛開的山村》《月是故鄉明》等都是這類主題。
大女主商戰劇中的女性角色擺脫凝視的身份認同路徑與新歷史主義所倡導的觀念不謀而合,將大女主個體敘事與宏觀歷史時代結合,尤其注重“家與國”之間的互相指涉。國家命運和個人命運交織在一起,個體人生境遇的千般變化則映射著國家的發展軌跡。以家喻國、以國喻家,從個人小集體的發展管窺國家大時代的進程。大女主形象往往將宏大敘事轉化為感性的實體,通過女性的成長軌跡使得抽象歷史可觀、可感,形成了對文化和人文生態反思的獨特敘事主題,兼具大眾文化的通俗性和精英文化的深刻性。如《風吹半夏》的女主角許半夏身上所折射出女性力量、時代精神正符合觀眾對新時代巾幗形象的想象和期許。她與原生家庭的抗爭與和解,她與“鐵三角”的福禍相依,她個人情感和事業,都以個人史的形式構筑起江浙地區經濟發展的地域史,在對一個產業地描摹中展現出一個時代的樣貌,深刻反映了歷史的變遷。時代性賦予該劇以深刻的現實力度,使得許半夏這個女性商人的形象走出了無意識凝視的大女主爽劇人設的窠臼,躍升為一個極具典型意義的、行進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的新型女商形象。該劇的工業敘事貼近生活本身,帶著現實主義的銳度,以“時代的弄潮兒”精神為注腳,于細微處闡釋時代洪流下的百態人生。這種宏大敘事和女性身份話語,剝除了大女主商戰劇中的凝視,是家國敘事策略的新歷史主義變奏。
結 語
大女主商戰劇敘事話語的轉變,使得女性形象更加豐富、多元,也使商戰題材電視劇的創作視野愈加廣闊,體現了業界在新時代對女性權利和女性話語表達的不斷探索。其中,女性角色擺脫凝視的身份認同路徑與新歷史主義所倡導的觀念是一致的。女性商人形象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影視作品中很難存在,在改革開放后一段時間內甚至也一度被忽視。當前商戰劇中女性商人形象的大量出現,意味著女性力量的崛起以及新時代女性社會身份認同感的增強。劇中女性形象折射出的女性力量、時代精神,正符合觀眾對新時代巾幗形象的想象和期許。大女主商戰劇的變化絕不是偶然,這其實反映了社會對女性認知的變化,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現實社會中女性主體意識、性別意識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