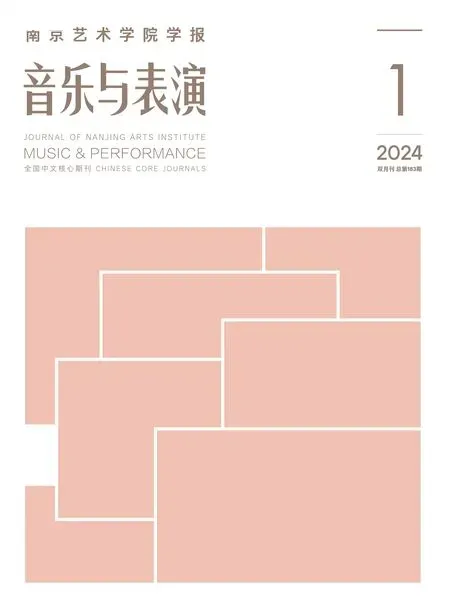技術賦能與價值反思:虛擬現實技術與表演藝術融合的演進與思考①
趙 樂 (中央戲劇學院,北京 100006)
孫 亮 (中央戲劇學院,北京 100006)
葉鍵平 (世界青少年合唱藝術家協會,中國香港 999077)
媒介技術的進步與革新不僅重塑著媒介生態環境,同時也推動著人類社會新的轉型。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1938—)將“視覺生成新的交互界面”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 ,他認為整個世界正處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初期:生產方式、消費方式和關聯方式正在物質世界、數字世界與人類自身相融合驅動下,發生根本性轉變。歷經半個多世紀的“跳躍”式發展和“降檻”式演進,“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技術從尖端科學領域拓展至人類日常體驗,成為“人人皆可用”的大眾化傳播媒介。
我國近年來發布了一系列政策鼓勵、推動虛擬現實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強調“虛擬現實+演藝娛樂”行業有機融合發展[1]。隨著虛擬現實與表演藝術的不斷融合,這一領域相關研究也成為學術界討論的一大熱點。總體來看,當前學界主要從表演藝術本體和技術實現路徑兩方面進行討論②如武昊然、王曉寧等從戲曲的表現形式舞臺的效果展現和文化傳播方面,強調虛擬現實技術對戲曲發展的影響和應用。鄧雅川、成嘯、朱雪峰等關注虛擬現實技術對于舞臺空間、表演形式與內容、呈現媒介等方面帶來的變革,思考技術和舞臺藝術之間的建構關系。對于技術路徑的探討,包蟠瑜、蒙曦、林凡軍等則從技術可行性層面如信息提取、虛擬建模、虛擬場景建構、交互設計等方面分析如何突破現有壁壘,與不同藝術形式相互交融及其轉型成本、盈利模式、數字技術紅利釋放等現實問題與挑戰。,但相較于近年來在新聞傳播與視覺如電影、影像傳播等領域的研究成果,以及虛擬現實技術與舞臺表演藝術領域的行業實踐,對于虛擬現實技術與舞臺表演藝術結合的思考不足以解決發展中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基于此,本文將梳理虛擬現實技術與表演藝術融合的演化路徑,探討虛擬現實技術如何賦能舞臺表演藝術以及深層的技術權力與治理問題。
一、路徑:虛擬現實技術與表演藝術融合的演進
(一)21世紀前:幻象空間的營造
傳統的劇場本身就是“最初的虛擬現實機器,它邀請觀眾進入既能互動,又使人沉浸的想象世界”[2]184。劇場作為一個封閉空間,如同巨大畫布,表演者通過寫意性的動作或道具暗示想要意指的事物,喚起觀眾想象力感知而共享一個虛擬幻象表演世界。而外在的舞臺虛擬空間和鏡像反射空間重塑著觀眾視覺體驗[3]。從16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初,“透視畫”(quadratura)①Quadratura是指一種在建筑天頂或墻壁上制造出三維空間的幻覺,從而在視覺上拓展建筑空間的裝飾技術。常常被使用在戲劇舞臺上;17世紀,藝術家們利用光源將透光的玻璃畫片投射到白墻或布幕上;到18世紀Phantasmagoria劇團恐怖戲劇秀出現立體投影、鬼影特效,大量投影燈具展現“鬼魂”,使得觀眾沉浸于虛幻錯覺之中;19世紀的“佩珀爾幻象”(Pepper’s ghost)利用玻璃板和燈光來制造透視效果,使得舞臺上的角色或物體忽然出現或消失,常被用來創造幽靈或幻像般的效果。正如奧利弗·格勞(Oliver Grau,1965—)的觀點:“歌劇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幻覺。……基于精確數學計算復雜廊柱大廳和奇幻建筑是通過光線反射、鏡子巧妙使用來實現其栩栩如生的效果。這些技術為舞臺帶來全新幻覺效果。”[4]37
進入20世紀,計算機成為一個強大的“混合”工具,計算機技術成為虛擬現實技術與表演藝術融合的物質基礎,從傳統封閉虛擬空間轉換至以計算機圖像控制的虛擬空間為主導。1936年是計算技術和媒體融合的重要節點,英國數學家艾倫·圖靈發表了著名的《論可計算數》的論文;同年,德國工程師康拉德·楚澤(Konrad Zuse,1910—1995)研制出了第一臺數字計算機。藝術家們利用新媒體工具進行藝術創新,如法國作曲家皮埃爾·舍費爾(Pierre Schaeあer,1910—1995)率先使用計算機創作了作品《地鐵練習曲》[5]、1979年的林茨電子藝術節(Ars Electronica),特·加洛維(Kit Galloway,1948— )和雪瑞·羅賓諾維茲(Sherrie Rabinowitz,1950—2013)制作的作品《一個沒有地理邊界的空間》(A Space with No Geographical Boundaries1977)[6]等。至此,“圖像、運動影像、聲音、形狀、空間和文本都成為可供計算機處理的一套數據。……計算機不再僅僅是一個計算工具……它變成了媒體處理器”[7]25。
“VR是一種沉浸式媒介體驗,它復制的世界可能來自現實環境也可能來自想象空間,用戶與VR世界的互動方式是身臨其境。”[8]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數據頭盔和數據手套為代表的虛擬空間裝置出現,標志著具有高度沉浸感的虛擬現實技術的蓬勃發展。1962年出現的 “傳感影院”(Sensorama)可視為虛擬現實設備的雛形;1966年,艾凡·薩瑟蘭(Ivan Sutherland,1938— )和鮑勃·斯普勞爾(Bob Sproull,1945—)為貝爾直升機公司研發頭盔顯示器,它能夠提供一種三維視圖,可以使人們投入在一個陌生環境中實現沉浸感。20世紀90年代,誕生了諸如“Placeholder”(1993)、“Dancing with the virtual Dervish:Virtural Bodies”(1994)、“Osmose”(1995)等一批具有開創意義的作品。②Placeholder是一個虛擬現實項目,由Banあ表演藝術中心與Interval公司制作的多人虛擬現實行動的新嘗試。Dancing with the virtual Dervish:Virtural Bodies 是1992年在Banあ藝術中心首次演出,結合身體、建筑和虛擬現實的作品。Osmose是一個頭戴式顯示器,具有沉浸式的互動虛擬現實裝置,帶有3D計算機圖像和交互式3D音效的一個作品。但這類作品大多是在特定地點的藝術裝置,只有極少數人才能接觸到,加之當時大部分技術都處于初創階段,制作成本較高,制作周期長,離大眾相對遙遠。早期的技術應用更像是藝術家們的實驗場,不斷打破原有的邊界,探索不同的表達方式和藝術體驗,將藝術的一系列新嘗試和變革引入了新時代。
(二)21世紀:虛擬現實技術與表演藝術融合的多元化發展
虛擬現實技術集合了人工智能、計算機技術、三維建模技術、傳感技術、輸入算法、交互技術等多技術融合,運用計算機生成圖像(computer generated imagery)、360度全景視頻(360-degree Video)、立體圖像捕獲(volumetric capture)[9]、5G通信技術等多技術構建出“無所不能”的虛擬世界,藝術想象力的邊界被無限延展,視聽景觀化的呈現方式為體驗者營造更加“真實”的沉浸式“在場”。基于國內外現有演出形式,虛擬現實技術與表演藝術融合的呈現方式大致可分為以下四類:
1.數字虛擬人表演(Digital Virtual Human Performance)。“數字虛擬人”是指通過“人格化”虛擬形象編碼,以真人配音與語音采集音源為基礎,后加入CG技術、動作捕捉等技術合成,從外表、動作到聲音都具備擬人化特點,以虛擬形象面向大眾進行展演。數字虛擬人表演的出現建構了新的演出主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虛擬歌姬(林明美)和虛擬偶像(初音未來)。
2.真人虛擬化表演(Human Virtualization Performance)。“真人虛擬化”是指利用信息技術與圖形學技術將其全身及肢體動作進行全方位數字化與模擬構建,運用全息投影、3D技術等相互結合,使某位藝術家復現現實舞臺演出。全息技術在舞臺表演藝術上使用較為廣泛,利用光電干涉與衍射原理,通過CCD記錄物體全息圖,傳入到計算機存儲空間,計算機后臺處理相關信息,并進行分析重現三維圖像的一種數字處理技術[10]。真人虛擬化表演以融合時空與虛實兩個維度滿足觀眾的感官刺激,如數字王國(Digital Domain)與3C科技精品商場三創生活園區于2017年推出《今日君再來:虛擬人鄧麗君音樂奇幻SHOW》。
3.人機交互表演(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Performance)。人機交互表演是由人類參與電腦游戲或VR(Virtual Reality) 中表演,由電腦軟件程序設定虛擬人、情境或者事件,虛擬空間中舞臺上展示是虛擬人物或角色,人的真實身體已經隱藏到熒幕之后,在其程序中投射的影像是以人為模擬對象,不斷在拓寬用戶體驗邊界,如2019年第三人稱射擊游戲《堡壘之夜》(Fortnite)“Marshmello魔幻電音現場”。除了游戲的人機交互表演外,另一種類型是借助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外部配備的感知設備參與表演,如2020年讓·米歇爾·雅爾在VRChat進行VR虛擬化表演的首場“Alone Together”音樂會。電腦軟件程序與可穿戴設備的出現為表演藝術的沉浸性、互動性提供可能,也強化了參與者的感官體驗。
4.人機協同表演(Human-machine Cooperation Performance)。人機協同表演簡單而言是“人”與“機器”之間“協作”,以真實表演者為主體,虛實變換的舞臺場景為輔助,或采取與數字化虛擬人合作的形式以達成“虛實結合”的舞臺表演。人機協同表演的出現得益于擴展現實(XR)、虛擬演播室技術、實時渲染技術等技術發展,人機協同大部分運用于線上直播演出。線上直播演出與XR技術結合主要體現于兩大方面:一方面是通過建立全虛擬環境,表演者在綠幕背景下進行表演,而后利用技術手段將綠幕背景轉化為預先設計好的虛擬視覺場景,諸如“90年代劇團”(Nineties Productions)的《死亡象征》借助ZOOM平臺空間演出,通過鏡頭運用、表演與綠幕達成特效構建了整個演出的敘事。另一方面則是在真實演出場景中,將制作完畢的圖像與真實圖像進行結合,實現疊加的視覺效果[11],如春節聯歡晚會節目《星星夢》《牛起來》實現了從2D維度技術運用開始向720度全景的三維立體實景圖像技術運用發展。人機協同表演為表演提供高度逼真環境和實時交互性,實現了人與人、人與機器間的高效協同創演。
在當代媒介技術推動下,虛擬現實技術與舞臺表演藝術在內容生產、傳播、接受等各個環節深度融合,重新定義了傳統舞臺表演藝術在視覺與聽覺、空間與時間、真實與虛擬等多個維度的呈現方式。數字供應鏈、創新鏈和產業鏈建設為演出行業提供更有效的服務供給,同時隨著產業化與數字化協同轉型所形成的新動能與演藝娛樂不斷融合,逐漸衍生出不同形態的呈現方式,從而構建出表演藝術內容與表達的全新范式。
二、賦能:觀者的狂歡與共創
在虛擬現實技術和表演藝術融合發展過程中,“虛擬現實藝術家”①“虛擬現實藝術家”特指藝術創作群體,他們作為表演的創作者和表演者,不再依靠傳統現場表演方式,而是越來越依賴科技公司以及科技公司相關聯的技術集成以及藝術產業(游戲、VR等)助力,借助屏幕作為載體展現“虛像”。(Virtual Artists)這一新型藝術家群體應運而生。作為表演創作者或表演者的他們不再依靠傳統現場表演方式,而是越來越依賴科技公司及其背后相關聯的技術集成與藝術產業(游戲、VR等)助力,以屏幕作為載體展現“虛像”,改變傳統觀演時空關系從而拓展新受眾群體,逐漸形成具有感官重塑性、具身參與性、虛實共創性等特點的全新表演形式。
(一)感官重塑性
虛擬現實技術的融入對重塑傳統現場表演時空關系發揮了關鍵作用。從空間角度來看,傳統的表演藝術強調特定演出空間的“現場性”,而虛擬世界中表演則通過沉浸和在場體驗來重塑觀眾的感知,重新定義表演藝術的交互性、敘事與“在場”,“將有限的劇場或某個物理空間延展成無限空間”[12],創造如帶有文化象征的空間和自然景觀空間等復合型表演空間場景,這不僅極大地擴展了表演空間的可能性,同時為演員提供了更為多樣的表演空間,也為觀眾提供了全新的感知體驗,使其也能作為表演者參與其中。
在虛擬技術的輔助下,觀眾變成了虛擬世界主導者和狂歡者。在這一新的時空關系中,每位觀眾都可以通過“虛擬身份”參與,不再有演員與觀眾的區分,而是作為獨立主體出現。在虛擬空間中,人們以“虛擬身份”作為個體的標識,忘卻了社會地位、文化層次、經濟地位等壁壘,共同參與巴赫金所描述的狂歡:“沒有舞臺,沒有腳燈,沒有演員,沒有觀眾……這是展示自己存在的另一種自由 (任意)的形式。”[13]借助虛擬現實技術,任何人都可以通過移動端體驗虛擬表演空間場景,并在預設虛擬空間中自我創造體驗。這項技術打破了表演藝術的傳統線性敘事結構和平面觀看視角,通過360度自由視角提供全景式敘事和體驗。觀眾能夠自主選擇觀看的角度,關注不同的細節或選擇偏好的互動方式,從而塑造個性化的體驗,實現了去中心化的個人場景構建,使得“每個人成為表演的中心”成為現實。
從時間維度上考慮,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揭示了“萬物皆流變”的本質。時間的存在是表達萬物生死存亡的順序。而虛擬現實技術制作的表演藝術是從持續性的時間長河中截取某一連續的時間段落進行重現。麥茨提出的媒介內容的時間觀念——即“講述故事的時間”(presentation time)與“故事講述的時間”(narrative time),兩種時間維度在虛擬現實中被重新定義,“當我們被徹徹底底拉進了故事講述的時間而全然忘記了講述故事的時間,那我們就是進入了沉浸的狀態”[14]。例如2023年北京廣播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上,虛擬鄧麗君與王心凌、韓雪同屏演唱歌曲《我只在乎你》,跨越時間的經典重現以虛擬共生的方式實現了對于觀眾感官體驗的升維再造。
(二)具身參與性
如果傳統技術作為工具拓展了觀演體驗,那么虛擬空間的表演則通過現實世界的數字化和幻象重構了新的“真實性”主體,身體的“具身性”參與就成為表演藝術未來實現人機共創的關鍵。一方面,“存在”構成了“真實性”基礎,雖然虛擬世界并非現實的直接反映,但它基于特定的“感知”創作而成,故虛擬角色的構建也依賴于人類的情感和社會經驗。在虛擬空間的表演體驗中,盡管缺乏現場表演環境的客觀真實,參與者在意識和情感層面卻能感受到身體的真實體驗。另一方面,身體作為我們與世界交互的第一場所,起到結構化信息流、創建和誘發問題解決所需要的數據和資料的作用[12]。身體能夠在虛擬表演空間中實現交互是基于計算機系統或如VR設備與數據手套等可穿戴設備的外部硬件的智能化,這些設備將身體感官與虛擬世界的圖像相連,通過外部設施如鼠標、計算機等,與認知形成緊密的聯合體,讓參與者全身心沉浸在虛擬世界中,形成具有虛擬身份形象和真實情感體驗的新型身體認知。對于受眾來說,他們成為虛擬空間實踐的主體,包括人的主體性和體驗主體的客觀真實性。每位受眾的主體性體現在他們作為主體通過控制虛擬實踐中介進行的行為上。虛擬空間的表演不僅是現實表演的反映和衍生,也是在強化人的主體性基礎上的創新,客觀真實體驗構成了參與者對表演的認知基礎。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迅速發展,AIGC(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生成能力為虛擬現實技術和表演藝術的融合帶來了更高的創造力、真實性和成本效益。提升技術應用效能的同時也產生了對于技術的“路徑依賴”,傳統表演藝術所強調的現場“靈暈”也被重新定義。在虛擬現實中,表演藝術的“空間”被重新塑造,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間,而是以屏幕作為載體,展現“虛擬圖像”。結合舞蹈、音樂、戲劇、視覺藝術等跨界融合,創造出超越現實的視覺和音響效果。通過“超現實表演”“虛擬互動式演出”“腦機接口表演”“感官拓展體驗”等多元素融合形式,擴大了表演藝術體驗的感官新組合。
(三)虛實共創性
虛擬空間的傳播帶來了雙向互動鏈條,打破了傳統觀演關系中表演者與觀眾之間的空間界限,還讓每位普通觀眾通過移動端就能體驗虛擬表演空間,并在其中自我創造與體驗虛擬內容。在此背景下,虛擬現實技術推動表演藝術共創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人物共創。以日本虛擬偶像初音未來為例,她是“音樂+動漫形象+網絡數字媒體”的結合體,是由雅馬哈公司2004年發布的“Vocaloid”音合成軟件生成的數字虛擬人。她的形象由插畫師KEI創作,日本CRYPTON FUTURE MEDIA公司基于雅馬哈VOCALOID系列語音合成程序開發,展示了數字虛擬人物在共創中的無限可能。
其二,空間共創。當可感知設備實現應用場景全覆蓋時,個人場景構建將是未來發展趨勢。與現在的集體狂歡不同,個人化意味著每個人都是“表演中心”。互聯網、移動客戶端等技術設備方興未艾,觀眾的關注點從傳統劇場場景向虛擬世界場景轉變。在虛擬環境中提供的可視化信息工具,還賦予了用戶在3D信息空間中自主構建和修改空間、進行藝術實踐的可能,游戲《第二人生》就是一個開放性與個人化的開創性實踐先鋒。
第三,場景共創。虛擬現實技術與游戲、音樂、視覺藝術等產業的不斷融合,形成了多感官的體驗。觀眾能夠在同一時間感知到越來越廣泛的內容。例如,在《堡壘之夜》與美國饒舌歌手Travis Scott合作的“Astronomical”演唱會中,玩家可以在虛擬環境中與其他玩家和表演者互動,體驗從海底到太空的豐富場景特效和電子音樂的視聽盛宴。這種全新的沉浸式體驗,是虛擬現實技術在表演藝術中共創場景的生動展現。
三、反思:人機共生的未來
人們使用互聯網的時長大幅增長,虛擬世界的角色由原先作為現實世界補充逐漸轉變成為現實世界的孿生空間,技術的發展不僅改變人們與表演藝術之間的關系,也改變人類自身對當下與未來的認知。
(一)被資本規訓的“觀者”
人對物的認知來源于感知與經驗,后經發展通過各類外在工具對外界信息把握不斷認識、分析與解讀。在蒙昧時期,人類多以感知和經驗進行想象,是以意識作為主觀性媒介。隨著書籍、戲劇、電影等媒介物產生,人類意識逐漸外化和遷移到媒介之中。而虛擬現實技術則以回歸自我意識作為主體性媒介,并采用觀者第一視角使其身臨其境。“存在”是“真實性”基礎,虛擬世界雖沒有現實所指,但必然是依據某種“感知”創作而成,而虛擬人物建構也基于人的情感經驗、社會經驗等,因此觀看者會順理成章地認同虛擬世界中所建構一系列“感知真實性”。
在虛擬世界中,視覺感知充當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在視覺奇觀的虛構世界會影響到觀看者對于真實世界的直接判斷和理解。一般來說,感知包括看、聽、聞、觸、嘗五感,其中視覺的優先性早已成為共識:約翰·伯格(John Peter Berger,1926—2017)提出“觀看先于語言……正是觀看確立了我們在周圍世界的地位……”[15]1;陳嘉映認為“視覺原則上都是上意識的,差不多百分之百意識到,你看到了你就知道你看到了”[16]53。與傳統電影的方形框視角不同,依賴虛擬現實技術的表演藝術在構圖上采用第一人稱視角,這種方式更注重于觀眾對于“附近”環境的認知和如何圍繞其建構世界。這種“視覺無意識”的觀看模式打破了傳統的表演藝術欣賞狀態,引起一種理解上的障礙,即“表演盲知”,由于視覺呈現的沖擊力,觀眾往往只能獲得淺層的審美體驗,難以深入理解作品背后的深層價值和情感共鳴。表演是用來表現藝術家觀念中的藝術形象、藝術構思、藝術結構的一種人的藝術行為[17]369。然而,在虛擬現實的環境中,觀眾逐漸習慣于接受和操縱“仿擬”信息,這導致了真實感的消失,虛擬現實技術將現實表演藝術完整復刻或重塑,受眾沉浸于虛擬現實技術所塑造的擬真環境中。所見的“超真實”[18]世界實際上是技術操作者通過捕捉、剪輯和變形所構建的,是媒介通過實時傳播功能“虛擬化”的紀實敘事作品。
藝術體驗來源于我們所處的時間、空間和環境對我們感知的影響。藝術家通過觀察、思考和表現捕捉瞬間,將其轉化為藝術作品,引導觀眾思考人類與現實環境的關系。然而,在虛擬空間中,奇觀化、情感化、陌生化的視聽表達可以被無限擴展和操控,導致觀眾可能會忽視對這些奇觀背后的更廣泛的文化、社會和人類關系的考察,以及對時間、空間和環境的深層思考。
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場景特效和虛擬形象的真實性不斷增強,觀眾的感官閾值也隨之提升。虛擬現實技術構建的奇觀化體驗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對觀眾感官的控制。表面上,觀眾在虛擬空間中體驗到一種狂歡般的愉悅,看似是一個全民共享、自由平等的烏托邦,但實質上是由虛擬現實技術構建的文化奇觀。新的感知體驗在潛移默化中重新規訓了人們對現實世界的感知。這一景象更加重現了柏拉圖眼中那些洞穴里的囚徒們:新的技術范式下壓縮了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和長度,“人們對層次感缺乏認知,世界趨于扁平化,既指向鄰里在個人生活里的‘隱身’,又指向社會生活認知中‘小世界’構建的不完整”[19]。
在數字世界中的數字層級及其權力的控制下,虛擬現實技術所呈現的表演藝術用于遮蔽社會的不平等,現實世界中身體的主體性被不同程度地消解。在虛擬世界奇觀中,觀眾無法感知藝術審美存在,一切都來源于技術所打造的幻象,觀眾的審美感知在技術的引導和規訓下進行自我審美調適和不斷的矯正,以適應虛擬世界的邏輯,最終成為虛擬世界的“感官囚徒”。
(二)藝術主體性的價值重建
虛擬現實技術是否會導致對傳統審美的異化?是否不斷威脅著人對藝術本質的理解?表演藝術生產和發展依賴于技術這一現象存在什么問題?對虛擬現實藝術作品的審美是否立足于視覺奇觀化體驗?那么藝術本質是什么?作品所表達的價值觀由誰塑造?隨著表演藝術的話語權不斷被資本和技術解構,誰在這一過程中更具有主動權?如何看待技術對于表演者、藝術作品和觀者的關系的改變?筆者認為,面對未來的變化和挑戰,以表演藝術主體價值為前提的意義重構是實現人機共生的關鍵所在。
馬克思在其論著《資本論》《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20]中對機器和技術的論述,為我們深入理解技術與表演藝術結合背后的權力結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機器觀念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且反映了資本剝削的合理化。機器僅是資本運作的一個環節,而非其全部。這一點對于理解虛擬現實技術在表演藝術中的應用尤為重要。這種視角可以幫助我們批判性地觀察機器在資本生產方式中的作用,理解其背后的運作邏輯,并探索其所隱含的世界觀和背后的權力結構。資本邏輯決定了技術融合的目標、形式和結果,因此,必須具體地治理資本對虛擬現實技術應用和控制的邏輯。在資本主義驅動下,對于虛擬現實技術在表演藝術中的價值,應采取辯證的視角進行考量,既認識到其潛在的創新潛力,又警惕其可能帶來的資本剝削和權力不平等的風險。
一方面,資本邏輯在推動虛擬現實技術應用于表演藝術領域時帶來了顯著的社會福利。這首先體現在生產力的顯著提升上,其中虛擬現實技術的應用不僅是對傳統表演藝術的創新,而且技術集成極大地推動了虛擬世界的建構,從而拓展了傳統“表演”概念的邊界。在此基礎上,虛擬現實技術與高科技產業、設計產業、虛擬文化商品服務以及文化資產等領域的進一步融合,突破了傳統表演藝術產業的局限,實現了與高科技領域的產業整合,并聚合了多種創意元素。因此,不僅要承認資本的重要性,還應當充分利用和發展資本,為表演藝術的發展提供更為豐富的想象力和物質基礎。
其次,資本邏輯驅動下的技術應用也使人的社會關系得到了更為開放、豐富和深入的發展。在虛擬空間中,人們作為獨立的虛擬角色進行社交活動,這不僅拓展了他們的社會關系網絡,還創造了一個多重社會身份和關系構成的新數字生活空間。正如麥克盧漢所言,媒介是人的延伸,在虛擬空間內也得到了體現,現實環境中的社會關系在虛擬世界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延伸。
另一方面,資本追求利潤的本質并未改變,因此需要最小化資本運動內在邏輯的負面影響。在科技和產業互動中活躍的“虛擬現實藝術家”群體成為具有當代意義的創意群體。他們認識到技術集成對表演藝術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而技術集成與表演藝術的融合通過“利益共謀”模式加以聯系。然而,資本運用技術建立信息繭房和數字鴻溝,打造了一種新的“美麗新世界”,而觀眾則在這個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淪為“感官囚徒”,最終大多數人的主體性被消解,只有少數人才能夠影響甚至決定技術應用。因此,在人類與技術相對平等的表象背后,實際上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這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資本的逐利本性,規范和引導資本的健康發展。同時,技術操控者也需完善其自我治理機制,強化技術使用的倫理。技術運用所構建出的“視覺景觀”并非衡量藝術作品價值高低的唯一標準,重視以藝術本體為前提的審美與價值觀念,藝術家與資本之間需要建立相互合作的伙伴關系。
蘇珊·朗格曾說:“所謂藝術……表現人類情感的外觀形式。”[21]105藝術是人類情感世界的客觀化表達,人是藝術的創造者也是其享有者,藝術的創造目的在于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地發展。在視覺文化占據主導地位的背景下,我們需要遵循表演藝術創作的規律,完善適合表演藝術的全產業鏈。在人機共創的未來,只有扎根于人類文化和共同價值的基礎上,依靠虛擬現實技術的表演藝術才能超越傳統意義上的表演藝術,在視聽呈現、傳播方式、受眾關系等層面實現新的突破,這將為表演藝術生命力的延續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結 語
新技術助力推動舞臺表演藝術的發展并不斷深度融合,是一個隨著技術不斷更新、變化的過程。不管是對其類型研究還是特性研究,對于未來表演藝術的高質量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如同尼葛洛龐蒂所指出的:“虛擬世界的技術能使人工事物像真實事物那樣逼真,甚至可能比真實事物還要真。”[22]112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當前虛擬現實技術對舞臺藝術發展造成的影響,如藝術審美變化、數字虛擬人A-SOUL“塌房”、文娛領域的資本退潮等問題都需要關注。虛擬現實技術推動“虛實相生”發展,虛擬現實與真實世界互相滲透互利共生,共同促進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總之,無論技術如何更新迭代,以藝術為前提的主體價值亙古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