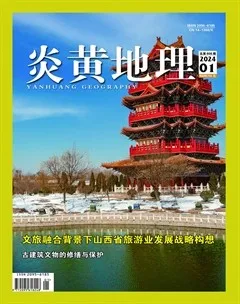周城白族栽秧會的功能及影響
楊潤豪



云南的多元民族文化和傳統民族村落是多元文化相互結合接駁的天然土壤,將旅游與民族文化相結合是新發展途徑。洱海周邊白族村落的栽秧會是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產物之一,在弘揚傳統文化的同時,也促進了文旅結合的地方旅游經濟的發展,不僅是對地方傳統文化的傳承,也不斷將新的時代內容加入傳統農耕文化活動之中。栽秧會不僅將村落的內部聯系得更加緊密,也聯結著地方經濟發展和文化共榮之間的關系。栽秧會不僅是白族三千多年農耕文明的文化結晶之一,也是以中華民族傳統農耕文化為主干,以鄉村旅游經濟發展為骨皮,以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為內在機理的文化盛事。
周城栽秧會概況
農業是大理地區人民早期的主要產業之一。大理農耕文明的出現距今已經三千多年,也因大理在滇西地區“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在我國歷代王朝對外開拓和交流的過程中,大理地區的少數民族文化與中原地區漢文化不斷加深著彼此的聯系。農耕文明的發展與變遷是漢文化與白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最直接的體現,大理地區白族的農耕文化既吸收著漢族和周邊少數民族先進的農業生產方式和耕作技術,也將先進的農業生產方式和耕作技術融入本民族的農耕文化中,逐漸形成了具有白族特色的農耕文化和一系列農耕活動儀式。周城白族栽秧會據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楊麟所述,距今已經發展了一千多年,在栽秧會出現、繁榮、復興的千年來,其內在的文化屬性和農耕屬性一直得到較為完整的保護和傳承。關于栽秧會在1949年前的歷史大多由秧官和村落老人口述記憶,在1949年后,栽秧會逐漸由村級單位自發進行舉辦;從20世紀50年代周城村成立互助組,以換工互工的方式組織村民進行規模化的農業生產活動;到20世紀70年代由生產隊牽頭出資舉辦;再到20世紀80年代因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廣泛推行,栽秧會儀式內容逐漸簡化和淡化。近年來,隨著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倡導,周城白族栽秧會在新時代煥發了新的生機,不僅于2017年被正式列為云南省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更演變成喜洲鎮周城村每年舉行的“白族農耕文化節”,吸引著來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游人。
最初的栽秧會僅是環洱海地區村落的農業祭祀活動,隨著大理旅游業的發展,周城栽秧會的規模也逐年擴大,并逐漸豐富著新的內容和內涵。在內容上,栽秧會活動秧官所使用的“圣旨”、樂手所吹的《耍龍調》內容是在大理地區與中原王朝深入的交流交往交融史中不斷產生的;在內涵上,栽秧會中所展演的節目折射農耕生活、天人關系、宗族社會、禮樂文明等內涵。栽秧會所體現的農耕文化不僅是白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的周城栽秧會已然成為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和旅游觀光相結合的文化、經濟共同體。
栽秧會的活動不僅僅是大理環洱海區域白族所獨有的,在長江中下游、淮河中下游地區的漢族聚居區域,也流行著插秧前的開秧門儀式,祭拜土地神、喝開秧酒、唱秧歌等活動。在貴州省從江縣西部的苗族人民為了感恩自然、祈求五谷豐登、風調雨順,也會在田間舉行為期3~5天或者7~9天的開秧門儀式,當然少不了情歌對唱、斗牛、斗雞等娛樂活動;在安徽滁州市的開秧門是農民在秧母田里拔秧的第一天,家主領埂下田栽秧,之后栽秧人才開始大面積栽秧,儀式中男女相互糊稀泥,預祝稻谷盈倉。栽完秧稱“了秧”,要喝“了秧酒”;淮河以南地區的農民視開秧門為辦喜事,以迎一年農事的開端;南平地區開秧門稱為“起田頭”,選擇吉祥的日子栽秧,帶上祭品到田里拜天地、求神靈,隨即做田埂,祈求自家風調雨順、年年豐收。栽秧會的舉行不僅是白族農耕文明的一部分,也是中華農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不同區域不同民族都有類似形式的活動,也都表達了傳統農業對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美好愿望。
周城栽秧會儀式程序主要由儀式準備、開秧門、關秧門三部分組成。儀式準備的內容主要包括確定栽秧會的時間、日程安排、扎秧旗等;開秧門主要是指在下田插秧之前舉行的出秧旗、祭秧旗等活動,出秧旗、祭秧旗分別在周城村的龍泉寺和周城村文化大院舉行,寓為“通知神仙,我們要舉行栽秧會了;將秧旗、秧鑼授予村主任干部,得到允許舉辦栽秧會的名義。”關秧門則是在下田栽秧后祭拜田公地母,由今年栽種秧田的主人家宴請賓客,以答謝村民的辛苦勞作。近年來隨著大理地區旅游業的復蘇和游客人數的增加,原本在關秧門階段舉行的宴請改為在栽秧會當天中午十二點舉行,不論是本村村民還是到此游玩的游客均可以參加宴會。
周城栽秧會儀式流程表
時間 階段 活動
前一周 儀式準備 擇期
前一周 制定日程
前一天上午八點半 扎秧旗
當天上午八點半至十一點半 開秧門 出秧旗
當天上午八點半至十一點半 祭秧旗
當天中午十二點 在贊助者家宴請賓客
當天下午兩點至四點 栽秧
當天下午兩點至四點 祭拜田公地母
當天下午四點至五點 霸王鞭表演
當天下午五點 關秧門 關秧門
資料來源:根據調研筆者自制
周城栽秧會的功能
栽秧會是農業社會白族勞動人民為認識和改造自然而產生的祭祀行為;是白族傳統文化在生產生活中的聚合體和集中反映;是白族人在農業社會中對宗教和原始信仰的一種敘事表達方式。周城白族村舉行以農耕生產為內核的栽秧會,目的是通過栽秧會祈福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并在舉行的過程中使參與者和觀摩者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進一步加深。在栽秧會舉行期間,周城村村民均是公益參與的,除去游客,參與栽秧會的村民就達到三四百人之多,負責抬秧旗的、跳霸王鞭的、扛農具的、背秧苗的、村民在栽秧會的整合下形成村落共同體,共同體內部分工明確,外部則呈現出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栽秧會形式和規模,這是栽秧會文化功能的體現。
栽秧會的社會功能可以分為兩部分,即調節社會關系功能和輔助基層自治職能的功能。據栽秧會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楊麟所說,栽秧會舉辦的經費來源于村中具有一定名望和地位的村民,由其出資其他村民出力共同舉辦,相應的插秧的地點也是位于贊助者自家的農田,是一種以報酬和勞動力鏈接的關系。但栽秧會的舉辦的內涵遠不止如此,實質上栽秧會活動是一種村落內部的農業生產互助行為,發展至今已經成為村落中每年隆重的節日和聚會。參與栽秧會的人群包含了村落中的各個群體,不僅需要村委會和秧官團隊從中協調,也需要村落的周德會、方廣會和蓮池會等力量的共同參與。因此,栽秧會在村落的生產生活中有著調節社會關系的功能。而栽秧會將白族傳統的民間信仰與在地方承擔基層自治職能的居委會相連接,將官方的用意與民間的想象結合起來呈現出豐富隆重的農耕祈福祭祀活動,栽秧會承接著政府對于發展地方文化與地方經濟的發展方針,也承擔著白族人民對于農業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美好期望。
對外交流功能。除了地區傳統農耕儀式的傳承外,周城白族村于2015年與湖南省桑植縣合群村結為姊妹村,周城村在桑植白族舉辦農耕文化節期間,為其提供幫助,并在第二屆桑植縣白族村舉辦農耕文化節時,由周城村村委帶領周城栽秧會人員一行60人對桑植白族進行定點交流和幫扶。通過對栽秧會農耕文化的再創造,幫助湖南桑植縣合群村振興鄉村文化經濟和旅游,不僅突破了地域和族際的邊界,形成周城村與合群村之間的文化共同體,還建構了兩村之間的經濟發展共用體。
農業祭祀功能。栽秧會出發時在龍泉寺的村落集體祭祀、午餐后在贊助者家中的家庭祭祀、栽秧期間對田公地母和本主的祭祀等的儀式流程,均體現出栽秧會的祭祀功能。在傳統農耕文明社會,農業生產的穩定性依賴于自然環境的相對穩定,因此,大理地區的先民對與農業生產相關的自然環境有著普遍的自然崇拜。對各路神明的祭祀和曲調唱腔中的祈福內容,既有著娛人的功能,也有著娛神的意涵。在栽秧儀式舉辦前栽秧隊伍會從龍泉寺出發,繞村落一周也是為了“讓神仙知道周城村要栽秧啦,要保佑我們呀。”發展至今的栽秧會不僅具有農業祭祀的功能,甚至栽秧會所祈福的神明也不局限于與農業生產有關的神明,而是表達了周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彰顯著白族人民生活中日常的神圣和神圣的日常。
周城栽秧會的影響
文化影響。周城栽秧會并不是白族獨有的節日活動,而是白族、漢族等民族共同參與的大型節慶活動。社區和政府對地方節慶文化的重視,再加上旅游的推廣和宣傳,久而久之使年輕一代對栽秧會產生或加強了文化認同,同時其中所體現的中華傳統農耕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景觀,既是白族人民對其他民族優秀農耕文化吸收和融入的物質文明追求,也是從最深層次的精神文化出發,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和歸屬的文化表達。具體而言,中華文化認同是由各民族成員在情感和歷史上的相互認同、在文化上的彼此聯系和對美好生活追求三者共同構建起來的。栽秧會所體現的白族農耕文化內容,從根源上講是白族與漢族在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產物,是各民族共同構建的文化認同。
生態影響。栽秧會中祭拜的龍王、田公地母等自然原始崇拜隱含著大理地區白族先民在農業耕作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關于人與土地、洱海的關系的生態哲學思想,以龍王、田公地母等為代表的自然原始崇拜大多出于早期先民有意地或無意地對生態環境進行保護的目的,它反映并注重人與自然之間的利弊關系,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以祭祀儀式的神靈名義要求人們關注大自然。因此,周城栽秧會農耕活動的一系列儀式不僅體現著白族人民對祖先的敬畏,也蘊含著原初的生態智慧和樸素的生態哲學思想。“(我們)把寺廟轉一道,意思向本主、向神仙說我們要開秧門了,(你們)保佑我們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無災無難。周城人民栽秧了,(我們)要好上加好,從寺廟神仙身邊過,就是通知神仙通知祖先,讓他們知道。”這些生態智慧、情懷和思想又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日趨沉淀、內化和積累,逐步形成了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價值依歸的,主觀取向層面的精神文化。“那些老媽媽們念的經文都念的是豐收經、風調雨順經,老倌倌們奏的樂器也是這個意思,不是(你)想念什么就念什么,都是有禁忌的。”上述的祭祀情境可以說是生態文化的地方性知識生產,傳統生態觀和現代農業生產模式的結合,說明了栽秧會是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連續性統一,也反映出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理念。
經濟影響。據栽秧會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楊麟所述,栽秧會人多的時候有接近6000人,受到疫情的影響,栽秧會期間前往周城觀摩的游客也有近千人,游客不僅有大理本地的漢族和少數民族,還有來自云南各地的傣族、彝族等民族,甚至還有不少外國友人。在筆者觀摩栽秧會時,看到除了穿著傳統白族服飾的周城當地人外,還有穿著傣族服飾的傣族人、穿著現代服飾的學生以及在老師帶領下來觀摩栽秧會的學生們。彼時作為白族傳統農耕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栽秧會,在此時成為不同民族、不同年齡人參加的集會,成為栽秧會這一盛大“劇場”事實上的觀眾和參與者。
周城栽秧會不僅促進著地方旅游經濟的發展,也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助力姊妹村的鄉村經濟復興。在桑植白族以栽秧會為載體建立農耕文化節的過程中,大理白族不僅基于族群認同的文化認同意識,立足于桑植白族發展的實情,在文化和經濟上不斷進行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牢實踐,也通過族群間的經濟和人才互助使得栽秧會這一傳統的白族農耕儀式在桑植地區煥發了新的生機與活力。桑植縣芙蓉橋白族鄉合群村是國家級貧困村,在和大理周城村結為姊妹村后,通過實地的調研和走訪,合群村村委會在周城村的幫助下,借鑒周城白族村栽秧會舉辦的成功經驗,立足自身村情村況,結合桑植旅游文化的發展實情,逐步恢復了栽秧會這一傳統農耕文化活動,并成為村子一年一度的文化旅游盛會。栽秧會的文化呈現,以服務業為支撐,將民俗活動和文化旅游結合,將農業生產、田園景觀與文化旅游結合,吸引游客親近自然、感受農業文化,通過文化旅游帶動地方經濟增長。除此之外,文化旅游為當地村落創造了新的收入來源,即通過開發和利用周城的白族文化,創造一系列文化展演、文化產品、飲食服務業等就業形式,為區域發展提供了新的機會。
周城栽秧會作為白族傳統農耕文化的重要載體,既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又在現代社會發揮著重要的社會功能。其影響深遠,不僅體現在文化、生態和經濟等多個層面,而且體現了白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對自然的敬畏。在新時代背景下,周城栽秧會以其獨特的魅力,不斷吸引著更多人的關注和參與,成為促進民族交流、傳承農耕文化、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平臺。從文化層面看,周城栽秧會強化了白族人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和歸屬,展現了白族農耕文化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中的獨特地位。在生態層面,栽秧會所蘊含的生態哲學思想,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為當前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在經濟層面,周城栽秧會推動了地方旅游經濟的發展,為鄉村產業振興提供了內生動力。總之,周城栽秧會作為白族農耕文化的瑰寶,值得深入研究和傳承。在新時代背景下,應充分發揮其在文化、生態和經濟等方面的積極作用,為推動鄉村振興和弘揚中華文化貢獻力量。同時,也要正視其面臨的挑戰,積極探索栽秧會的發展新路徑,使其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作者單位:大理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