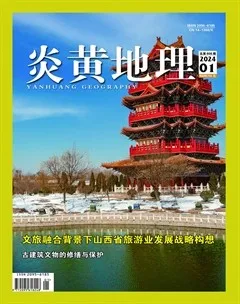文本視角下云南民族村火把節的表演呈現
張敏



作為可被接收者創造性閱讀,由封閉、自足、靜態走向多元、對話、動態的文本,火把節從原生地走向旅游場域的時空變換就經歷如此過程。云南民族村火把節在旅游舞臺上以“傳承文化,引領歡樂”為宗旨,煥發出了勃勃生機,緊扣“火”這一線索展開分析,從歷史角度看到了火把節的前世今生。而處于表演語境之下的火把節,經由作為表演者的村民與作為觀眾的游客之間的協商,與文化真實與表演的妥協,利用符號代碼的方式得以在旅游前臺構建出認同空間,于此極富生命力的表演文本得以呈現。
文本一詞,經歷了傳統觀念中基礎的文學作品表象,別于被符號或屬于某項藝術的材料組織起來的整體的作品,到20世紀70年代,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將作品與文本的關系完全翻轉過來,作品只是一個不斷重復的出發點,讀者可以不受拘束地加以利用,進行種種文本實踐,而這種實踐中的文本,不再是作品的精神價值的物質承載物,而是更加神秘的語言革命中的實踐行動,它并非具體的文字,而是一種永遠變動不居的過程。節日文本的研究也從傳說、故事這一書面文本掙脫,更關注于節日文化整體。部分學者們從節日的不同語境中,探討傳統與發明的并存以及相互間的權利關系。民俗文本從作為一種交流實踐的表演模式來看,文本是情境化的交流實踐的新生性結果。
本研究著眼于旅游前臺的展演,對云南民族村歡慶的火把節緊扣“火”為線索展開分析,先從表演主體出發,探究此表演文本對參與其中村民與游客身份的影響。再抽離出火把節中各民族共享的符號語匯,以覺察傳統與現代發明之間的糾葛,究其根本是多主體的協商與妥協的結果,是新舊文本的鏈接與碰撞,于此兼具娛人娛神功能的火把節得以呈現。
景區火把節的“前世今生”:從原始崇拜到旅游展演
火把節是我國西南地區彝族、白族、納西族、普米族、藏族等少數民族一年一度歡慶的傳統節日。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現代意義上的火把節,其形成經歷了從單一到多元,從小范圍到大范圍的發展過程。
祭火與祭祖、祭天融合。歡度火把節的民族同屬氐羌族系,氐羌族系各民族在文化早期階段,受原始宗教信仰的影響,較其他族系極為重視祭祀天地、祖先。不僅如此,火崇拜與祖先崇拜疊合的現象在各民族神話中有跡可循,如哈尼族的取火神話——《阿扎》。阿扎的阿爸向魔怪取火,被魔怪化成了石頭,于是阿扎決心替阿爸完成取火的使命。火是魔頭上的眉心燈,除非摘取時拔下魔鬼頭上的金雞毛,否則就會被追殺。阿扎在其死去父親的神助下,拿下眉心燈上的火珠,卻沒有來得及拔下金雞毛,情急之中吞下火珠。因此,魔鬼把阿扎心中的火珠變成一團燃燒的烈火,一路追趕。最后阿扎雖然把火帶回家中,自己卻被火燒死。從此哈尼族人就把火叫“阿扎”,于是這個原來祖先的名號就被賦予了火的神靈。讓祖先與火同名,讓祖先繼續以火的形態留存。人們認為人類火種就是祖先用智慧和生命換來的,與大自然的抗爭獲得了勝利,既合理解釋了火的由來也獲得自我的肯定,為生活尋找到了力量。火崇拜作為火把節的原動力,與祖先崇拜的疊合滿足了人們的心理需要。祭祖即為祭天,天地祖宗,本為一體,至為神圣,在各民族的祭天儀式上,充滿著濃厚的敬祖尋根的意識,通過儀式,以祈求祖先神靈保佑,以祖遺訓,規訓族人。火把節時以磨秋作為溝通天界與人間的途徑,哈尼族人認為天神就是沿著磨秋桿從天上降臨人間,因此對立磨秋、祭磨秋極為重視。
氐羌民族隨著從游牧生活轉為農耕生活的過程中,火把節中也增添了諸多農事要素。
農祀節日到綜合性節日的轉變。彝族《火把節》神話,天上的大力士斯熱阿比要和地上的大力士阿提拉比武,結果,天上的大力士被打敗了。天神大怒,便派大批蝗蟲來吃地上的莊稼,地上的大力士砍了許多松枝,帶領大家在六月二十四晚上點燃火把,把蝗蟲統統燒死,保護了莊稼。這則神話解釋了火把照田的由來,同樣也包含對天神的震懾,望他不再為禍人間。此外,還有火燒松明樓、皮邏閣火燒松明樓殺五詔、孔明擒孟獲、父老設燎相迎等說法,無法辨別原型為何,更是無法考據神話解釋儀式,還是儀式由神話而來,只能理解為神話與儀式互相解說,互相肯定。
對于火把節的由來各執一詞但其風俗已相沿成習。農事生產的豐收對于以此為生的人們來講就是最大的祈愿,因此火把可滅蟲害的功能自然為人所重,將火把節視為農祀節日也符合其脈絡。
在旅游行業助推之下,現已形成的官辦火把節有涼山彝族國際火把節、楚雄彝族國際火把節、石林彝族國際火把節,火把節作為文化旅游商品,在遵循農歷六月二十四傳統節日慶祝時間的基礎之上,依據不斷豐富的節慶活動所需,延長了整個節慶時間,繼續舉行祭火儀式、斗牛比賽、摔跤比賽,延續傳統活動的同時,衍生出了開幕式、主題晚會、火把狂歡、招商引資項目推介會、民族文化藝術展、各鄉鎮街道分會場等內容。于民眾來說是集祭天、祭祖、交游、歌舞、商貿等功能的綜合性節日。
作為表演文本的表演者與觀眾
民族村火把節雖為彝族、白族、納西族、普米族、藏族、摩梭人、哈尼族、拉祜族共同的歡慶,但通過筆者觀察,其隆重程度依次為彝族、白族、納西族。舞臺上的火把節由作為表演者的村民與作為觀眾的游客共同演繹,但事實上村民與游客都經歷著心理認同的困惑。
村民:“名副其實”。民族村過節的八個民族中,當屬彝族最為隆重,白族、納西族次之,其他民族村寨中無特別活動標識火把節的歡慶。對于過節的具體內容,民族村相關部門給出整體方案,主會場——團結廣場,分會場——彝族、白族、納西族村,活動的策劃充分尊重過節民族村民的意見,尤其是分會場各民族村寨的活動,經協商后得以呈現于表演前臺。
農歷六月二十四是彝族正節,這天彝族村舉行祭樹神儀式。祭神儀式并非所有彝族地區都舉行,甚至不是在火把節時舉行。
“樹神,這個是我們這邊有,姚安這邊,姚安其他地方有沒有不知道,但是我們村子那邊有,就像我們的祖墳,上完祖墳,然后專門有棵樹神,要在那里點香。”
祭樹神儀式被整合于火把節程式之中,體現彝族人民對自然物樹的崇拜,同樣在春節期間也舉行了祭樹神儀式。民族村作為旅游地在呈現民族文化時獨具開放性與包容性,村民作為文化持有者,給予他們一定的話語權,共同打造節日這一旅游產品;另一方面,村民充分且深入參與節日的全過程,以解思鄉愁緒。
農歷六月二十五是白族正節,這天早上各民族兄弟姐妹齊聚本主廟前為豎火把做準備,大家將貢果、貢香都插于火把上。隨后在本主廟進行了祭拜本主的儀式,貢品奉上,奏樂鳴炮。緊接著將火神牌位抬出至崇圣寺三塔(仿制)前進行祭佛,后返回戲臺廣場進行敬火神儀式,火神上座、貢獻祭品、祭師呈誦祭文,接著長者敬香叩首、敬獻祭品。祭師抱公雞于火把前念誦祝詞并模擬雞血涂抹于火把上的動作(實際未殺)以祈求豎火把儀式的順利與來年的風調雨順,五谷豐登。
民族村內納西族的火把節較彝族、白族程式簡單,農歷六月二十五16點在納西族村三多廣場舉行。開始前大家忙碌著擺放貢品,裝飾火把,在火把上栓起一根根紅布綢,插上松毛,燃起松毛堆。面對三多塑像,東巴手執經文誦讀,祭天祈福,村民站立其后。東巴示意開始豎火把,于是村民合力抬起將火把豎起,東巴繼續誦讀經文,不時蘸取祭品撒向遠處,朝松毛堆做拋灑動作,誦經結束后,村民將香插在火把節上,豎火把儀式就算結束。
村民在擁有民族文化基礎之上參與各項活動,開展相關工作,存在自我與他我的糾葛與困擾,“這項儀式我們沒有”“我們不是這樣過的,這里就是給游客看的”,兩種聲音的交織影響著村民的文化適應的程度,于此村民歷經心理掙扎才得以將展演呈現。
游客:借村民之名。民族村的火把節為游客提供了成為俗民的機會。游客與民族村的村民因火把節之機相遇在同一時空下,從而結成了群體關系。
火把節期間,民族村舉行了火把拍賣活動,拍下火神火把的游客,將成為當晚的點火嘉賓,一齊點燃團結廣場場中的天神火把。參與歡度火把節的八個民族各自準備了一支火神火把,每支火神火把都象征著不同的含義,每支火把從裝飾到含義賦予都展現了本民族特色。對于此項活動,部分游客積極參與競拍,且通過筆者的觀察,五天節期內,每天彝族火神火把都拍出了當日最高價,可反映出游客對于彝族火把節的認同心理;另一方面,居首位出場的藏族火神火把也拍出當日的次高價,“特意來過火把節,想要第一份祝福”,可見博得頭彩或許是游客出行的動力,也是對今后生活的祈盼。十支火神火把競拍結束后,游客與少數民族姑娘小伙返回舞臺,逐一接受畢摩的誦經祝福,隨后點火嘉賓借神龕之火點燃各自火神火把,最后共同將場中天神火把點燃。在畢摩的誦經聲中,熊熊火焰包圍著火把,發出噼里啪啦的響聲。這一時刻,游客借火把傳遞著自己美好的祝愿,希望能夠實現。
形塑表演文本的符號代碼
圓圈舞。圓圈舞是我國西部民族特有的一種歌舞形式。西部地區民族民間舞蹈的群舞中最多的運動路線就是圍圈而舞。云南是我國少數民族的聚集地,民間廣泛流傳少數民族兄弟姐妹“會說話就會唱歌,會走路就會跳舞”。火把節是民眾除舊布新的節點,夜色撩人,借火把的光亮人們拉手圍圈,踏地為節。圓圈是天體神界的象征,是人生和萬事萬物生存與發展的軌跡。圓圈運動,是宇宙循環和人生輪回象征。男女老幼在周而復始、通宵狂歡的舞蹈中,盡情宣泄、交流他們的情感以求得心理平衡。面對面,圍著火把向心運動,給民眾帶來極大的安全感,齊整的步伐,齊整的揮動,在他人的確證與自我生命真實的體驗之下,群體意識在這狂熱之中悄然扎根。村民與游客共同進行圈圈打跳,經過短暫的模仿學習,游客也可做出與他人整齊的動作,這個時刻,無謂男女,無謂職業,大家都為同跳一支舞而興奮。
火把。火把節中出現的火把因其所屬不同,分為四類,團結廣場中央為點火嘉賓點燃的天神火把;過節民族各自裝飾的帶本民族特色的火神火把;供游客參與火把狂歡的吉祥火把;彝族、白族、納西族村寨內所豎火把。不同類別的火把,有不同的所指含義。團結廣場作為活動的主會場,上演的節目集各民族之長,融現代與傳統為一體,場中的天神火把,一為團結各族人民歡度節日,二為祭祀天地祖先,是民族村內最大的火把,此火把由游客競拍所得的各民族火神火把來點燃,是為民族融合的體現;各民族的火神火把被寄予多種祝福之意,競拍所得的游客博此彩頭,并借這個機會為自己的心愿達成輔以神力;游客所購買的大、中、小型號吉祥火把,可看作參與節慶的標志,左手持火把,圍成圓圈舞動,是狂歡之夜最歡樂的時刻。彝族、白族、納西族村寨內火把,由各族村民自己點燃,相較團結廣場內的大場面,村寨內部更具家的感覺。火把燃起,歡歌打跳也開啟,節日的喜悅溢于言表。火把是火存在的載體,火徹底結束了先民茹毛飲血的時代,火帶來了安定、和平的生活,人們借火把燃燒的熊熊火焰以示對天地神靈最虔誠、最熱烈的崇敬,以期得其庇佑。
民族村火把節是經交流協商的表演文本。民族村火把節在其文本化過程中,結合旅游地的特點,因地制宜地進行再生產、再創造。作為旅游產品的火把節一方面為增加其吸引力而深挖民族特色,整合相關文化要素經舞臺化處理后進行展演。另一方面遵循風俗舊制,保留部分不可公之于眾的內部活動,為民族節日留有隱秘的自我空間。真實與表演之間的取舍以原生文本為基準,管理者征求本民族村民的意見,以期呈現出既符合游客要求又可充分調動村民工作積極性的表演。在此過程難免出現“我們不是這樣過的,這里就是給游客看”的妥協。旅游舞臺上的火把節是一種動態性的表述,不僅指其文化表演的過程,而是指表演的呈現通過交流實踐來實現,是村民與游客之間協商的結果。從心理認同上看,村民通過分離的方式實現文化適應,游客則在火把節這一場域中獲得了別于觀眾的俗民身份。村民呈現的表演前臺與游客的旅游前臺在旅游空間中相遇,雙方在互相凝視中作出選擇,游客依提供的環節結合自身興趣有所取舍,村民依游客的反應適時調整,共同努力之下構建出旅游的認同空間。在此空間之下,火把節這一表演文化獲得新生,展現出獨特的文化魅力。
此時的火把節,在其文化功能上是兼具敬天祭祖,交游娛樂的綜合性節日。畢摩參與的祭火儀式、祭樹神、祭火神,白族的祭本主等儀式活動是火把節最核心的要素,即使時空轉變,從原生地到旅游地,其神圣性也深刻影響著村民,“我本來想在豎火把時許愿的,但是沒空回去啊,沒趕上”。火把狂歡為游客與村民提供了釋放壓力的機會,圍圓打跳,納西三部曲、彝族阿細跳月、摩梭人的甲蹉舞等,身處其中,盡情感受。
(作者單位:云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