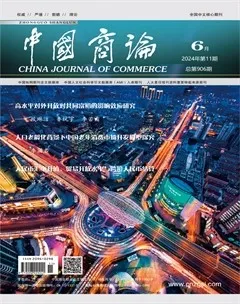東南亞國家FDI投資環境水平測度及時空差異分析
黃昭瑩 楊文華



摘 要:隨著我國與東南亞地區經貿投資合作日益加深,中國對東南亞直接投資額不斷上升且呈長期趨勢,區域間合作的深化也使得我國對東南亞地區投資更加便利,這些均與東南亞地區區位優勢及投資潛力有一定關系。本文采用熵值法與變異系數法對東南亞主要六國2006—2020年數據進行評價體系構建,最終得出經濟、金融、社會、政治、自然、技術六個環境系統得分,并對該地區總投資環境水平及各系統時空差異進行分析,給出相應建議。結論如下:自然環境對東南亞地區投資環境影響最大,其次是政治、經濟、金融與社會環境;投資環境得分最高的國家為新加坡,除了社會環境外,其他環境系統得分均遠高于其他國家,得分最低的為菲律賓,且其各系統得分均最低;各國自然與政治環境系統差異較大;時間變化上,各國投資環境水平均為上升趨勢,其中印尼增速最快,泰國增速最慢。
關鍵詞:東南亞;熵值法;變異系數法;FDI投資環境;時空差異
本文索引:黃昭瑩,楊文華.<變量 2>[J].中國商論,2024(11):-064.
中圖分類號:F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4)06(a)--05
1 引言
隨著《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全面生效、“一帶一路”倡議東南亞段發展及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經濟金融及政治各方面的聯系日益加深。在此背景下,越來越多中國企業選擇東南亞國家進行直接投資。根據商務部數據整理可知,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直接投資額占中外直接投資總額比重從2013年的6.7%上漲到2021年的11%。其中,中國對新加坡投資占中國對東盟總投資的25%以上。截至2020年,中國是東盟第四大外資來源地,且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國家非金融直接投資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
隨著國內產業升級、供給側改革及人口老齡化,我國人口紅利正逐漸消失,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也轉移到其他國家。相比之下,東南亞國家近年GDP增速快,且人口中位數處于青壯年時期。此外,龐大的人口基數及經濟總量體現了東南亞國家巨大的市場潛力。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得天獨厚的地理臨近優勢與相近的文化習俗,使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但東南亞國家間經濟發展差異較大,且均為多民族、多文化國家。由于政治體制或殖民遺留問題等因素,該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差異明顯,投資需考慮因素較多。此外,我國大多數企業缺乏海外投資經驗,盲目跟風可能導致經營失敗,影響企業投資積極性。因此,本文對東南亞國家投資環境,包括成本收益及風險進行度量分析十分重要。
2 文獻回顧
國內外學者通過構建指標體系研究某國或某區域投資環境文章眾多。根據研究區域可分為具體國家與區域的分析。如鄭明貴等(2023)利用Critic與Topsis權重法對巴基斯坦投資環境風險做出動態評價;Fontana(2010)通過分析國家的油氣投資現狀,認為國家經濟狀況、油氣供求關系、國際地緣政治等因素是影響石油投資的潛在風險因素。區域投資環境研究方面,劉玉等(2023)對“一帶一路”國家東道國制度環境進行研究;周偉等(2017)對“一帶一路”沿線39個東道國國家風險進行研究。
現有對東南亞國家投資環境進行研究的文章主要為區域性研究,如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RCEP成員國及東盟國家投資環境。按其研究內容可分為對單一環境風險研究。如潘思諭等(2023)對中國與東盟企業跨國合作政治風險進行研究;韋永貴等(2019)對東盟地區文化環境及其投資效應進行研究。此外,大多數學者通過對多個影響投資環境系統進行綜合分析。如衛平東(2018)通過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治風險、經濟風險、政策風險、支付風險分別舉例進行分析;李伊(2023)通過政治風險及經濟風險兩個維度構建指標體系衡量東南亞國家直接投資風險;王魏和袁航(2018)在測量東盟成員國風險時采用灰色關聯度模型研究政治與法律風險等。
現有通過構建指標體系對東南亞國家投資環境進行分析的研究主要以投資風險衡量投資環境,衡量維度包括政治、經濟、金融、社會及技術方面相關指標。同時,考慮投資動機收益及成本風險方面指標對東南亞國家投資環境進行指標體系評分的文章較少。因此,本文采用較為客觀的熵值法與變異系數法進行指標體系構建,同時考慮東南亞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優勢及潛在風險與成本,對2006—2020年東南亞地區主要國家投資環境水平進行研究分析,并給出相應建議。
3 東南亞地區投資環境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3.1 指標選取及數據處理
考慮數據可得性及統計口徑一致性,本文選用2006—2020年數據,對東南亞六個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越南、菲律賓進行研究。基于現有研究評價體系,本文從成本、收益、風險及投資動機方面構建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3.2 各系統作用機理
經濟環境主要反映東道國經濟自由、經濟發展水平、績效與潛力。經濟環境變化會改變市場環境。對于為尋求市場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公司而言,消費者市場發展水平及潛力至關重要,經濟自由程度也會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門檻,直接影響投資環境。因此,本文選用經濟自由度指數、國內生產總值、全球競爭力指數等作為衡量指標。其中,一國國內生產總值及人均國民總收入體現經濟發展水平,而全球競爭力水平衡量一國在中長期取得經濟增長的能力。一國經濟越自由、發展越成熟,且市場具有潛力時,越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資。
金融環境主要體現匯率波動及國際收支賬戶情況。跨國公司貿易及投資的收益成本均受匯率影響,而國際收支賬戶情況反映一國金融發展健康程度。因此,本文采用官方匯率、金融風險等指標對金融環境進行度量。對外直接投資涉及跨境業務及不同貨幣間的兌換,若匯率波動較大時,企業進行投資成本與受益成本不確定,不利于企業投資活動。國際收支賬戶情況體現一國金融環境健康程度,當外國直接投資及經常項目余額占比大時,說明該國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對外經濟發展,且該國對外經濟發展水平高,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資。
政治環境主要衡量東道國政府治理水平及政治穩定。根據張錚(2022)的研究,“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體制處于建立和調整時期,存在制度缺位,對政府權力約束較低,政府在資源和要素配置中的作用較強,政府政策行為的非連續性和不可預期性水平較高。政治環境影響企業經營與發展環境,且對跨國企業經營的影響具有一定的不可逆轉性和強制性。因此,采用政治穩定性、政府效能、政府監管力度等六個指標衡量東道國政治環境。
社會環境主要體現東道國社會穩定性及勞動力素質。根據鄒賀杰(2022)分析可知,在部分東南亞國家中,民族宗教和治安問題依然嚴重,主要涉及武裝沖突、民族宗教沖突、海盜、恐怖主義、海上跨國犯罪等。社會穩定及高素質勞動力均有利于母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而人口密度、失業率、高等教育水平等均是重要的衡量標準。政府教育支出比重及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體現該國政府對教育重視程度及勞動力素質高低。失業及恐怖活動均是引起社會動亂的重要因素,失業率越低且恐怖活動數越少,該地區社會越穩定,越有利于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根據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可知,對外直接投資動機包括戰略轉移型與逆向學習型,即利用東道國資源進行更低成本生產或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學習東道國相關技術。霍忻和劉黎明(2017)研究發現,逆向技術溢出效應會顯著提高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因此,本文采用自然環境對東道國資源稟賦及基礎設施建設進行度量及技術環境對被東道國技術水平和知識產權保護程度進行衡量。其中,資源稟賦包括重要戰略物資石油的總供給量及電產能、通電率;基礎設施主要指海運及空運設施,如港口基礎設施質量及航空貨運量。此外,高科技產品出口額越高,占制成品出口比重越大,則說明該地區技術發展水平高。同時,專利申請數可以體現該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程度,技術水平越高、知識產品保護越嚴格,則越有利于高科技企業創新發展。
3.3 指標體系測度結果與分析
3.3.1 測度結果
為確保權重賦值的準確性,本文通過熵值法及變異系數法進行指標權重衡量,并對比權重差異選出合適數值。由表2可知,熵值法與變異系數法賦權數值各子系統相近,因此采用兩者均值進行衡量。
3.3.2 結果分析
由測度結果可知,六個影響環境中,自然環境占比最大,為24.21%,其次是政治與經濟環境,最后是社會與技術環境,技術環境影響最小,為9.33%。由此可知,母國對東南亞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是其要素稟賦及相關基礎設施,特別是便利的海運交通及豐富的石油與電力供給。東南亞是世界最大的橡膠、油棕產地,且石油、錫等礦產資源豐富,糧食作物產量豐富,對相應資源密集型產業吸引力大。此外,東南亞地區大多數國家沿海或環海,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且地處重要戰略位置,長期的海運基礎設施建設及交通運輸建設使得東南亞國家在該方面較其他發展中國家地區具有較大優勢。根據Supply Chain Asia報告,物流業占越南GDP的15%~20%,預計占印尼GDP的12%。
另外,對東南亞國家進行投資時,政治環境也是投資者重點考慮的因素。政治體制、被殖民歷史及國家間信仰、主權、領土問題等常發生沖突,導致地緣政治不穩定。衛平東(2018)研究表明,對于發生戰爭沖突的國家和地區, 由于有很高的政治風險, 需要謹慎進行投資;對于進行政府更迭、換屆的國家, 基于政權的交接所引發的政策不確定性增加。這啟示企業在對東南亞國家進行直接投資時應重點關注政府腐敗程度及法治水平。
除自然環境及政治環境外,投資者更關注東道國的經濟與金融環境。通過對比兩者下屬二級指標數據可知,人均國民總收入、外商直接投資凈流入占比、經濟自由度及競爭力指數占比較大,即投資者更關注東道國市場發展水平、外商投資市場成熟度、經濟自由程度及經濟增長能力,這與投資收益息息相關。技術環境占比最小,可能是因為外商直接投資導向較少為技術學習型,可能與東南亞地區總體技術發展水平不高且知識產品保護制度不完善有關。付海燕(2014)指出,欠發達經濟體對一流發達經濟體進行直接投資,可以獲取技術外溢來提升本國技術水平,但對中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時,技術外溢不明顯,甚至顯示出抑制作用。
4 東南亞地區投資環境水平時空差異分析
4.1 各國投資環境水平對比
本文根據評價指標體系中各指標權重計算出各國投資環境綜合得分及國家內不同系統得分,具體情況如圖1與圖2所示。
由圖1可知,六國中除了新加坡得分為63.48外,其他國家得分均超過50,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分別排行第二、第三,最低是菲律賓,得分僅有22.36。具體分析各環境得分(見圖2)可知:除了新加坡外,其他五國金融環境得分相近,均在4.5左右;社會環境方面,綜合得分最高的新加坡反而得分最低,且除了菲律賓外,其他國家社會環境得分均在7左右,可能與新加坡政府教育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較低有關;各國在自然環境得分差異最明顯,其中得分最高的國家為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分別為13.7與13.3,菲律賓與越南得分均低于5,可見六國自然資源及基礎設施建設差異較大;六國技術環境得分均不高,除了新加坡得分6.89外,其他國家得分均低于5,特別是印度尼西亞,為1.53;政治環境得分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遠高于其他四國,其中新加坡得分18.59、馬來西亞得分9.35,而其他四國得分均低于4.5,可見六國在政治環境方面發展差異較大;經濟環境得分主要可以分為三梯隊,第一梯隊為新加坡(得分12.42)、第二梯隊為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與泰國(4~5分)、第三梯隊為菲律賓與越南(低于4分)。
綜上可知,綜合得分最高的新加坡除了社會環境得分外,其他環境得分均遠高于其他國家;得分第二的馬來西亞各項指標均穩居前三,各環境發展水平較同地區國家發展水平相對均衡;印度尼西亞除了社會環境排行第一外,其他指標也穩居第三,為該區域投資環境較好的國家;越南與菲律賓各項指標均居于較低水平,發展提升空間較大。
4.2 各國投資環境時間變化分析
本文對各國投資環境水平變化演變趨勢進行分析,具體結果如圖3所示。
由圖3可知,東南亞六國投資環境水平總體均呈上升趨勢,其中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及越南三國漲幅較大,泰國增長最為平緩。首先,綜合得分大于50的新加坡以較快增速波動上升,其中除了2007年及2019年外,其余年份均上漲。對比其他國家同期變化趨勢可知,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及印度尼西亞均有相同下降趨勢,可能與2008年金融危機及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有關。其次,綜合得分處于40~50變化區間的馬來西亞總體變化趨勢與新加坡相似,且近幾年呈下降趨勢,可能與2018年馬來西亞政變有關,馬哈蒂爾政府上臺之后撕毀中馬鐵路建設的合同,不斷釋放關于“一帶一路”合作項目的負面信號,使得馬來西亞投資環境不穩定性增加。最后,投資環境水平低于40的國家中,印度尼西亞增長最快,且于2011年超過泰國。此外,菲律賓及越南也呈緩慢增長之勢,兩者間越南漲幅相對較大,兩國持續增長,有望未來幾年超過泰國投資環境水平。
5 結語
5.1 結論
本文基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本、收益、動機及風險四個角度構建經濟環境、金融環境、政治環境、社會環境、自然環境及技術環境6個一級指標,一級指標下共設34個二級指標對一級指標進行度量。通過對比熵值法及變異系數法確定權重,并對標準化后數據計算得分,以衡量投資環境水平。最后對得分進行時空差異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對東南亞地區影響最大的環境系統是自然環境,其次是政治、經濟環境、金融環境與社會環境,技術環境影響最小。這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動機主要為該地區自然資源及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技術學習型投資較少。
通過對各國投資環境得分及系統間得分對比可知:投資環境最優的國家為新加坡,其次是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最后是菲律賓;新加坡除了社會環境外,其他環境系統得分均遠高于其他國家,而菲律賓基本上處于各個環境得分的最低值;除了新加坡外,各國在金融環境方面與社會環境方面不存在明顯差異,差異較大的為自然與政治環境。
通過對各國投資環境得分及系統得分的時序變化研究可知:各國投資環境水平總體呈增長趨勢,其中印度尼西亞及新加坡增速較快,而泰國漲幅較低;各國投資環境水平排行總體不變,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穩居前二,印度尼西亞保持快速增長并于2011年排行超過泰國成為前三名;環境變化方面,自然環境穩居第一,而技術環境得分常年倒數第一二名,其他系統中經濟環境與金融環境得分排名變化較大,前者呈上升趨勢,而后者呈下降趨勢。
5.2 建議
首先,投資選址角度方面。根據該地區國家投資環境得分及變化趨勢,東道國企業可優先選擇投資環境好且具有良好發展勢頭的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度尼西亞。根據各環境系統得分進行投資選址時,對社會環境指標如社會穩定性及勞動力素質要求較高的行業則可優先考慮除了新加坡外的其他國家;對自然資源及基礎設施建設或東道國市場發展水平要求較高的企業則可考慮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度尼西亞。
其次,已投資企業運營方面。對于已在某國進行直接投資運營的企業,更應注意各環境系統潛在收益及風險。如在新加坡投資企業應充分利用當地政府治理優勢,注意防范社會風險;在馬來西亞投資運營企業應充分利用當地具有優勢的自然資源及完備的基礎設施發展業務,而注意規避金融風險,主要包括匯率波動可能帶來的損失。
參考文獻
段秀芳,張格嘉.中國對RCEP國家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面板數據模型的實證分析[J].新疆財經大學學報,2022(4):37-46.
付海燕.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研究: 基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實證檢驗[J].世界經濟研究,2014(9):56-61+67+88-89.
霍忻,劉黎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影響因素與經濟增長動態效果探究: 基于主成分分析和VAR模型的實證分析[J].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7(5):81-94.
劉通. 中國對東盟國家OFDI的環境影響因素研究[D].沈陽: 遼寧大學,2020.
劉玉,唐禮智,金夢潔.東道國制度環境、市場規模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基于“一帶一路”國家的半參數變系數空間面板模型[J].統計研究,2023,40(3):85-99.
潘思諭,張騫,張藝維.RCEP背景下中國與東盟企業跨國合作的政治風險防控研究[J].時代經貿,2023,20(2):77-85.
彭劍峰,雎華蕾.中國企業對東南亞國家投資環境風險評價[J].荊楚理工學院學報,2021,36(5):61-69+79.
王巍,袁航.政治風險沖擊、制度質量與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J].東南亞縱橫,2018(3):72-81.
韋永貴,李紅,牛曉彤.中國-東盟文化多樣性與相似性測度及其投資效應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19,28(2):45-57.
張瓊,苑可鑫.“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對東盟油氣投資風險分析[J].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25(1):45-53.
張友誼.中國對東盟國家直接投資現狀分析[J].生產力研究,2020(12):121-126.
鄭明貴,張研博,邱均遠,等.巴基斯坦投資環境風險動態評價[J].江西理工大學學報,2023,44(1):52-58.
周偉,陳昭,吳先明.中國在“一帶一路”OFDI的國家風險研究:基于39個沿線東道國的量化評價[J].世界經濟研究,2017(8):15-25+135.
鄒賀杰. 中國對東盟國家直接投資風險的研究[D].濟南: 山東財經大學,2022.
FONTANA M. Ca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handle complexity? The fallacy of the oil spot dynamiclJl.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2010,76(3):584-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