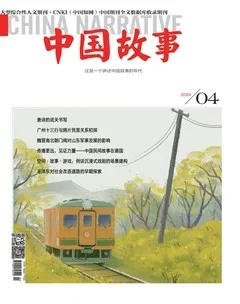唐詩的武關書寫
陳宏利 文員

【導讀】武關是唐代關中四大關隘之一,歷史悠久,占據著獨特且優越的地理位置,承載了厚重的歷史記憶與豐富的文化內涵,唐代詩人對其多有詠寫。武關戰事的成敗對于一個政權的興衰具有重要意義,故晚唐詩人多借詠武關來抒發對歷史興亡的感慨;武關也是自長安南行至湖湘嶺南的必經之地,故元和貶謫詩人途經武關時多書寫個人的遭際起落。從唐代武關詩中可窺見武關的地理景觀書寫價值與人文價值。
地理關隘書寫是唐詩的重要題材和元素。目前唐代關隘詩的研究主要圍繞蕭關、陽關、玉門關的相關詩歌展開,沒有專門論述唐代武關詩的文章。武關位于陜西省商洛市丹鳳縣武關鎮武關村的武關河北岸,其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已經建置的少習關,戰國時期更名為武關,為秦楚兩國相互制約抗衡的產物。本文整理歸納了《全唐詩》中涉及武關的詩歌,試從書寫內容與書寫價值兩方面對其進行分析論述。
一、唐詩武關書寫匯總
通過對《全唐詩》的翻閱和檢索,本文發現唐代有關武關的詩歌共有19首,見表1。以高棅《唐詩品匯》中唐詩分期標準“四唐說”為依據,對唐代不同時期詩人的武關詩歌進行整理歸納,可大體窺探出武關詩歌在唐代的創作情況。
通過以上的統計分析,可以看出,唐代武關詩歌的創作集中在中晚唐,盡管盛唐詩人李白也創作過武關詩,但其創作時間仍在安史之亂以后,創作時期應當被歸入中唐。中唐與晚唐的武關詩歌在創作數量上平分秋色,書寫內容卻大相徑庭。中唐武關詩歌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對個人遭際的思考,晚唐武關詩歌則主要借詠史表達對國家興亡的感慨。
二、唐詩武關書寫的內容
武關扼秦楚咽喉,為兵家必爭之地,武關戰事的成敗對于一個政權的興衰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武關作為關中東南的門戶,也是自長安南行至湖湘嶺南的必經之地,故感慨國家興亡和個人遭際成為武關詩書寫的主要內容。
首先,抒歷史興亡之感慨。
武關北依少習山,東西南三面臨武關河,春秋時即已建置,本名少習關,戰國時期秦國更名為武關,此關在史書中極負盛名。戰國后期,楚懷王被秦昭王困于武關,客死異國;秦末漢初,劉邦破武關得以直入咸陽;景帝時期,周亞夫統兵出武關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公元25年,赤眉農民起義軍分兵武關道攻入長安,推翻更始政權。故自先秦直至秦漢以后,武關常與建都關中王朝的重大政治活動甚至歷史命運息息相關。南朝周弘正稱其“涉地險”,宋人王應麟稱其“以限南諸侯”,清顧祖禹也說此關“一夫守壘,千夫沉滯”。因此關在王朝政治生活具有的特殊意義及其承載的厚重歷史信息,故唐代詩人對其多有詠寫,題旨則多集中在抒發歷史興亡之感慨上,如杜牧的《題武關》:
碧溪留我武關東,一笑懷王跡自窮。鄭袖嬌嬈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山墻谷塹依然在,弱吐強吞盡已空。今日圣神家四海,戍旗長卷夕陽中。
詩人駐足武關,嘲笑懷王的愚昧以致自己窮途末路。頷聯寫楚懷王聽信鄭袖讒言廢黜屈原,通過小人得勢而賢臣見棄的強烈對比,道出楚懷王的昏聵。頸聯寫武關的地形依然山高谷深,但戰國時期弱肉強食、諸國爭雄的局面早似過眼煙云、盡已成空。又指出安史之亂后,唐王朝國力衰微,藩鎮割據日益嚴重。“唐中衰,奸雄圜睨而奮,舉魏、趙、燕之地,莽為盜區,挐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警醒擁兵割據的藩鎮不管弱吐強吞,結局必然成空,不要自恃兵力強大,破壞國家一統。“今日圣神家四海”不過一句空語而已,武關上戍旗翻卷、殘陽如血才是唐王朝漸趨沒落的國運的真實寫照。這首詩起于武關,終于武關,將與武關相聯的歷史典故和山川自然描寫構筑在一起,抒發對國家興亡的慨嘆,立意深沉蘊藉。
再如胡曾的《武關》:
戰國相持竟不休,武關才掩楚王憂。出門若取靈均語,豈作咸陽一死囚。
這首詩同樣借武關的歷史典故批判楚懷王的昏聵無能。詩人們身處晚唐末世,借武關感懷歷史,評述興廢,以諷時政,但字句間都透露出一種末世的無可奈何之感。
其次,言個人際遇之悲喜。
唐代元和時期,南貶頻繁,但也有從貶謫地奉召還京的詩人。武關為長安與湖湘嶺南往返的必經之地,詩人們途經武關,際遇卻是有悲有喜。試將下列李涉、元稹的兩首絕句予以對比分析:
先看李涉的《再宿武關》:
遠別秦城萬里游,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
再看元稹的《西歸絕句十二首》(其二):
五年江上損容顏,今日春風到武關。兩紙京書臨水讀,小桃花樹滿商山。
劉拜山《千首唐人絕句》中稱李涉的《再宿武關》“可與元稹《西歸》‘兩紙京書臨水讀,小桃花樹滿商山對看,一寫入京之喜,一寫出京之愁,筆意相敵”。同樣的是長安—武關這條道路,不同的是,李涉是離開長安入武關,而元稹是由武關返還京師。元和年間,李涉被貶出京,所以看到的是“亂山”“寒溪”,加之詩歌的創作時間是夜晚,頗有“憂愁不能寐”之感,只能借一夜寒溪送走自己遠離長安的苦悶。元稹在元和五年(810年)被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元和十年(815年)復出為通州司馬。途經武關,他臨水細讀好友從長安寄來的書信,映入眼簾的是滿山的“小桃花樹”,即將返還京城的喜悅之情溢于言表。對于武關而言,詩人們只是匆匆過客。但武關屹立不倒的山河依然見證著詩人們出入長安時的憂愁與喜悅。
第三,述同路相思之情誼。
武關在唐代仍是出入關中、南來北往的要沖之地,因此亦有過往詩人借此抒發羈旅之思,如“元白”二人。元稹和白居易同為中唐時期的大詩人,有著相似的政治理想、人生遭際以及創作主張。二人私交甚密,可謂“一生休戚與窮通,處處相隨事事同”。據學者統計,元白唱和詩數量達400首,其中就有一組與武關相關的作品。元和五年(810年),元稹被貶江陵,途經武關南時,恰逢山石榴花盛開,他因而題壁作詩,表達對好友白居易的思念。此詩今元集不存。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貶至江州,途經武關時見元稹題詩,遂作《武關南見元九題山石榴花見寄》:
往來同路不同時,前后相思兩不知。行過關門三四里,榴花不見見君詩。
這首詩歌整體上通俗易懂而又耐人尋味,通篇采用自述口吻:我和你先后被貶,都經過武關。你寫詩時對我的思念,我不知道,如今我于武關思念你,你也無從知曉。你創作這首詩歌時,正逢山石榴花盛開。我現在來此,雖然沒有看到山石榴花,但看到你的詩就足夠了。表達出白居易對元稹深切的思念以及二人先后被貶的惺惺相惜之情。
后元稹再作《酬樂天武關南見微之題山石榴花詩》:
比因酬贈為花時,不為君行不復知。又更幾年還共到,滿墻塵土兩篇詩。
此詩元稹亦用第一人稱自述,他說:我再次經過武關為你寫下這首詩歌時,又趕上山石榴花盛開,如果不是因為你寄給我那首詩,我也不會再來此地,看到這美景。雖然你我現在分離兩地,但我相信,幾年后我們一定可以同來此處,一起欣賞美麗的山石榴花,那時在滿墻的塵土中,還會找到我們這兩首詩。元稹的這首詩歌除表達對白居易的思念以外,更展現出一份難得的豁達與從容。詩中沒有對兩人長期分隔兩地的埋怨,而是充滿了對二人重逢之日的期待。漫漫貶謫路上,武關詩見證了元白二人穿越時空的思念與情誼。
三、唐詩武關書寫的價值
盡管唐代武關詩的傳世作品數量未如詠寫華岳、驪山、黃河、潼關等其他秦地山河關隘的詩作那樣眾多,但此題材作品的書寫價值仍不容小覷,主要體現在地理景觀書寫價值與人文價值兩方面。
首先,是地理景觀書寫價值。
武關之所以能發展成一個文學意象,進而成為一道文化景觀,與它作為險關絕隘的雄奇險峻之美息息相關。“站在關城遠眺東南,只見懸崖深壑,石環水繞,真是險阻天成。”武關自秦漢以來即為雄關,作為戰火紛飛的兵家必爭之地,其雄奇險峻的特點為人熟知。如竇庠《奉酬侍御家兄東洛閑居夜晴觀雪之什》:
應念武關山斷處,空愁簿領候晨雞。
再如溫庭筠《題李衛公詩二首》(其二):
千巖萬壑應惆悵,流水斜傾出武關。
最后是杜牧的《將出關宿層峰驛,卻寄李諫議》:
孤驛在重阻,云根掩柴扉。
竇庠、溫庭筠兩人的詩主要從側面描寫武關的險峻,用“愁”“惆悵”等詞讓讀者體會武關的奇險。而杜牧則從正面入手,實筆刻畫武關所處的地理環境,重巒疊嶂,地勢高聳入云,實景山水,幾如畫卷。
詩人筆下的武關不僅有雄奇險峻的一面,也有“小桃花樹滿商山”的清新旖旎之景。如雍陶的《春行武關作》:
風香春暖展歸程,全勝游仙入洞情。一路緣溪花覆水,不妨閑看不妨行。
此詩應為雍陶大和八年(834年)進士及第后的返鄉之作。雍陶兩次落第,否極泰來,在歸途中經過武關,吹拂著和煦的春風,花香彌漫,不由覺得此行的愜意輕快足以勝過游仙。詩人緣溪而行,一路上花枝覆水,滿目春色。在作者筆下,當年秦楚、秦漢等在此留下的戰爭的硝煙早已消散,只有清新旖旎的春色讓人流連忘返。
其次,人文價值。
“邊關是一種自然與人文因素緊密結合的景觀形態,帶有濃厚而獨特的中國文化色彩,傳遞著歷史文化內涵。”武關承載著厚重的歷史記憶與豐富的文化內涵,因此唐代詩人在吟詠武關時,多書寫其中的歷史文化典故。如胡曾的《秦庭》:
楚國君臣草莽間,吳王戈甲未東還。包胥不動咸陽哭,爭得秦兵出武關。
這首詩化用了“包胥哭秦庭”的歷史典故。吳國攻打楚國,楚國不敵,“于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許。包胥立于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其實,對于晚唐每一位心系國家的文人來說,他們又何嘗沒有如包胥這樣力挽國家于狂瀾之中的抱負和決心呢?唐人對于武關的吟詠中,不乏對武關諸多歷史典故的書寫。這些典故是時代變遷的注腳、王朝更替的見證,也展現了心系國家的文人挽大廈于將傾的雄心和抱負。正是通過唐詩對武關的書寫,這些歷史典故得以千古傳誦。
除傳承歷史典故外,武關詩書寫的人文價值還在于能夠更好地打造當地文化名片。“文學書寫地理坐標本就是一個文化名片,它是文學傳承的產物,蘊含著豐富的人文精神、價值理念、精神追求,是地方文化自信、地方文化生長的重要基因,在營造地方文化環境、提升地方文化品位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唐代詩人對武關的書寫是研究當地文化的寶貴材料。驚心動魄的歷史難以僅憑簡單的文字介紹還原,卻能在內涵豐富、耐人尋味的詩詞中煥發新的活力。唐代的武關詩歌并非躺在故紙堆里的晦澀文字。在當今文化強國的大背景下,它們為打造當地的文化品牌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為傳承文化自信貢獻了獨特的力量。
武關之于國家,見證了其興衰更替;之于詩人,也記載了他們人生某個階段的起落沉浮。唐代詩人對武關的反復書寫,使得這座關隘不再僅僅是冰冷客觀的軍事要地,而成為一道有故事、有內涵的文化景觀。
參考文獻
[1] 彭定求,等,編. 全唐詩[M]. 北京:中華書局,1999.
[2] 逯欽立,校輯.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M]. 北京:中華書局,1983.
[3] 王應麟. 通鑒地理通釋·卷七[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4] 讀史方輿紀要(第三冊)[M]. 顧祖禹,輯著. 北京:中華書局,1955.
[5] 史記·楚世家[M]. 韓兆琦,譯注. 北京:中華書局,2010.
[6] 歐陽修,宋祁. 新唐書:卷二一四[M]. 北京:中華書局,1975.
[7] 富壽蓀,選注;劉拜山,富壽蓀,評解. 千首唐人絕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8] 曹云忠. 中華名關[M]. 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
[9] 邢宇晨. 唐詩中的邊關意象[J]. 新閱讀,2019(1).
[10] 史記·伍子胥列傳[M]. 韓兆琦,譯注. 北京:中華書局,2010.
[11] 趙樂. 元白唱和詩研究[J]. 北京大學學報,2009(6).
[12] 吳淑玲. 唐詩邊域書寫中的地理文學坐標[N]. 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08-25.
作者簡介:陳宏利,喀什大學。文員,喀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