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風景:革命情緒的共鳴板
劉鶴翔 王國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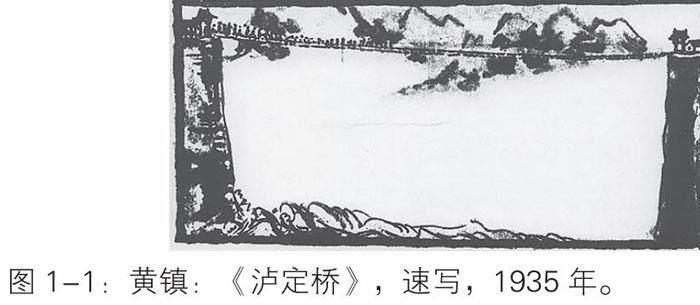


【導讀】風景是被文化中介了的自然景觀,那些著名的長征題材歷史風景畫也是如此。由于圖像資料匱乏,關于長征歷史記憶的重建更多地依賴于回憶錄文本。在這些文本中,對途中雄奇風景與險惡自然環境的描繪是一個突出的要素。風景成為英勇無畏的革命精神的表征形式。這種通過風景表現個人經驗與群體經驗的方式,在中國的風景美學史上都是全新的。
在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筆下,與紅軍長征的壯舉相比,“漢尼拔經過阿爾卑斯山的行軍看上去是一場假日遠足。”對國外的軍事家和作家來說,二萬五千里長征是極具魅力的遠征。穿行11個省,進行了大小600多次戰斗,經歷了無數奇險的地理環境,而主力仍然得以保存;對于探險家來說,長征也同樣是一場偉大的傳奇,紅軍的“荒野生存”顯示了人類的生命力所能達到的極限。
在歐洲繪畫史上,對翻越阿爾卑斯山的描繪是歷史風景畫著名題材,對巍峨的巉巖,險峭的絕壁、壯麗的冰川的描繪體現了雄偉風格。相比之下,長征穿越了大半個中國地理空間,沿途有著更能激發想象力的豐富的自然景觀。在這場蘇維埃國家的“舉國大遷移”(斯諾語)中,歷史文獻中提到的每一處風景,幾乎都意味著巨大的犧牲。但無論是出于革命意志,還是普通人的生命意志,長征風景都顯示了人與自然之間強大的精神張力。
對長征風景的體驗非親歷者不能真切。但由于攝影資料和繪畫資料的匱乏,長征時期留下的圖像文獻很少。藝術上成熟的長征題材畫作是在1949年后出現的。這些畫作通過再現歷史場景,表達對長征精神的崇高敬意,但這些繪畫仍屬于后建構的歷史記憶。因此,本文試圖從紅軍親歷者的繪畫文獻和回憶錄文獻入手,對文獻中的風景話語進行分析,揭示長征風景作為革命英雄主義與樂觀主義表征形式的起源,把握風景背后的精神意志。
一、黃鎮的長征圖繪
盡管長征紀實圖像極其匱乏,但并非一片空白。長征隊伍中有幾位專業或業余的畫家,如紅五軍團的黃鎮、紅二、六軍團的陳靖、紅四方面軍的廖承志等,尤其是黃鎮,他早年求學于上海美專,于新華藝術大學畢業,是唯一一位以紀實性長征題材美術作品傳世的畫家。
在長征途中,黃鎮即興而畫,描繪沿途革命人事和自然風光,一路上共畫了四五百幅,后來僅存二十四幅。黃鎮本來無意傳世:“我畫畫,是生活的紀實,是情感的表達,從來未曾想過輯集出版。在長征艱苦的行程中,許多難忘的場面,動人的事跡,英雄的善舉,我僅僅做了一點勾畫,留下一點筆跡墨痕。”1938年,這批作品曾以《西行漫畫》為書名由阿英編輯出版,作者誤作肖華。從題材看,黃鎮的畫作系以革命人事為中心,如《遵義大捷》《紅軍彝族游擊隊》等,但其中部分作品也可視為風景速寫。這批畫作盡管如阿英所說,在繪畫技巧上并不成熟,但“在中國漫畫中,有誰表現過這樣偉大的內容,又有誰表現過這樣的戰斗”?另外,黃鎮的畫也不完全是畫在紙上。有時畫在門板上,有時畫在石壁上,作為宣傳畫,它們傳達的是“把所有的人聯合起來的那種普遍的感情”。
西南地區是誕生長征傳奇的重點區域,其中大渡河上的瀘定橋爭奪戰是紅軍戰史上最著名的戰斗之一。這一題材最早出現在黃鎮的《瀘定橋》(圖1-1)速寫中。黃鎮回憶說:“我親臨了飛奪瀘定橋的場面,大渡河的洶涌、13根鐵索的險峻和20名勇士身上燃起的烈火,使我不能不留下歷史的畫面。”他的速寫采用了仰視視角,紅軍的隊形呈現為高處一連串的黑點。對后人來說,這張作品令人難忘之處在于其奇異的視覺性,這種圖式在歷代繪畫中都是未有過的。
川西的夾金山是當地傳說中“鳥飛不過”的神山,黃鎮的《翻越夾金山》(圖1-2)畫面采用幾乎垂直的構圖,山腳下的紅軍昂首闊步,在山道上作跑步狀,隨著時隱時現的山路,隊列直達最高處的隘口。畫作右邊題作“雪山高,鐵的紅軍鐵的意志更高”。
《草地宿營》(圖1-3)描繪的則是紅軍進入詭秘莫測的松潘草地的情景。近景中,兩名戰士從支起的人字形帳篷里探出頭交談。戰士在帳篷之間挑水、拾柴,他們的頭頂大風中是翻轉的云團。這樣的休憩場景透著一種松弛和樂觀。
事實上,草地的險惡卻也無處不在,含有毒素的水是黑色的,唯有草兜的根部才是可靠的落腳處,一腳不慎,泥沼隨時可能將人吞噬。在險惡的自然中,紅軍部隊的食物極為匱乏,最后僅靠煮皮帶和草根充饑。黃鎮速寫中背著干糧闊步邁進的情景應該是初入草地時畫下的。在接下來的行軍中,由于饑餓、疲乏、寒冷、暴風雨和傷病的折磨,大批的紅軍在草地上耗盡了生命力最后的儲備。走出草地時,三大主力的犧牲人數高達萬人以上。
二、“戰斗的樂觀主義”
紅軍的長征突破了數十萬敵軍設置的封鎖線,其中,紅一軍團就突破敵人封鎖下的47道關隘,一些關隘中的戰斗成為紅軍戰爭史上的傳奇。1937年,丁玲在延安將長征將領們撰寫的日記和追憶文章編成《二萬五千里》一書,至1942年由總政治部更名為《紅軍長征記》,在解放后僅存孤本,系由朱德簽名贈予埃德加·斯諾的一本,藏于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2002年才被發現并公之于世。從這些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風景作為媒介在革命精神建構中的微妙作用。
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書中“月光下的行軍”一節,描述的是紅軍從江西出發長征的情景。這一情景的更早版本出現在時任紅一軍團某師宣傳科長彭加倫筆下。在一篇題為《別》的回憶錄中,彭加倫所在的隊伍是在一個晴天的下午從贛南的于都出發的。在紅軍長征記的眾多回憶錄中,彭加倫是最有文采的作者之一,他描繪了紅軍家屬送別紅軍后夜幕降臨的情景:
太陽在遠山背后,漸漸地下去了,夜幕開始籠罩了大地。正在起著晚煙的村莊,和黃透了的田野,蔥翠的山林,漸漸地模糊,在隊伍的后面消逝了。紅色戰士們一面前進,一面談笑著,他們活潑愉快興奮的情緒,不斷地在他們的笑容上流露出來。
這段話洋溢著溫暖樂觀的情緒,從中難以看出紅軍是迫于國民黨的軍事壓力被迫長征的。其時,國民黨在關于“圍剿”紅軍的報道中頻繁地使用“流竄”“進竄”這樣的字眼,而在彭加倫的筆下,紅軍的長征是從容不迫地開始的。暮色中的于都,宛如江南故鄉的風景,紅色戰士們歡樂地離開,似乎前路并不遙遠,很快就會返回似的。而索爾茲伯里所謂“月光下的行軍”也的確是事實,據時為紅三軍團政委的李富春回憶,為避免敵機的偵察和轟炸,紅軍長征多夜行軍,特別是從出發到渡過湘江的前后,差不多都是夜行軍。在他的描述中,夜行軍呈現為一種人與自然的高度和諧的景觀:
特別是夏秋天氣,乘著月光夜行軍,卻很暢快,月朗星稀,清風徐徐,有時蟲聲唧唧,有時水聲潺潺,有時犬吠數里,野花與黃菜爭香,夜中更覺幽雅。經過村落時,從疏疏的燈火中,看到一村的全部男女老幼,帶著詫異而又愉快的眼光,望著我們這走不盡的“鐵流”的紅軍。
而對夜行軍的圖像化描繪在另一個段落中達到了極致。舉著無數火把的隊列仿佛點燃了沉沉夜幕:
點火把夜行軍,是很壯麗的,走平坦大道,真是可以光照十里,穿過森林時,一點一點,一線一線的火光,在樹林中,時出時現,如火蛇鉆洞,紅光照天!過山時,先頭的已魚貫的到山頂,宛如一道長龍,金鱗閃閃,十彎十曲地蜿蜒舞蹈!從山頂回頭下望,則山腳下火光萬道,如波浪翻騰,一線一線一股股的奔來,即在錢塘江觀潮,泰山上觀日,也無此奇跡。
將長征中行軍艱險再現為瑰麗的風景的情況,在《紅軍長征記》中比比皆是。將其看作一種刻意的修辭策略顯然是對革命文化的誤解,因為,其中的樂觀主義基調作為一種精神建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之一。按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一書中表達一種堅信:“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無權成為悲觀主義者。”按照布洛赫的理解,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建立在“已知的希望”基礎上的“戰斗的樂觀主義”(militanter Optimismus),它既反對虛無主義的悲觀主義,也反對自發的樂觀主義,馬克思主義者致力于呼喚新天新地,致力于打碎舊世界,建立一個新的人類共同體:“在這個世界上人自己必須檢查是否一切正常把他所期待的、可運作的事業照看好;于是幸福如意、戴著黑紗的、戰斗的樂觀主義向他招手。”
而在其他關于長征的回憶文本中,我們同樣能夠看到這種高度自覺的樂觀主義。在這些文本中,通過主體的介入,自然風景被再現為象征革命精神的“第二自然”。
作為四川人,朱德對川中風景深有體會。史沫特萊寫道:“將軍每次都會贊嘆四川的壯麗。聳立在他家周圍的群山,乃是大雪山向東延伸的一條余脈。”1908年12月,朱德與秦昆一起前往云南講武堂,二人還特意在雄奇山水中流連。當長征的隊伍進入滇川之間,朱德已是舊地重游。對于革命的行動者而言,對風景的感知未嘗不是審美活動,只不過這種審美活動在長征途中有著超越了審美的國家意識。按照路線圖,紅軍是先渡金沙江再過大渡河。穿行于川、藏、滇三省區之間的金沙江是長江的上游,這條河流的雄奇之處在于其巨大的水流落差。和金沙江一樣,大渡河水也在深山峽谷中洶涌咆哮,其聲勢足以湮沒激戰的槍聲。對沖過了無數生死關的紅軍來說,大渡河在他們的腦海中留下了重要的記憶圖像。時任紅3軍團第11團政委的張愛萍后來回憶道:
大渡河水的驚濤駭浪猶如萬馬奔騰。水流的吼聲,喚起了我們深沉的回憶:遵義、赤水河、扎西、婁山關、烏江、北盤江、金沙江這些令人難忘的地點和河流,那些英勇艱苦的戰斗場景,又一幕幕地浮現在眼前。
驚險的江勢加上偏僻的位置,兩條流域既非歷代士大夫所樂游,亦非崇尚“臥游”的山水畫家出入之地。在藝術地理學的意義上,近代中國對這兩條河流的書寫和藝術再現乃是藝術史上的創造,是對革命風景的詩性建構,在這種詩性的內在中體現出的正是對長征風景英雄式的建構邏輯,體現出親歷者在事件中展現出的樂觀主義精神。
三、長征風景的崇高性
通常認為“崇高”是一個源自西方美學的概念,是古羅馬時代的朗吉努斯在修辭學著作《論崇高》中首先提出來的。而崇高在中國則是一個現代性概念,是由近代的中國革命建構的新傳統。從旅行家的視角看,紅軍在長征途中所經歷的多樣的地理環境,是一場偉大的冒險。
按《紅軍長征全史》的記述,在翻越夾金山時,隨著山勢增高,寒風卷著飛雪四處飄舞,戰士一個個都成了“雪人”,皚皚白雪霎時就變得面目可憎了。當紅一軍團的前衛團第四團達到山頂時,發現這座飛鳥難過的“神仙山”其實也有人蹤,山頂上有人為立起的旗桿,還有寺廟矗立于此,代表當地人的信仰。如果說雪山信仰的崇高性體現的是藏人的精神境界,紅軍翻越大雪山則是基于另一種崇高信念,即革命精神。此外,翻越大雪山的國家地理意義也是全新的。
相比于雪山的雄偉,位于青藏高原與四川盆地過渡地帶的松潘草地則詭秘異常。當時,紅十一團已經渡過了班佑河,走出了草地,軍長彭德懷發現有幾百人還沒有跟上部隊,就派王平帶人去接。當王平帶著戰士返回到河邊時,在望遠鏡看到河對岸有八九人背靠背整齊地坐在河岸上,喊話也無人應答,他就帶通訊員和偵察員涉水過河察看,結果地上的紅軍戰士一拉就倒,他們已全部犧牲,人類歷史上可能從未出現過如此驚心動魄的生命現象。
而在對長征精神的認識和理解中,一個共同的主題詞就是集體的革命英雄主義。在接受史沫特萊采訪時,朱德反復提到紅軍隊伍中產生了新的英雄觀念:
“英雄主義是個舊觀念,”他說,“過去,個人英雄凌駕在群眾之上,輕視群眾,甚至奴役群眾。紅軍體現了英雄主義的新觀念。我們培養出革命的群眾英雄,他們不自私自利,不為任何誘惑所動,決心為革命犧牲,一直戰斗到我們的人民和國家獲得解放為止。”
在與長征有關的記述文獻和圖像文獻中,風景是一個建構性的要素,它體現了人與自然全新的關系。對于風景,旅行者的凝視或者“視覺占有”已失去了其傳統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人與自然之間高度緊張的關系。在自然面前,主體的情感和意志被激發出來,且具有一種崇高感。“崇高是偉大心靈的回聲”,如長征途中的紀實性文本和長征回憶錄文本所體現的,長征途中的奇險風景是革命情緒的共鳴板。
參考文獻
[1] 埃德加·斯諾. 紅星照耀中國[M].董樂山,譯.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 丁玲. 紅軍長征記[M]. 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6.
[3] 夢海.人的命運掌握在人手中——論恩斯特·布洛赫的戰斗的樂觀主義[J].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7(5).
[4]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M]. 梅念,譯. 上海:東方出版社,2005.
作者簡介:劉鶴翔,中南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副教授。王國祥,中南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
基金項目:本文獲中南大學高端智庫“中國共產黨重大歷史題材美術精品創作與國家收藏研究”(2021znzk10)項目資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