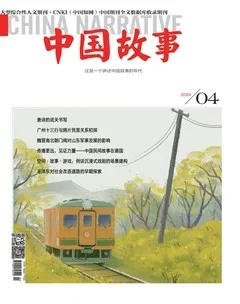泰州學派以庶民為對象的實踐活動
【導讀】泰州學派是16世紀發源自陽明學且有別于陽明學的一個思想流派。泰州學派中的很多人物如朱恕、韓貞、夏廷美等均是沒有功名的布衣儒者。他們個性張揚、言論大膽、自命不凡,有著英雄主義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其思想觀念帶有鮮明的“民間化”“庶民化”色彩。泰州學派的門人熱衷于講學,并致力于將講學活動擴展至庶民階層,泰州學派在繼承了王陽明“覺民行道”理想的基礎上,以“講學覺民”作為實踐“道”的重要手段。
一、前言
明代中后期政局昏暗,皇帝與文官集團關系緊張,知識分子難以通過在官場的努力實現政治理想。同時,社會人口激增,生員人數隨之增長,科舉名額卻并未增加,導致士人功名之路愈加艱難。因此出現大量無官無職、無所適從,但又有一定政治抱負的生員。陽明學在士階層廣泛傳播后,儒生受到啟發,展現出參與社會實踐的強烈活力和熱情。在以上因素的影響下,16世紀20年代后,社會上興起一股規模與普及程度均遠超前代的講學風潮。除開門授徒的學者講會外,還有朋友聚會、社會講學和地方縉紳定期講會等多種形式。后三種皆歡迎各階層人士甚至鄉民百姓的參與。
泰州學派是16世紀發源自陽明學且有別于陽明學的一個思想流派。泰州學派中的很多人物如朱恕、韓貞、夏廷美等均是沒有功名的布衣儒者,他們個性張揚、言論大膽,自稱“能以赤手搏龍蛇”,有著英雄主義式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其思想觀念帶有鮮明的“民間化”“庶民化”色彩。對泰州學派持有偏見的黃宗羲也承認泰州學派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陽明學的發展,說“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肯定了泰州學派在當時的影響力。泰州學派創始人王心齋出身于與科舉制度平行的庶民階層,他的思想觀點顯然包含了一些針對庶民階層的因素。總體而言,泰州學派的門人熱衷于講學活動,并致力于將講學活動推廣到庶民階層。他們在繼承王陽明“覺民行道”理想的前提下,以“講學覺民”作為實踐“道”的重要途徑。本文試圖分析泰州學派門人的觀點學說與具體實踐事例,以考察其在庶民階層造成影響的原因。
二、建立平民成圣的信心——以王艮為例
王艮(1483—1541),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王陽明入室弟子,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是庶民出身的鹽商,一生沒有功名,因此比專注科舉的士人更清楚庶民階層的需求和心理狀態。由于不追求功名,王艮的理論觀點少了富貴名利的負擔,顯得活潑自然,且帶有極強的實踐目的性。王艮主張從當下入手,以改變現實、改變自己為起點,并通過授徒、講學等社會實踐活動對社會造成影響,實現政治上的理想抱負,有突出的個人意識和實踐精神。
(一)滿街圣人、百姓日用即道
王艮的思想體系中,“萬物一體”論與“淮南格物”說最具特色,而“滿街圣人”與“百姓日用即道”則最能體現其庶民色彩。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記載了王艮對于“百姓日用即道”的表述:
先生(王艮)于眉睫之間省人最多,謂“百姓日用是道”。雖童仆之往來動作處,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聞者爽然。
從上文可看出,王艮善用生活中的具體事例比喻說理,將“道”去神圣化,讓平常百姓覺得通俗易懂。王艮言“圣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強調圣人生活同百姓日常生活無異,不但讓圣人不再遙不可及,也強調了日常生活行為的重要性。不過,“百姓日用即道”也遭到了異見者的攻擊,他們認為王艮強調本體、忽視功夫。若平常百姓的日常行為都看作是“道”或“良知”,就輕視甚至忽視了常人私欲的負面作用,進而模糊感性與理性的界限。王艮所講的“百姓日用即道”并非所有的“百姓日用”,而是特指百姓生活中無意識而為的點滴善行。雖然百姓沒有深層功夫的修養,但生活中的日常善行也是“道”的體現。通過工夫的修煉和自身的積累將小善轉化為大善,普通百姓就有望成為圣人。
“滿街圣人”一說可見于《傳習錄》的記載。一日,王艮出門回來,王陽明問他出游看到了什么,王艮回答道:“見滿街都是圣人。”這里的“滿街圣人”并非認為街上眾人均是現成的圣人,而是強調所有平常人均具有成圣的可能性。王艮力圖打破階級出身對人們思想的限制,喚醒庶民的個體意識,鼓舞平民百姓樹立成圣的信心。
無論是“百姓日用即道”還是“滿街圣人”,它們都有特定的思想背景與目的性。這種觀點并非客觀嚴謹的學理命題,更像是為引起百姓注意而提出的“思想口號”。王艮用通俗的例子來解釋“道”,試圖將圣人拉進現實生活,激勵平民成圣,是為了拉近心學與平民階層的距離。王艮強調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實踐和生活中的切實體驗,尋求簡單易行的修養方式,以便百姓的接受和實踐。同時,王艮對儒學的解釋也在盡力符合百姓的價值取向。
(二)安豐草蕩事件
嘉靖七年(1528年)王陽明逝世后,王艮回到家鄉泰州一帶開門授徒,積極推動講學,在當地造成一定影響。目前,我們尚無法確定王艮講學活動中的庶民比例以及其觀點在庶民階層中的接受程度。但下文試圖從一個關乎當地百姓生活的實際案例觀察王艮在當地的影響力,即發生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的安豐草蕩事件。“草蕩”是明代官撥以作煎鹽燃料之用的蕩地。為保證鹽課,官方規定即使在此開墾耕種也無需承擔正賦田糧,因此吸引了許多人前來開墾,過度侵占現象頻發,造成了社會經濟問題。蕩地占耕是一個普遍現象,安豐鹽場自然也不例外。為解決此棘手的問題,地方官向王艮求助。根據吳震在《泰州學派研究》中的考察,王艮通過重新劃定“經界”、發放“印信紙票”作為財產憑據等措施,有效地處理了這件令地方官十分頭疼的事件。
成功解決“安豐草蕩事件”,不僅需要熟悉地方狀況、體察問題所在、制定合理措施,還需一定的社會聲望,以得到當地士紳與民眾的配合來實施措施。這一事件充分展示了王艮的社會生活和處理現實問題的能力,也是他能將其學說影響擴展至庶民階層的原因之一。
三、將儒學通俗化、宗教化——以顏山農為例
顏山農(1504—1596),名鈞,字子和,號山農,又號耕樵,江西省永新縣人,是一位終生不曾沾染科舉的民間學者。他以社會大眾為主要宣教對象,社會角色更重于他在學界的角色。王汎森在《明代心學家的社會角色》一文中將顏山農的社會角色歸納為三種:社區改善運動者、打破士庶分別的講學活動者與心理咨詢和治療者。可以看出,顏山農試圖通過多樣的社會實踐活動在現實社會中說服民眾,傳播儒學精神,建立起領導性的思想權威。
(一)三都萃和會
顏山農十二歲才開始讀書,之后就讀于常熟學宮,十七歲時家道中落,后失學在家。二十五歲時,顏山農得到堂兄顏欽贈送的手抄《傳習錄》,讀后內心感奮。再三研讀《傳習錄》之后,顏山農閉關七日徹悟,又在山谷中潛居九個月,后回到家中,在當地聚眾演講孝悌良知。顏山農的演講在家鄉迅速取得成效,“人人親悅、家家協和、踴躍奮勵,雖少小童牧,盡知慚悔省發,皆知叩謝父母長上,竟為一家一鄉快樂風化”。顏山農即在家人的支持下舉辦“三都萃和會”,聚士農工商會講,“喧赫震村舍,閭里為仁風也”。三個月后,“三都萃和會”因顏母病喪終止。
年輕的顏山農在悟道后,迅速在家鄉獲得積極反響。當時顏山農并未建立系統的王學知識體系,也未受到專業的知識訓練,僅憑借研讀《傳習錄》后的一腔熱情和閉關七日中個人體悟,在家鄉舉辦面向社會大眾的講學傳道活動,并獲得了積極的響應。由此可見,顏山農的確有講學的天賦和魅力。盛極一時的萃和會雖因顏山農私人生活原因迅速結束,但此事給了顏山農極大的信心,此后顏山農一生四處講學,希望在全天下實現在家鄉取得過的成效。
(二)社會講學
顏山農為母親守喪完畢后,便前往泰州、如皋、江都等地游學,教化下層民眾。山農先跟從劉師泉學習,感覺沒有收獲,又拜師徐波石,接受泰州學派的思想教育。此后,顏山農更加積極地投身于打破士庶之分的講學活動。那么,顏山農的具體行動有哪些?引一段《急救心火榜文》中的文字說明:
會集四方遠邇仕士耆庶,及赴秋闈群彥與仙禪、賢智、愚不肖等,凡愿聞孔孟率修格致養氣之功,息邪去诐放淫之說,咸望齊赴行壇,一體應接,輔翼農講,成美良會。會以萃神協志,忘懷孚麗,人皆受學,學皆知正。
會集“仕士耆庶”表明講學對象范圍廣泛,從官員到庶民無所不包。后文強調以孔孟之學為依歸,提倡“萃神協志,忘懷孚麗,人皆受學,學皆知正”,這樣的理念對士庶階層皆有吸引力。吸引庶民階層的難度在于他們忙于生計,無暇顧及儒家家國天下的責任和情懷。但顏山農善于從人們的實際生活、實際感受入手,其講學內容除設計人際關系的指導,強調儒家的基本倫理與禮儀規范外,還致力于通過講學解決人們內心的“心火”,安頓人們的心靈。因此,可以說顏山農有時扮演著心理咨詢師的角色。泰州后學羅汝芳是當時的求助者之一。顏山農曾針對羅汝芳的“心火”問題說:“子惟不敢自信其心,則心不放矣。不能自見其心,則不敢自信,而心不放矣”,強調“自信其心”才能放心,“子如放心,則火然而泉達矣,體仁之妙,即在放心”。顏山農鼓勵人們建立起自信,達到放心的境界,從而使心靈得到平靜。
(三)宗教化
顏山農能在庶民階層取得一定影響,還與他講學中的宗教化特色有關。《自傳》記載,顏山農曾在心齋祠的講學開場求上天大開云蔽,令觀者驚嘆,這種場景如同帶著傳教色彩的宗教儀式。顏山農多次稱孔子為“神圣”,人人可成為“圣人”,但“神圣”卻獨指孔子,似乎有意將孔子塑造為一個遙不可及的最高標準,將孔子神格化。此外,顏山農獨創了一套修行方法——“七日閉關法”,這明顯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修行理念。這些方法盡管華而不實,脫離儒家精神,但它們確實對特定的人群有一定吸引力,讓部分百姓在情感上接受了儒學的精神價值。
通過顏山農的事例,人們可以看到民間學者迎合平民百姓的心理需要來傳播儒學的痕跡。顏山農有意避免了傳統儒學的枯燥說教,憑借自身魅力和口才能力揭示儒學對百姓現實生活的價值作用,幫助他們解決具體的個人生活問題,同時采用宗教式方法,讓百姓在情感層面產生共鳴和認同。
四、通過社會活動擴大講學影響——以何心隱為例
何心隱(1517—1579),本名梁汝元,字柱乾,號夫山,江西省吉安府永豐縣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成諸生。萬歷七年(1579年)被湖廣巡撫王之垣處死在獄中。何心隱是一個和顏山農一樣極具游俠精神的人,被視為“異端”思想家。他是典型的實踐派儒者,既反對革命又無心仕途,而是通過積極投身地方公共事務與政治活動來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
(一)聚和堂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何心隱在家鄉籌辦了具有鄉約性質的聚和堂,旨在通過籌辦鄉村宗族組織,推動儒學的民間化,使儒學精神落實在百姓日用間,注意對鄉村百姓具體行為的指導。聚和堂是一個相對成熟完整的鄉民組織,設有率養與輔養來統一管理錢糧、交收征糧,并設立率教與輔教來管理學堂、教育宗族子弟,倡導儒家的倫理價值。何心隱還撰寫了《聚和率教諭俗俚語》與《聚和率養諭俗俚語》作為施政綱領,甚至對婚喪嫁娶等事宜制定了相關規定,深入影響當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帶有地方自治性。與萃和堂的曇花一現不同,聚和堂持續運作了六年,直到何心隱因得罪新任知縣陳瓚,卷入“皇木銀兩”事件而獲罪才告結束。
何心隱以籌辦宗族組織的形式實踐所學,造成了一定反響。鄒元標說他“數年之間,一方幾于三代”,黃宗羲說他“行之有成”,容肇祖稱之為“鄉村教育的先導者”。可見,聚和堂作為心學家社會實踐的一個實例,確實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鄉村組織的建設往往依賴于地方官個人的態度。在與何心隱私交較好、樂意支持其事業的縣令凌儒離開后,聚和堂不得不面臨失敗的境地。
(二)講學
何心隱《原學原講》一篇強調人“必不容不有事于貌,必不容不有事于學”而“必學必講”。文章通篇使用反問句,語氣十分強烈,極具感染力,強調講學在儒家傳統中不可動搖的地位和意義。自1560年至1579年的十九年間,何心隱的游學足跡遍布福建、江西、安徽、浙江等地,他抱著淑世的精神,不斷從事講學活動,并陸續結交了程學顏、錢同文、羅汝芳等人。遺憾的是,筆者并沒有找到記錄其講學場面的詳細資料,而何心隱也未留下聲名顯赫的傳世弟子。
黃宗羲記載顧端文的觀點,稱“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重,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認為何心隱并無可取之處,只是憑獨到的“聰明”“鼓動得人”而已。從容肇祖整理的《何心隱集》看,何心隱注重實行、重友倫、重義氣,有急于拯救天下的愿望、強烈的進取意識和自我意識。擁有以上特征的人往往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這對現實的講學活動、人際交往有很大幫助。何心隱的思想看似淺顯,但他向下層百姓普及儒學所做的努力和新方式的嘗試,仍是功不可沒的。
五、結論
泰州學者盡力尋找讓庶民階層接受儒學的切入點,他們考慮日常生活需要、迎合平民百姓的心理需求,強調個體意識和實踐精神。他們通過鼓勵平民成圣的信心、解決人們的心理問題、積極投身社會活動等方式,力圖讓庶民百姓從情感上接受、從行動上落實儒家精神。論及對庶民階層對于心學的接受實例,泰州學者本人便是極佳的例證。他們以庶民身份接受儒家士大夫階層的意識形態,又轉而面向社會大眾,嘗試以庶民可接受的社會實踐行動教化地方百姓。他們或試圖從地方自治和宗族倫理建設入手,以社會實踐的方式改造社會,實現政治理想;或開展以庶民階層為對象的講學活動,嘗試與他們交流溝通。
泰州學者的努力確實取得了一定成效,它們將陽明學的影響擴大到了民間百姓階層。不過,泰州學者在實行社會實踐時,并未形成相應的思想理論、制定完善的制度。鄉村組織的籌建往往依賴于個人能力、家族財力和在當地的影響力,存在諸多不穩定因素,持續時間也有限。為了讓庶民階層更易接受,泰州學者在講學傳道中加大了感性情緒的比重,舍棄了很多陽明學的精華,導致其易被人找出破綻,招致責難和誤解。
參考文獻
[1] 黃宗羲. 明儒學案·泰州學案[M]. 北京:中華書局,1986.
[2] 吳震. 泰州學派研究[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3] 容肇祖. 何心隱集[M]. 北京:中華書局,1960.
[4] 呂妙芬. 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5] 余英時. 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M]. 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6] 左東嶺. 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7] 容肇祖. 容肇祖集[M]. 濟南:齊魯書社,1989.
[8] 彭國祥. 近世儒學史的辯證與鉤沉[M]. 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9] 余英時.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增訂版)[M].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10] 王汎森. 晚明清初思想十論[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11] 吳震. 泰州學案芻議[J]. 浙江社會科學,2004(2).
[12] 蔣國保. 儒學的民間化與世俗化——論泰州學派對“陽明學”的超越[J]. 南京大學學報,2007(6).
作者簡介:張柳然,河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