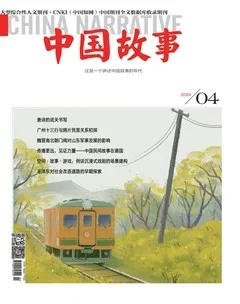空間·故事·游戲:例談沉浸式戲劇的場(chǎng)景建構(gòu)
【導(dǎo)讀】沉浸式戲劇是沉浸式體驗(yàn)產(chǎn)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典型代表,是目前年輕群體所追捧的戲劇形式之一。沉浸式戲劇的場(chǎng)景建構(gòu)包含空間、故事、游戲三大要素,具有全境性、開放性、交互性三大特征。沉浸式戲劇的所有場(chǎng)景設(shè)計(jì)都以滿足“沉浸”要求為核心,這也是它與傳統(tǒng)戲劇的最大區(qū)別所在。
當(dāng)代實(shí)驗(yàn)戲劇展現(xiàn)出多元生態(tài)。其中,沉浸式戲劇在藝術(shù)探索和經(jīng)濟(jì)價(jià)值領(lǐng)域受到的關(guān)注日益上升。2003年《不眠之夜》(Sleep No More)在倫敦開演,成為沉浸式戲劇正式走進(jìn)大眾視野的標(biāo)志性事件。國(guó)內(nèi)也不乏成功的沉浸式戲劇案例,例如何念的《消失的新郎》、孟京輝的《成都偷心》、王潮歌的《只有河南·戲劇幻城》等。本文從場(chǎng)景理論切入思考沉浸式戲劇的構(gòu)建機(jī)制,研究“沉浸”的生成與價(jià)值。
一、真實(shí)沉浸與具身感知的物理空間
哲學(xué)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從社會(huì)學(xué)角度提出了空間三元論,打破了人們對(duì)空間的固有認(rèn)知。學(xué)者埃爾登(S.Elden)對(duì)空間三元論的解釋是:“感知的空間是一種物理的空間;構(gòu)思的空間是一種精神構(gòu)造和想象的空間;體驗(yàn)的空間則是一種在日常生活中被加工過的空間。”在沉浸式戲劇中,空間更多地表現(xiàn)為“感知的空間”,它強(qiáng)調(diào)人與環(huán)境的相互依存。空間、演員、觀眾、故事等元素共同為作品的完成貢獻(xiàn)力量,構(gòu)建出整個(gè)戲劇場(chǎng)景。在“感知的空間”層面,沉浸式戲劇的空間特征主要體現(xiàn)為真實(shí)沉浸與具身感知兩個(gè)方面。
(一)真實(shí)沉浸
心理學(xué)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賴(Mihaly Csikszentmihalyi)提出了心流理論。當(dāng)一個(gè)人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愿意為之付出的某個(gè)目標(biāo)中,并及時(shí)獲得反饋時(shí),心中高度興奮和充實(shí)的感受便表明他進(jìn)入了心流狀態(tài)。沉浸式戲劇的核心追求就是使觀眾沉浸于作品之中。沉浸式戲劇使觀眾在清醒狀態(tài)下置身于聲、光、電等技術(shù)效果中,作品中的各個(gè)因素刺激著觀眾的感官與認(rèn)知,改變其感知能力,從而引導(dǎo)他們進(jìn)入心流狀態(tài)。
《只有河南·戲劇幻城》(以下簡(jiǎn)稱《只有河南》)是目前國(guó)內(nèi)最大的戲劇聚落群之一。園區(qū)內(nèi),無(wú)論是建筑的整體風(fēng)格還是文創(chuàng)商品等細(xì)節(jié),所有元素都緊緊貼合“河南”二字,傳遞著“黃河、土地、糧食、傳承”的主題精神。21個(gè)戲劇作品每天同時(shí)上演,全場(chǎng)景還原的布局、逼真的道具、行進(jìn)式的觀眾共同構(gòu)成了《只有河南》戲劇演出空間的關(guān)鍵要素。觀眾從進(jìn)入園區(qū)那一刻起,就進(jìn)入到屬于河南的世界里。這種觸動(dòng)在觀賞戲劇時(shí)達(dá)到頂峰,而在離開園區(qū)時(shí),觀眾仍能回味無(wú)窮,感受河南文化帶來(lái)的震撼與感動(dòng)。
(二)具身感知
“具身”強(qiáng)調(diào)人的認(rèn)知對(duì)身體的依賴性。近年來(lái),聲光影數(shù)字技術(shù)、人工智能技術(shù)、虛擬現(xiàn)實(shí)技術(shù)在沉浸式戲劇中的應(yīng)用越來(lái)越深入,此類高新技術(shù)是制造具身感知的必備條件。2014年荷蘭布雷達(dá)市交流與多媒體設(shè)計(jì)團(tuán)隊(duì)創(chuàng)作了《名人之死》。觀眾可以選擇進(jìn)入四個(gè)類似于停尸房抽屜的金屬盒中的任意一個(gè),在五分鐘里體驗(yàn)肯尼迪、戴安娜、卡扎菲、惠特尼·休斯頓的臨終時(shí)刻。金屬盒外連接著不同的氣味瓶和配樂設(shè)備,觀眾在特定的金屬盒內(nèi)感受名人臨死前聽到的聲音和聞到的氣味,沉浸于逼真的藝術(shù)世界中。
5G+VR+AR+AI等虛擬技術(shù)組合的應(yīng)用是沉浸式戲劇發(fā)展的趨勢(shì)。例如2019年國(guó)內(nèi)XR創(chuàng)意工作室Sandman Studios創(chuàng)作的《浮生一刻》,其靈感來(lái)源于《西游記》。該作品的最大亮點(diǎn)在于真人NPC(非角色玩家)與技術(shù)設(shè)備的完美結(jié)合。NPC分別扮演孫悟空與二郎神,穿戴全身動(dòng)捕及面部表情捕捉設(shè)備,不僅使用了HTC Vive Pro的頭顯,還采納了Intel的無(wú)線方案,在外部定位技術(shù)上的選擇則是Steam2.0以及Optitrack。這部作品的具身化形式包括視覺沉浸、動(dòng)覺激活、增強(qiáng)技術(shù)、真人與虛擬人互動(dòng)等。
基于列斐伏爾的空間三元論,本文認(rèn)為沉浸式戲劇中的感知空間具有全境性的特點(diǎn),空間中的一切構(gòu)成都應(yīng)該導(dǎo)向全方位的感官體驗(yàn)。通過構(gòu)建感性與理性的相互交織、共同存在的場(chǎng)景空間,將體驗(yàn)者從物理層面的真實(shí)場(chǎng)景引向心理層面的感受情境,從而創(chuàng)造出引人入勝的沉浸式體驗(yàn)感。
二、瓦解線性敘事邏輯的開放性敘事
科普利(Paul Cobley)如此總結(jié)沉浸體驗(yàn)式戲劇中敘事、故事、敘述三者的關(guān)系:故事是已發(fā)生的、有待被描述的事件;敘事是需要被闡釋的、一連串事件間的因果關(guān)聯(lián);敘述是對(duì)整個(gè)事件前因后果的演繹,往往帶有特定的情感色彩。它們共同創(chuàng)造出沉浸式戲劇的體驗(yàn)全過程。如今的沉浸式戲劇總體分為兩類:重氛圍的沉浸式戲劇與重文本的沉浸式戲劇。它們?cè)跀⑹路矫媾c傳統(tǒng)戲劇最大的不同在于對(duì)傳統(tǒng)戲劇中線性敘事邏輯的瓦解,開放性、碎片性是其主要特征。
(一)重氛圍的沉浸式戲劇
重氛圍類的沉浸式戲劇最能體現(xiàn)環(huán)境戲劇的“超文本”的特征,固定的文本在戲劇中被邊緣化,觀眾的參與性與自主性得到了更多的重視。
《不眠之夜》為此類戲劇的典型。它的主線情節(jié)改編自《麥克白》,在此基礎(chǔ)上根據(jù)演出地的文化基礎(chǔ)添加新的劇情元素。作為戲劇發(fā)生地,整個(gè)酒店處于一個(gè)“光滑空間”中,這是一個(gè)敞開的、無(wú)等級(jí)的空間,無(wú)固定路線,也不指代任何身份,觀眾戴著面具游走在這一空間中,自由地尋找探索故事線索與情節(jié)結(jié)點(diǎn),以此來(lái)接收或解析不同的故事內(nèi)容。在三個(gè)小時(shí)的演出中,演員沒有臺(tái)詞,文本也不是戲劇的重點(diǎn),環(huán)境氛圍感的營(yíng)造才是其核心所在。由于故事線細(xì)碎雜亂,觀眾注定無(wú)法知曉全部劇情,只能捕捉到劇情網(wǎng)中的一小部分。觀眾的觀劇重點(diǎn)并不在演員的表演,而是與自身對(duì)話。
2019年孟京輝執(zhí)導(dǎo)作品《成都偷心》在成都上演。戲劇發(fā)生在一處三層大樓內(nèi)。為營(yíng)造神秘感,觀眾在觀影前就已被系統(tǒng)隨機(jī)分配至不同的入口進(jìn)場(chǎng)。在情節(jié)敘事上,故事內(nèi)容有五條主線、十二條副線,但故事發(fā)生的時(shí)間順序、因果關(guān)系被徹底打破,觀眾接受的是大量碎片故事。《成都偷心》設(shè)計(jì)了一些模糊不清的臺(tái)詞,這些臺(tái)詞讓觀眾感到困惑,卻又因神秘人保持安靜的手勢(shì)示意而無(wú)法與他人交談,因此,觀眾只能依靠混亂拼貼的臺(tái)詞敘述故事,自行理解故事主題。
這種沉浸式戲劇已在國(guó)內(nèi)形成熱潮,受到年輕群體的推崇。然而,這種戲劇也因其重形式輕內(nèi)容而遭到詬病。同時(shí),高度自由的觀演模式可能會(huì)導(dǎo)致觀演行為出現(xiàn)混亂,觀眾過于專注地跟隨著某位演員或探索某條線路,導(dǎo)致錯(cuò)過了其他故事,最終無(wú)法拼湊出整個(gè)劇情。這種體驗(yàn)對(duì)習(xí)慣于傳統(tǒng)觀演模式的觀眾而言是欠佳的。
(二)重文本的沉浸式戲劇
重文本的沉浸式戲劇仍然遵循沉浸式戲劇基本的開放性、碎片性敘事邏輯,但表演中演員會(huì)適當(dāng)將觀眾引導(dǎo)回固定的流程中,回歸主線故事的結(jié)尾。
《只有河南》與《大真探趙趕鵝》為此類型戲劇案例。《只有河南》中的《火車站》《李家村》共同講述了1942年河南大饑荒災(zāi)難下李家村村民們的故事。《火車站》通過四個(gè)空間講述了火車站站長(zhǎng)李十八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故事。第一幕講述李十八從小與哥哥相依為命的經(jīng)歷。隨后,觀眾會(huì)跟隨引導(dǎo)四散進(jìn)入不同的村民家中,零距離聽他們講述挨餓的故事。隨著劇情發(fā)展,村民決定要去火車站搶糧,觀眾也來(lái)到糧倉(cāng)。作為站長(zhǎng),李十八的職責(zé)是守護(hù)好糧倉(cāng),但他看著面前飽受饑餓的村民,不禁陷入兩難境地。最終,哥哥的到來(lái)使他選擇違背命令,犧牲自己成全村民。《李家村》則講述李十八死后,他的哥哥與村民將搶來(lái)的糧食帶回李家村的故事。糧食有限,無(wú)法解決一村人的溫飽問題,于是,60歲以上的老人決定集體赴死。觀眾在逼真的場(chǎng)景氛圍下穿越回1942年,完整體驗(yàn)到村民的生死經(jīng)歷。
2023年在北京77劇場(chǎng)上演的《大真探趙趕鵝》的故事發(fā)生在1998年的北京南槐樹胡同。刑警林文科剛上任就遭遇兇殺案,他認(rèn)為這是連環(huán)殺人案,而師傅冉曦卻不以為然。兇案的再次發(fā)生使兩人放下成見共同戰(zhàn)斗。但因?yàn)橐粓?chǎng)意外,林文科和冉曦分別調(diào)崗至警務(wù)保障部和警犬隊(duì)。之后林文科飽受心理折磨,冉曦退休后不斷尋真兇卻無(wú)果,最終郁郁離世。知道真兇被捕,林文科心中才終于安定,但他卻早已不是當(dāng)年那個(gè)自己。整個(gè)故事有清晰的脈絡(luò),在主線之外還刻畫了北京胡同的生活細(xì)節(jié)。然而,戲劇沒有按照故事發(fā)展的時(shí)間順序進(jìn)行,而是采用了一種撕裂線性的敘事邏輯,借助不同的空間來(lái)進(jìn)行內(nèi)容講述。觀眾對(duì)故事的理解也不再按照時(shí)間線這一既定模板,而是自我組合接收到的信息片段,從而實(shí)現(xiàn)對(duì)內(nèi)容的理解。
不論是哪種沉浸式戲劇,觀眾對(duì)故事的解讀都會(huì)各不相同,這恰恰是沉浸式戲劇敘述多元化和不確定性的體現(xiàn)。沉浸式戲劇的敘事超越了傳統(tǒng)戲劇中以線性持續(xù)時(shí)長(zhǎng)為主的表現(xiàn)形式,從戲劇的起點(diǎn)到終點(diǎn),不同的觀演者與不同的參演者之間交互作用,產(chǎn)生網(wǎng)狀的情節(jié),而所有相互連接的故事又共同構(gòu)筑了情節(jié)的厚度。
三、賦予觀眾高度自由的游戲體驗(yàn)
沉浸式戲劇最重要的場(chǎng)景建構(gòu)因素是交互性,這種交互性賦予了觀眾高度自由的交互體驗(yàn)。鑒于沉浸式藝術(shù)的交互性與游戲中的交互性高度相似,故可稱這一特性為沉浸式藝術(shù)的游戲性。創(chuàng)作者將傳統(tǒng)戲劇與現(xiàn)代游戲的機(jī)制相結(jié)合,帶動(dòng)觀眾一邊欣賞一邊創(chuàng)造,共同參與到戲劇構(gòu)建過程中去。
2021年百樂門利用舞廳打造了《逆熵紀(jì)元百樂門》。參與其中的觀眾們有的身穿旗袍飾演一代名伶,有的身穿中山裝扮演愛國(guó)青年,還有的在扮演戰(zhàn)時(shí)特務(wù),穿梭于百樂門原址,完成故事設(shè)定的秘密任務(wù)。當(dāng)觀眾不知所措時(shí),就會(huì)有附近的演員上前引導(dǎo):“這位客人看著陌生,今天來(lái)這兒的都是上海灘的名流,我?guī)闳フJ(rèn)識(shí)認(rèn)識(shí)?”觀眾能在與演員的交互中獲得游戲的快感,也會(huì)在與演員的互動(dòng)中彌補(bǔ)生活中人際交往的缺憾,短暫逃避現(xiàn)實(shí)中帶來(lái)的壓力。英國(guó)秘密影院出品的《秘密影院:007大戰(zhàn)皇家賭場(chǎng)》同樣在觀影過程中不斷加深觀眾與戲劇的交互性。觀演前,所有觀眾都收到一份包含個(gè)人身份和秘密任務(wù)的郵件,身份與任務(wù)各不相同;演出當(dāng)天,觀眾來(lái)到底層外場(chǎng),演員們用酒水招待觀眾,觀眾游蕩其中,期盼接下來(lái)發(fā)生的事情;接著觀眾會(huì)跟隨指示牌來(lái)到陌生區(qū)域,或可能碰到一個(gè)行路人,或遇到幾個(gè)爭(zhēng)論的陌生人,或突然被演員拽住手,拉到角落對(duì)接暗號(hào),或被一群奇裝異服的人圍繞著跳舞。最后,大家的目光被吸引至頂層的皇家賭場(chǎng)內(nèi),大家熱血沸騰,一起共舞,成就這一場(chǎng)諜戰(zhàn)的高潮。整個(gè)過程中觀眾被賦予表演者身份,演員卻躲在暗處觀察一切,在最大限度賦予觀眾表演自由的基礎(chǔ)上保證戲劇表演的順利完成。
由此,演員與觀眾的關(guān)系變得模糊,雙方在不同情境中互為主體,一種去中心化的交流得以實(shí)現(xiàn)。在百樂門劇場(chǎng)中,不同角色的觀眾需要完成符合自身角色身份的不同任務(wù),在這個(gè)過程中,觀眾早已忘卻自己的真實(shí)身份,而將自己投射進(jìn)劇情中無(wú)法自拔,認(rèn)為自己與演員無(wú)異,這就是沉浸式劇場(chǎng)的魅力。沉浸式戲劇給予了觀眾前所未有的自主選擇權(quán)。在這里沒有絕對(duì)的主角與配角之分,每個(gè)人都能體驗(yàn)到不同的人生。
四、結(jié)語(yǔ)
在沉浸式戲劇的場(chǎng)景建構(gòu)中,空間、故事、游戲三者各司其職又相互協(xié)同。從鏡框式舞臺(tái)到全景式場(chǎng)景的全面沖擊,是戲劇空間的改變;從線性敘事到碎片整合的開放式敘寫,是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從演員與觀眾的分明對(duì)立到融洽無(wú)間的交互,是戲劇游戲的創(chuàng)造。三種要素相互影響、整體平衡時(shí),場(chǎng)景傳播才能獲得最佳效果。
參考文獻(xiàn)
[1] 羅伯特·斯考伯,謝爾·伊斯雷爾. 即將到來(lái)的場(chǎng)景時(shí)代[M]. 趙乾坤,周寶曜,譯. 北京: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4.
[2] Cf. Stuart Elden.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Possible[M]. London: Continuum, 2004.
[3] Paul Cobley. Narrative[M]. London: Routledge, 2001.
作者簡(jiǎn)介:楊茗馨,河北師范大學(xué)新聞傳播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