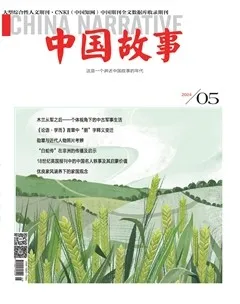傳統經典之美中的“言象意”
作者簡介:王子玥,長沙理工大學。
“言—象—意”三分法最早出現在《易經》中,是哲學領域所重點關注的內容,但同時它也對中國古代文學產生了深刻影響。它和羅曼·英伽總結出的四層次文本分析法相互對應,共同為文學作品的結構劃分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岳陽樓記》是我國北宋時期著名的文學作品之一,它以語言優美、意象唯美、意蘊真美而在文學史上有著極高的成就。本文旨在通過結合文學的文本層次理論,以“言—象—意”三分法為例,評析《岳陽樓記》的文學成就及其審美價值。
一、以言說美:文本語言中的音樂美
“‘語言是文學作品最基本的層次”。在《岳陽樓記》中,作者運用大量的修辭手法,再現岳陽樓的壯闊景象,體現其文學語言的“自指性”和“韻律性”。其中,作品中體現的語音美、韻律美更是最大程度上將岳陽樓“活”化,給人以生動之感。
朱光潛曾言:“聲音節奏在科學文里可不深究,在文學里卻是一個最主要的成分,因為文學須表現情趣,而情趣就大半要靠聲音節奏來表現。”在我國古代文學作品的創作中,從詩到詞再到散文,語言的韻律美始終是語言美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韻律的靈活運用往往使得文學作品讀來朗朗上口,有很強的音樂美感。《岳陽樓記》中大量雙聲詞和疊韻詞的使用正有如此效果:“瀟湘”“滿目”“遠山”“萬千”“長江”,等等,使得文本讀來一氣呵成、回環往復。同時,作品還運用了大量的重復手法,如:“浩浩湯湯”“淫雨霏霏”“薄暮冥冥”“郁郁青青”等。重復的疊音讓作品節奏鮮明,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讀者的感官,在場景變化的同時讓人有身臨其境之感。也在一悲一喜之間,加深了韻律之美,傳達出情景交融下的生動感。
通過韻律展現語言的美感既簡化了語言,使作品簡潔明快,也讓作品富有音樂美。在節奏變化間展現了漢語語音獨特的美感,讓平鋪在紙上的文字立體起來,讓立于水面的岳陽樓鮮活起來。
二、以象繪美:文本意象中的繪畫美
“象”作為最典型的象形字之一,其本意是指動物大象。在其演變的過程中,又逐漸被賦予“形象”“圖像”“象征”“意象”等意義。“象征”往往蘊含著大量的文化和精神內涵,與文字本身的意義有著更深層次的解讀,包含著作者更多的主觀感情和思考。而作品中大量意象的疊加與語言層面的碰撞則在主觀和客觀的融合中進一步再現了景觀之壯美,同時也深化了我們對作品的理解和解讀。
《周易·系辭上》中就曾提出過“立象以盡意”的觀點,在隱喻象征的藝術手法中,暗示作者的內心世界,在內容與概念的靈活轉化中,讓作家和讀者得以開展更多心靈上的交流與共鳴。中國傳統美學一般將意象表現為“情景交融”——完成景與情的契合,用心靈指引景物。在《岳陽樓記》中,作者刻畫了大量意象,如:“遠山”“長江”“陰風”“濁浪”“日星”“山岳”“沙鷗”“錦鱗”“皓月”“浮光”,等等。在對不同客體意象的描寫中,蘊含著作家獨特的思考和理解,如:用雨天表現出國家生存的現狀、用春和表現自己對未來的憧憬……不同意象的象征讓作品的內容更加豐富、內涵更加深刻,給了讀者大量的思考空間。意象的疊加使用也在言語之間,將碎片化的景象串聯起來,以一幅連續的畫卷在讀者的腦海中徐徐展開,表現出其繪畫美的獨特之感,韻味無窮。
同時“象”從實指大象慢慢演變為文學性的意象的過程則進一步表現了作家在對個人情感和心理的表達中希望尋找一個“中間物”作為寄托的美好愿望。對于作家而言,作品是他們與讀者溝通的“橋梁”。在搭橋的過程中,作家追求的不僅僅是其溝通功能的實現,同樣重要的是,要實現其作為溝通工具的審美價值。語言學家索緒爾在其《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提出“能指”與“所指”這一對概念。文學作品中意象的存在并不是一個“實體”,不是具體的所指,而是作家希望把心中的情感寄托在所指的語言符號中,讓讀者感受其內在的能指。
三、以意筑美:文本意蘊中的超越美
“文學作品的意蘊,是指由文學語言和文學形象所傳達的意義,屬于文學作品結構的最深層次。”創作于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中,對意蘊的雕琢始終是作家寫作的重點。意蘊絕不是單層次的,而是多層次的、富有生命力的外化。《岳陽樓記》之所以廣受稱贊,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范仲淹在文中所寫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不僅僅只是一句抒情之言,更是作家一生的為人準則,蘊含著其內心最真摯的追求。前兩部分提到的語言、意象手法上的運用,究其根本,都是為了凸顯文學作品的主題,體現作家的情感與抱負,在對主題的深化中表現文學作品意蘊的超越美。
在《岳陽樓記》中,蘊含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然開朗,也有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遠大理想。這里所展現的文學語言背后的意蘊遠遠超過了“言”的本意,達到了“意”大于“言”、“意”高于“言”、“意”深于“言”的無限潛能,跨越了傳統的記體文本的母題,也超越了自身。在“言象意”三者的共同引領下,產生了巨大的合力,共同構成了文學作品的張力。在文學意義實現的同時,更追求了文學藝術的美學意義。
《岳陽樓記》是我國古代文學中最經典的文學作品之一,在語言、形象、意蘊等方面都有著極高的成就。在“言意象”三力所形成的獨特空間中,傳統文學作品的文本層次得以明確,對傳統文學作品的理解得以深化。本雅明曾提出“影像是靜止的辯證法”。在今天,站在岳陽樓下重溫《岳陽樓記》,我們才真正感受到當下一瞬間與曾在之物的重合,真正體會到傳統經典為何為美、為何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