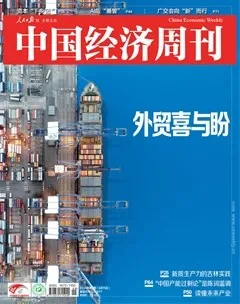資本“下鄉記”

作為新聞評論員,我經常到處調研,但這次有所不同,我跳開了熟悉的金融領域,進行了一次現代化農業領域的產業調研。
為什么?伏筆在2020年底,中國脫貧攻堅進入最后時刻,《中國經濟周刊》由我主持制作了一期特刊“我和我的鄉親們”,收錄了30個脫貧攻堅的故事。正是從那時起,在我心里留下了一系列問題:脫貧攻堅完成之后,中國的“三農”問題還有哪些困難待解?盡管鄉村全面振興已接續脫貧攻堅成為未來中國“三農”的發展主題,那鄉村又該如何全面振興?城市資本為什么愿意投資鄉村全面振興、訴求幾何、投資能否賺錢?除了鄉村旅游,沒有旅游資源的“綠水青山”也能變成“金山銀山”嗎?……
2024年春節和老伴自駕安徽度假,歸途在無為市石澗鎮探望好友,偶遇兩位執著于現代化農業發展的“癡人”,領頭的名叫陳號新,京淼源現代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京淼源”)CEO,另一位則是為了讓“京淼源”植根這片土地、三番五次去說服陳號新的“向導”——安徽省蕪湖市無為市嚴橋鎮牌樓村原黨支部書記、現任“京淼源”辦公室主任的陳偉。
也是出于好奇,讓陳號新領我到村里轉轉,結果沒想到,“京淼源”在這片土地上的一番創建讓我深感震撼:原來農業生產成本可以這樣來節省,原來農業生產效率可以這樣來提高,原來綠水青山可以這樣來升華,原來70歲的農民可以這樣來賺得數十萬元的年收入……
不過,鄉村故事背后,依然離不開金融的支撐,資本“下鄉記”還真有看頭。
小成本里的小故事
為了更加深入全面地讀懂“京淼源”,今年4月初,我再次來到牌樓村做深入調研。
4月2日,G41緩緩駛入巢湖東站,來車站接我的是陳偉。讓我沒想到的是,陳偉開著一輛十幾年前買的、手動擋的比亞迪來車站接我。車很小、膝蓋頂在副駕靠背上,駛往30公里開外的牌樓村;車很臟,腳下是泥土,座椅上還有個西紅柿。為什么?難道已經向土地砸了近2億元的“京淼源”沒有一輛商務接待用車?后來才知道,“京淼源”真沒有商務接待用車。公司一共11輛車,都是生產用車,從陳號新到陳偉,公司所有中高層管理人員用車都是自己的私家車。
陳號新的私家車也是十幾年前的現代SUV,那臟得更過分,駕駛位腳下的泥土至少有1厘米厚。這車開起來,偶爾還會發出突突的震動聲,而每當發生這種情況,陳號新都要下車去查看一番。
不過,陳號新座駕的后備箱里卻非常豐富,有無人機,這是他隨時查看“領地狀況”的必備工具;還有兩個紙箱,一個裝著面包、干吃面、餅干、火腿腸等,一個裝著各色飲料。為什么?陳號新說,我們現在管理的這片土地,總面積很大,這里邊養殖、種植、水力、電力一應俱全,就算開車查看一圈也需要幾個小時,所以不能回家吃飯是常事兒,餓了就打開后備箱對付一口。
先來說說陳偉。他是1984年進京,成為中國第一代農民工。開始在北京建筑工地去昌平拉沙子,還當過裝卸工,后來在北京站附近找了餐館服務工作,因為他為人忠厚,勤奮好學,深得餐館老板賞識,于是變成了這位老板熟食攤兒、水果攤兒的“掌柜子”,一干就是十幾年,也算積累了不少的經商經驗,并積攢了人生的第一個10萬元。2002年,陳偉回到家鄉,入了黨、蓋了房,還在石澗鎮開了一家小餐館。但不久,牌樓村的村支書退休了,于是鎮里找到陳偉,讓他成為月薪300元的村支書。
陳偉的目標就是改變村里的貧困,他當書記的15年間,為村里辦了兩個“采石場”,不僅改變了村里的面貌,而且成為嚴橋鎮第一利稅大戶。但最讓他感到驕傲的還是:軟磨硬泡多時,把“京淼源”從鄰村的響山社區拉到了自己所在的牌樓村,并甘心情愿輔佐陳號新去成就一份鄉村全面振興的事業。

“京淼源”的田間水渠不用鋼筋水泥,而是“一層塑料膜+一層網”。
鄉村全面振興談何容易?首先就是要往土地里砸錢,應當怎么砸?應當砸多少?實際上,往土地里投入金錢就像個“無底洞”,而且都埋在地下,什么也看不見,真干失敗了,什么也別想拿走。從4月2日到4月8日,我在牌樓村的6天,經常和陳號新、陳偉一起下地,邊走邊聽他們講,實地去看“京淼源”節約成本的“黑科技”。
當然,首先是國家每畝地2700元左右建設高標準農田,這對陳號新而言,應當是最大的一筆成本節省,但按照陳號新的測算,真正建成數字化、智能化的高標準農田,一畝地至少需要投入7000到8000元,“但無論如何,政府每畝地投入2700元那是我們的幸運,大大節省了我們企業的成本”。什么樣的農田是高標準農田?指標很多,但從外行人直觀看,那些“水渠平直,土地方正,田邊裝有一盞盞‘捕蟲燈”,而原來田間亂架的電線也都被有序歸攏的種糧耕地,就是高標準農田的基本樣貌。
陳號新非常看重這樣的高標準農田,但也有個建議,他說:“如果讓我們這些實實在在經營這片土地的人去參與設計規劃,那高標準農田建設可以更省錢、更切實。”比如,高標準農田里的“水渠護坡”都是水泥筑就,但陳號新讓我看了“京淼源”田間的水渠,這里的“水渠護坡”根本不用水泥,而是“一層黑色塑料膜+一層藍色織網”,在坡頂和坡底被石子兒壓住。膜不透氣、不滲水,讓水渠坡面不長草、不坍塌;網為膜提供保護,增加護坡的強度。這樣的做法:第一,成本只是水泥護坡的1/10;第二,不用水泥,保護農田的原生態;第三,這樣的護坡可以使用6到8年,到時候揭去舊的、回收賣掉、換新的。
因為“膜+網”的成本很低,所以,建水渠一是不用像其他高標準農田那樣,為節約成本而將渠道刻意拉直;二是水渠的深度、寬度更容易因地制宜,而不必按照固定標準,從而進一步節約成本;三是“田埂的彎彎曲曲,水渠的千轉百回”會讓田野顯得更加自然,讓走在田埂上的人心情更加放松。
諸如此類,在陳號新的潛心琢磨下,“京淼源”的土地上到處都是節約成本的細節。目前,“京淼源”承租的土地面積還在不斷擴大,也正是這樣的擴張,無為市嚴橋鎮牌樓村附近的土地流轉價格幾乎翻番,從5年前的300元/畝·年左右,上漲到現在最低也得600元/畝·年。4月6日,陳號新和陳偉領著“京淼源”管理班子來到十幾公里開外的農場村,和農場村村支書陳永翠一起丈量土地,很快,農場村的4500畝土地也將流轉到“京淼源”的旗下。據說,“京淼源”接手這4500畝土地的成本應當在650元/畝·年。
我問:“這么貴的地你還能賺錢嗎?”陳號新的回答是:“放心吧,我算過很多次。其實這個利潤吧,要從咱的經營本事里去摳,而不是從農民身上賺。”
大投入中的大智慧
陳號新哪兒來的自信?其實,膽識源自5年的潛心研究。這其中,最牛的是陳號新自己摸索出的“蟹麥輪作”技術。目前,這項技術被無為市乃至蕪湖市各級政府盯上了,并期待技術盡早成熟、盡早普及。為什么?為了國家糧食安全。目前在中國,除18億畝耕地“紅線”不能突破外,中央還要求,以2018年為界,此刻形成的存量耕地,絕不允許繼續“非糧化”,而且每年至少要種一季糧食。
安徽蕪湖、巢湖一帶,因為瀕臨長江、河道縱橫、雨水豐沛、山泉流淌,所以這里的水產養殖業發展很快。但由于“耕地建塘”搞水產,耕地“非糧化”也在所難免。這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矛盾:一面是耕地“非糧化”政策的剛性,另一面則是當地農民希望通過擴大水產養殖增收。怎么辦?

一條路兩邊,右邊是“暫養”蟹塘,左邊是蟹塘種麥,上海海洋大學把這里當成了養殖基地。
無為市是個縣級市,作為市長的匡健自然會有許多“鬧心的事”,而一度最讓他鬧心的是國家政策堵住了“耕地養蟹”的路子。這事兒很麻煩,國家政策是為了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這是關乎國家糧食安全的大事。但根據現實狀況,如果把蟹塘恢復為耕地,農民收入必然大幅減低,結果很可能是種糧無利可圖的農民進城打工,恢復的耕地也會撂荒,國家糧食安全同樣無法保證。所以匡健非常著急,怎么辦?匡健在調研解決方案時,在“京淼源”停下了腳步,而吸引他的就是“蟹麥輪作”技術。所以他囑咐陳號新“務必盡快取得經驗,盡快能在無為推廣”。現在,匡健保持著“陳號新熱線”,密切關注著“蟹麥輪作”的點滴進展,而在陳號新看來,這項技術的成功概率很高。
什么是“蟹麥輪作”技術?當年,陳號新通過調研發現,按傳統的蟹塘養蟹,無為的畝產只有200多斤,但在蕪湖、江蘇、浙江,畝產一般都能達到300到400斤。“從產量上我們就輸了,肯定得賠錢。必須想辦法提高產量。”陳號新說。
陳號新研究后發現:第一,假如一畝蟹塘的合理養殖密度是2000只,按傳統方法就是按一畝2000只投放蟹苗兒,因為這是一畝蟹塘能夠容納成蟹的極限。但是,按照成蟹需求去投放2000只“五角硬幣”大小的蟹苗兒(術語稱“扣蟹”),實際非常浪費,而且“扣蟹”領地寬松會加大其跑動范圍,很容易折胳膊斷腿兒,導致死亡率上升。怎么辦?陳號新的辦法是:暫養。用過去1/10的蟹塘面積,把“扣蟹”大密度養起來,這不僅可以大大節省人工成本,而且“扣蟹”密度達到一定程度,它們會互相搶食,不僅節約飼料,而且搶食還能讓“扣蟹”鍛煉身體,吃得多、長得壯。
“扣蟹”養殖密度加大,90%的蟹塘空出來了,這個“空當期”完全可以有效利用。螃蟹一生要蛻五次殼,死亡風險最大的時間段是蛻去“三殼”之前,但蟹蛻“三殼”要到5月底、6月初。原本,這個“空當期”可養兩茬小龍蝦,一下就能增加許多收入。但“耕地非糧化”政策出來了,小龍蝦不能養了,那能不能種小麥?當然能,而且剛剛好。于是,陳號新用2018年之前形成的“合法蟹塘”實施“暫養”,等到5月底、6月初小麥收割后,再把麥田翻土、鋪草、放水養蟹。麥根翻出后留在蟹塘里,既能給土地漚肥,又為螃蟹提供了“麥根上的大餐——各種害蟲”,還因此凈化了麥田。
這樣的做法收益可以說“特別好”。
蛻去“三殼”的小蟹生命力已經大大提高了,這時再按一畝2000只投放,不松不緊剛剛好,死亡率大大減低。
蟹塘養蟹時,螃蟹把農田里的草籽、草根吃掉了,所以“蟹麥輪作”的耕地完全不用除草劑;同時,養蟹殘留的有機物肥沃了土壤,不僅底肥用量節省了2/3,而且整個小麥成長期也只需少量施肥,這使得小麥品質大大提升。
蟹塘里會有大量水草,怎么辦?割下來,扔進歷史上早已形成的魚塘里去喂養草魚。
當然,還有許多“黑科技”。比如,陳號新每天都要夜觀蟹塘,為什么?因為螃蟹夜里出來活動。那觀察什么?很多。比如,蟹苗兒吃飽沒有?他要依據觀察確定投料水平。陳號新車上除了泥、食物、飲料和無人機,還有三只不同光強度的手電,這是他夜觀蟹塘必備的工具。強光下,吃飽的螃蟹會在肚子上留下一條上下貫通的“黑線”,否則就沒吃飽。要分析沒吃飽的原因,是投料少了?還是投料位置不對或風向變了?跟著陳號新下塘的那天,發現螃蟹沒吃飽,不僅“黑線”不飽滿、不清晰,而且塘里的水比較渾,陳號新說,投料少了螃蟹爭搶食物,就會造成水渾。
再比如,陳號新研究發現,喂螃蟹的食料必須順著風向,往下風處投喂。為什么?因為風吹水面,浮游生物會跑到下風處,螃蟹也會跟過去。所以,投喂必須在上風處投10%,在下風處投90%,但如果投料后風向變了,那螃蟹就要餓肚子了。
還有就是水草。養蟹先養草,水草的養護技術決定養蟹水平的高低。為什么?螃蟹白天要躲在水草里,尤其是蛻殼時,沒有水草,螃蟹的殼就蛻不下來,就會死去。但水草又不是越密越好,密不透氣,水草會死,水質變壞,螃蟹也活不成;水草過疏,水質得不到水草的充分凈化,而且不夠螃蟹用,扎堆兒打架,成活率也會降低。還有就是,從遠處把水草運過來、種下去,也是不小的成本。所以,必須掌握科學合理的水草密度。
如此等等的“黑科技”,真有什么了不起嗎?我的體會是:農業科技或許就是這樣,它需要的不只是農肥、農藥、種子等研發,更需要有心之人執著于此,天天浸泡在田間地頭去潛心地琢磨。就像陳號新,他并未受過專門的農業科技訓練,但就像他所說,農業養殖、種植就像養孩子,他經常是按照對人、對孩子的體會去發現“喂養”的好方法。比如,“扣蟹”高密度“暫養”就是從養孩子的道理中得到啟發,一個孩子不愛吃飯,孩子多了搶著吃,搶著吃就吃得多;孩子小,活動范圍也要小,活動范圍越大,出事的概率越高。
打通產業鏈,練就獨門技
按照陳號新的總結,養蟹有四大痛點:種蟹太貴,買苗太貴,技術傳統,產量不高。如何破解這四大痛點?陳號新用了3年時間,親自帶著團隊去做。現在,“京淼源”的種蟹自己培育、蟹苗自己培育、不斷技術創新。
養蟹,解決蟹苗數量和品質問題特別重要。據了解,種蟹必須在海水里產卵,然后由卵孵出沙粒大小仔苗(術語稱“大眼幼體”),黃燦燦、麻渣渣。從“大眼幼體”長成“扣蟹”通常需要9個月的時間,之后才能放入蟹塘養育。整個過程中,死亡率極高,專業性極強,所以在養蟹市場上,“大眼幼體”的培育、運輸、銷售都是專業化的,等到長成“扣蟹”下塘的程度,專業戶就會把“扣蟹”拿到市場上售賣,江蘇“扣蟹”一般在25元/斤,無為本地“扣蟹”大約40元/斤,但每年價格不一,2023年“扣蟹”價格最高時可達60元/斤。
為什么不能買苗養蟹?我在“京淼源”了解到原因。“扣蟹”同樣是養在蟹塘里,如何捕撈?通常要下地籠。前一天晚上,在蟹塘里放上一條長長的地籠,用誘餌把螃蟹引進來,第二天早上提起地籠完成捕撈。但遇到“京淼源”這樣的養殖大戶,蟹苗用量巨大,售苗專業戶等不及蟹苗“自投羅網”,怎么辦?他們就會把一種藥撒進蟹苗塘,讓蟹苗拼命往岸上跑,然后捉了賣給養殖戶。
結果是什么?“扣蟹”放進蟹塘后大量死亡。更嚴重的問題是:把“扣蟹”放入蟹塘之后,養殖戶根本不知道多少“扣蟹”已經死亡,只能等到螃蟹成熟捕撈時才知道產量,比如江蘇“扣蟹”,其成活率一般只有30%到40%。
不僅如此,蟹塘還會引來大量水鳥,據“京淼源”測算,每年因水鳥侵襲而導致養蟹損失就高達300多萬元。問題是:為了保障產量,蟹塘就要及時補苗,但補苗時,“扣蟹”供應已近尾聲,貨少價高,而且品質無法保障。所以,“京淼源”必須構建“種蟹、大眼幼體、扣蟹、成蟹”全鏈條養殖。實踐證明,全鏈條養殖后,“京淼源”的“扣蟹”成活率可達60%。按照陳號新的說法:“我們打通這個鏈條,再想讓我賠錢都難了。當然,除了發生自然災害。”
該補多少苗?“暫養”方式也給了“京淼源”游刃的空間。第一,“暫養”密度大,憑經驗觀測相對容易;第二,采用高科技手段,也可以實現水下觀察;第三,自己培育蟹苗,充裕程度大大提升,不僅可以隨時給蟹塘補苗,而且補苗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再比如種蟹問題,以前“京淼源”要700多元一只從別人那購進,然后回來讓種蟹交配繁育后代。但現在,“京淼源”自己培育種蟹,一只種蟹成本只有70到80元,一下就把種蟹成本拉低了80%到90%。同時,為了避免種蟹“近親結婚”,“京淼源”就拿著自己的種蟹去遠方去易貨。比如,拿自己的優質公蟹去交換其他地方的優質母蟹,一只換一只,沒有價格問題。
說到農業產業鏈,最關鍵的還是銷售環節,但這恰恰是“京淼源”的長項。
如今,“京淼源”在北京、上海、遼寧盤錦等大中城市都設有銷售網點,自家土地上產出的一切基本上是有多少賣多少。為了提高種糧收益,也為了提高銷售渠道收益,陳號新的眼睛已經盯上了糧食深加工。但是,加工車間的廠房已經蓋好了,卻遲遲沒有購進設備。為什么?陳號新不急,在他看來,糧食加工屬于第二產業,而干好第二、第三產業的關鍵是要有雄厚的第一產業做基礎,尤其是第二產業。什么意思?陳號新的解釋是:沒有足夠的農業產量,銷售部門還可以進他人貨銷售,但第二產業不行,機器一開,原材料供應就必須源源不斷,沒有足夠的糧食供給,要么停工,要么買糧生產,但無論怎樣,虧損風險會成倍增加。
其實,陳號新認真調研過,他發現,許多認為種糧不賺錢而轉向糧食深加工的村鎮或企業,都會因為原材料供給短缺而使生產斷斷續續,質量和數量難以保障,最后深陷困局。
誰在從事田間管理?在牌樓村,在“京淼源”管理的土地,隨處可見的是郁郁蔥蔥的莊稼和充滿希望的蟹塘,但卻很難看到人。要找到那些田間地頭干活的人,一定要在公司管理人員引領下,在特定時間和位置上才能找到。為什么?我了解獲知,原來在這里,兩位70歲開外的老人居然管理著1000畝農田,而同樣年齡的老人管理蟹塘,也是兩個人管理40到120畝。
沒有年輕人嗎?沒有,年輕人都進城了。這讓陳號新非常頭疼,“京淼源”一些技術工作需要年輕人,但月薪8000元工資都招不來,他們寧愿6000元待在上海。那70多歲的老人能夠承受田間勞動嗎?現在看問題不大,因為“京淼源”實行了一套特殊的管理方式。
第一,“京淼源”按照不同地塊、不同專業分了26個生產組,有專門種桃種梨的、專門種麥的、專門種稻的、專門養蟹的、專門養魚的等等,每個生產組都有一兩個領頭人,對產出品的數量、質量負責;第二,所有養蟹、種糧、打理果樹都有什么時候該干什么、怎樣去干的標準化操作流程,由“京淼源”統一制定,由生產組領頭人負責嚴格執行;第三,種植養殖所需全部機械、物料等生產資料,都由“京淼源”統一供給,“京淼源”有專業保障團隊,保證“你要槍要炮,第一時間送到”。
那種植養殖過程中出現問題怎么辦?分清責任,全力補救。如果是公司流程或提供的物料有問題,那公司負責;如果是執行中出問題,那由組長負責。現在,“京淼源”向組長提供的物料、價格、用量等都是公開的,也都要經過組長們的確認;確認后再出問題,那就是操作問題了,不用公司懲罰,收成降低,肯定影響組長收益。所以,組長們不敢懈怠,更不敢馬虎,他們就好像“一線指揮員”,需要犁地,拖拉機就來了;需要播種、噴灑農藥,無人機就來了,7秒一畝。

環境監測設施
田間管理需要老人們自己動手的工作當然會有,但蟹塘工作相對要多,比如每天要定時定量投喂,必要時還得給水草施肥等;糧田工作就少多了,主要是定時定量澆水、觀察長勢、防范病蟲害等,而就算是這樣的工作,實際也已被田間“智能設備”完成,但老人們的種糧經驗非常重要,陳號新很重視,借鑒他們的經驗能讓“智能更加智能”。目前,為“京淼源”工作的老人,平均年齡超過65歲,最大年齡81歲。
還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無論如何種地都需要用工,那工從何來?老人們自己去找,他們十里八鄉的關系多,招工也來得方便。用工支出,按照公司認可的標準,由公司統一支付。
26個生產組組長一年下來如何結算?第一,按照公司要求,老人們完成標準化的規定動作,每月可以拿到3000多元的工資。第二,每個生產組都有自己的賬簿,一年用工的工資連同田間管理所用機械、農肥、農藥等一切費用按照公開價格計入成本。第三,產品出售時,糧食由公司按照當年價格全部收購;但螃蟹不行,它要用地籠誘捕,不是一天兩天可以撈干凈的,而且出售也需要時間,所以螃蟹收獲需要按照當日市場價格,逐步出售,然后記賬。第四,等到螃蟹大致都捕干凈了,開始結賬,首先是在所有銷售收入中扣除一年之間所有的生產成本,算出銷售利潤,老人們將從利潤中分享10%到20%的提成,原則是收成越好,提成越高。
比如,在“京淼源”有10個大棚,里邊種的是陳號新精心選育的一種很有特色的“圣女果——小西紅柿”,口感非常棒,果還沒采已經被預訂了,不夠賣。管理10個大棚的陳利軍就是一位古稀老人,他們每天要從附近村里請來五六位兄弟姐妹幫忙采果,日薪120元。實在人手不夠,陳利軍會向公司求援,從其他地方調人過來。“一個大棚一年能賺多少錢?”陳利軍回答:“10多萬吧。”那陳利軍能得多少?每月4000元工資,加上大棚凈利潤的10%提成。算下來,總也有15萬元左右。
“京淼源”現有26個生產組,每位領頭人一年算下來,差點的能夠收入10萬到15萬元,強點的能夠達到20萬到30萬元,最棒的可以達到50萬元;而其他那些“高齡小工”,除去土地流轉收入外,也能通過力所能及的勞動每年獲得3萬到4萬元收入。而且,那些收入較高的大戶,也會給兄弟姐妹們一些“犒勞”,目的就是“請您來年還跟著我干”。
田間管理到此為止?當然不是。現在,走在“京淼源”的田間地頭,人們會看到許多信息顯示器,上邊顯示著土地和空氣的溫度、濕度等;另外,在田間還能看到星星點點的簡易小屋,里面除了暫時存放于此的農具、農肥等,還有一個“電腦機柜和監視器”,它的作用是把“所在區域”的田間信息實時送往“京淼源”的中心機房,由此形成“京淼源”完整的數據采集和分析系統,幫助公司作出農田管理決策。
目前,“京淼源”需要重點突破的是:“蟹麥輪作”田間管理數字化解決方案。按照方案設計,“京淼源”正在完善“衛星遙感監測+無人機近地遙感監測+地面傳感器監測——空天地結合的立體監測體系,以此全方位、全周期采集“蟹麥輪作”期間的各種數據;同時搭建數據處理、多源融合的大數據平臺,并形成“可視化、科學化”田間監管體系。據陳號新介紹,他們的初級目標是為“蟹麥輪作”提供大數據決策系統和讓無為市各區縣形成多個數字化“蟹麥輪作”的千畝示范田。
我有不解,“蟹麥輪作”是付出巨大代價得來的獨門絕技,別人知道了都去做,那“京淼源”不就沒有優勢了?面對這個問題,陳號新沉吟良久,然后“怯生生”地說了句:“咱不得有點家國情懷嘛。”我又不解:“干嗎不理直氣壯地說?”陳號新說:“沒人信,還背地里說我唱高調。”
實際上,經過多年潛心研究、反復論證,“京淼源”現在已經有了很多專利技術,但陳號新并不打算獨享它們。他告訴我,申報專利只是為了證明這個技術是他們發明的,如果有很多人使用,那是他們的一份榮譽。他說:“英雄都是為榮譽而戰的。”
保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但是,京淼源的“頭等大事”并不是自己的事。因為養蟹的水一旦被污染,那對“京淼源”必定是滅頂之災。所以,陳號新對水源、水質的保護也算是煞費苦心了。牌樓村地處銀屏山南側一個極緩的緩坡上,直接的上游水源來自它背靠的銀屏山,山中泉水匯集成澗,流入三個小水庫——幸福水庫、響山水庫和牌樓水庫。這其間劃分兩段:第一段是一股山澗溪水直接流入牌樓村的部分蟹塘和農田,然后流入牌樓水庫;第二段是三個水庫繼續向下,為“京淼源”的另一部分蟹塘和農田供水,然后流入下游山澗,匯入永安河,直至入長江。

蟹塘上下游串聯以確保水質
也就是說,“京淼源”的田地夾在三個水庫之間,山水有節制地順流而下,為牌樓村附近的土地帶來不竭的生機,但關鍵問題是:如何能夠利用好、保護好這滾滾財源?
曾幾何時,陳號新必須面對的是“大片早已撂荒的土地”。在陳號新的手機里,我看到一組視頻,反映的就是他剛剛接手這片土地時的景象,干涸的農田、干涸的水渠里長滿荒草,一片凄涼。很顯然,陳號新必須改變這樣的狀況。怎么改變?重新規劃一切。除掉荒草、修復土地、通水接電,這需要巨額資金的投入。那些日子,陳號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釘在這片土地上,全憑后備箱里的那堆吃喝,辛苦自不必說,而整個過程中,最讓他費心的就是:水該怎么辦?
怎么辦?過程一言難盡,但現在看,一個完整的水循環體系已經在“京淼源”的田野里成熟了。首先是把所有的蟹塘用水串聯起來,山上和水庫流下來的第一股清水養蟹,然后通過特有的水草養護技術,既保持水質,又讓自然活水提升了螃蟹的品質。其次是蟹塘出來的水流入魚塘,魚塘里養了大量的花白鰱,而花白鰱吃掉了水中絕大多數的有機物。然后水再往下流,流入同樣被水串聯起來的稻田,水在稻田里一級一級地流過,進一步吸收了水中的有機物,最后流入牌樓水庫或山澗溪流。
效果如何?目前,牌樓水庫常年保持一類水質。我們來到水庫邊上,陳號新捧起水來直接喝。他說:“沒事,這水可以直接喝。”我的腸胃不好,自然不敢,但我確實看到牌樓水庫的水清澈見底,沒有任何一點富營養化的水藻。水面上,各種水鳥自由嬉戲;水面下,各種魚類歡快游弋。另外,牌樓水庫養魚一年只捕一次大魚,原因是:水庫里的小魚多了,水鳥吃飽了,就不去禍害蟹塘了。
“京淼源”水循環系統還有一個“絕活”,就是“反抽灌溉”。在天降大旱之時,“京淼源”會在山澗臨時“筑壩”,其實就是用“堆土+鋪膜”的方式臨時攔水,然后用水泵把下游的水抽到上游,再通過設計好的溝渠自然流回到山澗當中,如此循環往復,確保了蟹塘和農田流水不竭。所以,陳號新不僅非常關注上游水庫的水質,同樣也要關注下游山澗的水質,從而整體保證了清水匯入永安河。為水能保質保量地循環往復,僅僅2023年“京淼源”就投建了38公里設施。
實際上,京淼源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初期投資6000萬元,第一筆錢花在污水處理上,用的是“京淼源”第一大股東朱銘從日本學來的污水處理技術。現在5年過去了,每年朱、陳二人都會把商業上賺來的錢,以及農業種植養殖取得的利潤又向土地繼續投入,總體已接近2億元。
“人家一年能賺多少億,也沒見誰舍得這么往土地里砸錢,這錢砸進去,收回來得好多年。可你這一年也賺不了多少錢,干嗎不去賺點快錢?”“賺快錢?說實話,真能賺到快錢的人沒幾個正路子,所以賺了幾十億、幾百億就惦記往外跑,為什么?經不住查,一查就露餡,一露餡就沒了。我們不干那事兒,價值觀也不允許我們干那事兒,咱就老老實實賺點辛苦錢,能讓農民把我們當成英雄,足夠了。”
如今的“京淼源”人,愛護水就像愛護生命。而為了更好地保護水源,“京淼源”把銀屏山上幸福水庫、響山水庫周邊和流經區域的幾乎所有土地都流轉到公司名下,進行統一管理,盡最大努力保護這片綠水青山,并正在讓它變成越發沉甸的“金山銀山”。
說實話,我之所以開始這次調研,正是因為我從朱、陳二人身上嗅到了一股“中國資本應有的味道”。他們根本算不上什么富貴之人,更看不到任何奢靡浮華,甚至連一輛像樣的高檔轎車都沒有,但他們卻把辛苦賺來的錢砸向了土地,借重政策之勢、市場機制和一己之長讓土地長出更多財富,去和那些愿意勤奮勞動的農民分享,而且心甘情愿、樂此不疲,這會不會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中國資本應有且特有的那個“精神家園”呢?
(本文圖片均由《中國經濟周刊》首席評論員鈕文新攝)
責編:姚坤 yaokun@ceweekly.cn
美編:孫珍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