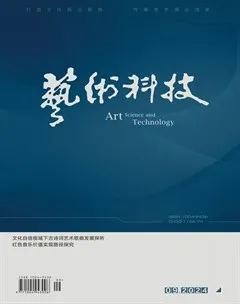新印象派作品中離散性表現的成因探析


摘要:目的:新印象派作品和數字成像有著相似的畫面組織形式,點彩表現的筆觸與像素一樣作為最基礎的離散單元構成整個畫面。這一離散風格的歷史成因在既往的圖像學研究中往往側重分析畫家創作的個人動機與繪畫史的前后關聯,尚未關注畫家的科學技術背景如何間接促成點彩風格的誕生。文章旨在通過數字技術脈絡分析這一表現風格的歷史成因。方法:文章從符號學和譜系學的角度探究新印象派作品背后的離散性成因。首先通過引入表象、失真的探討,區分新印象派作品中信息學和符號學的兩個維度;同時從符號角度分析離散表現的視覺性成因;最后從視覺性成因出發,探究從學院派到印象派再到新印象派的風格轉變中,筆觸作為一種媒介逐漸離散化的歷史性原因。結果:在“學院派—印象派—新印象派”的轉變過程中,承載信息的媒介逐漸離散化,其原因有三:第一,離散性媒介直接作用在人的身體層面,當時的人們逐漸意識到視覺的復雜性,用零散的筆觸構建畫面,迎合了這種認識;第二,創作者對表象的認識加深,同時其創作觀念受用數字表示世界萬物的畢達哥拉斯主義的影響;第三,技術的進步也為這種媒介的誕生提供了支撐,得益于化工化的顏料生產技術和標準化的生產工藝技術,工業化的顏料生產直接參與到新印象派的創作中。結論:在傳統的圖像學分析之外,譜系學視角強調促成離散性媒介誕生的權力和知識背景,從考察結果可以看出,新印象派中離散化表現的歷史成因分別在于生理、意識及社會生產三個方面,確實存在數字化的脈絡。
關鍵詞:新印象派;離散;表象;失真;譜系學
中圖分類號:J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4)09-00-06
0 引言
近年來雖然許多研究者關注到新印象派和數字成像之間的相似性,但研究目標卻各不相同:福本麻子[1]、劉曉巍[2]等研究者試圖運用計算機圖像的定量檢測去分析新印象派與其他流派在信息熵中存在的差異;羅賓·羅斯拉克[3]、加藤有希子[4]等另一部分研究者嘗試從文本和歷史的關聯性展開,探討新印象派作品的表現形式和意識形態的表達。出于研究目標的偏差,前者往往關心像素的應用等技術層面,沒有分析新印象派的各種歷史成因;后者往往從圖像學角度分析文本內容,形式分析缺乏信息科學理論的引入。二者從信息學領域或藝術學領域單獨展開,沒有從數字媒介的視角去審視新印象派作品的表現成因。
在當前的數字化背景下,歷史上美術流派的成因是否也存在數字技術的脈絡?要回答這一問題,有必要重新審視新印象派作品的表現成因,表現成因不僅涉及表現形式,還關乎表現形式背后的各種歷史推動力。思想史通常基于特定的時間線,試圖通過思想變化構建一個有邏輯的因果鏈。然而,與思想史的線性敘事不同,米歇爾·福柯在其“知識考古”中認為歷史文本是存儲人類知識和思想的片段,這些片段背后的知識和權力也如同地幔一樣斷裂著,歷史學者應該像考古學家那樣去發掘斷裂層中未被記錄的、隱藏在黑暗中的無限的歷史事實[5]。數字化表現僅僅是新印象派的一個側面,為了避免“新印象派作品僅代表數字表現”的敘事邏輯,從表現的相似性反推到表現背后的媒介技術、知識與思想成因時,需要警惕這些成因會自覺構建數字化的脈絡。因此,本文借用符號學概念分析視覺成因,僅從譜系學角度片段地考察表現的成因。
對于點彩畫和數字成像而言,筆觸和像素皆作為相互獨立又相互關聯的信息單元,二者“若即若離”的表現形式可以用離散性來表示,如離散數學中自然數在數軸上僅代表一個點,離散性就是這些局部間斷且整體連續的數值所反映的特征。實際上,當下如“8-bit”“像素風格”等數字藝術運動并非僅僅源于數字化浪潮,而是在數字媒介誕生前就已存在,從龐貝古城的馬賽克瓷磚到數字的像素,離散單元作為一種媒介,貫穿于視覺藝術的表現史。厘清新印象派作品的離散性問題,可以為回溯美術的表現史提供新思路。
在視覺上,點彩表現隨著畫面遠近距離的改變產生了不同的視覺感受,這種離散性表現的視覺體驗和真實世界有何關系,同時受這種真實感影響,離散性表現在傳達意義上和其他表現形式相比有何不同?實際上,隨著數字化社會中媒介的不斷融合,信息傳輸方式涉及媒介和符號等多個維度,所以本文旨在通過這些維度探究離散性表現的視覺性成因。
從壁畫、卷軸等無法復制且難以傳播的古代媒介形態轉向印刷媒介時,原先連續的內容被均分到每一個離散的頁上;印刷媒介向數字媒介過渡時,紙面上的內容進一步被均分到每一個像素。被劃分為均等單元的離散信息,以模塊化的形式讓傳播更高效。數字媒介是現今離散化程度最高的傳播工具,這一離散化進程是何時開始的,是否與現代性特征有關?首先,近代自然科學將人體視為一個可以測量、解剖和研究的物理實體,身體成為可被量化的對象;同時,宗教的祛魅和世俗化進程中,近代理性主義逐漸重視邏輯、分析和計量,促使以數字為宗的畢達哥拉斯主義回歸;最后由定量思維引導的生產分工化作為近代工業化的一部分,提高了生產力的同時也分解了生產流程。所以,作為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初的藝術運動,新印象派作品的離散性風格作為歐洲近代化的線索,其誕生受更深層次的歷史因素的影響。基于這樣的假設,本文嘗試以新印象派作品為研究對象,探討離散性的歷史性成因。
為了回答離散性的視覺性和歷史性成因,本文第一節通過論述可以投影現實的表象,引入真實性中的“失真”問題;第二節進一步通過失真現象解釋現實中的混沌信息在文本化/秩序化過程中存在信息學和符號學這兩個維度;第三節通過融合這兩個維度,用具體案例分析像素和筆觸作為離散性媒介的視覺成因;為了探究視覺成因背后的歷史性成因,第四節以視覺性成因為線索,從身體的內視現象、現代化中的畢達哥拉斯主義以及顏料生產的工業化三個角度進一步探究成因的譜系。
1 投影現實的表象:從“真”到“失真”
除了物理媒介之外,構成畫面的基礎單元也可視作一種媒介,液晶屏幕顯示的像素構成整個畫面,人在讀取畫面文本時并不會關注液晶屏幕,大腦為了讀取文本忽略了物質性媒介。帶有筆觸的作品在印象派之前就已經存在,但印象派誕生之后,筆觸的功能大大增加,成了再現作者腦內圖景的媒介。
在學院派的作畫方式中,用一層層透明的淡彩去疊加上色的技法被稱作“罩染法”,作為印象派之前的主流作畫方式,這一技法可以不留痕跡地塑造真實圓潤的過渡,采用罩染法的學院派畫家們極力避免讓筆觸出現在畫面上,他們追求將一個對象再現成一個完整的客體,為了讓畫面上的物體看起來和現實一樣,他們不得不去追求圓潤自然的過渡色。畫面上是否有筆觸痕跡作為衡量畫家個人繪畫能力的一個標準,畫面上出現筆觸會被斷定為這幅畫作處于尚未完成的狀態或畫家是個初學者。然而在印象派出現后,隨著物理光學的進展和管狀顏料的發明,描繪對象轉移到戶外,原先的景物和模特作為先驗的對象消失了,描畫對象的存在與否對于畫家而言并不重要,畫家只關心描畫對象的顏色如何投入視網膜上。印象派將描畫的對象由原來現實中的具體某一客體,轉向眼睛所看到的色彩。這種轉向源于人們逐漸意識到人眼及其聯動的神經組織作為外界信息的接收器官,并非真實可信的,自己看到的“真實”景象僅僅是腦內生成的“表象(represention)”[6]。
這種表象可以追溯到勒內·笛卡爾在《屈光學》中的論述,他用解剖的眼球模擬暗箱裝置的結構[7],以此證明眼球作為機械的器官區別于可以思考的大腦[8]48,然而在笛卡爾之后的視覺研究及神經科學研究皆指出眼睛并不是孤立于身體之外的,人看到的畫面也并非由單一的視覺器官產生,大腦的運作也參與其中[8]98。或者說,眼睛觀察到的“真實景象”,終究是腦內生成的圖景。從功能上講,當這個包含各種身體組織的視覺生成體系脫離機械性時,或者說不再被簡單看作一種視覺生成的“工具”時,這一體系就不可信了,這也是印象派所關注的:當眼見不一定為實的時候,古典主義式的再現真實就顯得徒勞無力了。照相機發明之前,繪畫作為記錄工具仍然受畫家的主觀性影響,但攝影技術成功地將畫家個人因素排除在外,攝影機器作為一個裝置成了更可信的記錄工具。這也就是說,記錄流程是否被人為干擾,是否具備機械性,決定了記錄的內容是否真實可信。
實際上,攝影機器塑造真實的可信性不僅源于機械地記錄,還源于膠片上的銀鹽感光顆粒足夠細小,離散的感光顆粒難以直接用肉眼觀察到,三維世界投影在二維平面上時,觀察者通常會忽視二維畫面的離散單元。而當數字照片放大至馬賽克時,原本真實過渡的表象被破壞,觀察者意識到眼前真實的圖景僅僅為像素矩陣構建的表象。
因此,離散單元通過隱藏自身將觀察者的注意力誘導至真實的幻覺中,而離散單元的暴露會使幻覺破滅,真實變得不可信,從“真”到“失真”,是離散單元從隱藏到被發現的過程。
2 失真的兩個維度:表象的離散化與抽象化
失真不僅是離散單元的暴露,還與畫面是否寫實有關,“真”的評價也源于人們對視覺對象的價值判斷,源于人們可否從具象/抽象的圖像中識別出真實信息。所以是否“失真”還需要從信息學和符號學兩個維度解答。
“模擬”最早是電子學中的一個名詞,如光、溫度、聲音等在自然界中各種連續的波,通過傳感器檢測并被轉化為電信號后,就在導體內得到代表自然現象的電信號,這樣的電信號被稱為模擬信號。電子學領域的這一名詞也被人們用于媒介學中,如紙質報紙、電影膠片等被稱為模擬媒介。“數字”一詞從字面意思上理解,“digital”本身源于拉丁文“digitus”,意思是“手指”,用于計數。區別于模擬媒介,數字媒介上的信息可被標記和計算,數字媒介相對于模擬媒介帶有可編輯性。尼爾森·古德曼從認識論角度列舉數字中可計量性和離散性的含義,他認為當模擬鐘表表盤上的秒針從數字1滑向2時,其表示的是一個時間帶的流逝,而數字時鐘顯示屏上的顯示從1跳到2時,表示的是“1”和“2”的兩個瞬間。模擬時鐘通過指針指示數字來表示時間,且對時間的判斷總是帶有誤差,而數字時鐘通過直接顯示數字來表示時間,意味著數字媒介本身是由數字構成的,不需要人為判斷便可得到精確的計量結果。同時,數字媒介通過時間帶的兩個端點來表示整個時間帶,實際上省略了中間無數個時間點[9]。與坐標軸上的自然數一樣,這種標記性使連續的整體被采樣為一個個獨立的數值點。所以,諸如膠片中的感光顆粒、屏幕中的像素作為信息單元相互孤立且連續的表現形式,可分別看作模擬媒介和數字媒介中的離散單元。
回溯數字技術的發明和對符號的探討,這種離散化的表象實則包含現實世界中混沌信息的兩個秩序化方向。二者都揭示了原始信息若要作為一種可交流的符號系統,信息的規律性傳輸至關重要。模擬媒介中用于交流的必要信息摻雜了電流的噪聲,為了秩序化地輸出這種混沌的信息,克勞德·艾爾伍德·香農提出信息熵的概念,并通過定量的方式用一個基礎單元去消解混沌信息中沒有價值的部分[10]。費迪南·德·索緒爾認為一般的自然語言文字需要一個特定和公認的符號指代實際交流中人們表達的事物,能指為代表事物的符號,而所指代表符號背后的對應物[11]。
比較自然語言和計算機視覺的符號系統會發現:如同包含噪聲和有價值聲音的能指被不斷簡化,而所指信息不斷特化一樣,當一張月亮的攝影照片先被簡化成寫實繪畫的月亮,接著簡化為卡通形象的月亮,最后簡化為甲骨文的象形文字時,符號的能指被不斷簡化,而所指被不斷特化。抽象化之前的現實圖像,如同數字化之前的連續信號一樣,信息處于最真實且最混沌的狀態,而無論是自然語言還是計算機語言,都基于一個確定的語法結構秩序化地輸出信息。
因此,表象的離散化與抽象化皆可看作符號系統生成的過程,也是現實中混沌信息秩序化的過程。作為判斷真實的兩個維度,當表象過于離散或抽象以至于無法讀取真實信息時,圖像就會“失真”。
3 離散性表象的視覺成因:能指的平均劃分
這兩個維度如何塑造了離散性的表現呢?新媒體學者列夫·馬諾維奇在論述數字電影成像時提出,“現代媒體中的離散性單位,跟詞素所具有的意義單位并非一回事”[12],減少離散單元的數量(降低分辨率)會使畫面損失大量表現上的細節與多樣性,干擾意義的解讀。這一點在梅雷迪思·安妮·霍伊的著作《從點到像素的數字美學譜系》中也有具體的描述。
霍伊認為,修拉根據尚未竣工的埃菲爾鐵塔繪制了作品《埃菲爾鐵塔》(見圖1),其低分辨率的視覺感受反而將鐵塔頂端尚未完工的部分補完[13]59,鐵塔頂端的色點和周圍的色點融為一體,仿佛塔尖在霧氣中若隱若現,這種模糊的處理手法淡化了鐵塔尚未竣工的事實[13]59-61。然而,如果不提示尚未竣工的信息或不了解修拉本人的創作背景,觀賞者并不會認為鐵塔不完整。這種模糊的感受反映了意義傳達的“精確性不足”問題,當筆觸本身成為一種計量單位時,計量單位內部的統一性就掩蓋了更精確的意義傳達,觀賞者只能看到朦朧的影像和色彩感受,并不知道具體畫了什么。物理作品一旦數字化,混沌的信息必然秩序化地輸出,這使得信息的特征發生了兩種改變,一是原始信息不可逆地損失;二是“精確性”問題只能通過像素單元的無限增殖來解決,即當可計算、可測量的數位點陣模型被投射在屏幕上時[13]62,若要保持其信息的精準,則不得不用更多的像素單元去表示。
圖1 喬治·修拉《埃菲爾鐵塔》(1889年,木板油畫,24.1×15.2厘米)
屏幕形狀決定了像素外邊緣(frame)的形狀,分辨率決定了像素外邊緣大小。與像素不同,筆觸的外邊緣(frame)由創作者確定,且難以精準控制物質材料,《埃菲爾鐵塔》的筆觸并非同像素一樣在形狀、大小上完全統一并連續精準地排列在一起,如膠片上的感光顆粒,這一“非平均劃分”的特征體現了新印象派并非完全意義上的數字化,它只能被看作修拉試圖將表象離散化的嘗試。即筆觸和像素都是視覺上的離散單元,且成因可以通過結構語言學中的能指和所指這對基礎性概念來解釋。
一個句子拆分成多個字和詞時,字詞與其背后的含義仍然相互對應,如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一樣,這些傳統的結構主義的思維都是按照事物的特征將整體劃分成若干部分以便更好地理解事物,且能指與所指的對應關系即使在劃分后也沒有被破壞。而離散單元在形式上完全統一,難以單獨構成完整意義的同時,通過自身有限的信息與其他基礎單元相互組合后可以構成完整意義,成為構成內容的基本元素。因此,筆觸和像素的相同點在于二者區別于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傳統,能指被無差別地劃分,能指與所指的對應關系被強行打破。能指的劃分并非以所指為標準,而是按照人為創造的信息單元為標準時,被平均劃分得來的單位便是離散的。
綜上,《埃菲爾鐵塔》中描繪鐵塔的筆觸數量可被大致統計出來,雖然鐵塔形象因為分辨率問題產生失真效果,但這一形象終究被平均劃分為離散單元,能指與所指的對應關系被強行打破。
4 從視覺成因到歷史成因:“學院派—印象派—新印象派”時期的譜系學考察
在《道德的譜系》中,尼采通過“譜系”這一概念追溯和解析道德觀念、價值判斷和道德規范的歷史發展,揭示它們背后的權力關系、心理狀態和生理條件。尼采反對那種將道德視為永恒不變、普遍適用的觀點,他認為道德具有歷史性,是在特定的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下形成和發展的。“譜系”在尼采的著作中,指的是一種歷史深度分析,旨在揭露道德現象背后的復雜根源和動力機制,而不僅僅是對道德現象的簡單羅列或分類。福柯繼承其中的譜系學范式,并在《監獄的誕生》中通過“譜系”這一方法追溯和解析權力運作、知識形成和主體性構建的歷史發展,揭示它們背后的社會結構、心理技術和身體實踐。福柯反對那種將權力和知識視為中立、客觀存在的觀點,他認為權力和知識是在特定的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下形成和發展的。在福柯的研究中,“譜系”指的也是一種歷史深度分析,旨在揭露權力和知識現象背后的復雜根源和動力機制。
對于歷史的歸因,譜系學的范式并不關心歷史事件中的個人選擇。探究歷史事件的成因,需要考慮當事人的生理、心理狀態,權力、知識的社會關系,以及經濟生產、媒介技術發展的背景。因此,新印象派點彩風格的成因,并不應拘泥于傳統圖像學研究對畫面信息的描述,相反這一風格的誕生與歐洲在工業化時期的生理現象認知、意識形態、生產技術密切相關。
“學院派—印象派—新印象派”并非作為獨立的事件線性地排列在時間軸中,三個流派的作品在歷史中平行交替出現。所以,本節以符號離散化的邏輯順序為中心,將這三者共時的歐洲近代化過程為對象,命名為“學院派—印象派—新印象派”時期。同時,區別于史學還原歷史真相的目的,譜系學研究質疑歷史文本背后的客觀性,試圖揭示這些話語權力體系背后的知識和權力運作機制。本節在論述離散性媒介的成因時,避開新印象派歷史上所記錄的直接原因,盡可能還原科技、社會及意識形態等方面促成離散性媒介形成的權力和知識背景,尋求離散性媒介形成的潛在因果關系。
像素或者筆觸作為承載信息的單元,也可以被看作承載信息的離散性媒介。媒介的特征主要體現在生理、意識及社會生產三個方面:第一,外部信息通過眼睛傳入大腦被觀察者所認知,在信息流通的過程中,身體與媒介的關系被普遍認識;第二,作為統一所有像素的信息維度,分辨率決定了像素媒介的幾何特征,筆觸在“學院派—印象派—新印象派”這一變化過程中逐漸離散,不僅源于作者本人的創作意圖,還源于西方工業化時期的意識形態;第三,色彩提供了使像素媒介可以區別于周圍像素的渠道,顏料生產技術的進步也促成了新印象派的離散性表現。
4.1 內視現象:離散化表象的生理學發現
最能體現表象和新印象派作品相關性的就是赫爾曼·亥姆霍茨的“內視”研究:區別于眼睛看到身體外部的圖景,內視可以在眼部結構層面觀測到身體內部的畫面。當在黑暗的房間中蹲久了或眼球視網膜遭到機械壓力時,視覺神經會錯誤地以為是光來了,產生“眼冒金星”[14]213-215的感覺。而這些游動著的“金星”實際上是懸浮在眼球玻璃體溶液中的微粒和斑點等,這些微粒組織結構如圖2所示,也暗示著與新印象派作品一樣的點陣結構。這一科學發現(1856)雖然不能和點彩的創作動機直接關聯,但這一現象早已被人注意到。喬納森·克拉里在論述觀看者與觀看對象的主體/客體關系時具體考察了亥姆霍茨的“內視”研究[14]374。對于克拉里而言,這種觀看方向從身體外部移至身體內部的現象對于修拉作品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將神經中的電信號作為信息,則眼內閃爍著的“金星”就如同承載信息的媒介一樣游走于人眼的視覺畫面中,這些視覺神經的顆粒雖然并沒有真正構成整個視覺表象,但作為離散的單元暗示人們觀察到的整個表象都可依此單位均分的可能性。
圖2 亥姆霍茨所觀測到的內視現象
4.2 畢達哥拉斯主義:幾何特征的離散化
自印象派誕生之后,色彩的分裂便開始取代色彩的融合,并在新印象派的作品中走向極端。新印象派自我宣稱的分色主義(Divisionism)一詞意味著,雖然對象是顏色,但更重要的是以何種形式分離這些顏色。如同分辨率一樣,畫布的大小和筆觸的大小構成面積上的對比,二者面積比的相對變化也可看作分辨率的變化。因此,從學院派的沒有筆觸,到印象派中塊狀、線條狀的筆觸,最后到新印象派的點狀筆觸,這一標準化的過程可以被看作畫家逐漸意識到分辨率的存在,并試圖提高分辨率的過程。
筆觸的出現和細化并非憑空而來,許多學者都試圖解釋新印象派這種機械冰冷的創作觀念。受數字思維的影響,修拉的作品如同被機器分析處理生成的一樣不包含任何感情。在喬納森·克拉里看來,這種冰冷的分析是用如同數學矩陣一樣的現代式定量思維[14]164對傳統視覺經驗進行祛魅。針對修拉的作品,克拉里在關于審美的現代性的注釋中解釋道:畢達哥拉斯派的主要論點支配了現代科學[14]164-166,即自然應該以數和數量關系來解釋,數字是現實的本質。可計量的觀念貫穿整個現代化過程,成為提高可信度的手段,受此觀念影響的新印象派畫家用點狀筆觸來計量所見之物,不僅創造了一種新的視覺語言,還在信息的傳遞形式上創造了新的媒介。
4.3 顏料的工業化:色彩的離散化
如今像素早已不是16色或32色,而是可以表現更豐富的顏色。雖然不斷細分的像素顏色相較于早期變得更加豐富,但每種顏色仍由固定的數值來表示,和像素一樣,畫布上一個單一筆觸的背后也被標示了具體的顏料生產型號,新印象派將工業顏料不經調和地點在畫布上,讓每一筆被數字標示的顏色表現在作品中。
早期印象派可以在戶外創作的原因便是管狀顏料的發明,除了顏料容器之外,顏料本身的工業化也和印象派有關。如信息的采樣一樣,手工顏料的生產工藝被工業化生產替代時,畫家使用的顏料也逐漸被離散化,具體表現如下:一是作坊并沒有能力精確控制生產的顏料都是一樣的,相反,由于標準化生產,人為原因出現差錯的概率大大降低,產品隨機產生色差的概率也降低了;二是相比于傳統的天然材料制作工藝,近代化學工業能合成純度更高的顏料,這種顏料的顏色飽和度更高,所對應的數值更精準[15];三是根據色相、明度、飽和度三個維度繪制出梯度色彩圖表,不同數值對應不同的顏色[16]。如果顏料生產線只有紅、黃兩種顏色,想要生產橙色就不得不新建一條生產線,生產線生產兩個相鄰顏色之間無數種變換的中間色是不可能的。這種對光的等比例采樣和科學劃分是工業化流水線生產顏料的前提,當顏色信息按照具體生產規格確定下來后,生產的顏料相對于原始的無數種顏色都可被看作采樣與壓縮后的信息。
自然界中無數種顏色本身作為連續的信息,在化工等學科的幫助下被采樣、壓縮和量化,最后成為離散且相互區隔的顏色。印象派將這些離散的顏色在調色盤上混合之后畫在畫布上,新印象派則將生產線中采樣過后的顏料直接點在畫布上,工業化的顏料生產本身就干預了點彩的實際創作,甚至可以看作創作的一部分。
5 結語
近距離觀看新印象派作品的視覺感受和遠距離不同,圖像“失真”的過程是離散單元從隱藏到被發現的過程,這意味著新印象派的點彩風格不僅包含符號及其意義的維度,還包含符號被重構的信息學維度。通過平均分割能指符號,打破能指與所指的對應關系,得以重構為可統計、可量化的離散單元。
本文從信息學、符號學及媒介學角度研究離散性表現的問題,但僅僅依靠基礎理論無法深入研究這一課題。同時,如龐貝古城的馬賽克瓷磚藝術、針織掛毯藝術等表現形式一樣,離散性特征并非僅存于油畫這一特定的表現形式中,更不會僅存于“學院派—印象派—新印象派”這一特定階段。如果將此階段孤立于美術史的發展脈絡中,不利于從過去到未來更全面地研究、發展離散化問題。正因如此,這一不足也是將來可以繼續延展和討論的空間,為美術史研究提供數字化的新視角。
參考文獻:
[1] 福本麻子,塚田浩二, 蔡東生,等.繪畫的色彩信息的復雜性與規律性的統計分析[J].圖像電子學會志,2005,34(4):311-318.
[2] 劉曉巍,普園媛,黃亞群.繪畫視覺藝術風格的量化統計與分析[J].計算機科學與探索,2013,7(10):942-952.
[3] 羅賓·羅斯拉克.審美和諧的政治:新印象主義、科學與無政府主義[J].藝術公報,1991(73):383-385.
[4] 加藤有希子.新印象派的實用主義:勞動·衛生·醫療[M].東京:三元社,2012:48-50.
[5] 米歇爾·福柯.權力的闡釋[M].嚴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06.
[6] 伏飛雄,李明芮.再現或表象:representation漢譯爭論再思考[J].南寧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41(6):1-9.
[7] 勒內·笛卡爾.笛卡爾哲學著作集:第1卷[M].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5:166,686-687.
[8] 喬納森·克拉里.觀察者的技術[M].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90:48,98.
[9] 尼爾森·古德曼.藝術的語言[M].印第安納波利斯:哈克特出版公司,1976:159-160.
[10] 克勞德·香農.通信的數學理論[J].貝爾系統技術雜志,1948,27(3): 379-423,623-656.
[11] 費爾迪南·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高明凱,岑麒祥,葉蜚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93-95.
[12] 列夫·馬諾維奇.新媒體的語言[M].車琳,譯.北京:后浪出版社,2020:89.
[13] 梅雷迪思·安妮·霍伊.從點到像素:數字美學的譜系[M].新罕布什爾州:達特茅斯學院出版社,2017:59-62.
[14] 喬納森·克拉里.知覺的懸置:注意力、景觀與現代文化[M].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2000:213-215,164-166,374.
[15] 約翰·豪斯.新繪畫:印象主義1874—1886[J].伯靈頓雜志,1986(128):704-705.
[16] 拉塞爾·約翰.塞烏拉[M].倫敦:泰晤士河與哈德森,1965:17-47.
作者簡介:杜若飛 (1993—),男,博士在讀,研究方向:數字成像技術與視覺藝術史、設計學以及視覺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