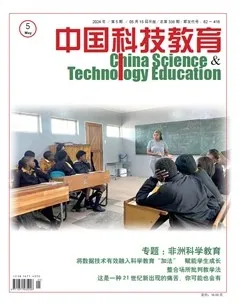這是一種21 世紀新出現的痛苦,你可能也會有
黑將軍



不愿意讓冰山融化的人
艾爾伯特是一名50 歲的登山愛好者,他從年輕的時候就喜歡攀登家鄉的一座雪山。但是這座他最喜歡的山受到了氣候變化的影響,其上的冰川正在加速融化消失。
“我幾乎看不到以往那種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的冰山了,我所能看到的只是消融。”在他看來,沒有冰川包裹的山是赤裸且丑陋的,他沒有辦法接受這種失落的風景。
漸漸地,艾爾伯特對于冰山的關注越來越多,在這一過程中還感受到了悲傷、痛苦、深深的焦慮,他羞愧于自己曾經不那么愛護環境。極度的痛苦甚至會觸發他強烈的內臟疼痛。
艾爾伯特認為,自己的以往已經與冰山建立了連接,現在他自己的一部分也隨著冰山的消失而消失了。在望著登山的舊照片時,他甚至有一種想家的感覺。
鄉痛癥是什么?
艾爾伯特并非特例。這種因生態環境惡化引發精神痛苦的現象越發常見,使得學者們開始使用“Solastagia”一詞概括它。這個詞中文翻譯為“鄉痛癥”或者是“環境憂慮”,最早由澳大利亞哲學家阿爾布雷特(Glenn Albrecht)于2003 年提出,定義為:“由于看到或想象到氣候變化或工業影響對自然世界造成不可逆轉的退化或損害,而引起的精神痛苦。”
鄉痛癥并非杞人憂天式的情緒困擾,原因在于生態環境變化引發的災難確實越來越多。
例如,世界氣象組織(WMO)已經確認,2023 年是有氣象記錄以來,人類歷史上最熱的一年。
溫度的升高伴隨著極端天氣和災難的頻發。21 世紀的前20 年,極端高溫事件增加了232%、洪澇事件增加了134%、風暴事件增加了97%、山火事件增加了46%、干旱事件增加了29%。
耶魯大學2018 年的調查顯示,69% 的被采訪者擔心氣候惡化,49% 的人認為這會傷害他們的個人生活。這種對環境厄運的慢性恐懼讓越來越多人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憤怒、焦慮、擔憂、悲傷等情緒,人們開始意識到自己深愛的家園正在遭受侵害。
面對這些巨變,除了鄉痛癥,人們還可能感受到生態悲痛(ecological grief)、生態焦慮(eco-anxiety)等一系列復雜情緒。
鄉痛癥屬于生態悲痛的一部分,所有的生態損失(物種消失、被迫改變生活方式等)都可能引發生態悲痛。
相比于指向過去和現在的生態悲痛,生態焦慮則是指向未來的、對人類文明與地球生態將何去何從的焦慮與擔憂。
總體來說,這些新詞匯的提出都是為了解釋同一件事——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將會以怎樣的方式影響人類的身心健康。
哪些人更容易有鄉痛癥?
對于環境的惡化,絕大部分人都會產生負面的心理感受,但是有些人受影響更為明顯,所承擔的風險也更高。
首先是與自然環境保持密切關系的人群,關系可能是工作、生活或者文化上的,比如農民、林務人員、土著居民、戶外運動愛好者等。這一類人更容易對特定的環境產生依戀,有的甚至會把這種依戀作為其身份構建的一部分,正如詩歌中所提到的“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生活在北極地區的因紐特人(Inuit)就存在著更為廣泛的生態焦慮。他們的居住地隨著冰川融化而不斷減少,年輕人不能夠再像父輩那樣在原住地建造自己的房屋。賴以謀生的狩獵和捕魚技術也因為獵物的驟減而失去用武之地。生活在大小興安嶺,與馴鹿相依為命的鄂溫克人,被稱為“中國最后的狩獵者”。他們也普遍顯示出了對原住地的依戀,以及對生態惡化的擔憂。
同樣的,因為直面氣候變化的機會更多(比如臺風、海岸侵蝕、農業用地鹽堿化等),沿海居民比內陸居民更關注生態風險信息。不過,也有研究顯示,強烈的居住地依戀可能會降低沿海居民對生態危險的感知,他們可能會以否認回應,也就是將生態惡化視為遙遠的、近期不可能發生的事件,以此避免鄉痛癥的產生。
其次就是社會經濟地位處于相對弱勢的群體。研究顯示,有殘疾的人、老年人、婦女兒童更不能接受因為環境惡化而背井離鄉,因為對于他們來說,居住環境的變遷往往意味著更多現實的挑戰。比如,在洪災中這部分人也更不愿意撤離到安全地區,即使他們知道繼續留在災區可能會喪命。
還有一些研究顯示,不同文化背景下(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人們對于環境的依賴也會有差異,一般來說,集體主義更易催生對環境的依賴,患有鄉痛癥的可能性也許就會更高。另外,本身就存在心理健康問題的人,更易受到與氣候災難有關的焦慮和情緒障礙的影響。
對外界環境保持警醒讓人類得以進化,但是現在這種對于環境惡化的敏感卻讓這部分人倍感痛苦。這份敏感從何而來?是刻在基因中對于大自然所產生的本源性的恐懼。
面對生態焦慮,我們可以怎么做?
想要減少生態焦慮,可以先嘗試轉變認知,比如我們可以試著不再將災害簡單地視為“敵人”。
英國杜倫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學仁(Chris Courtney)在《龍王之怒》中考察了中國長江洪水的歷史。他認為,洪水是自然風險,但是它是否擁有更多破壞力與致災機制(the Disaster Regime)有關。
致災機制涵蓋了將自然風險轉化為災難的基本因素,包括糧食保障和公共衛生、人居建筑和防洪設施的完善程度、政局動蕩、戰爭沖突、救災官員的腐敗等,它們可能會加劇洪水導致的破壞,甚至比洪水更加致命。也就是說,自然風險是客觀存在的,而人類的活動可能引發乃至擴大自然風險。
所謂天災人禍,在腐敗混亂的環境中,人禍比天災帶來的危險更大,甚至人禍會帶來天災。而在清明高效的社會里,人類的努力則可以反過來減小災難帶來的損失,盡可能地保全人們的性命和財產。
此外,我們還可以試著跳出“人定勝天”和“聽天由命”的二元對立,試著提前預測自然并“順其自然”。在《龍王之怒》中就提到,早在晚清,魏源等思想家就發現,“如果不是由于人類對環境的深刻改造,氣候不可能引發如此災難性的洪水”,當“人與水爭地為利”時,洪水就不可避免,因此需要為江水保留一些天然洪泛區。
如今,我們也可以在發展的同時,嘗試與自然和諧共處,既不過分追求改造與馴服自然,也不過度限制農業生產與工業建設,而是找到生態保護與發展的平衡點,為未來的人類留下一個更有希望的家園。
最后,要看清生態焦慮與生態悲痛的積極意義。適當的壓力和焦慮可以促使人采取行動,比如一些人能夠化悲痛為力量,以實際行動改變和對抗可能的環保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