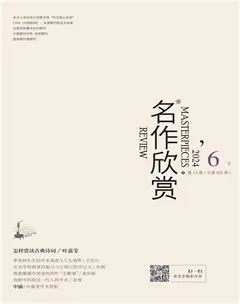北宋學校教育的振興與王荊公的學記文(上)
朱剛
我覺得在寧波講王安石非常有意義。王安石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改革家,他的很多改革思想形成于他早年在寧波擔任地方官時期。就他的改革措施來說,可能更多是屬于財政、軍事方面的。財政、軍事當然是他作為一個國家領導需要處理的主要內容,所謂“富國強兵”,就是指財政、軍事方面的改革。但是就王安石本人來說,在他個人的思想里面,財政、軍事之上,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新型的內容,是教育的改革。所以,我今天想談談教育。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講的教育是指學校教育。不是像孔子那樣,自己私人授徒的私學,而是官學。所以,我們首先要談一談中國歷史上公立學校的發展進程,對于北宋的教育改革來說,它是個背景;然后再談談王安石如何在他的一些作品里提出相關的思想,主要的分析對象是他的幾篇專門論述學校的文章,叫作“學記”;當然他提出來的觀點也不是被所有人都贊成的,他在當代就遇到了很大的一個挑戰者——蘇軾,我會對他們之間關于學校的不同思想加以分析。
學校的歷史與北宋的“興學”策
首先,我們從學校的歷史講到北宋的興學政策。如前所說,這里指的是官學,也就是公立學校。我們目前對于學校有什么樣的印象?這是一個人才培養的體系,從幼兒園開始,到小學、初中,接下來是高中,然后到大學。大學如果你讀得好,再上面還有碩士、博士,我們有這樣一套逐級上升的教育體系。我們現在對這個體系已經習以為常,這一套東西是近代以來我們從歐美不斷引進的,不是傳統遺留下來的。那我們傳統的學校怎么樣呢?我們無意貶低傳統的學校教育的歷史,但事實上,傳統的學校教育是圍繞著科舉考試展開的,其發展程度有限。我們平常在一些文藝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兒童會去學校上學,但是比如說一個秀才,他基本上在家里溫習功課,不需要去上學。沒有為秀才繼續深造的公共教育,要深造必須自己去尋師訪道。
不過奇怪的是,如果進一步往上追溯,回到中華民族的經典時期,從儒家那幾本經典記載的情況來看,卻是另外一個面貌。經典里記載的學校教育,看起來是非常發達的。以《孟子·滕文公上》為例: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這里說,夏商周時期學校非常多,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而三代都有“學”,學校的種類很多。人們都可以到這些學校里面接受教育,受教育以后就能“明人倫”,可以成為“王者師”。類似這樣的記載,在經典里面數見不鮮,給讀者的印象是三代學校教育非常昌明。這些經典以前的讀書人很熟悉,所以對他們來說,經典記載與現實的反差很大:經典里學校教育很昌明,現實中只有掃盲班而已。
這個現象怎么解釋?因為經典記載的是上古時代的貴族教育,貴族只是社會最上層很小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是世襲制,你祖父、父親做什么,兒子和孫子繼續做什么,天生有機會擔任這個崗位,在擔任之前要接受一定的教育培訓。所以上古時期的這些學校,我們一般認為它是一個范圍很小的貴族教育場所,它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跟我們要講的公共教育,其實沒多少關系。不過,秦漢以來閱讀經典的人可能不是這么看的,在中央集權的國家(朝廷)建立起來后,人們會習慣從“公共設施”的角度去理解經典記載的學校。所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秦漢以后朝廷要負責建立一些公共設施,其中就包括學校。那么,古人讀經典的時候,他們的理解方式就與此相應,他們不是從貴族教育的角度去理解的,而會認為這里講的都是公共教育。
這樣,經典里面記載的一些貴族教育的設施被后人理解為公共性的設施,如此就造成了經典記載和現實之間的一個巨大反差:經典記載里面,上古的學校教育那么開明、那么昌盛,現在學校教育幾乎沒有了。那怎么辦呢?我們知道,儒學是傳統中國的指導思想,深受儒學思想熏陶的政治家會以解決這個反差為己任,想要去振興教育,恢復經典所記載的這種昌明的學校教育局面。所以這就造成了一個什么問題呢?中國歷代學校教育的發展,根本動力來自政治改革。并不是說社會上有多少人需要接受教育,朝廷為了滿足這個需求而設立學校,而是說,為了實現儒家的政治理想,有必要先從教育入手。
那么,作為政治改革的重要環節,依靠自上而下的政令來實施學校教育,就成為傳統學校教育發展的一個非常基本的特點。不是因為教育市場的需求而發展,而是作為政治改革的環節而發展,其振興動力是政令。具體來說,學校(官學)被興辦起來,首先是太學,就是中央的學校,這是漢代辦的,那個時候地方上還沒有官學。中央的太學先辦起來,被歷朝繼承,每朝每代都有太學。至于地方上的學校,要到唐代才開始辦,但起初也不是專門作為一個學校去辦的,而是下令各州建立孔廟(孔廟也是到唐代才在各個州建立),這孔廟會附屬一個教學機構,成為后來各州“州學”的前身。在唐代,這個附屬于孔廟的教學機構,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宋代以后,以孔廟的附屬學校為基礎,發展為各地的州學,比較大的縣還有縣學。這是基本的發展脈絡。
從這個發展脈絡里看,我們可以說“興學”是北宋的一個政治特點。這個“興學”歷程也顯得波瀾壯闊,大致可以概括為三次大規模的興學,就是范仲淹的慶歷興學、王安石的熙寧興學、蔡京的崇寧興學。三次大規模的興學政策,都是和政治上的改革,或者說與當時采用的一套政治主張相適應的基本國策。興學可以說是北宋的基本國策,從此以后各地就有了很多公立的州學、縣學。
舉個例子,歐陽修為家鄉江西吉州寫過一篇《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于今者宜何先……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后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
他寫得非常清楚,從慶歷三年的政治改革開始,皇帝召見大臣說,我們要進行政治改革,從哪個舉措開始呢?然后范仲淹提出了要搞教育,所以第二年三月皇帝就下詔了,“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學校里面的教授是朝廷的命官,進入官僚系統,于是“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歐陽修很感嘆了,他認為慶歷新政留給后世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各地都有了學校。在他的理解中,有了學校才會有“王政”,理想的政治。他引經據典說,古代“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古代各個社會層面,國家、城市、鄉黨、家族都有相應層級的學校,所以他說,上古時期學校那么多,為什么現在沒有學校了?接著說,“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這次慶歷新政,皇帝下詔讓我們辦學校,宋朝已經八十四年了,一個新朝建立八十四年了,才開始在各地興辦學校,好像有點遺憾,但是他也自豪:這個學校是咱們辦起來的!下面記得很清楚,吉州的州學是當年十月辦成的,不過它有個基礎,就是“州舊有夫子廟”,原來有個孔廟,在城之西北,州長李寬上任以后,把孔廟附屬的教學機構“遷而大之”,遷一個地方,找一個大一點的地方,“以為學舍”,辦了學校。還是從孔廟的附屬機構發展起來的。這是吉州的情況,其他各地的情況也大抵如此。
歐陽修這篇文章叫“學記”,是關于學校的記文。宋代這種學記非常多,某個地方辦了學校,就會請人寫一篇學記。因為興學是基本國策,學記就成為宋代非常有特點的一類文章。
“學記”文的源流與荊公的成就
我們追溯這一類文章的源流,可以找到更早的,唐代有一篇學記。唐代古文運動的先驅作者梁肅,是韓愈的老師輩,他在大歷九年(774)寫了一篇《昆山縣學記》。根據他的交代,這個縣學其實也是從孔廟的附屬機構發展出來的,“先是,縣有文宣王廟,廟堂之后有學室”,文宣王廟就是孔廟,廟堂后面有一個學堂,把這個學堂發展一下就變成縣學了。他還認為,作為文章類型的學記,以前也有人寫過,只不過不叫學記,“昔崔瑗有《南陽文學志》,王粲有《荊州文學志》”,他找到了漢魏時期的這兩篇文章,說這個就是學記的前身。
整個唐代,我們只能找到這一篇學記。宋代以后,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學記,范仲淹、歐陽修、曾鞏、蘇軾等名家都寫過學記。由于學校本身是孔廟的附屬機構,有的人寫的就不叫學記,而是叫“夫子廟記”或者“孔廟記”“文宣王廟記”之類,但是寫的內容差不多。這種“廟記”,重點往往不在廟,不去描寫孔子長得怎么樣,重點往往是寫附屬的一個學校,說明地方官有多么重視教育,老師有多么負責,等等,主要內容還是這方面。所以雖然叫“廟記”,實際上還是寫這個學校。王禹偁、梅堯臣、歐陽修、曾鞏、司馬光都寫過孔廟記。還有像蔡襄和韓琦,他們也是參與慶歷新政的,寫過幾篇“廟學記”,就是既記了廟,又記了學。這個名稱很有意思,鮮明地反映出那個時候的學校和孔廟是在一起的。
本來學校就是孔廟的一個附屬機構,我們通過學記、廟學記、廟記,再往上追溯的話,孔廟的那種記文,其實最早不叫“記”,而是叫“碑”,比如唐初時候王勃寫過《益州夫子廟碑》。因為孔廟很莊重,要用碑文來匹配,顯得偉岸和宏大。王勃的碑文寫得很長,這是駢文。古文有柳宗元的《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柳宗元和韓愈都寫過廟碑,有意思的是,韓愈寫的《處州孔子廟碑》,有的版本叫碑,有的版本卻叫《處州孔子廟記》。這大概可以看作“廟碑”向“廟記”過渡的一個例子。
我再簡單概括一下這一類文章的發展源流:開始叫夫子廟碑,后來叫廟記,為了強調附屬學校的功能,有時候叫廟學記,后來進一步突出學校,就叫學記。就是這么一個發展過程,其實一開始和孔子崇拜有關系的。在學記文的源流里面,我們可以考察王安石的一些學記成就。王安石留下來的學記一共有4 篇:慶歷七年(1047)《繁昌縣學記》、慶歷八年(1048)《慈溪縣學記》、治平元年(1064)《虔州學記》、治平四年(1067)《太平州新學記》。
前兩篇就是在寧波寫的,最有名的一篇是過了十幾年以后寫的《虔州學記》,是他母親去世以后,他在江寧府(現在的南京)守孝時寫的,最后一篇是《太平州新學記》,寫完這篇他差不多就要去主持變法了。《虔州學記》最有名,宋人經常提到這一篇,贊同王安石變法的人夸獎這一篇不用說了,反對的人其實也夸獎過這一篇,比如黃庭堅,他到眉山碰到吳季成,他說“眉山吳季成有子,資質甚茂”,吳家的孩子很喜歡學習,他說要鼓勵孩子好好學習,“故手抄王荊公《虔州學記》遺之”。他認為研讀《虔州學記》,能“講明學問之本”(黃庭堅:《跋〈虔州學記〉遺吳季成》),這個評價非常高。至于后代的評價,像明代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的時候,就說“學記”這一種類的文章,要以曾鞏和王安石為代表作家,他稱為“曾、王學記”,是最好的學記。“非深于學,不能記其學如此”,如果作者自己學問不好,辦學校這一套不熟悉,就不能寫出那么好的學記。他舉出來的代表人物就是曾、王,但我們現在看曾鞏的集子里,只有2 篇學記。曾鞏的集子叫《南豐類稿》,里面只有2 篇,他原來還有一部《南豐續稿》,失傳了,也許他寫過更多,但我們找不到。那么,王安石有4 篇,所以北宋的學記,王安石是可以作為一個當之無愧的代表的。
概覽這4 篇學記,可以看到兩個主題:一是孔廟與學校的關系問題,二是學校教育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即荊公的政教統一思想。下面我們分述之。
孔廟與學校
現在我們分析王安石的學記。之所以要講學校和孔廟的關系,是因為唐代以來,學校和孔廟本來就在一起,這是一個現實,也是王安石首先要面對的問題。他首先顛覆了把學校作為孔廟附屬的思想。他認為,學校是國家要辦的機構,孔廟辦不辦是無所謂的。你要祭祀孔子,最多在學校里面設一個節目,把孔子作為教育家祭祀一下就可以了。這樣看兩者的關系,是應該以學校為主干,而孔廟作為學校的附屬,他認為這樣是合適的。現在卻把孔廟作為主干,學校作為它的一個附屬品了,他認為這是違反禮教的。這就是王安石的學記首先要顛覆的一個話題,顛覆孔廟和學校的現有關系。
有關論述見于早期的兩篇學記——《繁昌縣學記》和《慈溪縣學記》。他講得非常清楚:
奠先師先圣于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于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于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圣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繁昌縣學記》)
他說,以前我們紀念教育家,只是在學校里面把他作為值得紀念的前輩進行祭祀,那個時候沒有孔廟。他指的是三代的時候,當時孔子還沒出生,當然沒孔廟。但是,現在很多地方只有孔廟,沒有學校,這不合古。他也從經典里面讀到,古代從京師到鄉邑,每個地方都有學校,大家在那里面學習,但是學生們要知道學問是從哪里來的,所以有祭祀先圣先師的做法,就是“釋菜、奠幣之禮”,表示我們不忘記先賢。應該說,對于早期的學問家的紀念是因為我們要學習,不是因為要紀念學問家所以我們要學習。“然則事先師先圣者,以有學也”,因為有教學,所以我們要尊重老師,不是因為要尊重老師,所以我們要教學。這個關系王安石說得很對。他說“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空子,吾不知其說也”,現在不辦學校了,整天拜孔子,不知道這個做法從哪兒來的,他表示不理解。其實這是明確批判唐朝興建孔廟的政策,反之,他要提倡興建學校的政策。《慈溪縣學記》更進一步,說現在“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于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以前天下都有學校,現在沒有學校,天下只有孔廟,里面建一個孔子像,要么弄一段木頭,要么搞一團泥巴,做一個孔子像出來,這個孔子像戴著國王的冕旒,就像國王一樣。孔子并沒有做過國王,為什么要這個東西?他認為這是模仿佛教和道教,“浮屠”就是佛教。在他看來,這個東西是違反儒家禮教的。你要紀念孔子,應該發揚儒學,辦一個學校,在學校里面立一塊先圣先師的牌位,不要搞一個孔廟建一個像,像拜佛祖一樣拜孔子。這是他的一個講法,當然這個講法有唐代以來興建孔廟的背景在里面。
唐代以來對于孔子建廟祭祀的活動,本來是作為國家的一個重視儒學的政策來做的,曾經也獲得了很多人的贊揚,譬如說韓愈寫《處州孔子廟碑》,說各種各樣的祭祀里面,只有三種祭祀是從天子到各個地方官都要做的,“通得祀而遍天下”。一是土地神,就是“社”,二是稻谷神“稷”,因為傳統中國是農業國家,所以稻谷神要祭的,三是孔子。這三個是天下通祭的,他對此是肯定的。宋代以后,很多人也跟著韓愈表示肯定。宋代古文先驅王禹偁的《黃州重修文宣王廟壁記》就引了韓愈的說法,講天下有三個“通祀”,社、稷和夫子廟,說明國家對此很重視,他是贊揚的。歐陽修的朋友尹洙的《鞏縣孔子廟記》也引用了韓愈關于“通祀”的說法。他們認為這是值得肯定的,他們沒有像王安石那樣否定孔廟。
那么,怎么會走到像王安石那樣否定孔廟的局面呢?王安石是個著名的“拗相公”,總愛說些跟別人不同的話,這是一方面。但無論怎樣特立獨行的觀點,都不是無緣無故就能產生的,我們還是要考察一下產生的過程。唐朝雖然在各個州建立了孔廟,有的孔廟也附帶一個學校,但是唐末五代,天下戰亂,很多孔廟被毀了,更不要說附屬學校了,然后北宋建立,天下趨于安定,各種公共設施也處在逐漸恢復的過程中。所以,我們從《全宋文》里面可以找到北宋早期的一些有關孔廟的記文,它們基本上來自各種地方志。譬如說,我們可以找到宋太祖趙匡胤時代的記文,一篇是劉從刈的《重修文宣王廟記》,寫于建隆三年(962),一篇是梁勖的《重修文宣王廟碑》,寫于乾德二年(964),記的都是長安的孔廟。長安是唐代的首都,那里的孔廟保存得比較好一些。然后到太宗朝,我們可以看到狀元宰相呂蒙正寫于太平興國八年(983)的《大宋重修兗州文宣王廟碑銘》,他寫了兗州(就是曲阜)的孔廟,那是孔子的家鄉,那個廟也被保護得比較好。再往后,可以看到王禹偁寫的《昆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柳開寫的《潤州重修文宣王廟碑文》、田錫寫的《睦州夫子廟記》等,從長安、曲阜被保存得比較好的孔廟,逐漸延伸到其他的州縣。看來,這個新的朝代建立以后,孔廟祭祀慢慢地恢復起來了。在孔廟祭祀恢復起來的基礎上,可能附屬學校也在恢復過程中,這時候不可能像王安石那樣指責孔廟,指責的話,學校就沒有恢復的可能了。
經過亂世后,百廢待興,有一個恢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件比較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三代皇帝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他親自到曲阜拜孔廟。他是下拜的,當時討論皇帝要不要下拜,宋真宗說為了號召大家尊重儒學,就下拜了。這在當時是一件大事:皇帝為了祭祀孔廟,親自跑到曲阜去了。實際上,他是去泰山封禪,回程經過曲阜,順便祭祀孔廟。但這件事影響很大,我們可以看到第二年就有徐晟《大宋真定府藁城縣重修文宣王廟堂記》、孫僅的《大宋永興軍新修玄圣文宣王廟大門記》,都提到了此事。皇帝的表率作用很大,從此以后孔廟的翻修形成了全國性的規模,各地的地方官,不管是州長還是縣長,只要有經濟實力,都會做這個事情,因為有中央政府的號召。實際上,比親赴曲阜更早兩年,宋真宗就下過一道命令,說孔廟里面必須有個學校,不能只是孔廟,這就是所謂的廟學。我們看景德四年(1007)楊大雅寫的《重修先圣廟并建講堂記》:
大學士王公欽若上言:“王者之化,由中及外。古之立學,自國而達鄉。今釋菜之禮,獨盛于上庠;函丈之教,未洽于四海。興文之代,而闕禮若斯!”上以其言下之有司。去年詔天下諸郡咸修先圣之廟,又詔廟中起講堂,聚學徒,擇儒雅可為人師者以教焉。
這里說“去年”,就是宋真宗在景德三年(1006)便下達了詔令,其來源是大學士王欽若的建議。王欽若因為和寇準關系不好,經常被看作一個奸臣,但這里引了他的奏章,建議立學。他說“古之立學,自國而達鄉”,以前從國家到鄉鎮都有學校,這個是經典里面記載的,成為他們發言的根據。現在呢,“釋菜之禮,獨盛于上庠”,上庠就是太學,中央的太學里面已經在祭祀孔子了,但是“函丈之教,未洽于四海”,其他地方還沒有學校。他向皇帝提意見,然后皇帝詔令:“天下諸郡咸修先圣之廟,又詔廟中起講堂,聚學徒。”就是說,既要復蘇孔廟,又要復蘇學校。
這個詔令對于北宋官學的發展起到了鋪路的作用,因為孔廟的附屬學校就是后來州學、縣學的前身。有關曲阜孔廟的史料,曾經被匯集在一本書里,叫《孔氏祖庭廣記》,這里面就保存了一篇碑文,題為《景德三年敕修文宣王廟》,就是根據宋真宗的上述詔令,中書門下(宰相公署)發了一個敕牒,傳達到地方上,被刻成這個碑文,那上面還有當時宰相的簽名。中書門下的敕牒都有那天值班的宰相簽名的。景德三年的這個敕修命令,里面也說“依王欽若所奏施行”,根據王欽若的建議修孔廟,建講堂。
曲阜這么一搞,其他地方就跟上了,我們現在能找到一篇《改建信州州學記》,講到“景德三年春二月,詔修天下夫子廟祀,今上樞八座太原公之請也”,太原公就是王欽若,因為王氏的郡望是太原,所以叫他太原公。離我們比較近的余杭縣,當時也有一篇《余杭縣建學記》,作者章得一是地方官,他響應號召建一所學校。這兩篇的題目都只說“學”,實際的工程是先修孔廟。但是要注意,所謂“咸建講堂”,這孔廟是包含學校的。按章得一的表述,“加王者之袞冕,建都邑之祠宇”,把孔子的形象塑成一個王者,在各地的孔廟進行祭祀,這是“唐室之舊典也”,是唐朝的規則;而我們本朝的規則,是要有講堂的,這是“圣朝之新制也”。宋朝的特點是要有講堂,就是孔廟必須附帶學校,他認為這是進步的地方。這樣一來,景德以后“廟”和“學”這兩個東西一體化了,甚至產生了一個詞——廟學。
歐陽修的朋友余靖(1000—1064)是這方面留下文字最多的人,寫了4 篇學記,3 篇“文宣王廟記”,一共有7 篇與廟學相關的文章。他是王安石的前輩,比王安石大二十一歲。在余靖的筆下,我們可以看到“廟學”幾乎是一個詞,如“舊有廟學”“廟學草創”“廟學既成”等。可見宋真宗下詔以后,廟、學基本上一體化了,只要修了孔廟,如果遵從朝廷的命令,就應該附帶一個學校。而且,余靖對廟學關系這個問題也有反思,其《洪州新置州學記》說:
三代之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黨遂所居,必有庠序,釋菜之奠,其來舊矣。蓋孔子之道,萬世師表,故黃唐氏尊之以王爵,奉之以時祀,而禮用祭菜。夫祭菜之義,本于太學,存廟而廢學者,禮之失也。
他也是從三代之制,就是經典的記載講起。那時候大家都意識到,經典里面有那么繁榮的學校建制,為什么現實當中那么少?他對照經典,要求改革。方案上,當然先繼承唐代的孔廟,然后把孔廟附帶的學校發展起來。不過他強調:“存廟而廢學者,禮之失也。”如果只有孔廟,沒有學校,就不符合禮教。這樣的說法,是不是和王安石的觀點有相似的地方?
所以,到真宗、仁宗朝,逐漸地,你可以看到對于廟和學關系問題的反思了。原是依托孔廟發展學校,學校逐漸多了以后,大家意識到學校應該比孔廟重要,怎么會只是孔廟的附屬部分?于是有這樣一個反思。這種反思,在早期,其實也曾導出另外的意見。王安石說孔廟違反禮教,是對佛教、道教的模仿,這東西不好,但是也有人提出的意見正好相反,比如景德元年(1004)孫昱《重修文宣王廟碑》就說,連佛祖、道祖都有寺觀,為什么孔子不能有廟?面對同一個問題,大家反思,會有不同的意見。不過,把孔子搞得像宗教教主那樣,在崇拜和祭祀中會產生巫化的傾向。梅堯臣記錄過這種巫化的現象,他是王安石的前輩、歐陽修的朋友,有一篇《新息重修孔子廟記》,就是給新息縣翻修的孔廟寫的記文,說“予思昔忝邑時”,“見邑多不本朝廷祭法”,“往往用巫祝于旁曰:牛馬其肥,癘疫其銷,谷麥其豐”。這個愿望很好,但是孔子應該不管這些。巫師到孔子、佛祖和道祖面前都是這么說的,這就是基層組織的祭祀,就干這樣的事了。
如此一來,問題就比較大了。所以王安石寫學記的時候,一開始便講孔廟和學校的關系問題。他講這個問題,在他的時代,當然有了一個新的條件,那就是我們講的慶歷興學。慶歷興學的詔令下達于慶歷四年(1044)三月,詔令說:
諸路州府軍監,除舊有學外,余并各令立學。如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若州縣未能頓備,即且就文宣王廟或系官屋宇,仍委轉運司及長吏于幕職州縣官內薦教授,以三年為一任……
諸路(相當于現在的各省)的州、府、軍、監,這些都是北宋的州級建制,相當于現在的地級建制,除了本來有學校的,其他都要建立學校。這一點是明確的,以州政府的名義來建立學校,不再說先修一個孔廟,在孔廟里附屬一個學校。這個是州級政府要建學校,詔令是明確的。然后是州下面的縣級,考慮到教育市場,如果你有兩百人以上受教育的需求,你可以建縣級的學校。但是后面又加了一句,說“若州縣未能頓備,即且就文宣王廟”等,如果你辦不起來一個獨立的學校,那還是在孔廟后面附屬一下。可見,它的改革力度也不是很堅決。更有力的措施倒是后面一條,就是地方長官推薦教授,“三年為一任”,這句話很重要,這個教授本來不是官,但是地方官可以推薦教授,這個教授當了三年以后,可以被授予別的官職,進入官僚組織系統。這很重要,這一點對于北宋人來說太重要了:除了考進士以外,又有一條路可以當官了。科舉是一條路,學校又成了一條路。我們現在感覺不到,但是對于北宋讀書人來說,那可是非同小可的一道詔令,你考不上進士,如果你有學問可以當教授,然后你就進入了干部群體。確實,慶歷興學有非常創新的內容,但是它留了一個口子,某些地方如果不具備條件,你就照舊,還是在孔廟后面附一個學校。
王安石寫學記,對詔令有直接的反應。《繁昌縣學記》說:“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為。”他說宋朝跟著唐朝做孔廟附屬的學校,還不能改,到現在的宋仁宗下詔,才說天下的州都可以立學。注意,不是必須,而是可以立學,“皆得立學”。有了學校之后,學校里面要有紀念孔子的設施。他理解的學校和孔子的關系就是這樣的,以學校為主,學校里面有一個孔子紀念堂,他認為這是符合上古禮制的。這其實是他自己的觀點,慶歷詔令里并沒有明確這么說,而且詔令還留了一個口子,沒有完全改過來。《慈溪縣學記》里也有相應的內容,提到了兩百人以上有受教育的需求才能建立縣學的規定。王安石對此表示不滿,他說慈溪縣因此“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可能一直湊不滿兩百人,就長期沒有學校。浙東是文化比較發達的地方,但縣里一直沒有學校,一直只能辦孔子廟。所以王安石對孔廟的批判,有這么一個源流,我們梳理出它的來歷,從宋初到慶歷,在這樣一個過程中,王安石產生了這個思想,就是要擺正孔廟祭祀和學校教育的關系。
慶歷興學以后,我們確實可以看到,在某種程度上說孔廟和學校的關系倒過來了,對學校更重視。從一些有文化水平的士大夫來看,從慶歷以后的作者來看,在他們的觀念中,確實學校和孔廟的關系倒過來了。慶歷四年曾易占(曾鞏的父親)寫了《南豐縣興學記》,慶歷五年范仲淹寫了《邠州建學記》,慶歷六年遠在四川的張俞寫了《華陽縣學館記》,這些記文的關注點都從廟轉向了學。其實他們面對的還是廟學,因為很多地方沒有由州政府直接辦學校,還是讓孔廟承擔這個功能,但是作記文的人無不強調學。他們面對廟學,但寫出來的文章叫“學記”,而不是“廟記”或者“廟學記”。不管怎么說,這種對于教育的重視,是慶歷興學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