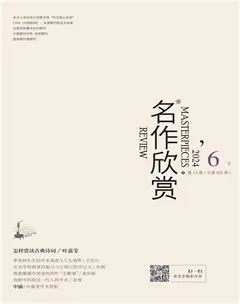文學的“文化”化與文化的“社會”化
袁先欣
根據我自己一點有限但不一定準確的經驗,現當代文學學科是特別喜愛反思、特別具有危機意識的。從我讀大學時接觸現當代文學開始,“重寫文學史”“學科危機”就一直是縈繞在耳邊的話題。當然,危機意識強并不一定意味著學科已經走到窮途末路,可能恰恰是其內部仍然保有著活力的表征。與反思學科危機一體兩面的,正是對重大問題的不斷追索。如果危機意味著舊范式的窮盡和極限,那么新的重大問題,也正呼之欲出。
過去三十年來,現當代文學經歷了幾次大的研究范式轉折。第一次發生在新時期,革命中心敘述模式被視為超越和批判的對象,“重寫文學史”由此濫觴。在“重寫”的浪潮中,出現過諸多提法和對文學史敘述模式的嘗試,但核心問題仍然產生于與時代主題的共振之中。20世紀80年代,“現代化”成為籠罩中國的重大問題,到90年代,努力“現代”自身的嘗試則被更多元、更具批判性眼光的“現代性”議題所替代。但總的而言,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一直延續到21世紀初,何謂“現代”、如何“現代”的問題,構成了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核心。當主導性概念從“革命”轉移到“現代”,也隨之帶來了文學史敘述框架、文學評判標準的巨大變化,這一現象已為今日學界所熟知,無須多贅。但值得注意的是,“現代”這一關鍵詞,因其內核的紛繁甚至互斥,并沒有真正提供一個穩定的敘述框架。正是在這樣的局面下,出現了多種“現代”話語的互相競逐,文學史不斷被“重寫”,絕難定讞。
當然,主導性范疇的開放、不穩定,不能說是一件壞事,從研究和討論的角度,這恰恰給出了爭鳴的空間。關于“現代”定義的不同理解,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回到歷史現場”的風氣,正是由于“現代”范疇本身的多義性,使得研究者不得不更切實和細致地去體察歷史發生的原初場景,而不能滿足于僅從理論出發的提示。但另一方面,我們仍然可以觀察到,圍繞著“現代”的種種文學史敘事模式,其實仍然有一個共同的、未曾言明的背離對象,即此前圍繞著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展開的新文學范式。在這個意義上,看似包羅萬象的“現代性”,仍然是有固定方向和確定邊界的。
從我個人的理解,過去十多年來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中國道路”等提法,包含了一個對新時期以迄21世紀初的現代化—現代性主題的反思,從而預示了一個新的范式轉折,其中的關鍵,是對中國革命的重新認識和評價。近年來,歷史研究領域重新出現了對革命史重視的趨勢,在現當代文學領域,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是左翼文學、延安文藝、“十七年文學”研究在沉寂多年后,再度成為新的學術熱點。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回到之前的取向和方式,借助更多元的理論資源和對革命史的多角度開掘,這些領域本身也呈現出遠較此前的敘述更豐富、生動的面貌。大量作家、作品、文學現象得到了更完整的關注,其所內在的歷史語境也得到了更多層次和更細膩的呈現。
但是,或許由于這場轉折仍在進行之中,我們同時也可以觀察到,前一個范式所遺留下來的某些思維定式和前提,仍然不經意地留存在新的研究思路之中,從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論題的方向和展開。20世紀80年代以來,與文學史敘述基本框架的調整相伴隨的,還有對“文學”的重新界定,從而強調個人獨創性、重視審美經驗的文學觀念得到確立。如果說,這樣的文學觀念的燭照,使得一大批此前在高強度的政治標準下被忽視的作家和作品重新受到重視,那么它也同樣包含著新的“排斥”機制,許多從前被認為是經典性的作品,現在則被目為“政治性損害了文學性”,其文學史位置發生下移。除了某些經典作品評價的升降外,更重要的恐怕是集體創作、重視口頭性和表演性而非書面性的大量作品和文學現象,在這一框架當中被放置到了邊緣性的位置——而在新時期之前,它們往往處在文學史敘述的中心。在這樣一種文學慣性的主導下,新的對左翼文學、革命文學的研究,仍然很大程度地集中在某幾個主要作家和他們的主要作品(尤其是書面文本作品)之上。
然而,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重新理解現當代文學與中國革命的內在關系,本來就要求我們有一個更開放的“文學”視野。在此,我希望提出的第一個話題,是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文化”化。所謂的“文化”化,是指我們應當將現當代文學的發生放置在一個更廣闊的文化運動的場景當中。在另一篇關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筆談當中,我曾經提出,如果現當代文學始終無法放棄“五四”作為其關鍵性的起點,那么這也意味著,現當代文學的某些“基因”正是經由“五四”來奠定的。事實上,“五四”開創了文學和文化成為廣義的文化運動戰線之一部的一個傳統,作為運動的文學和文化所改變的,不只是思想和情感,同時它也參與改造社會的實踐,這樣一種從思想文化到實踐的雙向運動,是20世紀中國革命最核心的特征之一。如果我們仔細去觀察30年代的左翼文化運動,不僅會發現左翼文學的蓬勃,左翼文人與政黨成員身份的重疊,而且也會看到文學與電影、美術、音樂等其他藝術門類的聯合,甚至文學與社會科學的互相呼應,從而文學并非孤立地,而是作為一個廣大的文化運動的一個內在部分,深刻參與了中國革命的進程。到了延安時期,這樣一種文學與其他文化類型之間的聯動與交叉,更推動了從單純的“文學”走向“文藝”,綜合性的“文藝”對“文學”的替代,不僅指示著文學藝術類型之間的互動、綜合與邊界消融,而且也指向了新的創作和審美原則:美術、音樂、舞臺表演等類型訴諸視覺、聽覺或綜合性的藝術感受,相較于以文字為載體、以識文斷字為前提的精英式“文學”,“文藝”無疑是更屬于復數的人民的。在這個意義上,延安文藝對集體性、人民性的強調,必然帶來對口傳文藝、民間文藝等一系列類型的重視。在共和國文藝當中,這些特征和方向,無疑也都保留甚至進一步放大了。
在最近的兩篇論文中,洪子誠老師提及了當代文學當中的“戲劇中心”和“去蘇聯化”問題。前者討論的是20世紀60年代戲劇超越書面文學成為共和國文藝的中心a,后者圍繞的是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國文藝路線對蘇聯式的精英化、專業化方向的批判和反駁,從而新民歌運動鼓勵工農群眾參與文學創作,要求作家深入生活、參加勞動等主張和實踐,構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脈絡b。如果從文化運動的角度,也可以說,正是在一個運動的機制中,才可能理解在文藝生活的重心從文字中心朝向更具有情緒聚集和動員能力的表演中心的轉移。而如果在精英化、專業化的蘇聯模式之外,共和國文藝更具特色的一脈是由去中心化與大眾化的傾向來支撐的,那么缺乏了綜合性的文化運動的視野,也必然會制約我們對現當代文學的整體面貌和內部邏輯的正確把握。從這個視角來看,盡管現當代文學已經經歷了幾十年的“深耕”,但仍然有大量未得到充分開掘的空間和具體的研究議題。
在文學的“文化”化基礎之上,我想提出的另一個主題,是文化的“社會”化。文學成為廣泛的文化運動的一個部分,從而也必然帶來另一個方向上的結果,文化深度參與了20世紀中國革命對社會的重塑,“文化”與“社會”的相互關聯,因此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化史、思想史乃至革命史、社會史均不可避開的一個重要主題。如果說,從20世紀中國文化生活本身的形態內部,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走向社會”的強動力持續存在,由此產生出大眾化、與群眾結合、重視口頭性和表演性等一系列特征與要求,那么從一個更外部的角度,文化未嘗不是在20世紀改天換地的進程中,重新塑造和結構“社會”形態的力量。
這種對社會的塑造是多層次的,而從我個人比較有限的理解,可能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文學、文化,包括廣義的思想討論,為把握社會的形態、構造提供了基本的認識框架和理解范疇。從時間線來看,“五四”提倡“為人生的文學”,到左翼文學摹寫大眾和社會,再到40年代之后文藝創作與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等主題的密切結合,一直存在一條強有力的從文學、文化角度來觀察和透視社會的線索,文藝創作摹寫和呈現了社會不同層面的狀況,塑造了一般人對此的基本認知。從主題上來看,階級話語、鄉村中國、民族等范疇是分析與理解中國社會內部構造的重要認知工具,它們的傳播與應用,當然并不是僅僅由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來完成的,而且是由多重、反復的文化辯論與論戰,由文學、藝術、學術討論、革命實踐等不同要素之間復雜的互動與往返來共同推動的。
在思想和認知的層面之外,隨著革命的深入,文化生活本身也被組織到社會改造的進程之中,這是中國革命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面。土地改革、農村合作化、工業改造等諸多重要話題在文藝作品當中被濃墨重彩地呈現,本身就說明了文化與社會的革命性重組之間的有機聯系。延安對舊藝人的改造,不僅是抓取某種民間文藝的類型并加以提高,而且也包含著將此前被歧視、被排斥的“邊緣群體”重塑為新社會人民主體的含義,文化從而扮演了“翻身”和“翻心”的雙重功能。封芝琴婚姻案被改編為說書、郿鄠、評劇等多個文藝種類中的劉巧兒故事,這是由社會改造的新人新事而進入新文藝的典型案例,新鳳霞在扮演劉巧兒的過程中,受到劉巧兒/封芝琴追尋婚姻自主的激勵,也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則顯示出文藝反過來傳播和內化了新的社會倫理,使得讀者/觀眾/演出者成為這一改造過程中的主動參與者。當工人、農民都大規模投入民歌、故事的創作,寫作家史、村史、社史、廠史時,這里蓬勃的不僅是新的文藝和歷史類型,更是人民大眾書寫自我的權利和豪情。盡管一定程度上,上述案例和現象已經受到了文學、藝術、歷史研究者的注意,但如何從一個更總體和綜合的層面理解文化運動在革命和社會改造中承擔的功能和作用,還沒有得到清晰的表述。
最近,在革命史領域和現當代文學領域,引入社會史的視野和方法、與社會史結合,構成了一個共同的趨勢。即便不考慮社會史研究過去在學術方法和議題上的積累,對革命史和現當代文學形成的刺激與啟發,僅從20世紀中國革命所造成的社會變革的強度和廣度,這一趨勢也是應當且必要的。但如果回到文化運動本身在社會改造進程中所發揮的多重作用,這一趨勢似乎不能單純地停留于借用方法和成果,從文學研究者的角度,似乎更應提出,文化的要素和實踐如何塑造了革命之后的社會形態?如果傳統的社會史更強調長時段和延續性的視野,那么在20世紀革命的疾風暴雨中,恐怕恰恰是眼光朝向未來的文化,提供了有關“新”的想象和可能,而經由文化與社會改造的實踐之間的緊密配合,這些設想也進入了千家萬戶的日常。從這個角度來看,現當代文學的意義和空間,還遠遠沒有窮盡,許多重大問題仍然在涌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