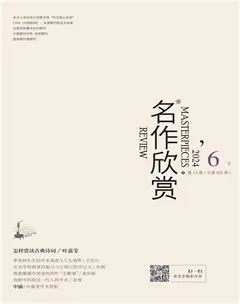“近一點,更近一點”
金理
當李浴洋兄賜來約稿函時,我正沉浸在《細節(jié):一部離作品更近的繪畫史》中,自春節(jié)迄今,法國藝術史巨擘達尼埃爾·阿拉斯的這部名著一直置于案頭,甚至不忍心讀完,在腦海中一遍遍想象“近一點,更近一點”的觀畫方式。1850年8月10日,為了觀看藏在安特衛(wèi)普博物館的魯本斯《十字架上的基督》,德拉克洛瓦當場借來一把梯子,在湊近畫面的過程中,終于發(fā)現(xiàn)抹大拉的馬利亞的“眼睛、睫毛、眉毛和嘴角是在下面的涂層還沒干的時候直接畫上去的”。在那個時代,“把臉像貼到一朵花上那樣貼到畫面上”,或者“把鼻子埋在一幅畫兒里聞來聞去,一連好幾個小時”的觀看方式極為流行。謝林則對此嗤之以鼻,因為“在真正的藝術作品中,個別的美是不存在的,唯有整體才是美的”,他對繪畫提出“最終的和最高的要求在于:它只是把握最美好的、最必要的、最本質的,而擯棄偶然的、多余的”。古典主義繪畫理想反對“細節(jié)的暴動”:首先,當目光獲得“飄蕩的自由”進而偶然駐足于“無關緊要的局部”時,就可能破壞畫面,拆解開隱藏于其中的“句法、意群、銜接方式和整體意圖”,在這樣的時刻,細節(jié)瓦解的是古典再現(xiàn)的全部秩序。其次,觀者必須在一定的距離上觀看繪畫,“這條具有重要理論價值的原則是扎實地構建虛幻三維空間的基礎”,而一旦離開“視點所在的位置”,趨近畫面,觀者將看到“世界的邊框一個接一個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多樣性”。
我一邊醉心于細節(jié)“賦權”所獲得的自由,一邊忍不住驚懼:為什么我自然地對“細節(jié)的暴動”樂見其成?浴洋兄的稿約是要求直截了當?shù)靥岢鲂哪恐小艾F(xiàn)代文學研究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實在慚愧,我的感受是,我這一代人的學術方式已漸漸喪失迫近、追擊“大問題”的興趣、能力與視野(這個陳述無可避免地存在代言、誤解,所以只能不避纏夾,在副題中加入“我眼中的”)。《細節(jié):一部離作品更近的繪畫史》所演示的兩類不同的、經(jīng)營細節(jié)的方式,倘若提取其中的關鍵詞,恰恰相應于我學生時代所目睹的以及當下我也投身其間的兩類學術方式與學術風氣。前者是:整體構圖、匯總效果、透視能力、“世界的邊框”,細節(jié)的豐富性不凌駕于畫面的整體尊嚴之上;后者是:偶然、局部、特寫、多元、“飄蕩的自由”,把臉貼近畫面,“近一點,更近一點”……
接下來試著談談“近一點,更近一點”的學術研究所導致的兩個現(xiàn)象。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迄今各種版本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著作共有七百余種c。老師輩的學者幾乎每個人都有文學史寫作的實踐與理想。可是,“文學史的神話”很可能在我這一代的學人身上消歇。“如果我們把一九一七年以來的新文學史,比作一條濤濤奔流的長河,那么在詳細欣賞兩岸風光之前,須先做一全面性的鳥瞰:首先看清源頭,其次看看奔流的方向,然后再試行劃分階段。”——這是司馬長風在其《中國新文學史》導言開篇的第一句話,其心態(tài)之自信,眼光之宏闊,對研究對象的思考邏輯、歷史貢獻、所處時代狀況的全面洞察,以及在此全面洞察前提下一條信而有據(jù)的文學史脈絡,無不躍然紙上……可是,我這一代人對文學史寫作不感興趣,更根本的是,對上述知識生產(chǎn)方式不信任。話說回來,司馬長風式的文學史寫作仿佛拉開一段距離、獲得穩(wěn)定的透視點后再觀畫;相反,“把鼻子埋在畫里”,自然容易促成史料與考據(jù)的蔚為大觀。一方面史料的發(fā)現(xiàn)與整理固然成績斐然,但另一方面注意力只在材料的拼湊和領地的占有,“人人從事于造零件,作螺絲釘,整個機器,乃不知其構造裝置與運用”(錢穆:《〈新亞學報〉發(fā)刊詞》)。章太炎嘗謂“清朝一代能夠考史,而不能撰史”,“考史”滿足于材料的征集與考掘,而“撰史”則需要史家“通古今之變”的識斷與手眼。“文學史的消失”,以及一個漫長的“考史”時代的到來,是我觀察(預測)到的第一個現(xiàn)象。
同時消失的,還有壓在紙背后的現(xiàn)實關懷。我這一代人的學術,似乎總無法兼顧深耕細作與元氣淋漓。趙園老師是我素所尊重的前輩,她從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退到”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卻絲毫不見尋向故紙堆的保守,我每每在她那淹博的史料排列中發(fā)現(xiàn)文學的活潑與“事事關心”的寄托。比如她談黃宗羲:“在黃氏,正是心性之學提供了學術的意義源泉,使學術境界與生命境界合致;而那種‘江漢源頭酣歌鼓掌式的精神發(fā)越、情感陶醉,應是其后的乾嘉學人所難以體驗的吧。”e與此旨趣神合的是,趙園老師的同代人、我的導師陳思和老師,在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過知識分子民間“崗位”的價值取向。表面上看,從“廣場”轉入“崗位”,似乎是一種退守;但是在陳思和老師的理解中,所謂“崗位”,一方面是指知識分子的具體職業(yè),當然在謀生之外,還包括了學術責任與社會責任;另一方面蘊含了一層更為深刻與內在的意義,即知識分子對文化傳統(tǒng)精血的維系與發(fā)揚。所以這是一個辯證的概念,具體而微的工作中有“上出”的旨向,而超越性的精神則融化于普普通通的崗位中。
前引趙園老師對黃宗羲的研究,在我心目中許是學術理想的極境吧。這段“學術境界與生命境界合致”的論述,總讓我想起竹內好對魯迅的評斷:“在他,是有著一種除了稱作文學者以外無可稱呼的根本態(tài)度的。”學生時代的我,一邊寫博士論文,一邊通過孫歌老師為媒介的竹內好,建立起對魯迅的理解。當竹內好決定《中國文學》廢刊時,感慨“安定到來了,持續(xù)的日子開始了”,于是“黨派性”變成了“學術”,這里的“黨派性”恰與世俗意思相反,是指通過不斷地自我懷疑、否定而謀求自我與環(huán)境的更新。竹內好的一身之勇是多么吸引我,當年跌跌撞撞地步入學術研究行列,正是憧憬著作為根本態(tài)度的“文學”:“文學是思想,是行為,是政治,是審美,但是它又是遠遠超過這一切的、催生也廢棄這一切的那個本源性的‘無,那個不斷流動的影子和不斷自我更新的空間。”最近重讀一遍增訂版《竹內好的悖論》,想到我從竹內好批評的起點,步入學術界,20年時光飛逝,猛回頭才發(fā)現(xiàn),原來是倒退著回到甚至固守于(用魯迅的話說,是“安住”于)竹內好批評對象的狀態(tài)中——那持續(xù)的、平庸的、自我滿足的“安定”中。
調子太低沉了,還是談談讓我起見賢思齊之心的同代學人。讀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運動》,尤其感興趣的論題是新文化運動的排斥機制與自我壓抑。“新文化”作為當事人和后來者共同建構的歷史事件,其內部本來容納著很多異質性,但是經(jīng)過后來的歷史敘述的處理,有的被改編為正史序列之外的前奏,有的被放逐到邊緣成為可有可無的插曲,甚至直接被掃除到隱沒的角落里不再為人所知……特別心有戚戚的是袁一丹寫劉半農和《何典》這兩章,其福柯式的、譜系學式的復原功力當然讓我佩服,更肅然起敬的,甚至羨慕不已的是一種研究中的“余味”。“余味”在《此時懷抱向誰開》溢出更多,因為是學術隨筆體,筆墨更自由,感慨抒發(fā)更隨性。《另起的新文化運動》畢竟是學術論文,但是在學術體例的限制下,依然可以看到“余味”。這個“余味”和知識的周密、體系的完整、考訂的謹嚴好像都不同,就是按規(guī)矩寫完之后忍不住總覺得還有些什么。劉半農這一章寫這位新文化人的自我改造與改寫,梳理得清清楚楚,學術論文寫到這里也就夠了,但是作為讀者我分明能感覺到,袁一丹對歷史中人在理想的“我”與現(xiàn)實的“我”之間、在追隨時潮與持守本性之間無止境的掙扎,抱有一種深切的同情。這就是“余味”,適足見出文學研究者的當行本色,也就是對一個個具體的、能動的、有血有肉的人及其身處境遇的體察。甚至用“余味”這個詞也不確切,“余”讓人聯(lián)想到剩余、多余、邊角料,但其實不是這樣的。讀陳寅恪《論唐高祖稱臣于突厥事》的結語部分:“初雖效之,終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杰之所為也。又合足病哉!合足病哉!”這里的復沓真是余音繞梁、三日不絕。這樣來看,“余味”就是主旨,就是力透紙背的關懷,就是人文學術研究的當然構成。這樣的細節(jié),本就貫通著整體吧!
2024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