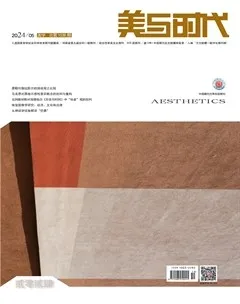西方環(huán)境美學中自然美建構覷探

摘? 要:自然美作為生態(tài)振興的重要引力,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助推器”。西方環(huán)境美學發(fā)展過程中,基于不同邏輯對自然美的建構,效果顯著并演化出多種理論形態(tài),對于進一步研究自然美創(chuàng)新性建構的方式,提供了重要參考依照。借鑒西方環(huán)境美學中自然美建構的經(jīng)驗,應充分認識到其自然美構建過程的進步與不足之處,結合當前自然美的建構現(xiàn)狀,完善自然美研究的思路,改正自然美建構中存在的問題,促進自然美研究的深入發(fā)展。
關鍵詞:自然美;環(huán)境美學;建構方式
“推動綠色發(fā)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的,自然對于人類的重要性和保護生態(tài)對于一個國家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意義日益凸顯。此背景下,關于自然環(huán)境、生態(tài)和諧、天然景觀等在美學研究中高頻出現(xiàn),自然美作為自然審美研究的對象,成為新時代美學領域的重要研究視閾。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美的研究仍在起步階段,學界至今尚未達成統(tǒng)一的共識,因此自然美在相關分支領域的研究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絕不能一概而論。環(huán)境美學作為推動自然美的重要理論,在長期學術研究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自然美構建的“理論框架”。本文著眼于自然美在西方環(huán)境美學中的構建肌理研究,從分析自然美建構的多維視角入手,探析自然美構建的研究邏輯,推進自然美研究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
一、環(huán)境美學中自然美概況
從環(huán)境美學的起源上來看,源于Ronald Hepburn (羅納德·赫伯恩)在1966年發(fā)表的《當代美學及其對自然美的忽視》一文,該文的核心關注點就是自然美的重建問題。赫伯恩通過這篇文章揭開了對自然美的叩問,極大地啟發(fā)了后來環(huán)境美學中“按照自然本身來欣賞”的認識,赫伯恩也因此成為“環(huán)境美學之父”。由此看來,當代西方環(huán)境美學發(fā)端于美學理論體系中對自然美的理論桎梏的反思,自然美與當代西方環(huán)境美學的發(fā)展是一脈相承的、交融互滲的關系。
20世紀90年代之后,環(huán)境美學傳入中國,在陳望衡、程相占、薛富興、曾繁仁、胡友峰等一大批優(yōu)秀學者的研究推動下,在國內(nèi)已經(jīng)發(fā)展成一門具有深遠影響力的理論。然而,20世紀以來國內(nèi)自然美的研究存在自然美概念缺乏合邏輯的界定,自然美經(jīng)常被景觀美、環(huán)境美、生態(tài)美、美的本質、如畫的自然美、藝術中的自然美等問題所混淆,如“環(huán)境美學的核心是環(huán)境美”[1]的建構表述就容易忽視環(huán)境美、自然美與環(huán)境美學之間的關系,胡友峰在他的相關研究中深入分析了自然美在19世紀西方美學中被“邊緣化”的原因,以及環(huán)境美學中自然美如何突破“藩籬”,重返舞臺[2],成為現(xiàn)階段環(huán)境美學研究中一個重要問題。
發(fā)展至今,當代西方環(huán)境美學在中國有影響力的研究體現(xiàn)在以英國的羅納德·赫伯恩(Ronald Hepburn)、加拿大的卡爾松(Allen Carlson)、英國的阿諾德·伯林特(Arnod Berleant)、芬蘭的約·瑟帕瑪(YrjoSepanmaa)等為代表的環(huán)境美學家(如表1),這些學者的理論著作成為認識和研究當代西方環(huán)境美學的“敲門磚”,通過研究環(huán)境美學的建構方式,可以從中管窺當代西方環(huán)境美學中自然美如何實現(xiàn)當代性重構的過程。
表1 當代西方環(huán)境美學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國家 代表人物 環(huán)境美學 著作 哲學傾向
英國 羅納德·赫伯恩 西方當代自然美學 《當代美學及對自然美的忽視》(1966) 反人類中心主義
加拿大 卡爾松 肯定美學 《自然與景觀》《環(huán)境美學》(1998) 生態(tài)中心主義
美國 阿諾德·伯林特 參與美學 《環(huán)境美學》(1992) 《環(huán)境與藝術:環(huán)境美學的多維視角》(2002) 《生活在景觀中》 生態(tài)整體主義
芬蘭 約·瑟帕瑪 環(huán)境批評美學 《環(huán)境之美》(1986) 人類中心主義
二、西方自然美學中的革新建構分析
羅納德·赫伯恩的環(huán)境美學首要貢獻在于掙脫了以藝術為中心的西方傳統(tǒng)美學理論的思想牢籠,發(fā)出了重現(xiàn)自然美的第一聲吶喊。從具體的表征來看以往美學理論對自然美的忽視,體現(xiàn)在從鮑姆嘉通創(chuàng)建美學之初,就將美學界定為藝術的科學(藝術哲學),到之后的浪漫主義文學運動以及黑格爾關于自然美的美學思想(自然美是一種不完善的美的形態(tài),是心靈美的反映),赫伯恩認識到自然美在美學領域長期被流放的原因在于:
(一)興起于18世紀末的浪漫主義文學中自然觀念的歸隱,人類審美情趣發(fā)生偏移。
(二)科學的快速發(fā)展也使得人類在關于自然美的審美欣賞方面產(chǎn)生許多迷惘與困惑,與清晰明確的科學結論相比,自然美的欣賞顯得更加主觀和淺薄,卻不知這種對比早已喪失了自然美的審美屬性,仍然以“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來裁定自然美的審美價值。
(三)自然的審美經(jīng)驗具有自身的獨特性,體現(xiàn)自然的審美經(jīng)驗由于自然欣賞處于無時無刻的運動變化中,并且自然物與背景具有強融合性,因而自然的審美經(jīng)驗很難從自然當中直接獲取,也無法實現(xiàn)藝術品一般可以準確引導欣賞者的情緒性能。
由此轉入了自然美獨特性研究和自然審美過程整體性的考察,從美學理論體系內(nèi)部對傳統(tǒng)美學的審美方式進行革新,從而建構起區(qū)別于藝術審美的、體現(xiàn)自然審美獨特性的審美方式。與藝術審美采用“分離模式”的審美方式不同,自然審美采用的審美方式是“參與模式”,強調(diào)自然審美的整個過程,欣賞者的欣賞始終沉浸在自然界之中,欣賞者自身也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與自然界融合在一起,因此,對自然的審美欣賞呈現(xiàn)為一種相互交融的整體生態(tài)系統(tǒng)內(nèi)的自然審美,對自然審美方式的革新式闡釋,極大地推動自然美重新納入美學的審美范疇。
此外,赫伯恩對于在自然審美革新模式中遇到的“客觀的科學知識與主觀的審美想象如何進行合理的結合”[3]問題,從而得出“即使在沒有許多科學知識的參與情況下,欣賞者通過情感與想象的方式也能夠實現(xiàn)自然審美”的見解,這就是赫伯恩后來提出的形而上學的想象模式,該模式旨在保證合理的審美態(tài)度的生成,推動環(huán)境美學的革新發(fā)展。
三、環(huán)境肯定美學中的顯現(xiàn)建構分析
卡爾松在當代西方環(huán)境美學中掀起了肯定美學的新思潮,對于肯定美學通常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肯定美學是自然美的新觀念顯現(xiàn),未經(jīng)人類干預的、人類未涉足的自然界本自具足地擁有完美的、積極的、肯定的審美價值與審美特性。第二種,類似于在自然美學中普遍認同的:自然美具有客觀顯現(xiàn)性,即自然本質上是美,這種積極的、肯定的審美特性是自然界與生俱來的[4]。無論是第一種自然美顯現(xiàn)的特殊觀念,還是自然本質上的積極意義,都指向肯定美學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一切自然物本質上都具有積極的、肯定的審美顯現(xiàn)特性、審美價值的美學,簡言之,也就是自然全美。
關于卡爾松肯定美學的理解,根據(jù)對自然肯定的程度強弱不同,又可以進一步分為自然絕對的只擁有肯定的審美顯現(xiàn)價值和自然本質上具有審美價值兩種。卡爾松的學術貢獻不在于提出“自然全美”思想,而在于他對自然美的價值論證明。第二種理解內(nèi)含這樣一層意思:只有當自然界在根本上具有客觀實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審美顯現(xiàn)價值,探討關于“選擇什么樣的審美方式?如何正確地選擇自然美的審美方式?什么樣的審美方式算正確的?以及如何運用所謂正確的審美方式來欣賞自然美?”等一系列問題才具有邏輯意義,否則,一切都會因為自然美在本質上是否具有審美顯現(xiàn)價值的爭議而無從談起。
緊接著價值論之后便是認識論,探討如何在自然本質上具有審美顯現(xiàn)價值的基礎上,如何找到正確的方式來認識自然美。此時科學在自然審美過程中的價值凸顯出來,科學提供豐富的自然知識以及對自然不斷進行探索與闡釋,不斷拓寬人類對美的認知范圍,越來越多的新鮮事物納入人類的審美范疇。瓦爾頓藝術欣賞的模式恰好給卡爾松提供有益的啟示,也就是人類在認識自然美的顯現(xiàn)過程中,離不開相關知識的支撐,自然對象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顯現(xiàn)出審美價值,自然美顯現(xiàn)的前提條件是把自然物放到正確的范疇中并進行適當?shù)闹X。例如,大自然中一塊不規(guī)則的大理石如果從規(guī)整、勻稱、均衡、對稱的角度來看,很難發(fā)現(xiàn)它的美,如果將它放進自然環(huán)境中,與周圍花草蟲木的和諧中,一種遵循自然規(guī)律的風蝕日曬的結果來看,它又成為了審美特性的事物。不僅如此,還不能證明“自然全美”,因為藝術審美采用這種正確的范疇也無法證明“藝術全美”,從而深入到自然審美對象與藝術作品之間存在的內(nèi)在差異,進一步辨析恰當?shù)乃囆g范疇與正確的自然范疇兩者在確立上的差異,從事物的區(qū)別上來看,而藝術作品的創(chuàng)造,自然對象是發(fā)現(xiàn)的,從二者正確范疇的確立上來看,正確的藝術范疇受到作品創(chuàng)作之初創(chuàng)作藝術家的意向、地點、創(chuàng)作契機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一件具體的藝術作品即使按照正確的藝術范疇,也可能沒有好的審美效果,而自然界中正確范疇之所以和藝術中正確的范疇不同,是因為自然界中對象和范疇是密不可分的。正確范疇是根據(jù)自然對象創(chuàng)造的,自然對象是在正確范疇中顯現(xiàn)的,也類似于黑格爾在《美學講演錄》中講的“世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fā)現(xiàn)美的眼光”,這里美的眼光就相當于正確的自然范疇[5]。“自然全美”最初表達的是一種感性的人文關懷和熱戀,后來被環(huán)境保護主義者發(fā)展為肯定美學,那時的肯定美學更加關注的是該理論的思想號召性,卡爾松對“自然全美”的論述使其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論高度,形成當代西方環(huán)境美學中肯定美學的分支理論。
四、環(huán)境參與美學中的融合建構分析
阿諾德·柏林特是一位“通過探索自然美融合建構研究為西方環(huán)境美學的發(fā)展做出重要貢獻”的美學家,他的“藝術與介入、審美經(jīng)驗的現(xiàn)象學和其他關于自然美學的思考”大大推動了西方環(huán)境美學的發(fā)展進程,為研究自然美在當代自然美學中的融合提供諸多有益啟示。他在借鑒吸收現(xiàn)象學領域的“懸擱”說(外在于主體的環(huán)境客體不存在)、生態(tài)學的普遍聯(lián)系觀(錯綜復雜而且相互聯(lián)系的復合體)和杜威的實用主義美學思想(人與環(huán)境的統(tǒng)一而非分離)后,形成了自己的參與美學理論體系。
傳統(tǒng)意義上的、與世隔絕的、從未被人類所涉入的“自然”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人類觀念中的自然是人類生存的外在環(huán)境,也就是“沒有完全脫離人類的、孤立的自然,也沒有自然之外的人”“環(huán)境是被人體驗過的自然”或者說“自然之外無一物”[6]。隨著現(xiàn)代社會的快速發(fā)展,藝術與環(huán)境的融合關聯(lián)性也越來越明顯,自然環(huán)境、文化環(huán)境、人居環(huán)境、生態(tài)環(huán)境都成為藝術外延當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藝術以各種方式改變或者說與自然環(huán)境交相輝映、彼此融合。柏林特關于自然環(huán)境的理解是,“從根本上來講,環(huán)境是與人類生活、生產(chǎn)相伴隨的自然生發(fā)過程,無論人類如何生活、怎樣生產(chǎn),以及如何與所生存的環(huán)境進行情感互動,環(huán)境始終是被人類所體驗的、所感知的自然,人們生活期間的自然”,環(huán)境美、自然美與藝術美相互生發(fā)、水乳交融、不可劃分。
在環(huán)境參與美學中正確的審美模式是所謂的審美融合參與模式,依托于審美場域、審美對象、感知者、藝術家和表演家,以一個知覺融合的審美主體感知自然環(huán)境之美,強調(diào)二者完全融合(神合),即審美主客體不再是相互分離的對立模式,而是“不可分離”的和諧統(tǒng)一。就審美體驗而言,自然環(huán)境是關于審美主體發(fā)生在場情境中的審美感受和情感投入,是不同層次的、多個觸點的、混沌未開的感官意識的復雜混合,它要求審美主體的審美感知力、審美鑒賞力、審美想象力等持續(xù)在場,涵括身體在場、連續(xù)性和知覺融合。知覺元觸點(感知者本身)與傳遞給審美主體此種感知的情境、在場的物理基礎條件和社會場域條件相交融時,才能談論自然環(huán)境的審美性,此處的自然環(huán)境不能理解為單純的物理自然,也不完全是審美主體的單方面知覺建構過程,而是審美主體與自然環(huán)境相互參與、和諧交融、相互激發(fā)的產(chǎn)物。概言之,柏林特的環(huán)境美學對自然審美的理解具有交融性、體驗性和多感官混合的審美融合特征。
五、環(huán)境批評美學中的批判建構分析
瑟帕瑪也是西方環(huán)境美學研究代表性的學者,曾向卡爾松學習過環(huán)境美學,瑟帕瑪?shù)沫h(huán)境美學思想建立在美的哲學和藝術哲學的基礎上,對自然環(huán)境的審美性研究,本質上還是屬于自然美的哲學范疇,基于對自然環(huán)境的直接感受、個體地審美情趣和多感官融合的觀察力組成的整體框架內(nèi),分析欣賞者對環(huán)境美的刺激所能夠做出的反應。研究遵循作為環(huán)境審美本質的、趣味判斷的依據(jù)——元批評(把環(huán)境批評的描述、闡釋和評價作為基礎批評)。
以藝術為參照系建構環(huán)境批判美學理論,環(huán)境與藝術都可以作為審美感知的批判對象,但在創(chuàng)作、對象和觀察者來看,藝術品是人創(chuàng)造的,自然環(huán)境是給定的,獨立于人類;藝術作品是虛構的、被界定的、感官的,而環(huán)境(自然)是真實的、無邊框的、動態(tài)的;藝術作品的觀賞場所是限定的,環(huán)境的觀賞是自由的,觀察者是環(huán)境的一部分,與環(huán)境直接進行多感官的接觸[7]。從二者的對比中,更能凸顯自然美的獨特性以及揭示其來源、本質屬性、鑒賞屬性等方面從而建構環(huán)境批判美學的學理邏輯。
綜上,當代西方環(huán)境美學家對自然的理解存在多維度的認識,一方面反映出美學家審美觀的差異性、自然哲學觀念的傾向性、多學科的交融性。各自的理論在建構理論的過程中,受到社會環(huán)境、理論背景、研究視角等多方面的影響,彼此之間相互的辯駁和觀點碰撞也促進了理論的“糾偏”過程,比如赫伯恩的形而上學的想象模式是基于卡爾松肯定美學中環(huán)境審美模式對科學知識的過度強調(diào)而提出的。另一方面,不同研究又相互促進,從環(huán)境美學的整體性上來看,強調(diào)對自然本體的尊重,使“自然美”這一美學范疇引起人們的重視,共同推動人與自然建立更加和諧的關系。瑟帕瑪環(huán)境批評的描述與柏林特關于描述美學對環(huán)境審美作用的解讀具有相通之處,而瑟帕瑪關于環(huán)境批評的闡釋研究又與卡爾松論述科學在自然審美中作用的研究相呼應,可以看到瑟帕瑪受到卡爾松環(huán)境美學的影響,并在批評的角度進行創(chuàng)新,認識到知識能深化審美體驗,同時也限制審美的擴大化,彼此之間也存在對自然美研究的共同認識,即對于自然美的研究不能脫離歷史性、自然審美必須是擺脫孤立進入整體性。由此來看,在當代西方環(huán)境美學中自然美的重構過程就是自然美的研究與時俱進、兼容并蓄、多元化發(fā)展的過程。
參考文獻:
[1]伍永忠.論陳望衡環(huán)境美學體系的內(nèi)在邏輯[J].江淮論壇,2015(3):121-126.
[2]汝信,曾繁仁.中國美學年鑒(2004)[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3]陳國雄,杭林.羅納德·赫伯恩環(huán)境美學思想研究[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1):10-14.
[4]薛富興.艾倫·卡爾松環(huán)境美學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8:108.
[5]彭鋒.“自然全美”及其科學證明──評卡爾松的“肯定美學”[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4):46-54.
[6]代君潔.阿諾德·柏林特的環(huán)境美學思想研究[D].太原:山西師范大學,2019.
[7]張文濤.作為環(huán)境批評的哲學——約·瑟帕瑪環(huán)境美學思想簡評[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4):117-120.
作者簡介:黃云虎,山東大學藝術學院藝術學理論專業(yè)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藝術美學、藝術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