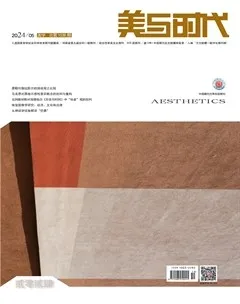《我腦袋里的怪東西》的空間敘事與記憶重構
摘? 要:帕慕克的小說《我腦袋里的怪東西》借助伊斯坦布爾街頭賣缽扎的小販麥夫魯特的視角記錄了他半個世紀的城市漫游經驗,他在西化后的伊斯坦布爾寒來暑往的記憶,架構起獨特的空間敘事模型。本文以空間敘事與記憶重構作為考察視角,重點分析該文本獨特的空間敘事策略,以期揭示潛藏在空間表征與記憶場域下的文本內涵。
關鍵詞:帕慕克;《我腦袋里的怪東西》;空間敘事;記憶重構
基金項目:本文系廣州華商學院青年學術項目“奧爾罕·帕慕克文學研究”(2023HSQX076)研究成果。
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在2014年出版了長篇小說《我腦袋里的怪東西》(Kafamda Bir Tuhafl?k)。帕慕克稱這部小說為“一部獻給現代土耳其的情書”。小說通過缽扎小販麥夫魯特(Mevlut)和他的親人朋友等多重視角共同繪制了一幅從1969年至2012年間的伊斯坦布爾恢弘而質樸的生活畫卷。小說一經發表便經由60多個語種翻譯并進行全球性傳播,英國《獨立報》稱帕慕克為“為數不多在斬獲諾獎之后還能寫出自己最佳作品的大師級作家”;《華爾街日報》將該小說視作“一部關于伊斯坦布爾的編年史”。
《我腦袋里的怪東西》對麥夫魯特視角的呈現既有空間敘事的特征,也有在時間維度上的記憶重構。小說敘事的張力來自空間與記憶的并置交融,空間是水平敘事軸,記憶是垂直敘事軸,縱橫軸敘事交流中必然潛存著多維度互相博弈的空間敘事,空間的延展又必然導致時間的重組,而空間敘事與記憶重構的相互交織又將呈現出個體的多層生存體驗。《我腦袋里的怪東西》記錄的是20世紀70年代土耳其社會全面西化的轉型時期,這意味著小說中的空間敘事不僅停留在現存的地理空間這一層面,同時還囊括了個體在既有生存體驗之外所聯結到的權力空間、虛幻夢境空間;而時間鏈條上的記憶重構必將由此綻放出更加斑斕的拼貼糅合。帕慕克藉此構筑了同時突破空間和時間限制的底層人物的典型,在時空交互的視閾下試圖藉此找尋當代無根漂泊的土耳其人亟需的某種與故土間存在的軟性聯結,讓他們在面對城市的破敗和冷酷時,不至于太慌張無措。
一、交錯并置的空間敘事
20世紀后半期,學界對文本的解讀突破了傳統的線性時間維度,轉而從地理和空間的視域考察文本敘事。在文學批評領域中,空間敘事是指在不同的文本情境和場所所串聯起來的視閾下,文本因之被賦予的特殊的文化底蘊。“小說內容是具有空間結構的……因為在它展開的書頁中為我們展現出目光靜止不動時候的組織和體系”[1],而構成這一組織和體系的是空間敘事的生成邏輯。人物與不同的生存領域會形成不同的情感聯結;而人物的空間置換這一動態過程往往暗含著人物的情感意識發生了轉變,人物發生被動的空間置換或者主動的空間置換影響著人物的內心建構。與此同時,“權力的作用通過空間發揮出來”[2],按照福柯的觀點,空間又具備了“權力”的意涵。靜態的空間秩序悄無聲息地決定了人物在該場域下的話語權,空間的使用者左右著空間的話語權。此外,人物關于任意空間的記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文本空間的延展性,以上多重空間維度的交織共同生成了小說文本空間敘事的豐富意蘊。《我腦袋里的怪東西》主要講述了賣缽扎的小商販麥夫魯特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城市的街道上販賣缽扎的43年(1969-2012),核心敘述了他在賣缽扎時不停歇地琢磨著腦袋里一個接一個的“怪東西”;帕慕克假借麥夫魯特在不同場所的游蕩和觀察,向讀者展示了底層人物在西方文明與土耳其傳統文明碰撞下的伊斯坦布爾城市的生存體驗,以及隨之而來的關于世界和存在的思考。
麥夫魯特的空間靈活置換是形成空間敘事的重要因素,這一過程表現為麥夫魯特存在的地理空間的變化。地理空間是小說空間建構的根基。帕慕克在小說中描寫了麥夫魯特存在過的小村莊、富人區和伊斯坦布爾的街道等現實存在的地理空間。麥夫魯特在一系列地理場所發生的空間位移為讀者呈現了個體在城市變遷的語境下真切的生活體驗。小說開頭,出生于僻遠小山村的麥夫魯特滿懷期待地與父親到“世界之都”伊斯坦布爾謀生。在他此前十多年的人生經驗里,他從小長大的小村莊是貧窮落后的,而伊斯坦布爾是幸福的,充滿希望的。然而,真實的伊斯坦布爾“關于街頭小販‘骯臟的錯誤觀念,通過電視和報紙迅速在年輕一代中傳開”[3]305,隨著城市的日新月異,麥夫魯特感受到“年輕一代對自己的排斥”[3]264。城市對他示以的拒斥、懷疑讓麥夫魯特認為自己“不再屬于這里”[3]470。帕慕克通過不同空間場所的置換展現麥夫魯特生存體驗的割裂感。在過去的小巷子里,麥夫魯特可以感受到人們對他賣的缽扎的喜愛與期待,系著繩子的籃子會從樓上緩慢地垂掛下來,等待麥夫魯特和爸爸往籃子里置放缽扎。那時,小販的生活是輕松快樂的,人與人的相處是多么和諧融洽。現在,他大部分時間要穿梭在富人區販賣缽扎,每每在要進入富人的家里之前,麥夫魯特都必須“恭敬地脫下鞋子”[3]26,甚至要面對顧客夾帶譏笑的諷刺。從過去的小巷子到富人區的空間調換過程,暗藏著空間政治權力內涵的轉變。在過去的小巷子里,文化空間的權力擁有者是傳統的土耳其文明。麥夫魯特扁擔上售賣的缽扎是一種土耳其傳統飲料,對過去小巷子里的人來說,“缽扎是一樣神圣的東西”[3]217,他們非常熱情友好地對待像麥夫魯特這樣的小商販。但是,在西化后興起的富人區,西方文化仿佛一夜之間成為支配該空間的權力所有者。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人們不再喜歡缽扎,賣缽扎的麥夫魯特成為富人區的異類,周邊的人們向他投去不屑和鄙夷。由此,與其說地理空間是麥夫魯特用腳步丈量過的場所,不如說它是一種帶著強烈隱喻性的空間。富人區象征著伊斯坦布爾城市內部西方文化的權力地位,帕慕克對富人區的人們那些膨脹、虛榮、無禮、膚淺的精神處境的描寫,恰恰也是他對骯臟、半西化街道城區示以的濃厚批判。以富人區為代表的西化改革中興起的城市建筑是矛盾的統一體,這是西方文化與土耳其文化角逐的權力運作場。在傳統空間秩序崩解的場域下,麥夫魯特這樣的底層個體的內心陷入無限的迷茫與困頓。
現實存在的物理空間無法予以麥夫魯特精神上的撫慰,他轉而向虛幻的夢境找尋精神的寄托。他喜歡夜晚在街道上漫游,以一種精神恍惚的狀態游蕩。在此種狀態下,麥夫魯特所看到的景象不再是實境或幻想,而是隨著空間的轉換記憶中碎片的流動、拼貼和重組。每當他“夢游般”行走在夜晚的伊斯坦布爾街道時,他的“內心便會充滿善意和幸福”[3]248。伊斯坦布爾街頭是小說故事發生的主要場所,而夜晚往往象征著虛幻飄渺,夜晚的伊斯坦布爾街道是麥夫魯特可以自由地思索著腦袋里一個又一個“怪東西”的空間。在這一場域下,帕慕克借助小說中麥夫魯特漫游在夜晚的街道完成了空間敘事中實境與虛境并置交融的描寫。一直到小說的結尾,在妻子拉伊哈去世和女兒們出嫁后,麥夫魯特依舊孤獨地游蕩在街道上。同一街道的不同時刻都蘊涵了麥夫魯特心態上的轉變,帕慕克借助空間記憶的轉承向讀者展示了不同空間下麥夫魯特的生存體驗。在小說中,實境空間與虛境空間是以無縫銜接的方式呈現出來。在小說第九章,帕慕克借助麥夫魯特對街道上神秘女人奈麗曼的尾隨隱喻麥夫魯特探索“讓城市成為城市”[3]91的東西。麥夫魯特只是遠遠地看著奈麗曼,就能感受到她傳遞給他的“一種奇特的力量”[3]91,甚至在彼此拉開的距離里,麥夫魯特感覺到“他們之間存在某種特殊的精神上的親近”[3]92。在草地上獨自冥想奈麗曼的時候,麥夫魯特期待著自己的雙腿能“更多地把自己帶去奈麗曼行走的街道”[3]94。要理解帕慕克文本里的男女情感聯結,就要將其置于伊斯蘭神秘主義文化結構當中。顯然,麥夫魯特與奈麗曼之間的情感聯系已經不是停留在現實層面的“世俗之愛”,而是超越世俗的“人神之愛”。在蘇菲神秘主義中,人可以通過不斷冥想“安拉之愛”來使自己忘卻在現實境遇中的精神苦痛,擺脫現實層面的各種世俗牽絆。以此為前提,帕慕克完成了對麥夫魯特漫游街道的虛實空間的置換描寫,一邊是現實世界的崎嶇坎坷,一邊是完全脫離經驗世界的蘇菲主義神秘空間的自我救贖。文本中的麥夫魯特在頻繁交替的現實空間和虛幻空間中來回往返,虛實結合的鏡像投射出自我,在這樣的過程中,麥夫魯特可以不停地在腦海里構想著一個又一個的“怪東西”,在人生的“朝圣之旅”中不斷前行。隨著空間維度的延展,時間的鏈條隨之也被賦予了廣延性的可能。
此外,小說最鮮明的空間敘事方式是多重視角的轉換。敘述視角的多次切換能使文本表達出豐富的空間效果,進一步打破了文本再現空間的單一性。加布里埃爾·佐倫表示,“敘事空間的重構決定了文本的視點,突破文本虛構空間的‘彼在與局限于文本虛構空間的‘此在會形成不同的關注焦點,二者在敘述邏輯的轉變中將形成不同的空間效果”[4]。帕慕克在小說中通過多重視角的敘述使讀者收獲不同的空間感知。在向讀者介紹麥夫魯特從小長大的地方時,帕慕克就借助了考爾庫特、阿卜杜拉赫曼、哈桑伯父、薩菲耶姨媽、維蒂哈、薩米哈、拉伊哈、蘇萊曼等人的視角感受來呈現他們共同的生活空間,以及在此基礎上他們對理想生活城市空間的想象。多重視角下不同人物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展示了一個僻遠、貧窮、落后,同時又兼具人情味、純潔善良的小山村。恰恰是在人物不同視角的切換中,彰顯個體生存體驗的撕裂感,由此向讀者展現了全知視角下伊斯坦布爾城市的真實面貌。以麥夫魯特為例,麥夫魯特對伊斯坦布爾的情感態度經歷了從過去的迷戀癡想到現實的殘酷挫敗,從幻想的美好富足到實際的困苦坎坷,這是暗藏在文本下無數個分裂的麥夫魯特。從某種程度而言,這部伊斯坦布爾的編年史就是在這種第一人稱視角的發散下筑建起來的。麥夫魯特的自我分裂產生了文本的多重敘事空間,由此,讀者在文本的引領下在多重敘事空間中來回穿梭,去陪伴麥夫魯特叩擊他的內心世界,重構一個更加真實的伊斯坦布爾。
二、歷史文化的記憶重構
帕慕克借助《我腦袋里的怪東西》里的空間敘事向我們展現了全盤西化模式下伊斯坦布爾城市所演繹的文化變遷。小說在對具有隱喻性的空間進行書寫的同時,還蘊藏了在時間維度上對民族文化記憶的審思與重構,因而增添了小說文本重構歷史記憶的功能。在小說中,帕慕克對麥夫魯特的記憶書寫彌補了“歷史”的不在場性,過去的歷史記憶參與到麥夫魯特當下的人生體驗之中,隨之而來的是民族的傳統記憶積淀延續并參與到當今的文化身份建構之中。由此,文化記憶依托著作家的文本得以延續和固化。
首先是麥夫魯特個人記憶的生成。從在街道上遭遇野狗的咆哮,到在街頭被流氓搶劫,再到去快餐店工作遭受排擠孤立,麥夫魯特在伊斯坦布爾始終干著卑微的體力活兒,城市像無邊的黑洞般耗損著他奮斗的意志,而麥夫魯特早期的城市期待也早已破滅。2002年11月,土耳其以創建一個更加開放包容的國度為由,在國內推行了大范圍、大規模的“土耳其模式”政策。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推進,諸多社會問題開始浮出水面。在新興城市里,像麥夫魯特這樣的底層人只能蝸居在山腳下的“一夜屋”,大量無家無業的人在寒冷的冬夜里只能蜷縮著身體取暖。在傳統社會秩序分崩離析之后,土地的分配混亂、社會的管理制度不完善、人們的物欲迅速膨脹,在社會轉型中的既得利益者之下,是千千萬萬像麥夫魯特這樣的底層人民。在窮困悲慘的生活面前,他們不由得心生悲傷。
既然當下的現實生活無法予以他們精神上的慰藉,那么對過去的回憶就成了當下最好的一種對抗方式。成年后麥夫魯特對安納托利亞小山村的回望,是在伊斯坦布爾命運多舛的他對自我的一種情感慰藉。帕慕克選取了一些自然素樸的意象來構筑麥夫魯特記憶中遙遠的家園。黃綠交加的樹葉,樹枝燃燒起的火苗,山下羊兒吃草的平川,可愛的白色清真寺等,這些特殊的景象共同編織了麥夫魯特童年的記憶網,質樸簡單的生活方式有如高大威嚴的清真寺,聚攏著他對于未來幸福生活的一切信仰。盡管村里的記憶在時間維度上已經愈行愈遠,但是過去記憶攜帶的情緒體驗一直潛藏在麥夫魯特的內心深處,這些情感體驗在麥夫魯特輾轉周折后再次被喚醒,而麥夫魯特對過去記憶的再現和重構,背后也隱含了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個體苦苦找尋的關于家園的歸屬感。
其次是集體記憶的建構。在集體記憶中懷舊,個體才不會是一個孤立的存在。麥夫魯特通過回憶的方式再現了各種土耳其傳統的文化記憶,例如麥夫魯特在敗落的老建筑中憶想著的舊房子和老宅邸,在清真寺做禮拜的宗教儀式,奧斯曼帝國時期的傳統酸奶飲料缽扎,在學校上課時,他對先輩們創造的光榮歷史記憶的發自內心的認同。這些傳統記憶共同串聯起了一個“記憶場”,蘊涵著過去人們共有的生活價值理念、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這種集體記憶對人們生存模式的影響是深遠且持久的。同時,當這些共有的集體記憶延續到當下時,它們就成了在伊斯坦布爾顛沛流離的人們內心的精神盛舉。在凱末爾西化改革下,土耳其人民要共同面對傳統文明的斷裂和隕落,這成了他們心中難以啟齒的民族創傷。“倘若我們不幸生活在一個急劇擴張的無情城市中,那么我們生活在此的房屋、花園以及街巷,那些塑造了我們記憶和自身靈魂的墻垣,就注定會被毀滅。”[5]245對于土耳其人民而言,集體記憶是他們所有成員共同的財富,它的意義不在于將本民族的文化與其他社區文化區別優劣,而是在過去的時間記憶橫向延續到當下的過程中收獲一種集體的歸屬溫暖,在縱向空間重構一個穩定可靠的、群體之間情感緊密相連的精神家園。
最后是重構民族記憶。伴隨著凱末爾的西化進程,土耳其傳統文化的歷史整體性遭受極大程度的摧毀,斷裂的民族命運與憂傷的民族亟需通過民族記憶的重構以重拾民族自信心。以古老街道、酸奶飲料缽扎、清真寺的禮拜儀式為典型代表的物象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承載物。正是這些蘊涵著自身文化傳統與特質的民族記憶使土耳其人民得以獲得文化歸屬感和群體認同。歸根到底,一個民族是否真正消亡取決于集體記憶是否永久喪失,人們在對過去民族記憶進行重構的同時,民族記憶也參與建構著當下人們的身份,在古老街道上游蕩的時候,麥夫魯特會記得在過去人們從小樓上騰空放下一個籃子的購物方式;在街頭販賣缽扎的時候,麥夫魯特常常會想起過去缽扎給他帶去的文化認同感;在清真寺冥想的時候,他會一次一次地發現自己被信仰之光懷抱著。以上所有場景的再現都重構著土耳其人曾經擁有的既平淡又彌足珍貴的民族記憶,承載著這些民族記憶的是曾經帶給他們榮耀的過去強大輝煌的國家,那些井然有序的生活狀態便是最好的證明,而在記憶的長河里重構關于過去的記憶堡壘,也是土耳其人一次又一次地強化自己民族身份認同的過程。
三、空間敘事與記憶重構
《我腦袋里的怪東西》旨在借助麥夫魯特的視角再現伊斯坦布爾城市半個世紀的變化,可以說,時間結構是整部小說最鮮明的線索。然而,時間的推移往往也伴隨著空間的轉換。在小說中,帕慕克有意識地強調麥夫魯特的空間置換來呈現時間的進程。在文本記敘過程中,帕慕克將文本空間性的翻轉置于前景之上,通過空間化的敘述推動敘事進程。
在小說中,一些空間意象成為時間的標識物,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時間的壓縮感。廢墟意象是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城市文學里面最常見的意象。甚至,“伊斯坦布爾的歷史,就是火災與廢墟的歷史。”[5]7819盛極一時的奧斯曼帝國文明由于連綿不斷的戰爭而日漸衰敗,伴隨著古老文明的敗落,帝國斜陽下的憂傷最終投射到奧斯曼帝國文明遺存的廢墟上。在客觀世界里,這些廢墟可能只是被損毀或肌體殘敗的瓦礫堆;但是對于像麥夫魯特這樣“穿梭在城市廢墟間的小販們”[3]42而言,城市的廢墟喚醒了他們的生活記憶,這些記憶可能直抵某個與父親一起在古樸的小巷販賣缽扎的午后,或者是對逝去的親朋好友的深沉緬懷。總而言之,廢墟承載了他們曾經共有的生存體驗,回蕩起他們內心關于過去的許多復雜情感。與此相類似的,還有小說里出現的墳墓意象。在小說的末尾,當奮斗了一生的中年麥夫魯特在伊斯坦布爾依舊畏懼街道上野狗的吠叫時,小說出現了麥夫魯特的妻子拉伊哈的墳墓這一情景。雖然是十分有限的墳墓空間,但它卻凝聚著麥夫魯特掙扎努力的一生。在拉伊哈的墳墓面前,麥夫魯特不再懼怕街上野狗的威脅;正如在命運多舛的伊斯坦布爾城市經驗面前,麥夫魯特持之以恒的拼搏已經是最勇敢的抗爭。在墳墓面前,在這種似曾相識的記憶里,過去時間的消逝才是一個慢動作。可以說,無論是廢墟意象還是墳墓意象,它們都促進了小說空間感的延伸,進而完成了對時間的超越。帕慕克的時間的空間化表述在這里鮮明地體現了出來,廢墟、墳墓因之成為“過去”植入到“現在”的意象橋梁,空間化的藝術形式對抗著時間的流逝。
在文本中,帕慕克的時間敘事并不單單是書寫現實時間,而是對時間本身進行闡釋。帕慕克常常將時間寄生于各種實在的空間和虛擬的空間之中。在“街道”這一空間中,麥夫魯特的時間體驗常常呈現為實在空間與虛幻夢境的交錯。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格格不入的麥夫魯特日復一日地重復著“悲觀、孤獨的日子”[3]121,但他的時間體驗并不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在街道的路口,麥夫魯特常常想起有關“過去幾個世紀、那些消逝的美好日子的記憶”[3]22,這使他在短暫易逝的當下能獲得些許溫和的快樂,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他在現今城市里的愁悶,使他在充滿不確定因素的日子里能稍微樂觀起來,麥夫魯特由此不自覺地“幻想著未來的美好時光”[3]139。在這里,同樣的街道空間,帕慕克卻讓麥夫魯特身臨其境地沉浸在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三個跨度巨大的時間段中;在故事之外,讀者也因為虛與實的空間鏡像在同一空間匯聚而打破了時間的線性敘事,最終形成現實空間與虛幻夢境的平行對照之感。
此外,在敘事過程中,“街道”這一空間自身蘊涵的不同事物的不同形態變化也隱藏著時間性的表征。街道空間重塑了麥夫魯特關于時間和生命的思考,重構了生命流動的可能,再次喚醒了人性中的質性蘊涵,建構了一個嶄新的立體的本我。于麥夫魯特而言,空間的權力結構發生的細微變化恰恰映照著他這一生的時間感知。在以往的小巷子里,麥夫魯特雖然是以緩慢的節奏在漫游,但是那時他至少還保有對周圍空間的掌控權,他和父親一起在街頭叫賣缽扎,他們并不需要為旁人的冷嘲熱諷而惶恐不安;在西化后的伊斯坦布爾,麥夫魯特在相同的街道空間卻喪失了曾經他所擁有的掌控感,那些“門口寫著‘小販免進的新建高層公寓樓”[3]121成了他自由流動的障礙物,正如帕慕克所言,“無目的的漫步也有它的界限”[5]213。在空間經驗不斷推進的過程中,主人公對時間距離的感知也愈加深刻。在實際存在的空間形態變化的背后,是麥夫魯特在城市的變遷過程中體會到的無盡的辛酸和委屈,是對遙不可知的未來感到迷惘,是在動蕩不定的人生漩渦中體味到的無邊的孤獨,生存空間的轉變承載著麥夫魯特生活的悲歡離合及生命體驗。至此,麥夫魯特的人生軌跡儼然伴隨著他的自我忖度,隨著小說中空間發生的細微變化,他在一步步地完成屬于自己的內省或內化的修行,最終,精神意識演變在麥夫魯特的靈魂深處打上了烙印。
四、結語
綜上,時間的空間化記敘已經成為小說的一條敘事暗線,在時間綿延的基礎上增添了空間的延伸,豐富了文本世界本身內在的表現力。帕慕克借助不同敘事視角在并置交融的語境下的互相碰撞與生發,賦予空間以更廣闊的延伸性,完成了時間的空間化的藝術呈現。最終,空間的延展抵抗歷史時間的壓縮,這也是文本空間感的深度所在。
進一步而言,時間的空間化敘述也是作者聲音的漂浮和嵌入,隱匿著帕慕克的個人意識。麥夫魯特在伊斯坦布爾街道漫游時所經歷的接二連三的自我分裂與自我抗爭也是帕慕克本人內心的掙扎。小說中,蘇菲神秘主義導引著麥夫魯特突破既有實體空間的束縛,以此獲得新生的力量。在現實歷史語境下,這也寄寓了帕慕克有關解除居民在伊斯坦布爾城市的話語禁忌和追求本我與自由的愿景。帕慕克的時間的空間化敘事使得自我在不同空間的碰撞帶來的矛盾運動中獲得充分展示的同時,為我們展示了溫暖而堅韌的底層人物事跡。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街道,既是囚牢,也是曠野,并且,這是一條通往永恒的街道。
參考文獻:
[1]塔迪埃.普魯斯特和小說 論《追憶逝水年華》中的小說形式與技巧[M].桂裕芳,王森,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224.
[2]袁超,李建華.論空間權力化[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4(6):72-77.
[3]帕慕克.我腦袋里的怪東西[M].陳竹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4]程錫麟.敘事理論的空間轉向——敘事空間理論概述[J].江西社會科學,2007(11):24-35.
[5]帕慕克.別樣的色彩 關于生活、藝術、書籍與城市[M].宗笑飛,林邊水,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作者簡介:林曼萍,廣州華商學院文學院教師。研究方向:文藝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