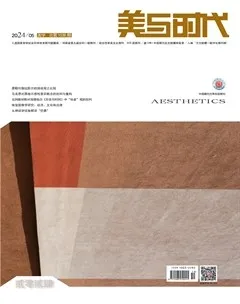通俗敘事的新時(shí)代現(xiàn)實(shí)題材創(chuàng)作變奏


摘? 要:文牧野執(zhí)導(dǎo)的兩部現(xiàn)實(shí)題材長(zhǎng)片在文本建構(gòu)中都采用了通俗敘事的模式。影片的具體創(chuàng)作繼承了華語(yǔ)電影通俗劇的敘事傳統(tǒng),并將當(dāng)下的社會(huì)意識(shí)融入其中,使通俗敘事呈現(xiàn)出了屬于新時(shí)代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表征。同時(shí),從文牧野的電影創(chuàng)作中還可看到通俗敘事在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題材電影創(chuàng)作中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讓影片可于商業(yè)類型化、現(xiàn)實(shí)主義表現(xiàn)和主流意識(shí)認(rèn)可這三者間尋得平衡點(diǎn),這也為當(dāng)下中國(guó)影人提供了一定的創(chuàng)作啟示。
關(guān)鍵詞:文牧野;現(xiàn)實(shí)題材電影;通俗敘事;我不是藥神;奇跡·笨小孩
文牧野是當(dāng)下中國(guó)影壇中出現(xiàn)的一位新銳導(dǎo)演,截止到2023年,他獨(dú)立執(zhí)導(dǎo)并參與編劇的電影長(zhǎng)片共有《我不是藥神》與《奇跡·笨小孩》兩部作品。文牧野的這兩部電影均為現(xiàn)實(shí)題材作品,劇作中體現(xiàn)出極強(qiáng)的社會(huì)意識(shí)。這種極具現(xiàn)實(shí)主義色彩的創(chuàng)作在使影片收獲優(yōu)異票房的同時(shí),也受到了當(dāng)前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高度認(rèn)可。若細(xì)觀文牧野這兩部現(xiàn)實(shí)題材作品,可看到影片在文本創(chuàng)作中對(duì)華語(yǔ)電影通俗劇的敘事傳統(tǒng)所進(jìn)行的沿用與創(chuàng)新。
“通俗劇”又名“情節(jié)劇”,本是西方的一種戲劇形式,后流變?yōu)橐环N劇作的敘事范式,因此亦可用以指稱運(yùn)用這一方法進(jìn)行創(chuàng)作的影視作品。彼得·布魯斯將其特點(diǎn)總結(jié)為“大喜大悲表現(xiàn)夸張并善惡分明”[1]。通俗劇的敘事模式隨著好萊塢情節(jié)劇電影傳入中國(guó),對(duì)中國(guó)早期的“影戲”創(chuàng)作起到了一定的影響。中國(guó)早期電影創(chuàng)作者在這一模式的創(chuàng)作成規(guī)中融入了中國(guó)的傳統(tǒng)文化,使其可實(shí)現(xiàn)一定的社會(huì)教化功能,華語(yǔ)電影也由此形成了具有民族性的通俗敘事傳統(tǒng)。
文牧野的兩部現(xiàn)實(shí)題材長(zhǎng)片都采用了華語(yǔ)電影通俗劇的敘事創(chuàng)作范式。但其并非簡(jiǎn)單套用既定的通俗敘事成規(guī),而是基于當(dāng)下的新時(shí)代發(fā)展,創(chuàng)作更新這一敘事模式,使其可以更好地實(shí)現(xiàn)對(duì)當(dāng)前中國(guó)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敘事書寫。本文將在細(xì)讀《我不是藥神》和《奇跡·笨小孩》這兩部影片的基礎(chǔ)上,對(duì)文牧野現(xiàn)實(shí)題材長(zhǎng)片中的通俗敘事所呈現(xiàn)出的具體創(chuàng)作特點(diǎn)進(jìn)行探析。
一、二元對(duì)立的社會(huì)寫實(shí)性設(shè)置
二元對(duì)立是通俗敘事模式中的經(jīng)典設(shè)置,可在劇作內(nèi)建立起兩方勢(shì)力的對(duì)峙,戲劇化的矛盾沖突也便能由此展開(kāi)。在新世紀(jì)以前,華語(yǔ)電影在通俗敘事中的二元對(duì)立通常表現(xiàn)為道德上的二元對(duì)立,在創(chuàng)作中將人物分為善惡兩個(gè)陣營(yíng),在雙方的沖突與碰撞中展開(kāi)并推進(jìn)情節(jié)發(fā)展。進(jìn)入新世紀(jì)后,通俗敘事作為一種成熟的創(chuàng)作范式仍被運(yùn)用于許多華語(yǔ)電影,但單純表現(xiàn)道德上善惡二元對(duì)立的敘事設(shè)置已較少出現(xiàn),通常被置換為新舊倫理或者不同觀念的二元對(duì)立關(guān)系。在文牧野現(xiàn)實(shí)題材長(zhǎng)片的通俗敘事中,二元對(duì)立是圍繞著當(dāng)前社會(huì)邊緣人的需求與社會(huì)主流觀念及規(guī)則的對(duì)立而進(jìn)行的設(shè)置。導(dǎo)演以此讓影片直指社會(huì)發(fā)展中形成的現(xiàn)實(shí)癥結(jié),在劇作構(gòu)思之初便顯現(xiàn)出了對(duì)時(shí)代與社會(huì)的關(guān)注。
在《我不是藥神》中,影片聚焦表現(xiàn)的群體是慢粒白血病患者。患有這一慢性絕癥的病人需要購(gòu)買昂貴的藥物來(lái)維持自己的生命,可正版藥的價(jià)格不是所有家庭都能擔(dān)負(fù)得起,所以他們只能去找渠道進(jìn)購(gòu)印度仿制藥。只是這種與正版藥有相同功效的仿制藥在我國(guó)法律中被判定為假藥,而走私和銷售假藥那便更是板上釘釘?shù)倪`法犯罪行為。在這里,影片已建置出了慢粒白血病人與醫(yī)藥市場(chǎng)以及法律制度之間的對(duì)立關(guān)系。這種對(duì)立關(guān)系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慢粒白血病人購(gòu)買仿制藥在法律的角度看是錯(cuò)誤的,但這又是這些患病的普通人在經(jīng)濟(jì)與疾病的雙重壓力下的無(wú)奈之舉;醫(yī)藥市場(chǎng)中的高價(jià)藥和威嚴(yán)的法律看似是冰冷不近人情的,但這也是對(duì)醫(yī)藥研發(fā)者和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正當(dāng)保護(hù)。
電影的男主角程勇本是一個(gè)和慢粒白血病毫無(wú)關(guān)系的一個(gè)平庸的中年男人,他起初是為了賺錢才接觸到了這一罕見(jiàn)的疾病。隨著影片的敘事發(fā)展,程勇逐漸與慢粒白血病人建立起超越金錢的情感關(guān)系后,他也失控地卷入了影片一開(kāi)始就建立的二元對(duì)立,即邊緣群體的需求與主流制度的對(duì)立中。電影將程勇設(shè)為主角并從他的視點(diǎn)進(jìn)行敘事,展現(xiàn)程勇從唯利是圖的商人逐漸轉(zhuǎn)變成舍己為人的“藥神”,使觀眾也隨著程勇的蛻變,不斷感受著這個(gè)在社會(huì)中真實(shí)存在的二元對(duì)立關(guān)系的復(fù)雜性。影片中,這種二元對(duì)立最終上升為“情”與“法”的博弈,影片最后程勇因銷售仿制藥而被判入獄。看似是正規(guī)的醫(yī)藥市場(chǎng)與法律制度贏得了這場(chǎng)“貓鼠游戲”,但在程勇被押送時(shí),道路兩旁站滿了慢粒白血病人,大家都摘下口罩,對(duì)已淪為階下囚的程勇表示著他們最高的敬意,法理此時(shí)便又在人性的光輝前黯然失色。所以在影片展現(xiàn)的二元對(duì)立中,對(duì)峙的雙方在此刻的時(shí)代與社會(huì)中都是輸家。不過(guò)在結(jié)尾時(shí),影片借曹警官之口提到了高價(jià)藥的專利過(guò)期和國(guó)家醫(yī)保系統(tǒng)的完善,慢粒白血人已不再主動(dòng)去購(gòu)買仿制藥,屬于二者之間的對(duì)立關(guān)系也因此由時(shí)代和社會(huì)的進(jìn)步而消解。
《奇跡·笨小孩》的敘事在二元對(duì)立的建置整體上延續(xù)了《我不是藥神》的思路,在影片內(nèi)呈現(xiàn)出時(shí)代轉(zhuǎn)型期中,底層勞動(dòng)者在實(shí)踐中獲得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觀念與掌握一定社會(huì)資源的精英階層所普遍持有的保守發(fā)展觀念之間的對(duì)立。該片將故事的講述背景定為2013年的深圳,在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蓬勃發(fā)展的時(shí)期,這座大都市自然蘊(yùn)含著諸多關(guān)于普通人發(fā)展的可能性。影片的主要表現(xiàn)對(duì)象是一群生活在社會(huì)底層且經(jīng)濟(jì)困難的勞動(dòng)者。主角景浩是一名20歲出頭的青年,他無(wú)父無(wú)母,但妹妹患有先心病,必須盡快進(jìn)行手術(shù)。而此時(shí)的景浩無(wú)力支付高額的醫(yī)藥費(fèi),只能去社會(huì)中尋找致富的機(jī)會(huì)。功夫不負(fù)有心人,景浩發(fā)現(xiàn)了拆卸殘次機(jī)零件反售給手機(jī)公司這一在電子產(chǎn)業(yè)中的空白領(lǐng)域,想就此大干一場(chǎng)來(lái)扭轉(zhuǎn)妹妹與自己的命運(yùn)。但這畢竟是一片藍(lán)海,手機(jī)公司的經(jīng)理不愿意接受景浩的提議。影片也由此正式拉開(kāi)了兩種觀念相互較量的帷幕。在景浩的堅(jiān)持中,手機(jī)公司的老總答應(yīng)了可收購(gòu)景浩拆分好的手機(jī)零件,前提是無(wú)定金,且不達(dá)標(biāo)不付款。影片敘事到這里,看似是保守的發(fā)展觀念進(jìn)行了妥協(xié),但景浩所代表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觀念也由此開(kāi)啟了更為艱辛的自我證明之旅。
影片中,景浩聚集了一批和自己一樣生活在底層的人一同奮斗,其中有的是殘疾人士,有的是“三和大神”①,還有人曾是階下囚。但相同的是,他們和景浩一樣,都是不被主流觀念所認(rèn)可的邊緣人,若計(jì)劃成功了,他們也能夠以此向社會(huì)證明自己的存在價(jià)值。隨著電影的敘事發(fā)展,景浩因沒(méi)有資金支持,一度陷入了困窘之境,在他向手機(jī)公司老總尋求一部分定金時(shí)遭到了無(wú)情的拒絕,保守的觀念就這樣在無(wú)聲的打壓中讓新的發(fā)展契機(jī)似乎永無(wú)出頭之日。但景浩并非單打獨(dú)斗,在他絕望之時(shí),和他有著同樣處境的元件廠員工愿意繼續(xù)為景浩的設(shè)想而奮斗。就這樣,在這些社會(huì)底層勞動(dòng)者的不懈努力中,那個(gè)一度認(rèn)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最終奇跡般地完成了,景浩等人在對(duì)時(shí)代賦予的新發(fā)展契機(jī)進(jìn)行勞動(dòng)實(shí)踐后改變了自己的命運(yùn)。在影片中,創(chuàng)新的發(fā)展觀念最終勝過(guò)了時(shí)代轉(zhuǎn)型期社會(huì)中存有的保守觀念,促成了皆大歡喜的結(jié)局。這一結(jié)果看似是理所當(dāng)然的,但不可忽視的是,電影以敘事中存在的這種二元對(duì)立展現(xiàn)出了時(shí)代轉(zhuǎn)型期的社會(huì)癥候,即處在一線的底層勞動(dòng)者往往能在實(shí)踐中敏銳地把握住行業(yè)當(dāng)下的發(fā)展命脈,但遠(yuǎn)離勞動(dòng)領(lǐng)域的精英階層人士卻總對(duì)勞動(dòng)者的實(shí)踐發(fā)現(xiàn)不以為意。影片雖以“奇跡”的方式讓二者實(shí)現(xiàn)了雙贏,但在現(xiàn)實(shí)中這仍是需要人們?nèi)ニ伎嫉膯?wèn)題。
由上述可看出,文牧野現(xiàn)實(shí)題材長(zhǎng)片在采用通俗敘事進(jìn)行創(chuàng)作時(shí),有意識(shí)地以二元對(duì)立的劇作設(shè)置去呈現(xiàn)復(fù)雜多元的社會(huì)問(wèn)題及現(xiàn)象,使得影片中所存在的二元對(duì)立元素不僅為情節(jié)敘事提供戲劇化矛盾沖突。同時(shí),導(dǎo)演也實(shí)現(xiàn)了讓“敘事空間轉(zhuǎn)變成弱勢(shì)社會(huì)群體與主導(dǎo)性權(quán)力機(jī)構(gòu)進(jìn)行斗爭(zhēng)或協(xié)商的重要話語(yǔ)場(chǎng)域”[2]這一建立在華語(yǔ)電影通俗劇美學(xué)傳統(tǒng)上的敘事意義呈現(xiàn),從而表現(xiàn)出了“轉(zhuǎn)型期的中國(guó)社會(huì)的時(shí)代癥結(jié)”[3],具有著一定的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意義。
二、傳奇敘事結(jié)構(gòu)的當(dāng)下紀(jì)實(shí)性建構(gòu)
為了敘事效果的凸顯,通俗劇的敘事模式極其倚重劇作內(nèi)的情節(jié)展現(xiàn),所以會(huì)有意去建構(gòu)曲折多變的敘事框架,用此來(lái)營(yíng)造跌宕起伏的敘述效果。這也使得情節(jié)編排中出現(xiàn)了諸多關(guān)于奇遇、巧合等敘事因素的運(yùn)用,導(dǎo)致通俗劇的整體敘事結(jié)構(gòu)都會(huì)呈現(xiàn)出一種由“奇”與“巧”匯聚所形成的傳奇性。這種帶有傳奇性的敘事結(jié)構(gòu)具體在創(chuàng)作中是由人物的傳奇經(jīng)歷所進(jìn)行的建構(gòu)。文牧野的兩部現(xiàn)實(shí)題材長(zhǎng)片所運(yùn)用的通俗敘事,亦是在人物傳奇經(jīng)歷的敘事展現(xiàn)中串聯(lián)起了影片整體的敘事結(jié)構(gòu)。
電影《我不是藥神》用一句話概括,可為講述了程勇從賣印度神油為生的落魄中年商販,靠著走私販賣仿制的格列衛(wèi)逐漸成為了慢粒白血病人眼中的“藥神”的故事;《奇跡·笨小孩》則可概括為生活困窘的青年景浩靠著辦電子元件廠,攢夠了妹妹所需的高額醫(yī)藥費(fèi),并帶領(lǐng)著和自己一樣的底層勞動(dòng)者走向了成功的故事。從中便可看出兩部電影在敘事的整體結(jié)構(gòu)中都呈現(xiàn)出了傳奇的特點(diǎn)。在這兩部影片具體的敘事呈現(xiàn)中,巧合與傳奇這樣的因素亦連接起了重要的敘事情節(jié)點(diǎn)。如《我不是藥神》中,程勇因?yàn)楦赣H加重的病情和兒子的撫養(yǎng)權(quán)急需用錢,在這時(shí)患有慢粒白血病的呂受益正好出現(xiàn),想讓他代購(gòu)印度制造的仿制藥。程勇本身就熟悉印度的進(jìn)貨途徑,而呂受益也有能力找來(lái)自己的病友幫忙解決翻譯和國(guó)內(nèi)銷路問(wèn)題。再加上國(guó)內(nèi)藥販又是恰恰因?yàn)闆](méi)有上述條件所以不愿意涉足這一類藥的倒賣,于是在天時(shí)地利人和中,程勇一躍成為了印度格列衛(wèi)的代理。而最后促使他由商人變成“藥神”的契機(jī),也是在呂受益自殺、“黃毛”車禍身亡等圍繞著自己所發(fā)生的各種意外中達(dá)成的。由此,該片在情節(jié)中巧合的不斷累加中最終造就了影片整體傳奇性敘事結(jié)構(gòu)的展現(xiàn)。
《奇跡·笨小孩》同樣如此,景浩本想要靠賣翻新機(jī)來(lái)湊齊妹妹的手術(shù)費(fèi),但當(dāng)時(shí)正好趕上了國(guó)家出臺(tái)政策打擊翻新機(jī)銷售,這便促使景浩必須改變策略去另辟蹊徑。而因?yàn)榫昂票揪褪强啃奘謾C(jī)為生,所以一下子就發(fā)現(xiàn)了電子通信行業(yè)現(xiàn)存的可發(fā)展之處。在他將自己的想法最終付諸行動(dòng)的過(guò)程中,也存在著許多巧合與傳奇因素。如他想法的完整闡述是在手機(jī)公司老總坐高鐵的間隙實(shí)現(xiàn)的,他在趕路的途中卻波折不斷。按照常理景浩根本不可能出現(xiàn)在那列高鐵上,而影片也沒(méi)有具有呈現(xiàn)景浩是如何趕上的那趟高鐵,這就使得景浩成功的經(jīng)歷在最初便奠定了傳奇的基調(diào)。到最后景浩只用了兩個(gè)月就和自己的同伴們完成了全部的零件拆卸且合格率超過(guò)了85%,這雖然和他們的不懈努力有著巨大關(guān)系,可這份努力在短期內(nèi)就化為了“成功”本身就是個(gè)“奇跡”,影片也因此在敘事結(jié)構(gòu)中顯現(xiàn)著明顯的傳奇色彩。但不得不承認(rèn),這種傳奇敘事結(jié)構(gòu)雖然稍顯套路,但也使得情節(jié)的編排更為緊密有致,并由此讓影片具有了引人入勝的敘事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我不是藥神》和《奇跡·笨小孩》這兩部影片所呈現(xiàn)出的傳奇敘事結(jié)構(gòu)在進(jìn)行創(chuàng)作建構(gòu)時(shí),背后都有著來(lái)自于現(xiàn)實(shí)的推力。《我不是藥神》是根據(jù)真實(shí)事件改編,影片男主角程勇的原型人物陸勇在現(xiàn)實(shí)中就是曾靠仿制藥維持生活的慢粒白血病患者,他同時(shí)也在無(wú)償?shù)貛椭约旱牟∮眩敲逼鋵?shí)的“藥神”。圍繞他所引發(fā)的“陸勇案”也轟動(dòng)一時(shí),300位慢粒白血病患者自愿為他寫聯(lián)名信向法院請(qǐng)?jiān)福罱K司法機(jī)關(guān)以陸勇沒(méi)有靠仿制藥盈利和沒(méi)有故意危害過(guò)他人健康為由對(duì)他免予司法起訴。這一事件也間接推動(dòng)了中國(guó)抗癌藥物列入醫(yī)保。陸勇不僅由此成為當(dāng)代現(xiàn)實(shí)中傳奇人物,他同時(shí)也為當(dāng)下社會(huì)創(chuàng)造了屬于這個(gè)時(shí)代的傳奇。《奇跡·笨小孩》雖然沒(méi)有原型,但它將鏡頭聚焦于新時(shí)代生活在深圳的普通勞動(dòng)人民,不僅讓勞動(dòng)者的形象久違地出現(xiàn)在大銀幕上,也展現(xiàn)著這個(gè)時(shí)代中勞動(dòng)者身上所具有的奮斗精神。同時(shí)不可忽視的是,電影也由此表現(xiàn)了深圳這一由改革開(kāi)放而崛起的前沿都市,在當(dāng)下時(shí)代中發(fā)展的每一步,都與無(wú)數(shù)在這座城市奮斗的人息息相關(guān)。所以影片中所呈現(xiàn)出的傳奇色彩既來(lái)源于當(dāng)下的新時(shí)代的新發(fā)展,也來(lái)自每一位于當(dāng)下敢于創(chuàng)造奇跡的普通勞動(dòng)者,這便賦予了電影敘事結(jié)構(gòu)中的傳奇性以現(xiàn)實(shí)的底色。
通俗敘事在被接受為中國(guó)早期電影的“影戲觀”后逐步實(shí)現(xiàn)了其在中國(guó)的在地性創(chuàng)作模式[4]。華語(yǔ)電影的通俗敘事在具體創(chuàng)作上將中國(guó)文化、尤其是傳統(tǒng)儒道的審美追求融入好萊塢情節(jié)劇的通俗框架中,以達(dá)到文以載道的中國(guó)式創(chuàng)作理想。由此,華語(yǔ)電影的通俗敘事在具有傳奇性的敘事框架建構(gòu)中也會(huì)與“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出現(xiàn)的各種政治性話語(yǔ)實(shí)踐緊密相連”[2],顯現(xiàn)出“家國(guó)同構(gòu)”的特點(diǎn)。文牧野的兩部現(xiàn)實(shí)題材作品也是由通俗敘事在影片中實(shí)現(xiàn)了“家國(guó)同構(gòu)”這一屬于華語(yǔ)電影傳統(tǒng)的家國(guó)敘事表達(dá),并且賦予其以一定的紀(jì)實(shí)感,在銀幕上呈現(xiàn)出當(dāng)下正在發(fā)生著的歷史。這使得其通俗敘事結(jié)構(gòu)中所具有的傳奇性并不是只是片中人物的個(gè)人傳奇,同時(shí)也是國(guó)家和人民在當(dāng)下的新時(shí)代中所真實(shí)書寫下的傳奇。就這樣,文牧野的兩部現(xiàn)實(shí)題材長(zhǎng)片在通俗敘事的結(jié)構(gòu)中形成了傳奇為表、現(xiàn)實(shí)為里的創(chuàng)作特點(diǎn)。這使現(xiàn)實(shí)題材電影實(shí)現(xiàn)了更為“通俗”的敘事,同時(shí)也讓通俗敘事呈現(xiàn)出了具有當(dāng)下紀(jì)實(shí)性的“家國(guó)同構(gòu)”書寫,拓寬了這一傳統(tǒng)敘事模式的表現(xiàn)空間。
三、煽情效果對(duì)時(shí)代
“痛點(diǎn)”與“暖色”的雙重呈現(xiàn)
通俗敘事使劇作展現(xiàn)出的引人入勝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來(lái)源于這一敘事模式中煽情效果的制造,即在進(jìn)行相應(yīng)創(chuàng)作時(shí)將情感效果的營(yíng)造直接注入到對(duì)劇作情節(jié)的編排中,以此來(lái)不斷刺激觀眾情緒。在華語(yǔ)電影的通俗敘事傳統(tǒng)中,一般是用“苦情戲”的方式在敘事中實(shí)現(xiàn)對(duì)煽情效果的營(yíng)造。《我不是藥神》和《奇跡·笨小孩》在敘事中分別有著苦情戲的創(chuàng)作展現(xiàn),這種“苦情”的情節(jié)在煽動(dòng)觀眾的情緒之余,也指向著當(dāng)下時(shí)代發(fā)展中我國(guó)社會(huì)所出現(xiàn)的一些裂痕。
在《我不是藥神》中,影片并未從一開(kāi)始就在敘事中呈現(xiàn)“苦情”的因素。電影的前半部分在劇作上加入了諸多喜劇元素,展現(xiàn)程勇和呂受益等人在齊心協(xié)作中拿下印度格列寧代理權(quán)的過(guò)程。在這一段的敘事中,屬于慢粒白血病人身上的那份沉重感在敘事的喜劇性呈現(xiàn)中有所緩解。呂受益、黃毛、牧師以及思慧等角色充分展現(xiàn)出了他們自身除去疾病之外的自我個(gè)性,源自疾病的威脅也因他們各自困境的暫時(shí)解決而在情節(jié)敘述中有所遮蔽。但疾病這層因素一直存在,也是劇作在敘事一開(kāi)始就埋下的“苦情”種子。所以當(dāng)喜劇因素在敘事中退場(chǎng)后,“苦情戲”便以摧枯拉朽之勢(shì)席卷了劇作情節(jié),它所營(yíng)造出的悲情效果也因曾經(jīng)美好的破碎而顯得更為尖銳。在影片后半段中,因?yàn)槌逃碌姆艞壌頇?quán),間接導(dǎo)致了呂受益病情的惡化。程勇再見(jiàn)到呂受益時(shí),呂受益已因化療掉光了頭發(fā),躺在病床上骨瘦如柴,但他仍和與程勇初次見(jiàn)面時(shí)一樣,臉上帶著笑容,給程勇遞來(lái)一個(gè)橘子,但一切已物是人非。這種具有前后悲喜反差的苦情戲設(shè)置極具戲劇張力,以強(qiáng)烈的煽情效果沖擊著觀眾的心靈。同樣的,影片中還有著像黃毛為保程勇而車禍身亡,慢粒白血病老人在警察面前聲淚俱下地講述出自己想活命的初衷,程勇被判入獄時(shí)慢粒病人的長(zhǎng)街相送等極具苦情色彩的情節(jié)設(shè)置,而這種苦情的表現(xiàn)始終繞不過(guò)疾病與法律制度之間的沖突。可見(jiàn),影片中苦情戲在營(yíng)造著煽情效果的同時(shí)也以現(xiàn)實(shí)的筆觸直擊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所存在的痛點(diǎn)。
另一部作品《奇跡·笨小孩》則在最初就于敘事中渲染“苦情”氛圍。片中的男主角景浩和妹妹是父親失蹤、母親離世的孤兒,而孤兒這一元素在通俗劇的敘事創(chuàng)作中也具有著典型性。景浩兄妹倆在大都市中相依為命,景浩靠著修手機(jī)維持著兩個(gè)人的生活。因妹妹有先心病急需手術(shù),身為哥哥的景浩只能想盡一切方法來(lái)幫妹妹湊齊手術(shù)費(fèi),電影的主線也就是從這種“苦情”的表現(xiàn)中展開(kāi)了敘事。該片的主體敘事部分基本上是圍繞著苦情戲而進(jìn)行的。先是手機(jī)公司那邊對(duì)景浩提出了極度苛刻的要求,讓景浩壓上全部希望的計(jì)劃變成了一場(chǎng)豪賭。后又表現(xiàn)了發(fā)不起工資的景浩即使手指骨折也要堅(jiān)持去進(jìn)行高空作業(yè),因拖欠租金太久景浩的元件廠被房東收回,所有拆卸好的零件都埋在了板房下等劇情。而在這期間,景浩基本上一個(gè)人扛下了所有,再難也會(huì)去照顧妹妹,對(duì)妹妹永遠(yuǎn)保持著微笑,妹妹也對(duì)景浩說(shuō)出了“等我長(zhǎng)大后換我照顧你”。兄妹兩人在苦難中的相濡以沫將影片敘事中的悲情色彩推至了高峰,影片也在這種極具煽情效果的通俗敘事中展現(xiàn)出了生活在底層的勞動(dòng)者在奮斗中所經(jīng)受的苦難。
但文牧野現(xiàn)實(shí)題材電影中的“苦情戲”所營(yíng)造的煽情效果并不只是單對(duì)時(shí)代轉(zhuǎn)型期的社會(huì)痛點(diǎn)進(jìn)行表現(xiàn),同時(shí)也留有溫情的展現(xiàn)。而這恰似灑在社會(huì)裂痕上的陽(yáng)光,寓意為希望。《我不是藥神》中,曹警官一角是社會(huì)正義的象征。作為神油和仿制藥走私犯的程勇與曹警官最初的關(guān)系是水火不容的,此時(shí)的曹警官一直堅(jiān)持著自己司法正義的立場(chǎng)。但在程勇后期轉(zhuǎn)變成為無(wú)償幫助白血病人的“藥神”后,曹警官動(dòng)搖了。影片中,有兩次極具煽情效果的情節(jié)都有曹警官的參與。先是在派出所,一位病患老太卑微地請(qǐng)求曹警官不要再追查仿制藥,后是在黃毛因車禍去世后,程勇悲痛地質(zhì)問(wèn)曹警官黃毛想活著有什么罪。在這兩場(chǎng)“苦情戲”后,曹警官對(duì)程勇的態(tài)度也有了直接的變化。他知道了程勇就是警局在捕的假藥販子,但他沒(méi)有向上級(jí)匯報(bào),他選擇了自己心中的正義。這也使影片于苦情戲中流露出了幾絲溫情,而這種溫情背后正是代表著社會(huì)未來(lái)進(jìn)步的希望。在電影最后,曹警官已與程勇冰釋前嫌,在五年后接程勇出獄,將現(xiàn)在格列衛(wèi)已入醫(yī)保的消息告訴了曾經(jīng)的“藥神”程勇,這在影片敘事中也象征著幾年前曾經(jīng)在社會(huì)中出現(xiàn)的那一縷希望之光如今已經(jīng)隨著時(shí)代與社會(huì)的發(fā)展照進(jìn)了現(xiàn)實(shí)。
在《奇跡·笨小孩》中,苦情戲在煽情效果中營(yíng)造出的溫情與希望相較于《我不是藥神》便明顯很多。影片整體雖都圍繞著“苦情戲”展開(kāi)敘事,但因片中“奇跡小隊(duì)”的每位成員都有著頑強(qiáng)抗?fàn)幍木瘢沟糜捌阡秩颈楹螅杂兄鴾厍榕c希望的浮現(xiàn)。如在片中的一段敘事情節(jié)中,因工作而失聰?shù)耐舸好繁凰瓉?lái)工作過(guò)的電子廠逼著和解。爭(zhēng)執(zhí)期間,她的助聽(tīng)器直接被工廠派來(lái)的人打碎。就當(dāng)悲情的氛圍已呼之欲出時(shí),“奇跡小隊(duì)”的其他人路見(jiàn)不平拔刀相助,幫春梅出了氣。此時(shí)關(guān)于這群在底層奮斗者之間的溫情展現(xiàn),已經(jīng)蓋過(guò)了個(gè)體苦難的呈現(xiàn)。類似的,在景浩發(fā)不起工資,廠房被收回,徹底走投無(wú)路步入黑暗時(shí)刻時(shí),“奇跡小隊(duì)”的成員們依舊對(duì)他不離不棄。所有人都愿意不拿工資,陪他一同完成手機(jī)公司開(kāi)出的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在這里,“苦情戲”所煽動(dòng)的溫情再次壓過(guò)了悲情。在影片最后,景浩等人拆卸的零件通過(guò)了質(zhì)檢,獲得了老總的認(rèn)可。此前“苦情戲”營(yíng)造的悲情在此刻被他們親手創(chuàng)造的“奇跡”所消解,使影片最終呈現(xiàn)出了溫暖的氣質(zhì)。該片的敘事也由此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當(dāng)下無(wú)數(shù)底層勞動(dòng)者所具有的奮斗精神的呈現(xiàn),而這正是當(dāng)下社會(huì)發(fā)展的驅(qū)動(dòng)力。電影在敘事中肯定了這種由時(shí)代精神所創(chuàng)造的奇跡,展現(xiàn)出了當(dāng)下時(shí)代所蘊(yùn)含著能消解苦難的無(wú)限希望。
由此,文牧野現(xiàn)實(shí)題材長(zhǎng)片于通俗敘事中,不僅以“苦情戲”所具有的煽情效果指出了時(shí)代與社會(huì)在發(fā)展中所存在的不足之處,同時(shí)也會(huì)表現(xiàn)并傳遞出當(dāng)下社會(huì)中的希望與溫暖。這就令其作品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傳達(dá)不會(huì)落入片面化,而這一創(chuàng)作方式也使通俗敘事傳統(tǒng)中由“苦情戲”所達(dá)到的煽情效果更具層次,呈現(xiàn)出了對(duì)當(dāng)下社會(huì)的思辨色彩。
四、結(jié)語(yǔ)
通俗敘事作為華語(yǔ)電影在百年發(fā)展歷程中所形成的一種創(chuàng)作傳統(tǒng),不但有著一套穩(wěn)定的創(chuàng)作系統(tǒng),同時(shí)還具有“通俗現(xiàn)代性”的重要特點(diǎn),即“其表征在不同時(shí)代可以不斷地進(jìn)行轉(zhuǎn)化”[5]。文牧野的兩部現(xiàn)實(shí)題材長(zhǎng)片在敘事中正體現(xiàn)著通俗敘事的這一特點(diǎn),它將存在于當(dāng)下的社會(huì)意識(shí)融入了通俗敘事的創(chuàng)作中,更新了通俗敘事的劇作效果,賦予其新時(shí)代的創(chuàng)作內(nèi)涵。同時(shí),通俗敘事也以固有的“通俗性”,成為了這兩部作品中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表達(dá)、類型化與主流意識(shí)呈現(xiàn)之間的有效粘合劑,使現(xiàn)實(shí)題材電影既可實(shí)現(xiàn)商業(yè)類型化創(chuàng)作,也能得到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認(rèn)可。由此,通過(guò)文牧野現(xiàn)實(shí)題材長(zhǎng)片的敘事創(chuàng)作,可看到現(xiàn)實(shí)題材電影與通俗敘事耦合所迸發(fā)出的屬于華語(yǔ)電影創(chuàng)作的新活力,這亦為當(dāng)下中國(guó)影人“講好中國(guó)故事”提供了一定創(chuàng)作路徑。
注釋:
①“三和大神”指在深圳三和人力市場(chǎng)周邊產(chǎn)生的一種新一代農(nóng)民工群體,他們身背債務(wù),與家人鮮有往來(lái),靠著低廉的生活成本與日結(jié)的薪資過(guò)著工作一天玩三天的生活。參考袁潯杰,羅強(qiáng)《脫軌的“三和大神”》。
參考文獻(xiàn):
[1]汪方華.通俗電視劇美學(xué):當(dāng)代中國(guó)文化語(yǔ)境中的通俗電視劇[M].汕頭:汕頭大學(xué)出版社,2005:67.
[2]馬寧.從寓言民族到類型共和:中國(guó)通俗劇電影的緣起與轉(zhuǎn)變(1897-1937)[M].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1:6.
[3]路文.文牧野導(dǎo)演的符號(hào)景觀與電影美學(xué)[J].電影文學(xué),2022(13):99-102.
[4]黃望莉,毛旭峰.海派主流電影敘事:通俗劇的命名及其通約性[J].上海藝術(shù)評(píng)論,2022(5):9-12.
[5]黃望莉.《奇跡·笨小孩》:用通俗敘事傳遞時(shí)代強(qiáng)音[N].中國(guó)電影報(bào),2022-02-16(002).
作者簡(jiǎn)介:楊茉,上海大學(xué)上海電影學(xué)院電影學(xué)專業(yè)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電影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