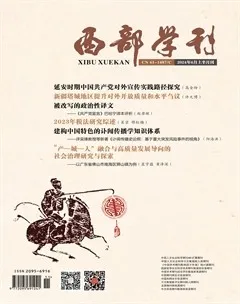“圣人”與“哲學王”:孔子與柏拉圖理想人格思想比較
摘要:孔子和柏拉圖是東西方哲學的奠基人物,他們分別構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圣人”和“哲學王”。“圣人”是個人修養的最高境界,“哲學王”是擁有真知識的人。兩種理想人格的相同點在于,“圣人”和“哲學王”都是國家的統治者,其意在實現的政治目標都是構建理想的和諧社會;兩種理想人格的不同之處在于,“圣人”的本體論基礎是“道”,“哲學王”的本體論基礎是“善”的理念;“圣人”的塑造方式是“志”和“學”,“哲學王”的塑造方式是“優生學”和“回憶”。不論何種理想人格,都為后世進行人格修養和營造和諧的社會環境提供了理論基礎。
關鍵詞:孔子;柏拉圖;理想人格;比較研究
中圖分類號:B222.2;B502.2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4)11-0140-04
“Sages” and “Philosopher-King”:
A Comparison of Confucius and Platos Ideal Personality Thoughts
Jin Rui
(School of Marxism,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Abstract: Confucius and Plato were the founder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y constructed their ideal personalities— “sages” and “philosopher-king” respectively. A “saint”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personal cultivation, and a “philosopher-king” is a person who possesses true knowledge.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wo ideal personalities lies in the fact that both the “sage” and the “philosopher-king” are the rulers of the state, and the political goal to be achieved is to build an ideal harmonious societ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deal personalities is that the ontological basis of the “sage” personality is “Tao”, and the ontological basis of the “philosopher-king” personality is the idea of “goodness”; the “sage” is shaped by “zhi” and “learning”, and the “philosopher-king” is shaped by “eugenics” and “memory”. No matter what kind of ideal personality, it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cultivate their personality and create a harmonious social environment.
Keywords: Confucius; Plato; ideal personality; comparative studies
孔子和柏拉圖都在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內構建了最高的理想人格,“圣人”和“哲學王”是他們各自構建的理想人格。“圣人”和“哲學王”的概念是什么?它們有何異同?對兩者概念和異同的探析,能夠推進中西方哲學思想的交流。
一、“圣人”與“哲學王”的概念
“圣人”這一概念,是孔子理想人格思想的最高體現。何為圣人?孔子曰:“所謂圣人者,德合于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識其鄰。此謂圣人也。”①由此可知,圣人的品德應當與天地之道相符合,與天地之道合而為一。可以說,圣人是孔子心目中真善美的化身。
圣人有何種特點?《論語》中有這樣的表述:“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②“仁”是孔子政治哲學的核心,“圣”比“仁”更高,是更高的德。在這里,“圣”不僅僅是個人修養的最高境界,更是最高的政治功業,連堯舜都難以實現。
“哲學王”這一概念是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的理想人格。柏拉圖認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現實世界構成,前者是后者存在的依據,理念世界里的事物才是本質事物,現實世界中的事物通過“分有”理念而產生。只有能夠突破思想桎梏的人才能認識到本質事物,獲得真知識,成為“哲學王”。
二、“圣人”和“哲學家”的相同點比較
(一)社會地位的相似性:國家的最高統治者
孔子生活在中國古代的春秋末期,此時周王室的實力已經大不如前,政治局勢由大一統轉向諸侯混戰;奴隸主貴族的勢力削弱,新興封建地主的勢力增強,階級矛盾激化;諸侯割據,禮崩樂壞,社會狀況很不穩定。孔子追求穩定的社會關系,主張恢復周禮。他曾在魯國擔任中都宰、司空和大司寇,意圖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然而,魯國國君沉溺于游樂后便對孔子的主張不理不睬。孔子周游列國,卻發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因與統治者的思想不符合,難以被采納。在這種現實背景下,孔子熱切呼吁一個理想君主的出現,他能夠帶來社會的穩定和人民的安居樂業,“圣人”這一理想化人格和理想的君主就應運而生了。
在孔子思想體系中,圣人觀念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他對于“圣人”的定義非常苛刻,只有上古三代的先王才能夠稱得上是圣人。在他的觀念中,圣人皆為王者,他尊崇的周制是“先王之道”,又以“先王之道”為基礎構建了更高水準的“圣人之德”[1]。可以說,圣人具有最高的政治地位,簡而言之就是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是權力與知識、道德的結合。
柏拉圖出生于古希臘雅典城邦的一個貴族家庭,是蘇格拉底最杰出的學生。這時候的古希臘城邦林立,雅典城邦在波斯戰爭中取得了霸主地位,但又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失去了霸主地位,迅速衰落下去。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逐漸被專制制度取代,“三十寡頭統治”了雅典,民主政治轉化為暴徒政治,蘇格拉底因“不敬神明”被處死。經歷了這些的柏拉圖認為,一切國家都治理得不好,他意圖借助好的機遇對國家進行變革,這促使了柏拉圖“哲學王”理念的誕生。他認為,一個完美的國家應該是哲學家和統治者融為一體的,這是一個叫“理想國”的完美國度,它的統治者則被稱為“哲學王”。
(二)相似的政治目標:“大同”和“理想國”
《禮記》描述了孔子心目中理想的社會形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孔子設想,“圣人”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其樂融融的“大同”社會會出現,選賢舉能代替了任人唯親,人人各有所用,社會風氣良好。
柏拉圖在自己的《理想國》中構想了“哲學王”統治下的理想城邦——理想國的圖景。他認為整個世界是由“善”的理念統轄的體系,掌握了“善”的理念的哲學家應當成為國家的統治者。國家是放大的個人,柏拉圖將人的靈魂的組成成分劃分為三種:理性、意志和欲望。這三個部分各有德性,分別是智慧、勇敢和節制。當靈魂的每個部分都分別恪守自己的德性時,靈魂就達到了一種和諧狀態,也就具有了最高的德性:正義。與個人靈魂的三個部分相對應,國家應該有三個社會階級,分別為統治者、保衛者和勞動者,這三者各司其職時,遵循“正義”原則的理想國便誕生了。遵循智慧、勇敢、節制、正義這四種德性而運行的理想國,便是柏拉圖“哲學王”思想提出的政治目標。
三、孔子與柏拉圖理想人格思想的不同之處
(一)本體論基礎和治世方式:“道”和“善”的理念
孔子的理想人格思想是以“道”為核心展開的,“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道”處于孔子哲學思想中形而上學的本體論層面,是最高的范疇。“仁”和“禮”分別作為“道”的內在經驗層面和外在經驗層面,共同構成了“道”的形而下基礎。“道”之發用具體地落實在復禮和歸仁兩個方面[2]。“仁”與“禮”各自為對方存在的前提,“禮”來源于“仁”,復禮的社會需要以仁心為前提。
孔子認為,世間最根本的終極價值是人自身的生命存在,特別強調生命的自然形態應該向價值形態超越。所以他認為人們求“道”應該建立一個終極目標,即達到“圣人”人格,通過“志于道”“志于學”的方式去追求目標的實現。一方面,“道”引導人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另一方面,圣人如果為“道”,實行道德教化,那么“復禮”的實現指日可待,和諧的人倫生活秩序就能得以實現。有了“道”作為孔子哲學的本體論基礎,“仁政”“復禮”就成為圣人治理國家的方法。對于仁,他有著這樣的表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論語·子路》),王者實現仁政需要一世的時間。他又講“仁者愛人”,將“仁”直接定義為愛人。對于“圣”與“仁”,《論語》認為王者追求仁政,“圣”又比“仁”的層次更高,所以圣人治國的方法是施行仁政。“仁心”的培養和造就依賴于“禮”,所以孔子認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圣人與民眾之間具有相同的人性論基礎,其不同于人是后天努力的結果,各階級之間能夠憑借教化互聯互通[3]。
所以,“道”是孔子哲學觀中的最本質思想,而且“求道”這一方法能夠構建“圣人”理想人格和仁禮結合的社會生活秩序,“道”是孔子“圣人”思想構成的本體論基礎。“仁”和“禮”是“圣人”治國的方略,也可以說孔子期冀的圣人治國方法是以“德”治國,帶有明顯的以人為本的“人治”色彩。
柏拉圖認為,“理念”涵蓋世界的一切方面,不僅是獨立于事物的實在本體,也是獨立于頭腦的客觀精神,現實事物通過對理念的“分有”而出現。“善”是整個世界的最高原則。“關于正義等的知識,只有從它演繹出來的才是有用和有益的”“(善的理念)的確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確者和美者的原因”出自《理想國》。。正如前文所說,一個城邦具有與靈魂相同的三個部分,分別是智慧、勇敢、節制,對應到城邦中的社會階級,分別是統治者、保衛者和勞動者,這三個階級分別是金、銀、銅鐵三種材料制作而成的。三者各司其職,一個符合“正義”原則的理想國就誕生了。理想國中等級森嚴,這種等級劃分完全將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隔斷開來,各等級之間不可能相互逾越。而且,一個由哲學王統治的城邦應該是四德統一的,它們之間可以互相作用[4]。與孔子的“仁政”思想相比,柏拉圖對城邦中的人作了更加嚴格的等級劃分。這兩種理念在實踐中會形成不同的國家治理模式,孔子倡導的仁政更注重道德的感化,柏拉圖的等級制度則強調秩序和規則。
(二)理想人格的塑造方式:“志”“學”與“回憶”
普通人要如何通過自己的修養而成圣?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出自《論語·為政》。。“志”與“學”在成圣的過程中占據重要地位。“志”指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學”指的是后天的努力和學習,它的對象即以“仁”為核心的政治哲學,這段話就是孔子對圣人的修養階段的描述。
但是,在孔子看來,“圣人吾不得而久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論語·述而》),圣人境界在現實世界中是難以達到的,但是通過自己的努力修養,人有可能達到“君子”這一標準。不僅如此,孔子否認自己能夠達到圣的境界。太宰曾問子貢:孔子“多能”,能否稱得上“圣”?孔子認為自己“多能”只是因為“少也賤”,并不能被稱為“圣”,成“圣”的一個必要條件是上天賜予賢明君主的統治地位。也就是說,“圣”是與神秘的天道結合在一起的,“天道”是上天賦予的能力。自己僅僅有“德”無“位”,不能“博施于民而能濟眾”,是不能被稱為“圣”的。他還認為君子應該“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更是將“圣人”提到了一個新高度。不過,孔子倡導“內修圣人之德”,主張后天的自我修養能夠使一個人的道德修養趨同于圣人。總的來說,孔子認為可以通過“學”的方式使人無限趨同于“圣人”,但是很難真正達到“圣人”的境界。
柏拉圖認為,“善”的理念是引領人們進行人格修養的指南針。整個世界是一個至善的、絕對公正的神創造出來的,而理想人格的目標就是“變得像神”。“靈魂”是貫穿于“哲學王”思想的核心觀念。我們的靈魂在進入肉體之前居住在“理念世界”里,本具有關于各種理念的知識,因為后天依附于肉體而被遮蔽了。想要使得靈魂回到原本的澄澈狀態,就要通過“學習”恢復靈魂的本性,使之重新變得超凡脫俗。這種“學習”在柏拉圖看來是“回憶”的過程,而回憶是一個不斷上升的過程,靈魂需要通過不斷地“轉向”,才能夠使知識呈現為一個線性的上升過程。
如果能彌補靈魂中“無知”的缺陷,最終能夠看到“善的相”,從而擁有真正的知識,才能夠達到正義和至善的境界,變得“美善”。要達到這個目的,柏拉圖首先主張,通過優生學原理由國家統一安排優秀男女的結合,他們的孩子也交由國家撫養。然后,讓這些青少年學習基本的“四藝”——數學、幾何學、天象學、諧音學,用這些課程鍛煉他們的基本能力,再讓他們學習辯證法,對哲學知識的學習可以促進努斯(來源于古希臘,其本意是指心靈。編者注)的覺醒,促使他們實現靈魂的轉向,實現迷狂和愛欲的升華。不過,“迷狂”和“愛欲”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迷狂”是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時突然實現的飛躍,“愛欲”沒有被柏拉圖明說,但是這兩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神的恩賜”。完成了這些步驟以后,一個正義和至善的哲學王就出現了——很顯然,柏拉圖認為哲學王可以通過后天塑造的方式形成,雖然學習的過程充滿艱辛,但是理想國中依然有真哲學家會誕生。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便是這樣一位“美善”的人[5]。
總的來看,孔子的“圣人”思想和柏拉圖的“哲學王”思想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它們的相似性在于,它們的政治目標都是在戰亂的社會背景中建立一個和平的國度,并為這個國家尋得一位賢明的君主。它們的相異性在于,“圣人”思想的本體論基礎是“道”,這要求人們以“道”為追求目標,尋求“仁”與“禮”的結合,奠定了古代中國“人治”的基礎。柏拉圖以“善”的理念為本體論基礎,構建了等級森嚴的治國系統,是古代西方“法治”的前身。要想達到“圣人”的標準,需要通過“志”和“學”的方法進行自身修養,但是,因為“圣人”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君王,統治地位由上天賜予,所以一般人不能達到“圣人”境界,只能達到“君子”境界。“哲學王”是可以通過后天的努力達到的,優秀的青少年由優生學的方法被挑選出,然后被教授“四藝”和辯證法,雖然達到“哲學王”的標準還需要努斯的覺醒和愛欲的迷狂,但是這些條件并不是無法達到的,所以“哲學王”是可以通過自身后天的修養培養起來的。
四、孔子和柏拉圖理想人格思想的啟示
(一)加強自身人格修養
雖然孔子和柏拉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有很多不同之處,但是他們都強調后天修養的重要性。無論是追求“圣人”還是“哲學王”的境界,都需要不斷地學習和自我提升。正如孔子所說,“志于學”是成為圣人的第一步。我們需要明確自己的人生目標,并為實現這一目標付出不懈的努力。不僅如此,加強自身人格修養還要采取正確的方式。柏拉圖認為人的靈魂是通過“轉向”而認識到事物本質的,轉向即為反思和再反思。在現代社會,我們要結合自身實際,不斷學習、實踐、反思,以實現自身價值,為社會作出應有的貢獻。
(二)營造和諧的社會環境
孔子和柏拉圖都生活在戰亂的時代,所以他們都提出了建立理想國家并尋求理想君主的思想。他們的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那就是在動蕩不安的世界中,應該思考如何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環境。孔子提倡的“仁政”和柏拉圖的“哲學王”思想,雖然具體實踐方式不同,但都在尋求一種能夠平衡社會矛盾、實現國家安寧的領導力量。這對于我們今天的社會治理有著重要的啟示,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需要尋找一種能夠使社會和諧、人民安居樂業的治理模式。同時,注重道德教育和理性思維的培養,使每一個公民都能夠具備良好的道德品質和獨立思考的能力,這對于構建一個文明、和諧的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宮浩然.從“圣吾不見”到“涂人為禹”:荀子、孔子圣人觀比較[J].開封文化藝術職業學院學報,2022(6):1-3.
[2]王新華.孔子道學形而上學探本[J].湖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2):28-31,79.
[3]施凱文,梁濤.圣的起源與先秦儒家的圣人觀[J].道德與文明,2021(5):80-89.
[4]鄧向玲.四德何以為“一”?:柏拉圖《理想國》中德性關系辨析[J].現代哲學,2023(5):86-92.
[5]王璐.試論柏拉圖理想人格思想[D].徐州:江蘇師范大學,2017.
作者簡介:金睿(1999—),女,漢族,湖北黃岡人,單位為蘇州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
(責任編輯:馮小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