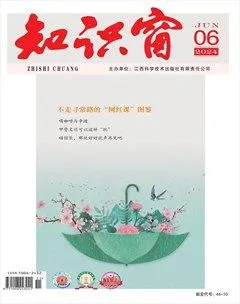閱讀不需要方法
葉燕莉
《閱讀的方法》一書分為四個章節:強勁的大腦、遙遠的地方、奇妙的創新、極致的體驗。用作者羅振宇的話說,閱讀每一章節,你都會有奇遇。我對這本書特別感興趣的是“小書展”部分,就是在正文中穿插了很多其他書里的有趣片段。閱讀這些文字的時候,我常常被打動,迫不及待地想去找原書來看。這真是一個奇妙的召喚。
羅振宇在《閱讀的方法》中提到一個觀點:閱讀時的我們“就像一個闖進游樂場的孩子,奔跑撒歡,輾轉于各個項目之間,碰到不感興趣的,轉頭就走;遇到喜愛的,就玩個不亦樂乎,單純享受玩耍帶來的快樂”。這一觀點與我們從小遵循的“有目的性的學習觀”背道而馳,但回顧我的讀書經歷,與羅振宇的觀點倒是異曲同工。
剛工作那會兒,我將全部精力都用來應對工作,讀書成了我僅存的一點娛樂。我最早任教的學校有一間圖書室,僅有幾千冊書籍,選擇性不多,我只好拿到什么讀什么。令我印象深的有《張愛玲文集》《最后一個匈奴》《霧月牛欄》等。其中,《梁實秋散文》被我借閱的次數最多。因為喜歡梁先生的淡泊和風趣,凡是沒書可看時,我就去借他的書來看看。因為相對冷門,《梁實秋散文》這本書幾乎沒人借閱,以至于再一次捧讀時,我還能看到前一次我看書夾著的小紙條。真正是“如交友般擇書,如玩樂般閱讀”。
回想那段時間,其實我過得既混亂又迷茫,閱讀這些書籍,給我補充了營養,提供了生活和成長的能量,最終使我成為心智更健全的、認知更完善的自己。
羅振宇說:“書籍的世界,不是一座山,而是一張網。”網有幾個特點,從一個節點跳向另一個節點,處處相通,沒有前后高低之分,每一個節點都可能成為樞紐。關于這點,我在近些年感觸頗深。在一次聚餐時,我吃到一盤好吃的茄子,想到劉姥姥在大觀園吃的那道“茄鲞”。我回到家又翻開《紅樓夢》第四十一回,重溫了一遍茄鲞的做法。突然,我想到一個問題,茄鲞的做法是王熙鳳說出來的,看她如數家珍的架勢,難道她會做菜?
帶著這個問題,我翻看了一個紅學家的專著《王熙鳳篇》,書中闡述了一個觀點,彼時豪門大族對女眷的管家能力、社交能力等的培養中,并不包含“下廚做飯”這一項。但以賈府貴族女眷的生活水平和見世面程度,必吃過諸多山珍海味,縱使不刻意鉆研美食,對美食也應有很好的品鑒能力。也就是說,王熙鳳夸大其詞地敘述茄鲞的做法,只是為了給劉姥姥顯擺大觀園生活的奢靡。因為真有像我一樣好奇心重的人,按照書中茄鲞的做法試做了一回,結果味道不過爾爾。看到這里,我不由會心一笑,心滿意足地合上書。
在這些年的讀寫生涯中,我經常為了找一個詞、一個句子、一個典故、一個拿不準的觀點,費勁地翻了一堆書。我有時翻開一本書就看了進去,在看得疲憊不得不停下時,卻忘了自己為什么翻開這本書,是來尋覓什么的,就像一個稀里糊涂的織網者,左邊編織幾下,右邊編織幾下,待停下來一看,居然也編織了一大片了。
羅振宇說:“不必把讀書太當一回事,任何一本書,都可以隨時翻開、隨時合上……隨便翻翻、到處戳戳,就挺棒的。”中國古人讀書,講究與自然同步,天人合一,所謂春讀詩,夏讀史,秋讀諸子,冬讀經。依我的習慣,真要讀書,什么時候都能讀,只要看得進去,哪有那么多講究。所以我認為,不把讀書太當一回事,是一種正確且務實的讀書觀。
如今的我已至人生的中途,已經實實在在地觸摸到了歲月,也于時間和經歷的縫隙里,發現了生而不得已的種種,但在工作和生活中,很多時候我仍是個迷惘的人,需要在書中挖掘活著的意趣,如同在生活的夾縫中尋找一點糖的存在。明朝詩人于謙說:“書卷多情似故人,晨昏憂樂每相親。”就把書當作一個老友吧,晨昏相伴,這已經是讀書能給予我的最好禮物了。
羅振宇自述,寫《閱讀的方法》這本書的目的,權當自己是一個敬業的導游,站在一個叫“人類偉大精神寶庫”的景點大門口,高聲吆喝:“這位客官,里邊請!”如此說,我也僅在這個景點走馬觀花了一圈,更多盛景,還需要付諸行動,努力探索。正如《閱讀的方法》最后所寫的:閱讀不需要方法,行動本身就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