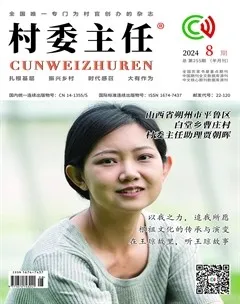長平古味
劉鳳果



“肩挑油燈漫街游,爐中黎起燒悲啼。來人傳送長平史,不吃豆腐難慰藉。”這說的正是白起豆腐。白起豆腐也稱高平燒豆腐。高平的燒豆腐是最著名、最正宗的,是高平市傳統豆腐制作技藝的典型代表,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深受當地百姓的喜愛。2009年,白起豆腐制作技藝入選山西省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燒豆腐,熱喀嚓。一塊錢,兩疙瘩。”高平的大街小巷傳遍了這樣的吆喝聲。關于高平燒豆腐,當地有這樣一段傳說。據傳,公元前260年,秦趙兩軍在長平地區對峙,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長平之戰。趙國將領趙括受其父趙奢影響,自幼熟讀兵書,每每談到排兵布陣、兵法謀略便滔滔不絕,有理有據。鑒于趙奢在戰場上英勇神武,為趙國立下了赫赫戰功,因此趙國上至君王下到百姓都對其子趙括寄予了厚望,希望他子承父業,為趙國再創戰功。
秦國崛起后,開啟一統六國的計劃。韓國是秦國進攻的對象之一,面對號稱“虎狼之師”的秦軍,韓國只能向當時唯一可與秦國對抗的趙國求助。長平之戰中,秦趙兩國皆有損傷,趙軍不敵秦軍,全軍覆滅。這一戰中的秦軍將領白起身經百戰,無一敗績。白起之名,六國聞之膽寒。然而,趙國將領卻是毫無作戰經驗,只會紙上談兵的趙括。因此,當趙王啟用趙括代替廉頗時,就已經注定了趙國的失敗。
趙軍落敗后,有超過四十萬的將士向秦軍投降,但卻被秦將白起在一日之內坑殺于長平地區的谷口村(也叫殺谷)。白起的過度暴虐激起了當地百姓的極度憎恨。長平百姓為了紀念被白起坑殺的趙國將士,便將豆腐當成白起肉,用火烤,用水煮,將豆腐渣當成白起的腦漿以蒜泥生姜調味后,與燒豆腐同食之,以泄心頭惡恨。這種因恨而產生的美食被長平人世世代代流傳下來,并稱為“白起豆腐”。因此,高平燒豆腐可謂歷史悠久。
如今,高平市谷口村有一座廟院,因其外形貌似骷髏而取名為“骷髏廟”。“骷髏廟”是迄今為止我國唯一一座紀念戰國時期將士亡靈的廟宇。高平燒豆腐做得最正宗的地方,正是谷口村,這里的每家每戶都會做燒豆腐。
用于做豆腐的大豆是高平本地黃豆,豆腐做得好不好直接關系到燒豆腐的口感。當地百姓會在前一天晚上將做豆腐所需的黃豆浸泡好,目的是讓黃豆膨脹。第二天早起燒水時,將浸泡后的黃豆用石碾壓碎,使之成為生豆漿,之后用紗布將生豆漿進行過濾處理,過濾后紗布上遺留的廢渣——豆腐渣也不會扔掉。待生豆漿煮開時,再用鹵水點制并將其倒進木制的豆腐模具中進行沉淀和壓制。就這樣,一塊塊白豆腐就大功告成了。
豆腐備好后,就可以制作燒豆腐了,烤制燒豆腐時最好用炭火。將豆腐從模具中倒出來,并將其切成一寸厚、二寸見方的小塊,把鐵架放置于炭火上,將提前切好的白豆腐均勻地碼在鐵架上,就可以開始烤制了。在烤制的過程中,需要對每一塊豆腐進行翻面,直到豆腐塊的兩面均被炭火烤到焦黃。享用這種美食時,人們通常要搭配由姜蒜泥和豆腐渣混合而成的蘸頭,或是先用白水將燒豆腐煮熟,后再配上蘸頭,趁熱蘸食。燒豆腐滑嫩可口、外焦里香,蘸頭香氣撲鼻,常令人垂涎三尺,此兩者的搭配著實巧妙!
白起豆腐不僅是百姓對趙軍的紀念,更是當地勞動人民的智慧結晶。俗話道:“好吃難做。”要想將白起豆腐做好,不僅原材料極為講究,配料的比例也十分嚴格。例如,點豆腐的酸菜漿、鹵水的多少,火候以及蘸頭的配料比例等,都不能有絲毫差錯。
今年60歲的申宏才是白起豆腐制作技藝的傳承人。每天凌晨兩三點鐘,申宏才和妻子便起床開始制作燒豆腐。夫婦倆先將已經浸泡好的豆子磨細,再用開水燙、過篩、熬豆漿、點豆腐、壓豆腐、切豆腐、烤豆腐等,十幾道工序費時費力。這小小的白豆腐工序復雜,通常需要六七個小時才能完成,如今已經很少有人做了。當地制作過豆腐的老人講,燒豆腐太費功夫了,而且成本高,利潤低,這種不對等的付出與回報,是賺不到錢的,年輕人也不會將其作為在社會上謀生的一項技能。又因豆腐難以入味,一般人很難將其做得好吃,因此,豆腐也不再受年輕人的追捧。
然而,傳統技藝總得傳承下去,傳統技藝也總會有人喜歡。申宏才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對做豆腐情有獨鐘。從他爺爺申隨來開始,再到父親申年順做豆腐起家,現在又傳承到申宏才這一代,家族三代都以此謀生。如今,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越來越重視食物的營養價值,也越來越喜歡吃手工制作的豆腐,申宏才制作的燒豆腐名氣也越來越大,小小的豆腐坊吸引了大批客人,高平市更是有多家飯店和申宏才合作,雙方簽訂合同,申宏才將自己制作的燒豆腐每天定時定點配送到各個飯店,小小的豆腐坊竟到了供不應求的地步。對此,申宏才說道:“我有信心一直把它做下去,讓高平的燒豆腐在市場中永不間斷。”
高平燒豆腐是一種地方特色美食,同時高平人對燒豆腐也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存在。期望在傳承人的努力下,高平燒豆腐可以更好地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