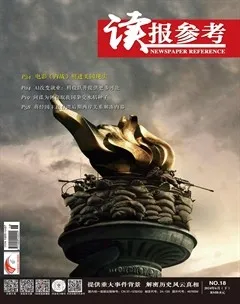“失意文人”曹植是如何“制造”出來的
曹植是漢末三國時代最有才華的文學家之一,與他相關的“七步成詩”“八斗之才”等典故在后世也廣為世人所知。只可惜,曹植的坎坷經歷與他的驚才絕艷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通行版文學史以及歷代評價中,曹植“悲劇文人”“落魄皇族”的形象幾乎已蓋棺定論。
此類觀點的主要依據之一,在于曹丕稱帝前后,曹植詩風大變。但從正史記載來看,曹植與曹丕之間非但沒有達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反而還一直保持著相對融洽的關系。
被裹挾的繼承之戰
曹植成為曹丕的有力競爭對手,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于曹操。在建安十六年(211年)時,曹植并不具備與曹丕相爭的資格。這一年,曹丕任五官中郎將,置官屬,以“丞相副”的身份處理政務。這樣的地位,顯然是其余諸子不能比擬的,曹植也不例外。是年,曹植被漢帝封為平原侯,與他一同封侯的還有另外兩個兄弟曹據(范陽侯)與曹林(饒陽侯)。可見,曹植并沒有受到特殊照顧。可沒過多久,曹植就異軍突起,以驚人才華得到了曹操的另眼相看。這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的銅爵臺(即銅雀臺)。
這座高臺始建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冬,至建安十七年(212年)春落成。建成之后,曹植登臺作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得到了父親的欣賞。次年,曹操進爵魏公,卻沒有立即設世子。歷史學者柳春新先生指出,此時他已有考量曹植之意。又一年,曹操征孫權,并未如往常一樣令曹丕留守鄴城,而是將這個重任交給了曹植,對曹植的看重不言而喻。
在這之后,曹植初步擁有了與曹丕對抗的資本。但需要指出,在這場所謂的“競爭”中,曹植自始至終都十分地被動。首先,曹植幕府中的大多數成員,都是曹操精心挑選、一手安排的。如河北高士邢颙,時人稱“德行堂堂邢子昂”,曹操親自下令,讓邢颙去做平原侯府的家丞。又如當世碩儒邯鄲淳,曹丕、曹植皆對他有招攬之意,卻被曹操指派給后者。還有鄭褒、徐斡、司馬孚等人,也都是曹操“甄選”的賓友。
其次,在“繼承人之爭”中發揮出主要作用的丁儀、孔桂等人,投靠曹植另有目的。如孔桂,他選擇曹植的理由,只是因為后者當時頗受曹操喜愛,這才刻意逢迎。至于丁儀,則是因為與曹丕有私人恩怨。此前,丁儀與清河公主的婚事曾被曹丕破壞,懷恨在心的他“恨不得尚公主”,而與曹植親善,“數稱其奇才”。
丁儀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屢屢攻訐曹丕的擁護者。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在丁儀的攀誣下,毛階、崔琰二人一廢一死。同時,這也標志著“曹植黨”與“曹丕黨”的斗爭已趨于白熱化。但到了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兄弟二人就分出了輸贏——曹植與摯友楊修酗酒,擅闖司馬門,曹操大怒,賜死楊修。至于曹植的下場,在“司馬門事件”后可能是通過削爵而免去了死刑。
曹植雖然保住了性命,卻失去曹操寵信,喪失了與曹丕競爭的資格。隨即,曹丕被立為世子,這場鬧得沸沸揚揚的“繼承人之爭”,終于落下帷幕。
曹植或有意退讓
通過對“繼承人之爭”的梳理,不難看出,曹植與曹丕并沒有直接對抗。與其說,這是曹植與曹丕的私人斗爭,毋寧說是以曹丕、曹植為首的兩個“集團”之間的斗爭。尤其是曹植的擁簇者,多以此為借口,滿足自己的投機行為。如丁儀,他如此賣力地攻訐曹丕及其黨羽,既不是出自公心,也并非是因為他對曹植本人的維護。且兩個“集團”真正擺在明面上的“斗爭”,也不過一年多的時間。由此可見,曹植與曹丕之間的關系,遠遠沒有達到文學史中所說的“你死我活”“勢同水火”。更何況,以曹操的手段,他也斷然不會坐視曹魏內部因此而產生分裂。
曹植在“繼承人之爭”的關鍵節點酗酒誤事,竊以為,未嘗不是因為他已有主動退讓之意。盡管曹植曾在《與楊德祖書》中說過:“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但這場所謂的“競爭”,終究是在曹操、丁儀等人的推動下進行的,曹植雖一度想要建功立業,也默許丁儀為其奔走,但他還是放棄了與自己的兄長曹丕相爭。使他喪失繼承人資格的“司馬門事件”,正是曹植退讓的一個表現。試想,一位專門寫過《酒賦》,并指出酒是“先王所禁,君子所斥”的曹植,何以會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酗酒呢?南宋劉克莊就認為:“植素無此念,深自斂退。”
以曹植重情重義的性格看,他不會故意坑害自己的摯友楊修。所以,竊以為,“司馬門事件”并非曹植策劃,而是他在無心爭嗣后的任性之舉。只是曹植也沒想到,曹操會一反常態,不再包容愛子,而是借此事大做文章,不僅處死了楊修,還再申“諸侯科禁”,以維護魏王權威。
正是因為曹植的退讓,曹丕并沒有仇視自己的弟弟;相反,兄弟二人的關系一直都不錯。又據《三國志·鐘繇傳》注引《魏略》記載:“后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言。密使臨菑侯(曹植)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這件事發生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彼時,曹植與曹丕依然保持著較為融洽的關系。在曹丕稱王、稱帝后,曹植還撰寫了不少文章,宣傳夸耀兄長。
《世說新語》的塑造
在后人看來,曹丕對曹植并不好,甚至有些刻薄。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曹丕甫一即位,就處死了丁儀、丁廙兄弟。其二,曹丕稱帝后,派監國謁者對曹植進行密切監視,并動輒對曹植呵斥、責備。那么,這到底算不算是曹丕對曹植的苛待呢?其實,如果將丁儀之死理解為曹丕的秋后算賬,并無不可。而曹丕對曹植的監視,卻并非是針對他個人。曹丕重用曹仁、曹休、夏侯尚等宗室部屬,卻對自己的手足兄弟多加防范,核心原因在于曹操的其他兒子同樣具有繼承大統的資格,會對曹丕的帝位造成潛在威脅。更何況,就算曹植本人無心爭位,但在一些特定情況下,難保不會有人利用這層關系大做文章。據《三國志·明帝紀》注引《魏略》記載:“是時訛言,云帝已崩,從駕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群公盡懼。”時隔數十年,朝堂上依舊流傳著“曹植有即位資格”的輿論,從帝王的角度來看,曹丕對曹植的防范并無不妥。
日本學者津田資久認為,陳壽在撰寫《三國志·曹植傳》時,有意塑造了曹植的“不遇”。因為司馬攸在西晉一朝屢遭打壓,故而陳壽便假托曹丕、曹植的關系來闡述“曹魏皇室壓迫諸侯王而招致滅亡”的道理,希望晉武帝司馬炎能夠重視自己的兄弟司馬攸。這一說法有待商榷,但其揭示的一個道理是值得注意的——史學家、文學家在撰寫自己的作品時,往往會加入自己的想法。這其中,以南朝劉義慶組織編撰的《世說新語》最具代表性。
后人論“曹丕苛待曹植”,必然離不開“七步詩”。時至今日,該詩有多個版本,分見于《世說新語·文學》《太平廣記》卷173“曹植條”引《世說》,以及《文選》卷60《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李善注引《世說》。無論哪個版本,源頭都是《世說新語》。這部作品貶低曹操、曹丕父子而同情曹植的傾向十分明顯。作為以漢室后裔自居的劉宋皇族,劉義慶當然對曹操、曹丕沒有好感;可他與曹植又恰恰都是被排擠打壓的宗室,感同身受之下,他難免會對曹植產生同情。于是,《世說新語》所見“曹植”,雖有錦繡文才,卻始終不得志。
在后世無數文人的共情下,“失意文人”這一刻板印象不斷被深化,幾乎成為曹植身上最難摘掉的一個標簽。
(摘自《北京晚報》嚴保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