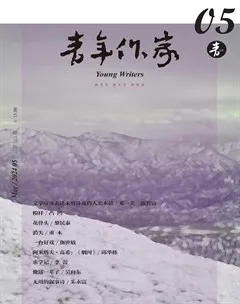青堤之戀
你還記得青堤嗎,涪江邊上的那個老碼頭,一個古老的場鎮,一個終生也繞不開的地方。
30多年前一個初春的早上,我騎著一輛“28大杠”,吃力地在涪江東岸山林中的碎石路上穿行。累得實在騎不動時,我就停下來,吹吹河風,眺望山腳下浩淼的涪江,暗自給自己打氣。那是我第一次去青堤,雖說路途遙遠、顛簸,但青春的激情讓我停不下腳步。騎行20多公里后,涪江在前面劃了一個大圈,繞江中小島形成了廣闊的弧面,那個弧頂對應的連片山丘處就是青堤。
離場鎮口還有一段距離,碎石路變成了石板路,道路兩旁或遠或近分散著一棵棵枝干粗壯的大樹,仿佛已守候了上千年。進場鎮,連綿的青瓦房高低錯落,曲折的檐廊一眼望不到頭,蒼翠如華蓋般的大樹佇立路旁,又或在房前屋后探出了身,給古鎮增添了幾分神秘和寧靜。我推著車,問著路,向青堤中學靠近。
那時,同在師專讀書的你和另幾個同學被分到青堤中學當實習教師,而我則分在老家縣城的一所中學。記得我曾經問過你對這里的印象,你的回答如你黑色的眼珠一樣明亮。我心里不由得產生了同頻共振的顫動,從那之后,我喜歡上了和你一起坐船、戲水、野炊、爬山……
學校位于集鎮所在山頂最高處。登上教學樓頂,山下的青堤郁郁蒼蒼。透過樹梢,一幢幢房屋的飛檐斗拱露出了頭,山嵐拂過,那掛在廟宇翹角處的風鈴“叮叮當當”直響,奏出天地間最美妙的合聲。你揚起臉,嬌媚的面龐和烏黑的長發被微風浣洗。你回過頭來,撲閃著一雙大眼睛,望著發呆的我笑了笑,提出一起去鎮上逛逛。
街頭巷尾,茶館、酒肆、鐵匠輔……自由地散落在各處,金屬的敲打聲、推杯換盞的嬉笑聲趕著趟似的,追隨著眾人的腳步。順著場口再往下,彎彎曲曲的石板路一路相隨。道路兩旁,錯落的大樹開枝散葉向我們伸出了熱情的手。路邊、石縫中、房前屋后,綠茵茵的野草、松軟的青苔成片成團地鋪染開。那枝頭綻放的蓓蕾迎風搖曳,我的心也像這初春一樣暖融融的。
來到山腳下的渡口邊,一條綿延近千米的石脊彎彎繞繞匍匐在我們眼前。石脊上裸露的地方光滑、濕潤,兼有一洼洼水凼。你躡著腳,間或一個小跳。我怕你摔倒或是崴了腳,幾次去牽你的手。你臉有些發紅,像春芽的芽尖,不待我握穩你的手就暗自掙脫,第一個來到江邊,雙手掬起江邊的水,向我拋灑出顆顆晶瑩。
江水清澈見底,滌蕩著柔荑般的水草,映照著你的青絲秀發、衣袂飄飄。習習微風吹拂著我們的臉,灑下的笑聲乘著清波飄得好遠好遠。
踩著坑坑洼洼的石板路我們回到學校。天南地北的暢談持續到山腳下的燈光漸次熄滅,我們的房間宛如山頭上掛著的一顆星。睡在你曾睡過的床上,耳邊只剩下山風撫慰著樹梢的沙沙聲,恰似你的喃喃細語。此時,你枕頭上散發出的洗發水香味,合著被褥上殘留的體香以及微風送來的陣陣果木香,伴我進入了夢中。
回到師專,我們不自禁地靠攏。上自習、進圖書館,無論誰先到,總會在身邊給對方預留個位置。很多個夜晚,我送你回宿舍樓后,徘徊在外面的高岡上,直到你寢室里的燈光熄滅。但我始終沒有對你表達出我的心意,不是我羞于口、不善表達,而是你說要回到家鄉——那個千里之外我不可觸及的地方。畢業那天,我送你到學校山下的芙蓉溪畔,汽笛聲聲,催我不停地回頭,目送你離開。
一年后,我從鄉鎮被借調到青堤對岸的柳樹鎮工作。很多次,我將目光投向河對岸,在被陽光所皺褶的山林中尋找當初的記憶。
秋日的某一天,對岸朋友邀約我去青堤。
渡船“突突”地響,每一聲都敲打著心弦。從渡口隔岸相望,對岸山體裸露著一大片赭紅色的山巖,猶如被風揭開的傷疤,看著觸目驚心(后來得知,這是修路擴山體造成的)。
河邊上,三五成群的婦女在搓洗著衣物;挑著籮筐推著車的人們在等待著過河。蜿蜒的石板路、孑立的吊腳樓、一叢叢的青瓦白墻掩映在綠色蒼茫中。
這樣的景致溫暖而又傷懷,我恍入夢中。隨著渡船的靠近,河邊上那大片的石脊映入眼簾。石脊上高低起伏遍鑿大大小小、各種形狀的孔洞,昨夜的一場雨使石窠中盛滿一汪汪清水,仿佛映照出了我們的身影。
手指從石孔上斑駁、堅硬又溫潤處劃過,我不禁熱淚漣漣。都說這石窠是古時候泊船系纜繩鑿的。而我這顆心又該為誰而泊,為誰而解纜?
從渡口上行到半山腰,轉過一道彎,地勢變得開闊,右邊一山頭上,目連寺聳然獨立,凝望著從他腳下走過的有緣人。
目連寺中幾座殿依山勢縱向排列,三三兩兩可見來祭拜的游人。后殿旁邊有條小路直通山頂,沿途草蔓纏繞,遮林蔽日。待我氣喘吁吁登上去,極目遠眺,涪江逶迤著向我迎面走來,大地給群山投下了濃墨淡彩的剪影。陣陣清風拂面,頭頂上的枝條搖搖晃晃飄落下片片枯葉,似乎在與眼前的山林作最后的告別。
辭別時,朋友送了我一把當地純手工打造的“青堤菜刀”。端詳著手中刀刃鋒利的菜刀,我想,我已斬斷了過往,不再為你而牽絆。
2008年夏天,你打來電話,說自己出差,順道要來看看同學,還想順便去青堤走走。
那年從青堤回來后不久,我就調回了縣城。這十多年間,我數次與青堤擦肩而過。我趕緊向朋友打聽青堤的近況,還找了些資料,只是為了不愿在你面前顯得孤陋寡聞。
青堤是傳說中圣僧目連的故里。那些年,當地挖掘并打造目連文化,和“鐵水火龍”項目一起申報省級非遺。小時候我聽過“目連救母”的故事,在縣城看過一兩次鐵水火龍表演,但都沒有把它和青堤發生關聯。也許,印象中的事物不與自己發生關聯就不會產生共情吧?
那是畢業后我們第一次相見。上午10點過,我約了家鄉的兩個同學去車站接你。你出了站,抬頭觀望那一瞬,我們的目光交融在一起。我幾乎是第一時間認出了你,你也認出了我吧?你微笑著向大家問好,第一個向我伸出手來。我竟有些發懵,直到你臉上泛起紅暈,暗自抽出手才清醒過來。
來之前,你說要趕時間。于是接上你,我們就開車直奔青堤。
汽車穿行在東岸的山林中。離青堤還有幾公里,涪江開始出現在山腳下,一路山纏水繞、波光蕩漾。你打開車窗,興奮地望著窗外,向我們求證著記憶中的一切……
青堤的石板路、住家戶的門窗明顯修護過,但清風還是在上面擦拭出了斑痕。一篾器店里,匠人坐在凳子上,前后左右輪轉手中的竹條,用竹刀修理上面的毛刺。旁邊一個用篾片編制的龍頭已具雛形。你詫異青堤何時有了龍,我隱而不語,帶你往目連寺而去。
目連寺主殿內墻上新繪了完整的“目連救母”壁畫,幾座配殿也修葺一新。我這才向你詳細介紹目連的傳說、“鐵水火龍”的前世今生。你感嘆當初實習的一個月也抵不上這半天所知所曉。
不知不覺我們放緩了腳步,拖行在同學的后面。你向我詢問家庭和孩子的情況,還將手機里丈夫和孩子的照片翻給我看,幸福的感覺溢出了嘴邊。回到縣城,你馬不停蹄地要趕往綿陽開會,我只得再次為你送行,默默地看著班車消失在視線中。
也就是那年春節,我有幸作為縣直部門代表,被邀請到現場觀摩“鐵水火龍”表演。
我告訴你這個消息,你在電話那邊興奮得就像個孩子,一再叮囑我拍一些照片發給你。
傍晚時分,我從縣城出發。暮色已合,前方的青堤就像群山環抱中的一座孤島,隨著車輛的轉彎,那片黑黢黢的叢林中從山腳到山頂透閃著點點燈火。青堤街上幾乎看不到人,昏黃的路燈下,青石板透出悠悠的光,引導著路人向鑼鼓喧天的目連廣場走去。
那晚的表演讓人震撼。場內,鼓樂手開道,手挑宮燈身著對襟小祅的十多個婦女兩人一組魚貫而入;場中,精壯漢子雙手舞動著“鐵流星”,時而作雙星輪式旋轉,時而將雙星拋向天空,時而上,時而下,時而左,時而右;火龍進場了,那龍在鐵水被擊打而化為的漫天彩蝶中奔騰跳躍、上下回旋、左右環繞、前后翻身、內外穿花,引得眾人驚呼不已。
我不停地從各個角度拍照,適時向你分享現場的畫面。我能感覺到你在那邊的愉悅和激動,你把我發的照片一組組發在朋友圈里,還附上我給你的說明資料,就像自己離開后就未曾走遠。
2022年秋天,千里之外的你打來電話,說自己臨近退休,退休后想約上當年一起實習的同學再到青堤看看,還要我發幾張青堤現在的照片。
這么多年過去了,我發現自己在你面前仍然軟弱得一塌糊涂。我勸說自己,要盡量滿足你的心愿。
如今,到青堤的路有多種選擇。上游10公里左右是年初剛通車的瞿河涪江公路大橋,下游5公里處是幾年前建成的沱牌電航橋工程,均可從橋上開車直達青堤。
而我決定舍近求遠,重走當年騎行的老路。汽車一路顛簸,一路上都很少見車輛和行人。場鎮外,道路兩旁的大樹還在那里靜立佇望。越往里走,越沉寂得讓人發慌。青堤街上人單影孤,很多房屋都是大門緊閉,還有一些只剩下斷壁殘垣,仿佛不堪歲月的磨難。
我趕緊找來一個老者詢問。老者告訴我,電航橋修起后,青堤不再擺渡。撤鄉并鎮后青堤劃歸對面的沱牌鎮(原柳樹鎮)管,原來鄉上的學校也遷往他地。如今,青堤不再逢場,除了一些留守老人外,年輕人基本上都常年在外。“鐵水火龍”也搬到了離此十多里地的青龍村。
古渡口邊,電航蓄水淹沒了大片的礁石,哪里還有“拴船石”的身影?江水拍打著岸邊“嘩嘩”響著,光禿禿地被淹至腰身的麻柳樹不停地在水中搖曳。目連寺幾乎看不到游人,只有間或撞響的“晨鐘暮鼓”;目連廣場野草恣肆瘋長,滿眼都是荒蕪凄涼。
回到家,我托搞攝影的朋友找了些青堤過去的照片一并發給了你。合上電腦的那一刻,我想,并不是有心要騙你,因為,我們記憶中的青堤就是這樣!
【作者簡介】王海全,生于1968年7月,曾在《西藏文學》等刊發表作品;現居四川射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