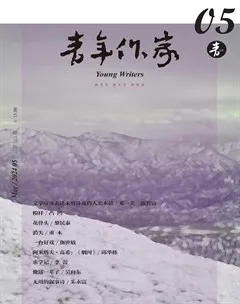無用的敘事詩
一天
如果倒敘,天上那枚月亮
就得早早升起。甚至都可以略過
從月暈里爬出來,剛剛它費了
九牛二虎之力,
明亮得沾不上人間煙火。
而事實是時序還在進化,
入秋后不溫不火的天氣,有人卑躬屈膝地
活著,有人理所當然赴死。
生活的幻想,敵不過一紙麥芒。
陰暗的一天,烏云駁了太陽的面,
這本身是一件憂傷的事,而細雨
將落未落,我又承了烏云的情。
矛盾還在矛盾中,矛盾還在
矛盾本身。只是對臺的腳本,分工了不同的
爭議和說詞,任那些暗處的糾結,
像一根打結的麻花。人間
還是諸多趣味的冒險,有人上山鋤草,
有人下水摸魚,無事可干的人,
就坐在自己心中,
把一生濃縮成一個夢。
苞谷地
嘩啦嘩啦的聲響,
一定會把秋風割傷,所以
風學會了隱忍和折返,
一遍遍在北高原逡回。
太陽火辣,汗水辛辣。
兩個辣字之間,我看到父親
順著高低不平的石梯
在白云下登高。
訓誡一樣蒼老的苞谷地,
它有魔力讓一個農民
把腰板挺得筆直。
父親把褲腿綰得老高,
暴露出一雙青筋蠕動的細腿,
雜草太深了,
他又握緊手里的拐耙子。
在秋天,太陽的焦糊味隨處可聞,
鋒利的苞谷葉
會把一雙裸露的膀子割得生疼。
嘩啦啦的苞谷地不說,
父親也沒有告訴過我。
無用的敘事詩
水龍頭的流水,沒有聲音,
他從食堂的玻璃門
提水出來,在流水一樣反光的
玻璃上,一個幽居于
塵世的中年人,像一張弓。手的兩端,
是黑桶的下墜力,不斷
晃動和持平。操場上
斑斑點點的積水,鈴聲響起時,
學童們被收集進窗子的畫框。
孤寂,是天空和大地的顏色,蝴蝶牌的
呼吸機,再沒有花的聲音。
在一個漫長的下午,他變身為
兩只黑色的水桶
勻速從村小學的操場上經過。
水桶里的水,并沒有晃出一絲
聲響,中途下梯子處,有過
一次沉重的停歇。與詩歌無關的烏云,
像一張偌大的舊棉絮,
又爬上天空。
當第一場冰雪來臨的時候
突然覺得還有很多事沒做,
突然就覺得還有很多事要做。
父親尚未運完山間的草垛,母親
尚未收拾完樓上的苞谷。
舊的日子,又在紙上飄蕩,
忽如炊煙。我們依舊是
生活的孩子,對忽然的變故仍缺乏
安全感。又一年,沒有人知道
北風該如何總結這潦草的人間?
那六角形的飄,漫無目的,
大地的繡卷上唯遼闊可填補。
在一場雪與另一場雪
之間,我們都停下來成為孩子,
不斷變化,又慢慢長高。
登金蟾大山遇雨
這中年的汗珠兒,肥胖而渾圓。
大口喘息的人生,
得準備好一袖子潮濕的云,
不斷從臉頰的左邊擼到右邊。
我的孤獨,是一只麻雀的
孤獨,松針在前,雷聲其后,
細碎的啾啾聲里,一念悠悠,
二念恍惚。
我的同類,是箭竹、灌木和藤蔓,
一場雨坐著云朵來了,
我的衣袋里鼓著風。這二分一的
人間高度,我看到羊群像花朵一樣
在天底下奔跑,而遙遠的群山,
一如沉重的蝸牛;
雨就要來了,辣蓼在奔跑,黨參和
雞毛花在奔跑……叫得出名字的
領著叫不出名字的奔跑。
這眼前的事物都在奔跑,有的抬高幾寸,
有的離地三尺,只有我
急于想逃回人間。
【作者簡介】朱永富,生于1984年,貴州納雍人,鄉村教師。詩歌散見《人民文學》《十月》《山花》《芙蓉》《詩刊》《星星》《草堂》等刊,曾獲貴州優秀文藝作品獎等,著有詩集《稻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