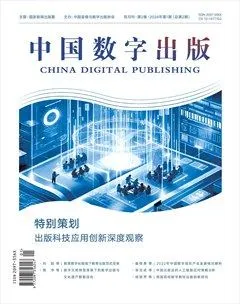數(shù)字文明轉(zhuǎn)型背景下的數(shù)字出版與文化遺產(chǎn)數(shù)智活化
簡華?王曉光?侯西龍

編者按:當(dāng)前,在數(shù)字中國和文化強國戰(zhàn)略的政策支持與保障下,我國數(shù)字出版產(chǎn)業(yè)正處于利好期:一方面,數(shù)字出版與文化遺產(chǎn)傳承與活化深度融合,不僅是數(shù)字出版自身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也是文化數(shù)字化戰(zhàn)略的重要推動力量;另一方面,數(shù)據(jù)管理不僅為讀者提供了更多優(yōu)質(zhì)數(shù)字化閱讀產(chǎn)品,也改變了傳統(tǒng)出版時代出版社與讀者之間霧里看花的局面,使出版社的市場競爭力明顯增強。基于此,本期《行業(yè)熱點》欄目組織了兩篇文章,分別介紹了武漢大學(xué)文化遺產(chǎn)智能計算實驗室通過數(shù)字出版創(chuàng)新發(fā)展賦能文化遺產(chǎn)傳承與活化的實踐路徑;外語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通過打通內(nèi)部生產(chǎn)和銷售數(shù)據(jù)(比如在售產(chǎn)品的同比和環(huán)比數(shù)據(jù)、銷售曲線、用戶數(shù)據(jù),還有數(shù)字化產(chǎn)品和服務(wù)的研發(fā)進度以及在計劃內(nèi)還是超時等)實現(xiàn)數(shù)實融合的情況。通過這兩篇文章,我們在回應(yīng)行業(yè)普遍關(guān)切的同時,也希望引發(fā)更多對數(shù)智活化、數(shù)實融合以及更多數(shù)字出版行業(yè)熱點的關(guān)注和思考。
摘 要 在漫長的人類社會發(fā)展過程中,出版自誕生起就被委以文化生產(chǎn)與傳播的重任。現(xiàn)今人類社會正邁向數(shù)字文明,數(shù)字出版也將在印刷文明之后作為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先鋒,成為數(shù)字中國和文化數(shù)字化的重要陣地。文章首先探討了邁向數(shù)字文明的轉(zhuǎn)型邏輯,即三個世界協(xié)同并肩實現(xiàn)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才能從根本上促成數(shù)字文明的到來,數(shù)字文化將承擔(dān)起引領(lǐng)者的重要角色。其次,文章由史及今地分析了數(shù)字出版在數(shù)字文明發(fā)展中的角色、定位及重要作用。最后,文章提出數(shù)字出版創(chuàng)新發(fā)展賦能文化遺產(chǎn)傳承與活化的實踐路徑。
關(guān)鍵詞 數(shù)字出版;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文化遺產(chǎn);智慧數(shù)據(jù);活化利用
就其本質(zhì)而言,出版是知識生產(chǎn)的過程[1]。技術(shù)發(fā)展帶來的認識論革新以知識生產(chǎn)為渠道[2],由此出版作為技術(shù)進步作用于社會變遷的重要中介,與文化積累、文明轉(zhuǎn)型密不可分。2022年,《關(guān)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shù)字化戰(zhàn)略的意見》(以下稱《意見》)[3]指出,要實現(xiàn)中華文化全景呈現(xiàn),中華文化數(shù)字化成果全民共享;《關(guān)于推動出版深度融合發(fā)展的實施意見》[4]從出版內(nèi)容建設(shè)、技術(shù)支撐、重點工程等方面提出指導(dǎo)性意見,都為出版業(yè)數(shù)字化建設(shè)和融合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2023年,《數(shù)字中國建設(shè)整體布局規(guī)劃》[5]提出要推進文化數(shù)字化發(fā)展,深入實施國家文化數(shù)字化戰(zhàn)略,建設(shè)國家文化大數(shù)據(jù)體系,形成中華文化數(shù)據(jù)庫。這些政策都反映了在國家建設(shè)和人民現(xiàn)實需求中,數(shù)字文化建設(shè)和數(shù)字文明轉(zhuǎn)型都已成為新時代面臨的重要且艱巨的任務(wù)。數(shù)字出版作為數(shù)字中國與文化數(shù)字化戰(zhàn)略的重要陣地,在數(shù)字文明轉(zhuǎn)型的進程中理應(yīng)發(fā)揮更加積極主動的作用。
當(dāng)前各種數(shù)字技術(shù)迭代不窮,已成為社會運轉(zhuǎn)的基座。基于此共識,本文從“三世界”理論出發(fā),探討分析數(shù)字文明的轉(zhuǎn)型邏輯:三個世界協(xié)同并肩實現(xiàn)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才能從根本上促成數(shù)字文明的到來。在轉(zhuǎn)型過程中,數(shù)字文化將起到先鋒示范作用,引領(lǐng)數(shù)字文明轉(zhuǎn)型的方向。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出版一直承擔(dān)著文化生產(chǎn)與傳播的重要角色,未來也將由數(shù)字出版接續(xù)承擔(dān)起數(shù)字文化建設(shè)的重要任務(wù)。最后,面向數(shù)字時代文化遺產(chǎn)活化的新任務(wù)和新場景,本文提出了數(shù)字出版創(chuàng)新發(fā)展賦能文化遺產(chǎn)數(shù)智化活化的實踐路徑。
1 基于“三世界”理論的數(shù)字文明轉(zhuǎn)型邏輯
哲學(xué)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在其文章《沒有認識的主體的認識論》中首次提出并闡釋了“三世界”理論,將世界劃分為:①物理客體或物理狀態(tài)的世界;②意識狀態(tài)或精神狀態(tài)的世界以及關(guān)于活動的行為意向的世界;③思想的客觀內(nèi)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學(xué)思想、詩的思想以及藝術(shù)作品的世界[6]。客觀內(nèi)容世界是由語言、藝術(shù)、科學(xué)、技術(shù)等所有被人類儲存起來或者傳播到地球各地的人工產(chǎn)物所記錄下來的人類精神產(chǎn)物[7],即文化層次中的器物層面[8],如語言、文學(xué)、藝術(shù)、圖書等文化制品。這三個世界相互獨立,又相互作用。在當(dāng)下數(shù)字浪潮中,三個世界分別進行著各自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共同構(gòu)成了當(dāng)今數(shù)字化的世界。
世界1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指對客觀物質(zhì)世界的數(shù)字化采集,對物理客體和狀態(tài)的數(shù)字化表示,即用數(shù)據(jù)編碼重構(gòu)物質(zhì)世界。世界1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是奠定于現(xiàn)實基礎(chǔ)上,在數(shù)字空間的映射,再進一步搭建獨立的物質(zhì)生態(tài)系統(tǒng)。物理世界是精神世界的前提[9]。當(dāng)下世界1在數(shù)字世界具體呈現(xiàn)為數(shù)據(jù)、基礎(chǔ)設(shè)施、通用算法、數(shù)字技術(shù)等。世界2指人類的主觀精神世界。世界2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核心在于借助腦機接口技術(shù)(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在人或動物大腦與計算機及其外圍設(shè)備之間建立起信息交換的聯(lián)系,用于輔助、修復(fù)或增強人的行動、表達和感知功能[10]。由此,捕捉人類的思維意識具有現(xiàn)實可能性,突破了原先完全個體獨立、無法外部觀測的限制,蘊含著給人類生存帶來顛覆性改變的潛能[11]。腦機接口提供了人類思維意識信息的收集、觀測與分析方案,同時也作為人腦外部介入手段,為世界2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解決了最為棘手的執(zhí)行方案難題。世界3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指承載客觀知識的文化制品及其生產(chǎn)過程的數(shù)字化。互聯(lián)網(wǎng)和數(shù)字技術(shù)極大地增強和拓展了人類的認知能力,通過知識載體虛擬化、知識傳播網(wǎng)絡(luò)化、知識生產(chǎn)復(fù)雜化,改變了知識生產(chǎn)、貯存、傳播和生產(chǎn)的方式,但并未改變知識本身[9],因而有關(guān)世界3的理論仍然適用于當(dāng)下。客觀知識作為人類思維活動的產(chǎn)物,見諸體現(xiàn)人的意識的文化制品,如各類出版物。圖書作為歷史最悠久的出版物之一,在我國最早可追溯到夏朝的竹簡木牘[12],距今四千余年。直到20世紀(jì)60年代,美國化學(xué)文摘服務(wù)社(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CAS)用計算機編制的《化學(xué)題錄》磁帶版的問世,才標(biāo)志著數(shù)字出版物的誕生[13],開啟了數(shù)字出版時代,從根本上改變了知識生產(chǎn)、組織和傳播,在出版領(lǐng)域萌發(fā)出專屬于數(shù)字時代的數(shù)字文化。世界3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將與文化數(shù)字化、出版數(shù)字化同頻。世界3在數(shù)字世界將通過各類數(shù)字出版物呈現(xiàn),囊括數(shù)字文本、數(shù)字圖像、數(shù)字模型、數(shù)字音頻、數(shù)字視頻、軟件等多種知識文化存在形式。
文明是人類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中創(chuàng)造的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成果的總和,是歷史發(fā)展不同階段的映照[14]。在人類文明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之中,單個世界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不能稱為數(shù)字文明,只有三個世界在緊密關(guān)聯(lián)、相互協(xié)同中完成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才能最終促成人類社會向數(shù)字文明的轉(zhuǎn)型。在世界1中探索和體驗,形成對客觀物質(zhì)世界的感覺、認知、思考、情緒、記憶、想象等,引出世界2。代表主觀認識世界的世界2指導(dǎo)著人類在客觀物質(zhì)世界行動。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和理解中形成客觀知識,經(jīng)過記錄和編碼,形成了哲學(xué)的、科學(xué)的、歷史的、文學(xué)的、藝術(shù)的、工藝的等各類文化制品,世界3由此形成。基于客觀知識,人類能夠?qū)陀^物質(zhì)世界進行合理地分析預(yù)測,表現(xiàn)為世界3對世界1的反作用。社會文明形態(tài)的轉(zhuǎn)型不僅包含著以物質(zhì)為基礎(chǔ)的物理世界和以意識為基礎(chǔ)的精神世界的轉(zhuǎn)型,也更應(yīng)該重視文化制品及其生產(chǎn)傳播的轉(zhuǎn)型。數(shù)字文化和數(shù)字出版作為先鋒軍推動著世界3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向,是向數(shù)字文明轉(zhuǎn)型中從此岸邁向彼岸的引領(lǐng)者,三世界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邏輯如圖1所示。
2 數(shù)字文明轉(zhuǎn)型中數(shù)字出版的角色與價值
出版的本質(zhì)在于“依賴印刷術(shù)實現(xiàn)的標(biāo)準(zhǔn)化知識生產(chǎn)與傳播”,它既是文化生產(chǎn)模式的表現(xiàn)形式,反過來也是文化生產(chǎn)和社會變革的深層力量。出版上承宏觀層面的文化建構(gòu)、價值引導(dǎo)與文明推進,下接具體的出版活動及其工作流程[1]。在漫長的人類社會發(fā)展歷史中,出版一直作為文化記錄與傳承的基本手段[2],照亮了人類文明的征程。出版業(yè)則是文化記錄與傳承的專業(yè)化。在中國,春秋時期的傳抄出版打破了貴族壟斷知識的局面,推動中華文化第一次“百家爭鳴”的盛況[15]。隋唐時期出現(xiàn)的雕版印刷術(shù)被廣泛地運用到書籍的印刷,知識傳播方便,使文化日益普及,更易流傳,滲透到社會各階層,獲得知識的權(quán)力進一步下移。在印刷出版技術(shù)中取得的進步,效應(yīng)輻射到知識的生產(chǎn)與傳播中。雕版印刷術(shù)推動了大規(guī)模印書,印刷書籍?dāng)?shù)量爆發(fā)式增長、文本主題日益豐富,也逐漸形成了藏書文化。卷帙浩繁的古籍不斷生產(chǎn)與積累,文化的積累日漸深厚,延續(xù)著中華文明。中華文明以印刷書為載體,在漫長的歲月長河中,抵御住了時間的反復(fù)沖刷,存留至今。在西方,古登堡活字印刷術(shù)點燃歐洲文藝復(fù)興運動和啟蒙運動之火,給西方文明帶來關(guān)鍵性進步——3R教育,即閱讀(Reading)、寫作(Writing)和算術(shù)(Arithmetic),造就了大量識字人士,提高了識字率,向大眾敞開了文字傳播的大門。識字是一種信息解碼能力,將民眾從教會此類的單一信息渠道中解放出來,信息的流動渠道從單向轉(zhuǎn)為多向,知識從神性的不可辯駁的形態(tài)轉(zhuǎn)化為民間的可改良的世俗化狀態(tài)。通過識字閱讀,民眾在思考、提問與回答中,參與知識的構(gòu)建。世俗化的知識被質(zhì)疑、被爭辯、被證實或證偽,知識的積累開始成為可能,現(xiàn)代意義的知識時代至此開啟[16]。印刷書成為西方文明最有力的推手[17],同由此搭建起的西方大規(guī)模社會化文化生產(chǎn)體系,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學(xué),加速了整個歐洲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新知識載于出版物,被進一步傳播,現(xiàn)代知識在生產(chǎn)與傳播的循環(huán)中不斷積累。印刷媒介深刻改變了文化的載體、渠道、中介物以及技術(shù)手段,帶來的是人類知識存儲介質(zhì)、知識生產(chǎn)系統(tǒng)、知識傳播途徑等方面的劇烈變革,同時更加深刻地引發(fā)社會結(jié)構(gòu)的重組、社會生產(chǎn)方式的轉(zhuǎn)型,助推文化的積累和文明的轉(zhuǎn)型。
文化是人類過去所有精神與物質(zhì)創(chuàng)造的總和[18]。物質(zhì)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無論文化形式多么千姿萬態(tài),其核心都是精神。精神是文化的靈魂,內(nèi)容是流動的血液,技術(shù)則是支撐文化的骨架。2005年,美國總統(tǒng)信息技術(shù)咨詢委員會的報告《計算科學(xué):確保美國競爭力》[19]提到,計算科學(xué)本身是一門學(xué)科,同時具有促進其他學(xué)科發(fā)展的作用。“計算賦能”同樣在文化領(lǐng)域也能煥發(fā)出強大的生產(chǎn)力。文化元素的獲取、處理、表現(xiàn)、傳播、生成等都可以借助數(shù)字技術(shù)轉(zhuǎn)化為數(shù)字態(tài),從而對信息和內(nèi)容進行統(tǒng)一建模,同時實現(xiàn)多模態(tài)數(shù)據(jù)之間的自由轉(zhuǎn)換和活化。當(dāng)下火熱的多模態(tài)大模型帶來更加令人振奮的文化生產(chǎn)力:不僅實現(xiàn)了文化生產(chǎn)的規(guī)模化、高速化、多樣化、開放化、共享化,而且支持不同模態(tài)信息之間相互轉(zhuǎn)換,極大地釋放了文化的活力,加快了文化的流動。沒有任何一種技術(shù)像數(shù)字技術(shù)如此強大,它改變了文化表現(xiàn)形式,拓展了文化的存續(xù)空間,增強了文化的體驗?zāi)J剑瑸槲幕瘎?chuàng)造了歷史上未曾出現(xiàn)過的新形態(tài)。
出版業(yè)生產(chǎn)文化制品,歷經(jīng)從農(nóng)業(yè)文明、工業(yè)文明再到數(shù)字文明,始終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助推器。當(dāng)前,“文化數(shù)字化”已被提升到國家戰(zhàn)略高度,將是未來幾年國家在文化領(lǐng)域重點推進的藍圖。文化數(shù)字化戰(zhàn)略不僅是中華文化發(fā)展的轉(zhuǎn)型點,也將成為數(shù)字出版高質(zhì)量發(fā)展,發(fā)揮更加關(guān)鍵作用的機會。印刷書曾構(gòu)建了長達數(shù)百年的文化生產(chǎn)與傳播秩序,近幾十年,數(shù)字技術(shù)和互聯(lián)網(wǎng)打破了傳統(tǒng)印刷出版中的知識秩序,數(shù)字出版接續(xù)承擔(dān)印刷出版在知識生產(chǎn)、文化積累方面的任務(wù),帶來新一輪的文化變革與文明轉(zhuǎn)型。在網(wǎng)絡(luò)社會中的知識秩序,是鏈接而不是容器;是多重拼貼下的意義,而不是單向度的意義;是未竟的,而不是確定的;是混雜無序的,而不是涇渭分明的[20]。以大數(shù)據(jù)、物聯(lián)網(wǎng)、通用大模型、數(shù)字建模、知識圖譜、VR/AR/MR等為代表的數(shù)字技術(shù)正引發(fā)出版業(yè)又一次革命:自由開放的環(huán)境、去中心化的生產(chǎn)主體、混雜多變的載體形式、高速便捷的流動渠道等。與傳統(tǒng)出版相較,數(shù)字出版加速了文化生產(chǎn)的速度、推動了文化數(shù)據(jù)的建設(shè)、延展了文化呈現(xiàn)的形式、構(gòu)建了文化體驗的新場景,搭建起數(shù)字文化的生產(chǎn)體系。特別是近年來,數(shù)字出版重點關(guān)注了文化遺產(chǎn)資源的開發(fā)與建設(shè),為中華優(yōu)秀文化繁榮與延續(xù)提供了基礎(chǔ)載體,更主動地承擔(dān)起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傳播和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光榮使命。
3 數(shù)字出版創(chuàng)新賦能文化遺產(chǎn)數(shù)智活化
文化遺產(chǎn)是人類文化的重要載體,它承載了歷史背景和文化象征意義,蘊藏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和價值體系[21],是貫通過去、當(dāng)下和未來的重要紐帶和橋梁,具有顯著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科學(xué)價值和藝術(shù)價值。文化資源高度共享是當(dāng)代文明的深度展現(xiàn)[14]。將文化遺產(chǎn)資源表現(xiàn)為數(shù)據(jù)態(tài),不僅記錄和再現(xiàn)了文化遺產(chǎn)的本體特征,也是對其承載的文化內(nèi)涵的二次編碼和表示[22]。在數(shù)字出版技術(shù)的支撐下,數(shù)字出版和文化遺產(chǎn)得以相互融通,實質(zhì)上是用文化遺產(chǎn)拓展數(shù)字出版的主題內(nèi)容邊界,構(gòu)成數(shù)字出版的新業(yè)態(tài)。數(shù)字出版與文化遺產(chǎn)傳承與活化深度融合,不僅是數(shù)字出版自身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也是文化數(shù)字化戰(zhàn)略的重要推動力量。
3.1 數(shù)字出版產(chǎn)業(yè)鏈延伸,助力文化數(shù)據(jù)資產(chǎn)化
文化遺產(chǎn)的數(shù)字化和數(shù)據(jù)化過程中產(chǎn)生了海量的、多模態(tài)的、異構(gòu)的數(shù)據(jù)資源,包括學(xué)術(shù)研究資源、實體資源、數(shù)字化資源等。這些數(shù)據(jù)資源不僅記錄和映射了人類歷史文化的整體脈動,還細致刻畫了特定個體和組織的行動軌跡與重要歷史事件的演變過程[22]。眾多出版機構(gòu)積累了大量高價值的文化遺產(chǎn)資源,然而,仍然有海量的資源未被有效地開發(fā)利用,甚至未被數(shù)字化,引發(fā)了嚴重的資源流失和浪費現(xiàn)象。《意見》[3]提出,要繼續(xù)推動文化資源采集、加工、交易、分發(fā)、呈現(xiàn),加快文化產(chǎn)業(yè)數(shù)字化布局。在數(shù)字出版技術(shù)的支撐下,出版業(yè)不斷通過自身產(chǎn)業(yè)鏈的變革與更新,將數(shù)字出版納入國家的文化數(shù)字化戰(zhàn)略之中。具體而言,數(shù)字出版借助技術(shù)優(yōu)勢,通過已有資源的采集與加工,推動文化遺產(chǎn)資源的數(shù)字化和數(shù)據(jù)化。同時,文化遺產(chǎn)資源在數(shù)字化、數(shù)據(jù)化后依然難以被計算機理解,所以亟須通過智能計算將數(shù)據(jù)轉(zhuǎn)化為文化遺產(chǎn)智慧數(shù)據(jù),使其具有可信的、情景化的、相關(guān)切題的、可認知的、可預(yù)測的和可消費的特征[23]。以高級組織形式存在的文化遺產(chǎn)智慧數(shù)據(jù),具有了更高的價值,通過數(shù)據(jù)資源的資產(chǎn)化,在數(shù)據(jù)市場中合規(guī)地開展交易,實現(xiàn)數(shù)據(jù)價值變現(xiàn)[24]。
3.2 數(shù)字出版服務(wù)模式重塑,打造文化體驗與消費新場景
通過對文化遺產(chǎn)原貌進行數(shù)字化掃描,在數(shù)據(jù)處理、語義關(guān)聯(lián)、知識加工的過程中深度挖掘和揭示文化遺產(chǎn)的價值,能讓不可再生的文物資源倍增為可永世流傳的數(shù)據(jù)資源[21]。文化遺產(chǎn)數(shù)字傳承與數(shù)智活化不單指借助數(shù)字技術(shù)實現(xiàn)文化遺產(chǎn)保護與繼承,更強調(diào)以利用促進保護,對蘊藏于其中的物質(zhì)和精神價值進行解碼、詮釋、繼承和重構(gòu)[25],將文化遺產(chǎn)從靜止、無活性的狀態(tài)轉(zhuǎn)變?yōu)閯討B(tài)、有活性的狀態(tài)[26]。文化遺產(chǎn)智慧數(shù)據(jù)的建設(shè)提供了良好的數(shù)據(jù)支撐,利用數(shù)字出版技術(shù)開發(fā)數(shù)字內(nèi)容產(chǎn)品,借助沉浸媒體技術(shù),實現(xiàn)文化遺產(chǎn)被更加身臨其境地表達。VR/AR/MR、人機接口、數(shù)字孿生及全息呈現(xiàn)等數(shù)字出版技術(shù)能更逼真、多維立體地虛擬復(fù)原與再現(xiàn)文化遺產(chǎn)體驗的場景,“數(shù)據(jù)+呈現(xiàn)技術(shù)=體驗場景”的服務(wù)模式成為創(chuàng)新文化消費的新方向。
3.3 數(shù)字出版生產(chǎn)主體擴大,創(chuàng)新文化生產(chǎn)方式
以ChatGPT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開啟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全新時代,已成為工業(yè)革命級的生產(chǎn)力工具。通用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圖像繪畫、智能問答等任務(wù)中形成了遠超人類的文化生產(chǎn)力,未來大量的文化生產(chǎn)將依賴于以通用大模型為基座的衍生工具。結(jié)合文化遺產(chǎn)領(lǐng)域知識訓(xùn)練而成的文化遺產(chǎn)大模型,將提供自然語言智能問答、文化遺產(chǎn)圖像增強、考古回溯、文物推薦等服務(wù)。通用大模型在數(shù)字出版中的運用,突破了傳統(tǒng)數(shù)字出版活動中,以文化機構(gòu)和領(lǐng)域?qū)<覟橹行牡闹R生產(chǎn)和數(shù)據(jù)建設(shè)方式。這種受益于大模型的內(nèi)容生產(chǎn)方式變革,為古籍?dāng)?shù)據(jù)構(gòu)建與知識活化、古文字的預(yù)測與解讀、圖像要素識別與抽取等提供了更加高效的手段。
3.4 數(shù)字出版產(chǎn)品形態(tài)再造,促進文化傳承傳播
數(shù)字出版產(chǎn)品形態(tài)在不斷革新與再造中,傳統(tǒng)的書報刊早已被數(shù)字形式的電子書、電子報紙、電子刊物取代,并且涌現(xiàn)出更多形態(tài)各異的數(shù)字出版產(chǎn)品。網(wǎng)絡(luò)游戲、短視頻、數(shù)字藏品、數(shù)據(jù)庫等象征了數(shù)字出版產(chǎn)業(yè)中新的出版形式和產(chǎn)品形態(tài)。它們以更多維的呈現(xiàn)形式、更具互動性的體驗方式、更龐大的知識內(nèi)容,在文化遺產(chǎn)的敘事傳播中愈發(fā)受到重視。以數(shù)字藏品為代表的新型數(shù)字出版物正為數(shù)字出版拓展新的疆域。以科技手段保護和傳承文化遺產(chǎn),傳播中華優(yōu)秀文化為目的,部分出版單位已率先踏出進入數(shù)字藏品市場的第一步,積極融入數(shù)字經(jīng)濟中。新的數(shù)字出版產(chǎn)品形態(tài)不僅以更加豐富多元的形式重新表達中華文化、促進文化的保護和傳承,而且有利于突破語言和傳統(tǒng)媒介的限制,以更加通用、可理解、可感知的方式向外傳播中華文化,展現(xiàn)中華文化的魅力。
4 結(jié)語
在印刷出版史上,古登堡活字印刷術(shù)發(fā)明后的早期印刷時代,圖書在字體、標(biāo)點符號、版式及紙張等方面均與后來有所不同,圖書生產(chǎn)尚不成熟,這段時間被稱為“搖籃本時代”,意謂“猶如人生初期的搖籃時光”。與之類比,人類社會才剛剛邁入數(shù)字時代,當(dāng)今的數(shù)字文明尚且處于“數(shù)字搖籃”時期。在數(shù)字中國和文化強國戰(zhàn)略的政策支持與保障下,我國數(shù)字出版產(chǎn)業(yè)正處于利好期,更要始終牢記出版的本質(zhì)和使命,找準(zhǔn)自身定位,通過出版的創(chuàng)新性、高質(zhì)量發(fā)展,加快推動出版業(yè)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升級。數(shù)字出版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亦將賦能新時代文化遺產(chǎn)的數(shù)智化活化,成為數(shù)字文明的加速器,實現(xiàn)中華文明的數(shù)字化賡續(xù)。
參考文獻
[1] 范軍.出版本質(zhì)上是一種知識生產(chǎn)[J].出版科學(xué),2022,30(3):1,50.
[2] 常江,朱思壘.作為知識生產(chǎn)的數(shù)字出版:媒介邏輯與文化生態(tài)[J].現(xiàn)代出版,2021(5):19-24.
[3] 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wù)院辦公廳.關(guān)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shù)字化戰(zhàn)略的意見[EB/OL].(2022-05-22)[2023-12-30].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5/22/content_5691759.htm.
[4]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guān)于推動出版深度融合發(fā)展的實施意見[EB/OL].(2022-04-24)[2023-12-30].https://www.nppa.gov.cn/xxfb/tzgs/202204/t20220424_666332.html.
[5] 中共中央 國務(wù)院.數(shù)字中國建設(shè)整體布局規(guī)劃[EB/OL].(2023-02-27)[2023-12-30].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27/content_5743484.htm.
[6] 卡爾·波普爾等.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M].舒煒光,卓如飛,周柏喬,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123.
[7] BROOKES B C.The foundations of information science.Part I.Philosophical aspects[J].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1980,2(3-4):125-133.
[8] 郭斌.淺析“世界三”與卡西爾符號世界的異同:從卡西爾的符號世界看波普爾的“三個世界”理論[J].自然辯證法通訊,2015,37(6):131-137.
[9] 趙濤.電子網(wǎng)絡(luò)與知識生產(chǎn):基于波普爾“三個世界”理論視角的考察[J].學(xué)術(shù)界,2013(10):74-84,308.
[10] 肖峰.腦機接口技術(shù)的發(fā)展現(xiàn)狀、難題與前景[J].人民論壇,2023(16):34-39.
[11] WOLPAW J R,WOLPAW E W.腦‐機接口:原理與實踐[M].伏云發(fā),楊秋紅,徐寶磊,等譯.北京:國防工業(yè)出版社,2017:12.
[12] 吳永貴.中國出版史·上·古代卷[M].長沙:湖南大學(xué)出版社,2008:12.
[13] 陳丹,章萌,侯欣潔.數(shù)字出版概念的演化與界定[J].數(shù)字出版研究,2022,1(1):38-45.
[14] 謝中起,索建華,張瑩.數(shù)字生產(chǎn)力的內(nèi)涵、價值與挑戰(zhàn)[J].自然辯證法研究,2023,39(6):93-99.
[15] 孫寶林.印刷出版文化照亮人類文明征程[J].中國出版史研究,2019(2):9-16.
[16] 覃慶輝.從媒介延伸到社會變革:重審古登堡印刷術(shù)在文藝復(fù)興中的作用[J].新聞知識,2019(11):3-8.
[17] 費夫爾,馬爾坦.印刷書的誕生[M].李鴻志,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6:3.
[18] 郭蓮.文化的定義與綜述[J].中共中央黨校學(xué)報,2002(1):115-118.
[19] REED D A,BAJCSY R,F(xiàn)ERNANDEZ M A,et al. Computational Science:Ensuring America's Competitiveness[J/OL].[2023-12-30].http://www. nitrd.gov/pitac/reports/index.html.
[20] 師曾志.生命傳播:自我·賦權(quán)·智慧[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8:346-347.
[21] 祝蕊,劉煒,付雅明.Web3.0環(huán)境下文化遺產(chǎn)價值重構(gòu)研究[J/OL].(2023-08-29)[2023-12-30].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746.g2.20230829.1053.002.html.
[22] 王曉光,梁夢麗,侯西龍,等.文化遺產(chǎn)智能計算的肇始與趨勢:歐洲時光機案例分析[J].中國圖書館學(xué)報,2022,48(1):62-76.
[23] 曾蕾,王曉光,范煒.圖檔博領(lǐng)域的智慧數(shù)據(jù)及其在數(shù)字人文研究中的角色[J].中國圖書館學(xué)報,2018,44(1):17-34.
[24] 謝亞可.數(shù)字出版融入文化數(shù)字化戰(zhàn)略的現(xiàn)實意義與實踐進路[J].出版發(fā)行研究,2023(1):8-14.
[25] 林凇.植入、融合與統(tǒng)一:文化遺產(chǎn)活化中的價值選擇[J].華中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7,31(2):135-140.
[26] 王曉光,侯西龍.面向活化利用的文化遺產(chǎn)智慧數(shù)據(jù)建設(shè)論綱[J].信息資源管理學(xué)報,2023,13(5):4-14,43.
Digital Publishing and Digital Intellectual Acti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Transformation
Hua Jian1Xiaoguang Wang1,2,3Xilong Hou4
1.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2. Cultural Heritage Intelligent Computing Laboratory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3.Publishing Research Institute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4. Qufu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Communication,Shandong Rizhao 276826,China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publishing has been entrusted with the important task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since its birth. As human society moves towards digital civilization,digital publishing is poised to lead the wa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ter the era of print civilization,serving as a crucial domain for Digital China and cultural digitization.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logic of transitioning towards digital civilization,emphasizing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the three worlds to achie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the fundamental realization of digital civilization,with digital culture assuming an important role as the leader. Secondly,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it analyzes the role,positioning and it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of digital publish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Finally,it puts forward a practical path of digital publish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empower the inheritance and acti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Digital publishing;Digital transformation;Cultural heritage;Smart data;Activation and utilization